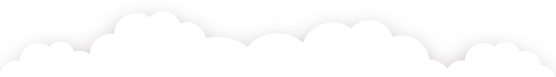很多讀者留言,讓我談一談羅翔教授關於“辛亥革命排滿”的相關言論。
我認為我不是最有資格談論這件事的,應該讓那些“90後”們去談——經歷過清王朝和辛亥革命的“1890後”們。魯迅先生是“80後”,毛主席是“90後”,沒有誰比他們更有資格了。
他們同樣也對“美化90年代”的事情感到過憤怒,也就是美化大清。
這其實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後,對於“滿清餘孽”和“國黨餘孽”過於寬容,完全沒有對“前朝”的政治勢力進行所謂的“清洗”,反而試圖從思想上、精神上去“改造”他們,溥儀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按理說他這一個末代皇帝,又投靠了日本人做漢奸,不管在蘇聯、英國、法國,都是妥妥上斷頭臺的反面典型,然而新中國卻寬容地把他改造成為了新公民。

好的地方在於,這確實能夠團結大多數,壞處就是保留了不少“前朝餘孽”的負面影響。毛主席後來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現在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壟斷了。解放後,我們把他們都保下來,當時保下來是對的。但現在要搞革命……(因為)他們先挑起鬥爭。”
在同年5月份的另一篇文章中,毛主席進一步分析了這一問題:“那麼多小學,我們沒有小學教員,只好用國民黨留下來的小學教員;我們也沒有自己的中學教員、大學教授、工程師、演員、畫家,也沒有搞出版社和開書店的人員。”
彼時有一大波革命中成長起來的文學藝術家們,給死氣沉沉的文壇帶來了一股新鮮潮流,但是改造舊世界畢竟是很難的,是需要一個長時間的歷史程序的。那些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舊勳貴們,自然無法進入政治經濟核心部門,但是文化部門好說啊。
因為自古以來,唱戲、聽曲、搞文藝、寫話本,都是要一定程度上的“脫產階級”,即不需要從事勞動生產,才有心情鼓搗研究這些東西。如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有一對鮮活的人物形象——小文夫婦,就是前清遺老、落魄貴族,但是唱戲非常在行,靠“當角”維繫了很高水平的生活。

首先必須承認的是,這些舊勳貴們為我們保留了很多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這是必須要肯定的。但另一方面來看,這些遺老遺少們久而久之就佔據了文化口的重要地位,成為文藝內容的重要產出者,甚至是規則制定者、裁判員,這就對文藝的整體氛圍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導致了很多“半殖民地半封建”殘留。
建國之初,在文藝領域有兩項重要的批判,即批判《清宮秘史》和批判《武訓傳》,二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用“溫情脈脈的面紗”去掩蓋血淋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就好像《繁花》中塑造了一個容貌姣好、風度翩翩、能力超群、敢闖敢拼、有情有義、道德完人的寶總,力圖掩蓋“先富起來的人們”財富積累過程中的原罪。而且關鍵的是,武訓這個人好歹是真的,寶總的原型壓根就是一個進監獄的投機犯。
正好又回到了今年《文化革命的意義》《文化革命的內涵》這兩篇文章的討論範疇,批《清宮秘史》《武訓傳》可以視為批《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李慧娘》的前奏。

明面上來看武訓是千古義丐、乞討辦學、支援教育,多麼高尚多麼值得肯定啊,但是為什麼被禁呢?歷史上,武訓三十歲和哥哥分家得地三畝,變賣得錢一百二十吊,合討飯所積九十吊,共二百一十吊,跪求鄉紳婁峻嶺,楊樹芳替他向窮人放債生息,從三十歲到五十歲,武訓積得土地二百三十多畝,現錢二千八百多吊,成為地主兼高利貸者。
看到問題了吧,武訓乞討得來的錢,離辦學遠遠不夠,他是以“辦學”為名,央求當地鄉紳為他發高利貸——二十年時間土地增長八十倍,現錢翻了三十番。
說白了武訓辦學的實質就是,以為統治階級宣傳價值觀為名,成功進入統治階級的吸血體系中獲得利益,再用所獲利益宣傳封建價值觀培養新一代奴隸。當然,武訓這個人沒有這麼高的見識,他可以是高尚的、不謀私利、懷有美好願望的,但是他做的這個事,在當時把舊社會舊價值觀砸的稀巴爛的共產黨人那裡,不被批判才怪。
簡而言之一句話:武訓就是被封建社會儒教價值觀PUA的人,而他要繼續維繫、宣傳、鞏固這個PUA體系,成為了這個價值觀的幫兇。

再來看一看對《清宮秘史》的批判,最主要有三大問題。第一,過度美化光緒皇帝,超越歷史真是拔高珍妃的形象,然後把所有“問題”都歸於大清有一個慈禧太后。言下之意如果沒有慈禧這個大反派,那皇帝如此英明神武,后妃如此賢良淑德,我大清中興指日可待!
早年的共產黨人,首先都是追隨孫中山先生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雖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本質問題,但是終結了中國兩千餘年的帝制,讓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所以這才過去多少年啊,就要鼓吹“皇帝其實是好的,都怪慈禧這個老妖婆壞了事”,真把這個革命勝利當兒戲了?
第二,過於美化帝國主義,傳遞出一種“只要帝國主義支援中國,那麼中國就會有一個好皇帝,中國就會脫離積貧積弱的現狀”這種邏輯鏈,完全忽略了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殘酷的傷害、侵略、剝削與掠奪。引用一段當時批判《清宮秘史》的文獻:

第三,抹黑義和團運動。正如上面引用的段落,影片傳遞出的一種感覺,義和團是“愚昧的暴民”,而帝國主義竟然好像是幫我們“維持秩序”呢。繼續引用一段當年的歷史文獻:
關於義和團的問題我也寫過很多文章討論了,落後確實是落後、愚昧確實是愚昧,但是是誰先去別人家裡殺人放火搶劫強姦呢?是誰讓他們變成這樣呢?
“你們把農民當作什麼,以為是菩薩嗎?簡直笑話,農民最狡猾,要米不給米,要麥又說沒有,其實他們都有,什麼都有,掀開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儲物室,一定會發現很多東西,米、鹽、豆、酒…到山谷深處去看看,有隱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會說謊,不管什麼他們都會說謊!一打仗就去殺殘兵強武器,聽著,所謂農民最吝嗇,最狡猾,懦弱,壞心腸,低能,是殺人鬼。
——但是……是誰令他們變成這樣的?是你們,是你們武士,你們都去死!為打仗而燒村,蹂躪田地,恣意勞役,凌辱婦女,殺反抗者,你叫農民怎麼辦,他們應該怎麼辦。”——《七武士》黑澤明

下面幾張圖非常言簡意賅,以後我就不用廢話那麼多,就直接放這幾張圖了: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落腳點是【我】或【我們】,作為一個有記憶的活生生的【個體】,所經歷的“大下崗”年代。
就像福柯當年對於美化德國法西斯的現象很憤怒一樣:納粹誰沒見過啊?這才過去多少年啊,就想翻案?看見那哥們沒,讓-保羅·薩特,坐過納粹的牢、進過集中營、參加過法國共產黨的游擊隊;看見那姐們沒,漢娜·阿倫特,海德格爾的親傳弟子,人家老師就納粹,希特勒還沒上臺的時候就把她當成眼中釘了;再看看東邊那兄弟們,齊格蒙特·鮑曼,參加了蘇聯組建的波蘭紅軍,親身經歷瞭解放柏林的戰役,是波蘭最年輕的陸軍少校,人家親手擊斃的法西斯比你一輩子見的都多。
同理,如上文所述,毛主席等老一輩革命家們,對於“美化帝制”“美化大清”“美化舊社會”的內容很憤怒。
同理又同理,我們對於美化“先富階級”、美化“90年代”的一系列文藝作品——如《繁花》,也是跟福柯一樣的心情:90年代是什麼樣子我們沒經歷過嗎?那些“先富起來的人”究竟是怎麼富起來的我們心裡沒數嗎?

就像我在講《年會不能停》這部電影時,為什麼我一眼就能看出這是以網際網路公司裁員為一個“表”,但本質是講98年下崗潮的電影?因為電影中的太多場景我都親眼見過、親身經歷過——

就比如下崗工人擺攤這個場景,小學時候上下學頻繁會在大街上看到,因為很多下崗工人的工資、遣散費,都是用工廠生產的產品抵押的,所以一眼就能感知到電影所要隱晦地為我們表達什麼。
說起下崗工人擺攤這個話題,我又想起城管的問題,現在的城管普遍沒啥存在感了,估計05後一代永遠不會親身感知到曾經的“城管”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存在。

當時我小學一年級放學的路上,就看到了城管暴力毆打在街邊擺攤的下崗工人:工人被打的頭破血流,不住求饒“我們是XX廠的下崗工人”,然後城管一邊打一邊罵“打的就是你XX廠的”。
那時候我們放學是一個方向的學生結伴一起走,領頭的學生舉一個小黃旗,過馬路的時候還要對禮讓的車輛鞠躬——如果是光榮的少先隊員就要敬少先隊禮。看見城管打人的時候,我們整個一隊的同學都站在原地嚇傻了,真的是瑟瑟發抖一動不動。

後來我看《動物世界》,講老虎捕食的時候,會有鹿驚嚇過度,反而就在原地一動不動了,我就想起來這件事了,我們整整一隊小學生,都觸發了原始本能的條件反射了。孔子云:苛政猛於虎也。
這種影響是極其惡劣的,因為我們這種小城市都是熟人社群,就這麼幾個工廠家屬院同學家長之間隨隨便便都能找到關係,馬上就能想到那位同學爸媽就是XX廠的、那個認識的叔叔阿姨就是XX廠的。所以我們這還算好的,還有更暗黑的可能性,就是真有同學親眼看著自己父母當街被城管毆打。
而且那些城管非常之兇殘,按理說不讓擺攤就算了,這也是你的職責範圍,我們也承認。但是他們一定要肆意打人,還要把下崗工人擺攤賣的日用品一件一件砸碎,在地上摔碎了還要上去跺兩腳,我至今都不能理解這是一種怎樣的獸行。

而且小孩子的記憶是非常好的,小學時候經歷過的事情往往比大學都印象深刻,就拿之後我歷史課上學到鬼子進村之類的內容,腦海中浮現出的永遠都是那一群“打的就是你XX廠”的城管們。
當然,必須要承認的是,在經過十數年的社會輿論的不滿、人民普遍訴求、治理水平的提升、公務員隊伍素質的進步,城管暴力執法的惡性事件越來越少,甚至有些“矯枉過正”,城管本應的工作職責會被“流氓無產階級”(俗稱刁民)反制,以至於形成了“按鬧分配”“誰橫誰有理”的局面。
但是,這種進步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並不能否認城管群體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的負面形象,也不能忽略人民群眾的訴求、社會輿論的不滿對於治理者執法水平提升的倒逼。我上述所說的是我小時候真實的記憶,用現在城管的文明執法甚至有些矯枉過正,試圖去表達“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現在沒有無所謂了”等觀點,無異於對歷史的背叛、對受害者最大的不公正。


我為啥不寫80年代呢?因為我是個90後,我沒有經歷過80年代,我如果要寫,也只是“轉述別人的記憶”,價值就低了很多。但我相信80後對80年代、70後對70年代也有很多獨特的寶貴的記憶。
本文從大清講到了城管、先富,結論就是:“人民的記憶”是對抗“被既得利益集團書寫的歷史”最好的武器。
福柯看了《索多瑪120日》很憤怒:誰沒見過納粹啊,這才幾年過去,你們就想美化法西斯;
毛主席看了《清宮秘史》很憤怒:誰沒見過大清啊,這才幾年過去,你們就想美化帝制;
我們看了《繁花》也很憤怒:誰沒見過“先富起來的人”啊,這才幾年過去,就想把他們塑造成“勤勞致富”的典型了?

相關閱讀:大浪淘沙十週年,最火文章大合集
◆ ◆ ◆ ◆ ◆
上一期內容的影片更新了,歡迎多多點贊:


第二本新書正式連載完畢:《資本囚籠》全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