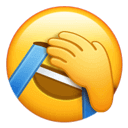陳粹盈,山東大學歷史系77級,畢業後從事婦女界的宣傳報道以及擔任幹部教育領域的歷史教師,1990年作為自費訪問學者赴加拿大里迦納大學進修。現任加拿大聯邦政府公務員,在海外中文媒體上發表紀實文章,隨筆和詩歌。
原題
青島二中文宣隊
卅七年後再聚會
作者:陳粹盈
2012年金秋十月,我的中國探親之旅意外趕上了一次中學文藝宣傳隊的師生聚會,自1975年畢業離校後,這是三十七年之後的首次重聚。
三十七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浪花一簇,然而這時間跨度,幾乎等同於在清末民初大家各奔東西,於開國大典上又偶然相遇。從十七八歲到五十多歲, 人生經歷了多少起伏跌宕,得意失落,恩怨情仇,真假善惡? 更何況時代的波濤曾是怎樣地彼伏此起,翻天覆地,大浪淘沙,一瀉千里!

青島大門口看二中老樓
令人驚喜的是老師同學們一下子就認出了我,有的一時叫不出名字,稱我 “小柳琴”, 因為我是樂隊彈柳琴的。還有的說 “咱們可是世交”!一聽這話我雖認不出眼前這位大腹便便的男人, 但名字卻準確地脫口而出。可不是嘛? 自祖輩起, 三代的交情了。還有兄弟倆, 稱呼我為 “發小” , 是的,他們的母親在市立醫院工作,與我在青島市醫務界工作了一生的母親關係甚好,總是開玩笑互稱親家。
所有的同學中最大的高我兩級,最小的低我兩級,最年輕的是1960年出生的,這年已經52歲,兩位老師女的小王老師64歲,男的朱老師58歲,當年是公認的美女帥哥。還有一位老王老師,老太太已經90多歲,為免閃失,未敢請來。已經作古的魏校長的兒子也是宣傳隊隊員,父子倆活脫一個模子,他長得簡直比魏校長還像魏校長。
這些當年的青少年,如今兒女們遍佈幾大洲,有的已升級為祖輩,含怡弄孫享受天倫。他們本人多數仍在青島市,有的活躍在市廣播電臺,電視臺,歌舞團成為資深主持人,導演編劇及團領導,也有的以拉小提琴為專業至今。還有些人已經退休。一位當年滿臉稚嫩的小男生在聚會中作了如下發言:
“光陰荏苒,歲月如梭。親愛的老師同學們,兄弟姐妹們,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今天的聚會,是對近四十年前青島二中文藝宣傳隊成立的紀念!它記錄了我們曾經的青春、美麗和英俊;留下了我們英姿颯爽,龍騰虎躍、帥氣瀟灑,婀娜多姿的身影。此時此刻,我們彷彿又聽到了那悅耳的歌聲和優美的音樂。那是時代的烙印,是我們這代人珍貴的記憶。
普希金的詩最能表達我們的心聲:‘那過去了的一切,都將成為我們親切的懷念’。
此時此刻,我們除了懷念、敘舊,更加有意義的是,回味我們的過去,審視我們的經歷。大哲人蘇格拉底說:沒有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當年,激動過我們靈魂的那些樂章,是否還在我們心中迴響?
真正的藝術是崇高的、聖潔的,它能淨化人的心靈,昇華人的人格,並且,它也能盪滌汙泥濁水、陰險醜惡。
物是人非,就是雖然我們已年過半百,不再年輕,但是,那承載過我們夢想的二中,是否還有當年的精神?!
人是物非,即使二中已今非昔比,東遷擴建,但是,那曾經年少真誠的我們,是否還有當年的真摯?!
讓我用《柴達木之戀》上感人的話語,來表達此時我們的心聲:“‘清晰地記得你青春的臉,清晰地記得你純潔的笑’。難忘今天的相聚!難忘今宵 !”

青島二中北樓
宣傳隊組建於1974年秋,那年,學校初三,高一和高二的三個年級的全體師生,到萊西縣學農支援秋收。本來我隨班級下鄉,與同班其它五個女生分到一家老鄉家住。因為西屋的炕上擠不下六個女生,有一人必須挪到東屋去與房東女兒睡一屋同炕,其它女生不太情願,我就捲起鋪蓋搬到了東屋,以後還和房東的女兒保持了幾年的通訊聯絡。後來文藝老師來各大隊,召集一些學生組建慰問同學娛樂老鄉的文藝宣傳隊,我隨之搬到了縣城所在地,與另外兩位拉小提琴,同級不同班的姑娘坤和萍,以及小王老師住在一家,脫產排練。
其中坤發展成為我中學同學的頭號閨蜜,友情一直延續至今。她自幼就靚得出眾,四十歲時還相當引人注目。人們紛紛說她酷似香港女星關之琳。可惜坤不上相,集體照中並不出彩。她的一些生活照,以及在我鏡頭下的一些倩影,可些許反映出本人神韻。
2011年秋,我們在青島八大關拍了些兩人合影,坤將它們用軟體加上框作了註腳,其中一張的題語是:“如今風華不再,舅舅不疼姥姥不愛,只有自己把自己厚待。”
萊西的短暫三週逗留,多少年過去,仍象一幅畫,印映在記憶深處,有些片斷,今天回想,不僅啞然失笑——
片斷之一: 小王老師比我們三人雖然年長不少,但彼此之間相處沒有任何隔閡。一天,在炕頭她拿出錢包,我瞥到裡邊夾了幾張她和一小夥子的合影,便要求分享。她欲遮掩反而激發起我們的好奇心。我搶過錢包往院外跑去,她羞又氣又笑,追了上來。坤和萍也追上來充當同夥,替我拽著小王老師。當距離拉開,定睛一看照片,我不禁愣住“怎麼不是張老師?”當時學生中傳說是教體育的張老師與小王老師是一對戀人。這個片斷在聚會上被我重提,大家不禁捧腹。
片斷之二:當樂隊朱老師在萊西望城中學教室裡指揮我們樂隊練習時,一位舞蹈隊的高我一級的女生在教室門口外隨樂旋轉起舞,樂曲時而節奏明快時而舒緩悠揚,她的舞步亦步亦趨,緊密配合,只是眼睛時刻凝視追隨著朱老師,而朱老師一直目不斜視,心無旁騖,引起屋內我們奏樂者竊笑不已。這位女生在恢復高考後考上了某校導演專業,現在京工作。不知回首這戲劇性的一幕她會作何感想?年輕人嘛,冒冒傻氣也正常,這是青春的副產品。
片斷之三:我們這一屋三個女生,同高二的三個男生被分在一位老鄉家用餐,坤和萍極愛笑,尤其是坤經常為一點小事大笑不停。不止一次在飯桌旁,她倆不知為什麼笑得一發不可收拾, 我也跟著傻笑。那三位憨頭憨腦的男生, 搞不懂我們是否在笑話他們, 吃也不是, 笑也不是, 面面相覷, 手足無措。儘管他們的名字早都被忘到九霄雲外, 但這飯桌旁的笑場,卻留在了記憶中。
片斷之四:由於下鄉的學生分佈在幾個不同的生產隊,我們的演出也必須步行到各個不同的地點隊部。經常是在晚霞滿天的黃昏,宣傳隊員們排成一人字行隊伍手提肩馱樂器道具,跋涉穿行在鄉間小道,田陌溝壑。從其她女生那裡,我學會了唱“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一直通往美麗的遠方。我要沿著這條迷茫的小路跟著我的愛人上戰場” 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聲與情景交融,多麼難忘的歲月!當回到我班同學所駐的大隊那晚,無論是原來同屋同學還是房東女兒,到後臺來找我時都象久別的老友一樣興奮莫名,尤其是2007年去世的縻子格外高興(見另文《紀念高考緬懷摯友》)。

北樓北面的操場臺
萊西演出了什麼歌舞都記不清了,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呂劇(山東地方戲)“退彩禮”,內容是某女青年訂婚講究新事新辦不落俗套,將婆家送的訂婚禮品一塊上海全鋼表,婉轉地退還了婆家,用今天的話就是裸婚。那時的人們真好打發,當年的聘禮三大件手錶腳踏車和縫紉機,朋友送禮常見的臉盆毛巾暖瓶等物件,現在的年輕人聽了恐怕要笑掉牙。
萊西之行以後,宣傳隊的活動延續了下來。整個第二學期即1975年上半年,每晚我們都回校排練歌劇“紫曲河畔”,是朱老師創作的,內容是藏族與解放軍軍民魚水情的故事。據朱老師說,是受我這位“小老師”的啟發而作。1974年,我忽然興起迷上了作曲,自編自樂地寫了一些詞和曲。其中有一首六八拍節奏的“中朝友誼之歌”,被我北師大77級英語系的堂姐,當時北京某工廠的女工,以手風琴伴奏廠裡女工小合唱受到好評;在大學歡迎1978年新生入校的聯歡會上,我和另一位同班女生作了二重唱表演。1974年,有人在青島將我引見了作曲家冰河先生,即那位創作“金瓶似的小山,山上雖然沒有寺,美麗的風景已夠我留戀……”歌曲的作者,給我上了一堂作曲原理課。那一晚課結束之後,我才明白,作曲原來有這麼多規矩學問,條條框框。從此不再戀戰,偃旗息鼓多年。
言歸正傳,“紫曲河畔”的女主角,那位當年天真稚氣,穿著土氣,一臉嬰兒紅的初一女生,聽說還曾為朱老師及前女友之間傳遞過紙條或扮過類似紅娘的角色,後來與朱老師同屆考上某師大79級藝術系,順理成章地喜結良緣,最後他們在青島同一所大學藝術系任教。她現在舉手投足,穿著談吐都很有文藝“範兒”,今非昔比。
當晚到會的校友中,有兩對離婚夫妻,其中一對兒戀愛多年,只維持了半年的短暫婚姻,今日相見,據說若在路上遇到,還未必能認得出來。另一對兒,育有一子,年輕輕分手之後女方至今未再嫁。女生張口閉口“這是我前夫,別看他現在老眉喀嚓眼的,當年可是一帥哥!” 本來這兩對前夫妻四人要一起合張影,我手慢了一個節拍,尚未按下快門,忽然那位未再嫁的女生一甩手賭氣不拍了,勸了半天也決不回頭。後來我才明白原因是前夫不肯挽著她合照,而寧可挽著別人的前妻,是否怕現任知道了吃醋,不得而知。
除了夫妻幾對兒,前夫妻兩對兒,宣傳隊裡還有親兄弟和親兄妹。萍拉提琴,哥哥是吹小號的。說起萍兄,想起了一段插曲,他長得酷似一位高我們三級的校友。這屆高中校友是71屆初中畢業,1974年夏高中畢業的,他們上高二時我們上初二,對這屆學長印象極深。那些年,文革後期,學校秩序很亂,周圍這些初中小子們,不諳世事,頑冥不靈,胡天胡地,亂鬧一氣。但每當走近高二級四個班的課堂,總是鴉雀無聲,學生們全神貫注聽老師講課,秩序井然。他們之中不乏才華橫溢者,活躍在學校的各種場合,不但與我們初二年級的12個班聯合組成多個團支部傳幫帶,還多次在學校舞臺上表演相聲,器樂獨奏,話劇廣播劇,不一而足。那位長得酷似萍兄的校友,在一話劇中扮演了一位外號叫“小廣播”的角色。萍說“小廣播長得像我哥”,的確如此。
1980年初夏,濟南諸高校舉行聯合匯演。我隨山東大學文工團歌唱隊到山東醫學院禮堂演出並觀摩表演, 在臺下坐在我身旁的觀眾恰恰就是“小廣播”。我問他:“你是青島二中的吧?”“你1973年在二中扮演過‘小廣播’吧?”他大為驚奇,“你怎麼記性這麼好?我怎麼不認識你?”我說:“當然,一般大孩子都不注意小孩子,再說你也看不出我本來面目(我尚未卸下舞臺濃妝)。我記得你是因為你長得太像某某某了”。他是山醫77級的,這次聊天,聊到了許多當年二中的校友。這屆高中學長畢業之後,校園頓時冷清了不少。
1975年夏天,我們初三和高二的兩屆學生畢業,7月初,宣傳隊全體師生到我後來工作的照相館合影留念,見下圖。

老照片, 第三排左四為筆者
當時,我並沒有想到一個月之後,為了避免下鄉,我會放棄升高中的機會選擇留城就業,更未預料到年底會來這家照相館就業。
朱老師在聚會上談到了他當年血氣方剛時打抱不平乾的蠢事。小王老師有一天走進課堂,被一初中班男生事先架在門框上的條帚簸箕落下砸個正著,哭得梨花帶雨地跑回音樂教研室,朱老師義憤填膺自告奮勇:“這節課我來上。”他走進教室,宣佈如果不找出肇事者,全班留下,不許放學。終於,闖禍的小子被檢舉出來,朱老師命他站在講臺前,然後飛起一腳踹到了教室後面,下課後他帶著這男生到了體育教研室,和幾個體育教師又來了一頓猛揍,直到男生一再告饒表示決不重蹈覆轍為止。“要這事放到現在,我早進監獄了。” 朱老師說。
我說:“小王老師當年多美麗啊,”朱老師說:“可不是嘛,我都給迷得不行了,可是年齡差距太大了呀。”六歲,在今天姐弟戀不稀奇,那時,好像還是個事兒,除非再早些年代,由父母包辦的舊式婚配。他娶了小六歲的學生,也蠻好。接著他的話,我趁機和老師開起了玩笑:“你當年也很帥氣的又多才多藝,是吧?” “你怎麼當年不告訴我,要是我知道的話,領回家去好了。” “噢嗬!你家房子不夠大呀,裝得下十三釵嗎?哈哈……”
用朱老師的話說,“這麼多年過去,我依然非常懷念我帶領大家一起排練的時光。” 是的,這點大家都有同感。七十年代中期,文化資源貧乏,生活單調枯燥,沒有電視網路,電訊極不發達。大家普遍生活拮据,物質供應極端匱乏。然而那時自然生態環境良好,食品安全,貧富差距不大,貪腐現象幾乎絕跡。雖然經歷了文革,中國文化中的精髓仁義禮智信橫遭顛覆,但人心與現在比較還算單純。我們聚會合影的背景橫幅上,我問為什麼要寫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而不是文藝宣傳隊,答案是故意這麼標明,以反映時代特色。

2012年10月宣傳隊重聚合影, 前排右四為筆者

我們這一桌同學與小王老師和朱老師(前排左二右二)合影

部分女生
青島二中三年半的初中生涯,給我留下極其美好的回憶。每當我路過當年的校門口,都不禁激動莫名。我們這一代人,是經歷豐富的一代,曾見證過許多歷史的動盪磨難和轉折。我們與今天養尊處優在應試教育下嬌生慣養成長的下一代迥然不同。
1970年代二中學生的來源,家庭背景比較特殊,大批的高校教師,科研所研究人員和醫生們的孩子,幹部子弟,陸海空軍人後代特別是北海艦隊軍官的家屬,以及舊時工商界人士的後裔,構成了相當比例的生源。這所全市最好的中學,多年來向社會輸送了許多傑出的畢業生。儘管當年的老教學樓已經不復存在,校園也改變了模樣,依傍在前海沿兒東部的學校周邊的氛圍和空氣,依然是那樣地歷久彌馨。
這美好的回憶中,那一段充滿了歡歌笑語無憂無慮的宣傳隊的生活佔了很大比重。大家撫今思昔,不停用青島話感嘆:“日子真不抗混!” 即歲月匆匆,人生轉眼成空之意。我們那時都是青少年, 如今大多數人的兒女都遠遠超過了這個年齡段,老師們當時也不過二十多歲。青春,就是價值連城的財富,不,青春是無價之寶,不是嗎?
2012年11月11日寫於多倫多

舞蹈隊真活躍

補記:
下面這首詩歌是最近寫的, 可以部分反映出我對青島二中的眷戀之情。
我的青島二中
依然是那熟稔的海岸
時而浪潮喧騰
時而波瀾不驚
依然是朝起暮落的雲霞
夾雜著溼潤溫馨的金紫粉橙
捲走夢般氣息的笑語歡聲
啊,青島二中
我心盤踞的校園
傾注了半世紀的懷念深情
即使時光不再,物換主易
記憶不曾遺落,也從未塵封
啊,我最愛的青島二中
你得天厚賜,位佳獨勝
你園側生香,景如畫屏
我懷念那樓宇裡外的
淺月深燈
懷念紛亂世道欲休還起的
朗朗讀書聲
常憶師長的
解惑授業,循循善誘
不同凡響的涵養底蘊
不一樣的育人水平
教誨學子,精益求精
傾心打造靈魂的工程
你們是尊者更是園丁
啊,我的青島二中
莫問我為何情有獨鍾
最靈敏最有效的學府生涯
與你相輔相成貫穿始終
最相宜最生動的氛圍
結遍金蘭,一生至情
尋常細節,等閒談笑
歷歷如昨,愉悅朦朧
啊,我的青島二中
從這裡走出了多少精英
莘莘學子,濟濟人才
無論是霍霍有名
還是一顆鉚釘
誰不愛母校
誰不道情濃
荊棘年代,波譎雲詭
黑霧壓頂,雹虐雷驚
際遇充滿了怪異
不和諧的韻律穿插縱橫
即使蹉跎歲月帶來怎樣的不堪
我懷念的是花樣年華
獨有的青春饋贈
那個學緣戛然而止的夏季
猝不及防地巨浪轟鳴
似把桅船席捲而去
又如鴻雁驟墜草叢
多少次回眸昔日的校園
慼慼扼腕過早消失的光影
每一個岔口的惘然與失誤
演繹了迥然而異的命運之途
多年之後,萬里漂零
重履斯地,疾車而過
忽而顫動莫名
少年之河的閘門重啟
難禁淚如濤湧
這是一首盤旋經年的詠歎調
迴盪不已而逐次攀升
是追尋亦是珍藏
從青絲到白髮,記憶之弦
在牽念中律動始終
為那優美短促的青澀時節
為那春夜一再排練的樂曲長鳴
為那相聲落地的鬨堂大笑
為那多屆畢業生備考的凝神聆聽
為那奔赴考場的擦肩而過
為那終生不會上演的夢裡重逢
這是我穿越大洋難捨的彼岸
這是我思念纏繞不止的青藤
遙遙心靈深海的回味
佳釀已然貯存了半生
昔日之歌,終成絕響
舉杯邀到的,唯有
唯有那, 習習海風
2019.8.10.
延伸閱讀
陳粹盈:追憶祖父,一個老派的中國知識分子
文圖由作者提供本號分享



表揚小號
就摁下識別二維碼吧

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