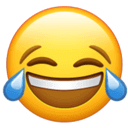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十點人物誌 (ID:sdrenwu)
作者:洋平
編輯:三金、野格
題圖來自:AI生成

“他們是在‘活著’。”
在為幾位老人寫過回憶錄後,巴一(化名)深切感受到了“活著”這個詞語的力量,正如餘華所說,“這種力量在於忍受,忍受生命賦予的責任、現實給予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在此之前,巴一是一名運營,因為熱愛寫作,她轉型成一位自由撰稿人,並在在今年五月辭去工作。為老年人代寫回憶錄是她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像巴一這樣熱愛寫作的年輕人不少,他們敏銳地發現了這潛藏的需求,在社交網路、線下集市以及養老行業中尋找希望被書寫的老人們。與他們聊天、梳理他們的回憶、寫下他們一生的故事。
越來越多的人湧進這片藍海,代寫回憶錄成了“銀髮經濟”裡的一條新賽道,是一次面向老年人的情緒價值消費。一本回憶錄有時是兒孫送給長輩的禮物,有時也是老人希望留給子女的一點念想。對一些老人來說,僅僅是向一個年輕人回憶自己的一生,就是種安慰和釋放。
這也是同屬於寫作者和老人的獨特情感體驗。在那廣闊又瑣碎的記憶之海里,年輕人與祖輩相遇,試著尋找老人們那早已模糊不清的小小“自我”。

在回憶錄裡,
老人們延續著過去的生活
在湖北農村一個自建房的客廳,青梅(化名)看到對面的那位老年女性沉默著、獨自陷入了記憶裡。
老人正在回憶自己的婚禮。等她想好了開始說,青梅發現,那遙遠的屬於少女的嬌羞重新在她皺紋間漾出來。
老人著重描述了一件衣服,那是她結婚時姑姑親手給她縫的嫁衣:大紅色、龍鳳褂,用金線繡上了龍和鳳的圖案。“它好豔”,老人說,“我從沒穿過這麼豔的衣服。”那一年,她剛滿二十,要與經人介紹認識的男人結婚,兩人還不太熟。但此後,他們共度了一生,有了子女和第三代。
青梅採訪這位老人時,她的孫女也坐在一旁,聽奶奶講起這段她從未聽過的故事。正是她在社交平臺上找到了青梅,希望將這部回憶錄作為禮物送給奶奶。採訪結束後,青梅用第一人稱寫下了這位老人的回憶錄。
老人們大多願意傾訴。老年學的持續活動理論認為:老年不是一個獨立的階段,而是人生延續的一部分,比起進入新的生活狀態,老年人更傾向於延續過去的生活。回憶錄便是這樣一部時光機,幫助老人在情感上延續曾經的生活,從中獲得慰藉。
從2023年初開始,青梅已經為多位老人寫完人生的回憶錄。一部五六萬字的回憶錄,從前期溝通、採訪、成稿、裝訂成冊,花上她兩個月工夫,收入二到五萬元不等。
這是個誘人的數字。進入2024年,越來越多年輕人發現了其中的商機,他們中有教師、白領、從事寫作的自由職業者,以及逃離網際網路“牛馬”生活的打工人。

〓 工作中的青梅。受訪者供圖
陳穎一(化名)是一位四處旅居的自由寫作者,從今年八月開始代寫回憶錄,她的第一位客戶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當時,這位客戶正在與妻子離婚,小孩在上小學三年級,未來將跟著妻子生活。
這位父親平時和孩子的交流很少,到現在,父子之間已經找不到開口的方式。他想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書給兒子,希望他以後能瞭解父親是個什麼樣的人。為此,他主動找上陳穎一,想寫一本回憶錄。
對客戶來說,回憶錄成了一種情感連線的方式,講述者說出自己的故事,與晚輩對話,也在其中再次遇見年輕的自己。

1萬元一本的回憶錄,
最難的是尋找客戶
今天,中國社會60歲及以上的老齡人口達2.97億,超過總人口的兩成。“銀髮經濟”被視作超級風口。老一輩人節儉慣了,卻也願意為了情緒價值消費。代寫回憶錄的服務本身附帶著高昂的情緒價值,自然也成了被風狠狠颳起的熱門賽道。
這兩年,坊間開始傳聞,“靠代寫回憶錄、兩個月能提一臺車”。但事實上,這項私人訂製服務的收費並沒有標準可循,全依賴寫作者是否能接觸到高淨值客戶(願意為回憶錄付出高額費用的客戶)。
有媒體報道稱,這類為普通人撰寫的回憶錄的體量基本在3萬字以上,按照每萬字5000元到6000元的收費標準,一部回憶錄的價格在1萬元到8萬元之間。
針對迫切希望入門的年輕人,行業已經發展出了自己的上下游,產生了培訓班、幫助作者和客戶對接的平臺、專門的AI寫作服務等。
代寫回憶錄看似門檻不高,與其他文字工作相比,它不公開出版,只有老人和兒孫閱讀,只需要記憶被平實地記錄,因此對文筆的要求不高,但在從業者看來,這其中仍然包含著大量的工作。一本回憶錄包含了採訪、資料整理、內容架構和行文表達這一系列過程,還包括了後續的設計裝幀。
“一本五萬字的回憶錄,如果開頭的兩千字枯燥到難以卒讀,又如何能讓人讀完這一生的故事。”巴一解釋。
當越來越多人瞭解到代寫回憶錄這門“好生意”,亂象也多了起來。青梅曾遇到一個熱情的客戶,天天來諮詢,宣稱要請她為自己奶奶寫一部回憶錄。青梅已經買好去南方的車票、發去了採訪大綱及合同。臨行前一晚,對方說:“不寫了,不好意思。”青梅猜測,這是“同行”在騙採訪大綱和合同。這樣的情況她已經遇到多次,很多人衝著掙錢來,卻很難沉下心來完成整個流程。
在這一系列難以標準化的工作中,最不可控的就是獲客。
電商平臺上有一些為寫作者提供服務的店鋪,同時也需要外包作者,但一筆交易完成,店家通常會抽走40%。比如說一本五萬字、收費兩萬元的回憶錄,作者忙活兩個月,也許只能賺到一萬出頭。
個人寫作者要接觸老年顧客,方法也是五花八門。青梅和巴一都是透過在社交網路上發帖尋找客戶,前來諮詢的絕大部分是想給父母祖輩送這份禮物的年輕人。
也有寫作者會去老年活動中心發名片、去養老行業展會擺攤,甚至加入夕陽紅旅行團,與老人們聊上一路。
之前就在養老行業工作的寫作者無疑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胖丁在一家養老服務公司工作,在一個養老行業從業者的群裡,他聽人聊起自己遇上一些老年人想寫回憶錄,詢問有沒有寫手。胖丁當下發現了商機所在,今年5月,胖丁(化名)與雷根——一個同樣看準了這一賽道的前網際網路運營,合夥成立了一家專門為老年人代寫回憶錄的公司。
兩人分工合作,胖丁負責引流獲客,雷根負責編寫運營。他們招募寫手,也開設了訓練營教授寫作技巧。胖丁發現,經驗還是得在實操中積累,新手寫的成品,都需要他和雷根再次潤色。
雷根和胖丁也試著用AI來寫。有公司開發出了供老人對話記錄的AI工具,但在當前的AI技術下,寫的東西仍然需要真人潤色,如果提示詞用不好,文筆則更為幼稚。AI只會用第一人稱記錄下最表面的東西,比如“小時候我去釣魚了,我很開心。”AI不能理解生活,也不理解個體經驗之中凝結著的時代。

在回憶錄裡,找到那個理想的自我
胖丁介紹,他們剛完成了創業以來第五部回憶錄的寫作,寫的是趙明才老先生的一生。
這位老人很特別,他是雷鋒的老戰友,在雷鋒去世後,他把踐行雷鋒精神,當做自己一生的事業。趙明才形容雷鋒,“個子不高,長得很英俊。”在他的講述中,這個被典型化的遙遠英雄變得清晰可親了起來。
趙明才在家裡辦了個雷鋒紀念館,和胖丁他們聊起往事來根本就剎不住車,一兩個小時的溝通中,他甚至一口水也顧不上喝。胖丁和同事也隨著趙明才的講述回到了那個特殊的年代,在文字中重現了戰爭時期的炮火、困難時候的草根野菜,還見識了發黃的糧票和依舊被擦得鋥亮的肩章。

〓趙明才的雷鋒紀念館。受訪者供圖
胖丁敏銳地感覺到這份工作中的陪伴屬性,“有些老人的子女不在身邊,採訪的時候,我們幫他回憶過去,傾聽老人的故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老人進行心理上的疏導,提供情緒價值。”
回憶讓那些衰老的臉再次活泛起來。當他們努力而享受地打撈往昔的記憶碎片時,經常會不斷提起同一件事,來回說同一句話,沉醉其中,像一盒老磁帶,總是在最熱鬧毛糙的地方卡殼。

〓為趙明才寫的回憶錄。受訪者供圖
一個國企老員工曾向雷根講起一段經歷。這個故事裡,因為領導卡了自己的調令,憤怒的他衝到麻將館,一腳踹開門,指著領導的鼻子罵,如果不是周圍人攔著,兩人就打起來了。
胖丁懷疑,這段誇張的描述帶著不少美化的成分,畢竟這其中的反叛意味在當年實在罕見。但這個故事早就在老人的記憶裡被反覆重拾、體味,被磨得鋥亮,成為他人生的高光時刻。
青梅也聽過一位老人滔滔不絕講述自己沒有成功的愛情,那是他滿堂兒孫都沒聽過的事情。最後,為了體面,這段遺憾的感情,在回憶錄中被一筆帶過。
回憶始終是不可靠敘事。記錄者大多也不打算在這個時候追求客觀,他們願意為私人訂製的回憶錄罩上玫瑰色的濾鏡。
一個人一生的記憶,長又龐雜,要從中整理出一條線索並不容易。但老人的講述順勢而下,有時會不知不覺走出一條貫穿的線索,那是他們理想中的自己。
女性總忍不住講述自己為家庭的奉獻;離退休老人說話大多有清晰的邏輯重音且熱衷於談論信仰;成功的商人則會渲染坎坷,他們擅長總結出自己最正確的時刻。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獨特的腔調。
也有特別的女性,更自豪於事業而非為家庭犧牲。她找到青梅,想要讓她記錄自己把一間小飯店開成連鎖店的創業史。青梅把“俏江南”張蘭的自傳給她參考,她卻不喜歡其中講述婚姻和兒子的部分,她想要一個更加單純的企業家奮鬥史。
“家庭的部分可以再少點。”她說。
青梅的一位客戶講到自己的發小。兩人當年一起參加高考,兩分之差,考上大學的客戶成了離休幹部,沒考上的發小當了一輩子農民。這位老人會清晰地總結:生活由偶然構成。

兩代人的相遇
大多數時候,講述這些跌宕生活的語調,卻往往是平靜的。
巴一的客戶中,無論是老醫生、老教師,還是成功商人,他們講起過往的語氣都是淡淡的。“很普通啊”“算不上牛啊”,他們總是這樣說。
一位老奶奶護士回憶起自己工作一輩子的醫院的初建,自己是院裡唯一的護士。巴一感慨:“那您是‘開國元老’呀?”老人想了想,微笑著說:“我是。”
說自己的光輝時刻是這樣,說自己的苦難也照樣平淡。老人家已經波瀾不驚,在遲暮的年紀裡,消化掉了所經歷的苦難。
巴一把這些平淡的描述概括為“小小的自我”。一位阿姨講起她生下三個孩子,放棄了自己的事業,流露出的後悔是淡淡的。一位奶奶講小時候看到飛機轟炸後樹上掛著的殘肢,語氣裡甚至已經沒了害怕。有個叔叔講起自己小時候遭遇的家暴,也只是反覆說一個詞,“非常疼”。
雷根的一個訪談物件曾面對無可奈何的分離。他是東南沿海的農民,努力自薦、各處求人,終於找到了一份藥廠的工作。他去了縣城,而妻子只能暫時留在村子裡。每隔兩個月,他才能騎幾個小時腳踏車回村裡,遇上狂風和暴雨,就又會困住他兩個月。講起這些的時候,這位先生連語速也照樣平緩,表情沒什麼變化,倒像一個局外人。
“如果是我,一定會渲染苦難。”雷根說。
也許是時間撫平了劇烈的痛苦,也許是從稀缺時代走來的那代人的共性,他們如此剋制,把自我壓縮成小小一個,以便於從苦難中倖存下來。
而在寫回憶錄過程中,這代人大大的自我,與上一代人那小小的自我相遇了。
青梅的一位客戶講起自己的妹妹,兩人父母早亡、相依為命。14歲的姐姐挨家挨戶討糖水養大了妹妹。妹妹長大後,愛上了一個男孩。姐姐像個母親,不同意這段愛情,強硬地拆散了她倆。後來,妹妹在23歲的年紀意外離世。從此痛苦像背景音樂那樣跟隨姐姐,她總忍不住想,如果不是自己阻撓,妹妹是否會進入婚姻,會有一段不同的人生。
“你說,如果我妹妹還活著,她會原諒我嗎?”在近60的年紀,姐姐哭著問青梅。
青梅突然也哭起來,這段敘述使她想起了自己一段因家人反對而終止的感情。兩人對著流淚,最後老人把紙遞給她。
青梅替妹妹回答:“也許會吧,應該會吧。”
代寫回憶錄所包含的情緒價值,不僅屬於老人,也分享給了他們的子女。
採訪時,巴一總是習慣問客戶們:年輕時候遇到了什麼事?你當時是怎麼想的?她也這樣問了自己的父親。
對巴一來說,父親很少表露自己,是她“最熟悉的陌生人”。她也想了解自己的爸爸有著怎樣的青春歲月。一次外出聚餐,看著爸爸心情不錯,巴一和他聊了會天,像訪談客戶那樣聊起當年。她看見了父親,也看見了代寫回憶錄的意義。
記憶是兩代人互相看見的通道。
作為記錄者,也由此可以閱讀各種不同的人生,從中吸取經驗。巴一說,這正是自己喜歡這份工作的原因。別人的故事總讓她感到新奇,她也願意看種種人生樣板,以此來審視自我。
儘管目前,代寫回憶錄仍然很難作為一份全職工作養活她。不過巴一覺得,未來會有越來越多老人願意留下一本回憶錄。隨著行業壯大,也許代寫回憶錄會像家裝設計服務一樣,讓有不同需求的被書寫者,去匹配不同風格的寫作者。每一部回憶錄會是一次精準的私人訂製。
RECOMMENDED

微信又改版啦
為了讓「鳳凰WEEKLY」出現在您的時間線
星標一下 ★ 為了更好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