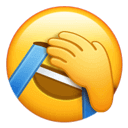來源:脆皮先生(ID:cpxs2009)
01
逃課的時候,我們往往拉著鄭一道去瘋。那是四月微風細雨的午後,已將近畢業了。關、鄭和我,一人一杯軟雪糕,晃盪晃盪地盪到飛機場,立在鐵絲網外看飛機的升降起落。關說過她爸媽看上了夏威夷大學,遲早是要飛走的。突然,我像要發洩一點什麼,迎著輕風朗聲吟:“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才誦了兩句,關推了我的腦殼一下,“去你的!小鬼頭,念什麼念,也不怕傷感。說完就走了,留我愣在原地。
其實,關,聚散本是等閒事啊!何必呢?你素來是這般的灑脫。只要透過升中試,我們還有好長的一段快樂時光,不是嗎?縱然未可如願,但我們共同踩過那許多路途,只須回身拾掇每一個足跡,自是一番溫馨!只要我們有情,天涯何嘗分隔得開?好像一輪彈簧,無論扯到多遠終究還是彈回來的。那時候,就像此刻,一個無雲的午後,陽光灑得我們滿身滿心,我們一人一杯軟雪糕,徜徉藍空下,真真是永恆啊!
——鍾曉陽《祝福》

02
那年(一九六三年)暑假我從芝加哥到波士頓,搭的是順風車,隨身只帶一兩件簡單的行李,其他書籍和雜物都沒有帶(記得是後來寄出去的)。我如此輕裝簡行,為的是表現我的流動性(mobility),似乎隨時都可以到處漂泊流浪,到處為家。至於在哈佛可以待多久,我卻從來沒有想過,反正申請入學攻讀的“東亞地區研究”(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只是一個碩士班,兩年即可修完,以後如何打算以後再說。現在回想起來,我初進哈佛的時候,其實沒有太多的誠意,也沒有什麼抱負。這種得過且過的心態,完全是我的芝加哥經驗令我對自己過去的志願——做一個外交官——完全失去信心所致。大學四年的雄心壯志,在芝大一年之間化為烏有,從這一片烈火的餘燼中如何重新塑造一個新的自我?這是當時我最感困惑的問題。
——李歐梵《我的哈佛歲月》

03
有一天,我從哈佛校園“破帽遮顏”而過,可能當時心情太沉重了,抬不起頭來,迎面幾乎撞到一位老人。他對我大喝一聲,聲若洪鐘地說:“年輕人,抬起頭來,天下沒有應付不了的難事!”我就像碰到禪宗師父的當頭棒喝,頓時醒悟過來。
這一段“奇遇”,我曾多次重述,甚至在最近一篇談我退休的文章中又一次舊事重提,並且說:“我這四十多年在美國的學術生命,就靠這位陌生老人一句話之賜!”他到底是誰?我至今也無由得知,因為當年自己太過靦腆,似乎也沒有向這位老人道謝一聲,就擦肩而過了。
——李歐梵《我的哈佛歲月》
04
那時已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或“四清運動”)前夕,對這些書、畫、音樂的鐘愛(以及我們聚在一起的創作嘗試)可說已經具有了某種“另類”或“地下”的性質。但我自己在當時絕無這種明確的身份意識。只是在若干年之後,當一些文化學者開始發掘地下詩歌和美術的時候,我們的這些活動才被寫入文字並加以“前衛”的桂冠。實際的情況是:我們那時還太年輕,不像老一輩那樣已經沉浮了大半生,知道歷史的重量,因此也不可能像他們那樣或沉默無語或自投絕路。
——巫鴻《豹跡:與記憶有關》

05
下課之後,很多同學擠到保健室來看我,把我團團圍住。我感到很灰心,沒想到寂寞也是鬧哄哄的。
對於失去了玩捉迷藏的樂趣,我一直耿耿於懷;我的生命似乎從此缺少了什麼——那種沙金一樣沉甸甸又閃閃發光的東西。
——袁哲生《寂寞的遊戲》
06
非常美,非常荒涼。但是我怎麼會在這個立體夢境中?我是怎樣到那兒的?不知怎的,那兩輛雪橇已經悄悄離去,留下了一個沒有護照的間諜,穿著他的新英格蘭雪靴和風雪大衣站在那條發藍的白色道路上。我耳朵中的振動已經不再是雪橇遠去的鈴聲,而只是我年邁的血流發出的嗡嗡聲。萬籟倶寂,一切都被月亮這面幻想的後視鏡迷醉、征服。然而雪是真實的,當我彎身捧起一把雪的時候,六十年的歲月在我的手指間碎成了閃光的霜塵。
——納博科夫《說吧,記憶》

07
前進時,在他遇到溝壑,或者碰破頭皮以前,總以為他的一生還在前面,他高傲地看待過去,也不能正確地評價現在。但是當經驗摧殘了春天的鮮花,吹涼了夏日的紅霞,當他醒悟到生活實際上已經過去,剩下的只是尾聲,這時,他對少年時期那光輝的、溫暖的、美好的回憶,就會改變態度了。
大自然以自己永恆的狡計和簡練的手法,把青春賦予人,又把發育成熟的人據為己有,將他安插到、編織到那張四分之三不取決於他本人的、社會和家庭關係的大網中,誠然,他會使自己的行為帶上個人的色彩,但是他的絕大部分不是屬於自己的,個性中的抒情因素削弱了,因此情感和樂趣也愈來愈貧乏,只有智慧和意志依然如故。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

08
風起的時候,我一定要來體育場,一人坐在整個空空灰灰的石階上。風會揚起我的短髮,黑裙子,和地上的紙層。我坐一下午,或想事情或不,或哭或笑或不,都沒關係,走出體育場後,依然又是太陽底下無新事,風已吹乾了我的淚和笑。
藝術家們常愛取景一個滿臉皺紋的老頭孤單一人坐在空蕩蕩的體育場裡。我常想穿綠衫的女孩託著腮坐在那裡會是個什麼樣子,慘綠少年?……卻道天涼好個秋。這種時日真是好,恣意地賴在母親懷裡,笑可以笑得好傷心,哭可以哭得好快樂。
看風看雲看夕陽,想朋友想稻垣想天父,想我海棠葉上的斑斑點點。
啊,我曾經迤邐過怎樣一條又一條紅磚路的少年淚。
——朱天心《擊壤歌》
09
今天是個大好天。一早被鳥兒從夢中喚醒,晴空豔陽,這種天最是叫人手足無措,好像該寫些詩的,要不到海邊或山裡去,要不坐在後院的柳樹下看《創世記》,總該有些美麗事情的!但是面對這樣一個好天,我反而會窩在床上,想,該如何消受這一天,結果總是就如此地在家躺上一天。同樣的,面對這大好的一個青春,日日都覺著該有一些轟轟烈烈的大事才對的,因為青春是如此的好,可是過著過著就兩年,什麼事情都沒有,我也安然。
——朱天心《擊壤歌》

10
爺爺書裡寫過:“再過幾年,朱天心在北一女的那些同學都就職的就職,結婚的結婚了,又若干年後開起同學會來,見了面個個變得俗氣與漠然,像《紅樓夢》八十回後有一章是‘病神瑛淚灑相思地’,昔日的姑娘都嫁的嫁了,死的死了。這時你對變得這樣庸庸碌碌的昔年同學,你又將如何寫法?這不是一句往事如夢可以了得。
以前你曾與她們是同生同死的,現在她們不同了,而你還是昔日的你,你今是拿旁觀者的態度看她們嗎?但她們雖變得漠然了,她們的身上亦還有著你自己。你是如同神,看著現實的她們,也看著你自己嗎?
以前你與她們一道時,其實你也是有著高過她們的,現在你真高過她們了,依然是儕輩啊!《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是永生的,但今你已不能再像從前的與她們玩了,昔年的男孩子也是一樣,他們也不能再與你玩了。以前是大家都年紀小,大家都與天同在,與神同在,所以你與那些女孩子男孩子如同一人,而今是離開了神,只有你與這些人們,以前你是不知不覺都是寫的神的示現,神的言語,而現在你是用的什麼語言,寫的什麼現象呢?”
幾年間我屢屢讀此皆掩卷,直不忍啊,完全無能為力。此時抄錄下來,邊讀邊思之再三,心生恐懼。爺爺我仍無能接此招,請您再等等,再等一等好嗎?
——朱天心《擊壤歌》

11
對於相信不疑的,我們是分享共有了那個一切明朗有情的陽光世界,在那裡,此書是我們的黃金盟誓之書(朱天文語),封存少年的精魄。我所謂的黃金盟誓,是在所有的嬉戲、所有的童音稚嫩言語、所有被眷顧的(走馬鬥狗賞花冶遊,理直氣壯的不事生產)每一太陽之日、所有的祈禱之後,那信仰之所在的核心,如此純粹,我們即是神光靈光,是自轉長新的法輪。何需召喚,大風起兮,我們自己的光照亮了自己。那是少年的本色。
但是少年終究不是物質不滅。漢娜鄂蘭寫班雅明的文章有這麼一段:
生命雖然註定毀於時間的蹂躪,衰敗的過程同時卻也進入結晶化的過程,在海洋深處,曾經活過的生命沉沒、分解,有些東西“受到大海的催化”,以結晶化的新形式與新形狀存續下來,保持原貌,等待採珠人有一天來到,帶回眾生的世界——是為“思想的碎片”、是為“無可名狀”之物,或許更是永恆的“元始現象”。
鄂蘭解釋元始現象,
是一種可以在宇宙表現中發現的具體東西,在其中,意義與表象、語言與事物、觀念與經驗都是同一的。
同一的,約略等同八十回前的大觀園的純真直觀,不證自明?一旦吃了禁果,張開了眼睛,離開伊甸園,憂患開始,磨損開始,兩難開始,我們遂恆處於分裂不堪?
(“一個人不快樂,因為他說了他想說的,另一個人快樂,因為他不說他心裡所想的。”)
許多年後步入中年的今日,少年遠矣,讓人怯於相認。流年似水,不捨晝夜,我不懷舊,不傷逝,更不眷戀動心、願望逆轉時間再來一次(將子無死,尚復能來?),雖然閱讀中偶爾不免要笑出聲要臉紅,我暗暗驚訝書中的陽光世界何曾黯淡?青春早期的熱血何曾冷淡?那些如同精衛鳥鳴的自創言語又何曾弱去?
是我們這一代夜深忽夢的那一塊陸地漂移的彼岸彼世界。
——林俊穎《從前有個陽光世界》

12
我們常常出去爬山游水,坐在山頂海邊,大談文學人生,好像天下事,無所不知,肚裡有一分,要說出十分來。一個個胸懷大志意氣飛揚,日後人生的顛沛憂患,哪裡識得半分!
——白先勇《樹猶如此》
13
“綠鬢舊人皆老大,紅梁新燕又歸來,盡須珍重掌中杯。”——這是晏幾道的《浣溪紗》,鄭因百先生正在開講《詞選》,我逃了課去中文系旁聽,唯有逃到中國古典文學中,存在的焦慮才得暫時紓解。
鄭先生十分欣賞這首小令,評為“感慨至深”,當時我沒聽懂,也無感慨,我欣賞的是“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晏小山的濃詞豔句。
那幾年,聽鄭先生講詞,是一大享受。有一個時期鄭先生開了“陶謝詩”,我也去聽,坐在旁邊的同學在我耳根下悄悄說道:“喏,那個就是林文月。”我回頭望去,林文月獨自坐在視窗一角,果然,“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聯想起司空圖《詩品》第六首《典雅》中的兩句詩來。日後有人談到林文月,我就忍不住要插一句:“我和她一起上過‘陶謝詩’。”其實《現代文學》後期與臺大中文系的關係愈來愈深,因為柯慶明當了主編,當時中文系師生差不多都在這本雜誌上撰過稿。
臺大文學院裡的吊鐘還停頓在那裡,可是悠悠三十年卻無聲無息的溜走了。逝者如斯,連聖人也禁不住要感慨呢。
——白先勇《樹猶如此》

14
《現代文學》創刊,離現在已有三十二年,距八四年正式停刊也有八年光景了,這本雜誌可以說已經變成了歷史文獻。醞釀三年,《現文》一至五十一期重刊終於問世,一共十九冊,另附兩冊,一冊是資料,還有一冊是《現文因緣》,收集了《現文》作家的回憶文章,這些文章看了令人感動,因為都寫得真情畢露,他們敘述了個人與這本雜誌結緣的始末,但不約而同的,每個人對那段消逝已久的青春歲月,都懷著依依不捨的眷念。
陳映真的那篇就叫《我輩的青春》,他還牢記著一九六一年那個夏天,他到我松江路一三三號那幢木造屋,兩人初次相會的情景——三十年前,我們曾經竟是那樣的年輕過。
所有的悲劇文學,我看以歌德的《浮士德》最悲愴,只有日耳曼民族才寫得出如此摧人心肝的深刻作品。暮年已至的哲學家浮士德,為了捕捉回青春,寧願把靈魂出賣給魔鬼。浮士德的悲愴,我們都能瞭解的,而魔鬼的誘惑,實在大得難以拒抗哩!柯慶明的那一篇題著:《短暫的青春!永遠的文學?》回頭看,也幸虧我們當年把青春歲月裡的美麗與哀愁都用文字記錄下來,變成篇篇詩歌與小說。
文學,恐怕也只有永遠的文學,能讓我們有機會在此須臾浮生中,插下一塊不朽的標幟吧。
——白先勇《樹猶如此》
2.《我的哈佛歲月》,李歐梵 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9月
3.《豹跡:與記憶有關》,[美] 巫鴻 著,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2022年6月
4.《寂寞的遊戲》,袁哲生 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後浪,2017年9月
5.《說吧,記憶》,[美]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著,王家湘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4月
6.《往事與隨想》,[俄] 赫爾岑 著,項星耀 譯,四川人民出版社|後浪,2018年9月
7.《擊壤歌》,朱天心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2016年6月
8.《樹猶如此》,白先勇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2011年11月






長按下方圖片
識別二維碼 關注正反讀書




聽說轉發文章
會給你帶來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