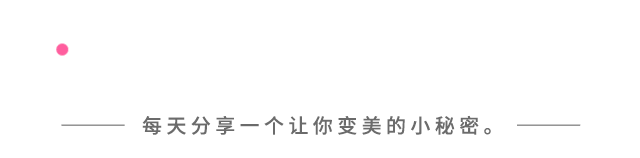文| 徐楊
編輯 | 江臾
出品 | 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室

“我可能要放棄打藥了”
5月6日,又到該化療的時間了,鄧靜沒有出現在醫院裡。
第二天,她在自己幾十萬粉絲的社交媒體賬號上發了一條影片,說自己心裡悄悄做了個“不容易,但或許能帶來改變”的決定:“我可能要放棄打藥了。”
賽博世界裡的鄧靜,以“鄧靜媽媽(長命百歲版)”的名號出沒,帶著這樣幾個關鍵詞:乳腺癌晚期,超強生命力,時時在放聲大笑,永遠樂觀。現實中的鄧靜是一個38歲的普通“貴州嬢嬢”,十幾歲職高畢業就出來打工,做過加油員,賣過化妝品、炒飯、爆米花,還兼職做過房產中介,朋友圈裡裝滿房源資訊,微信名後面跟著手機號。
患癌以後,她開始拍短影片,在影片裡她“挑戰完成100個人生遺願”:跟母親和解,和老公重新約會,“爆改”自己,嘗試新中式、亞文化,跳女團舞,玩滑翔傘……

她的檔案傳輸助手裡還存著很多願望:“認真地和(兒子)何子申呆一天,陪他做他想和我做的事,沒有煩躁,沒有批評,沒有拒絕(我覺得我對兒子有很多要求,我希望能沒有要求的和他在一起)。”
“我想洗澡自由(生病後洗澡要看天氣,關鍵連搓澡都會累,這是現在想做的)”
“我想和媽媽好好呆一天(我和媽媽沒有親密接觸,在她面前我都很勇敢,都能獨擋一面,我想和她去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旅行,放下家裡的所有,走走看看,玩玩)”
“我想給我妹夫講,我很不喜歡他,但是我希望他和妹妹能幸福”
“我想哭(我覺得這輩子太苦了,小時候苦,長大苦,現在更苦,很多時候都無能為力)”
一開始,她拍影片的初衷很簡單。只是為了“給孩子留下一些念想”,沒想到踩中巨大的流量。一個“普普通通的貴州嬢嬢”,莫名其妙擁有了幾十萬粉絲,有商務找來,她賺到一點治病的錢。

後來的事情像個奇蹟一樣,一種對她的病最有用、但她負擔不起的藥在今年1月被納入醫保。靶向藥DS-8201,在此之前這種藥打一次要三萬,她在影片裡說,即使賣掉房子也打不起幾次。那天從醫院回來的路上,她仰天大笑,笑出了眼淚和大牙:“這一次,是我贏了。”
幾年來,她面對絕症展現出的明亮和勇氣鼓勵了很多人,不斷有人發來長長的私信,講自己人生中的至暗時刻,以及從她這裡獲得的力量。甚至有一個人在私信裡告訴她,自己在想要跳樓前一秒刷到她的影片,決定活下去。
或許因為這樣,當鄧靜在影片裡宣佈“我可能要放棄打藥了”的時候,一切變得如此令人難以接受。人們七嘴八舌地湧入評論區,多數是勸她堅持。有人說自己的親戚得了癌症,吃癩蛤蟆吃好了,讓她去某個地方看“神醫”。有人勸她不要放棄,“現在有藥可打,是幸運的”“熬過這5年,醫療一定會進步”。還有人讓她想想家人,“不要停。娃兒怎麼辦?”翻著那些評論,鄧靜想起和丈夫何哲爭吵的時刻,她問他:“我能不能為我自己?”丈夫說:“不行。”
她在影片裡說:“從今年開始,每次打了那個維持了特別久的藥,身體的反應就特別特別的大。以前也是21天打一次藥,難受個幾天,但是總有十多天是可以恢復的。去做我想做的事,去擁抱生活,去完成我一個個的願望。但是現在情況變了,同樣是21天為一個週期,打完藥之後,身體要十多天甚至更久才緩得過來。”

“每次在副作用裡面苦苦掙扎的時候,我都在思考,生命的意義到底是啷個?這個藥是為了讓我活下去,可如果代價是大部分時間都在痛苦和虛弱中度過,那我活起的質量到底在哪裡嘛?”

悲傷也是一天,快樂也是一天,
為什麼不快樂呢?
現實中的鄧靜如同她自己所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貴州嬢嬢”。她長著一張圓圓的臉,皮膚很白皙。頭髮烏黑濃密,非常光亮。這讓我常常感到恍惚,忘記她是個病人。但有時說著話,我聽見句子中間會飛快地掠過一口嘆息,那表明她又沒有力氣了,隨時可能睡過去。

她怕冷,空調要全天開著,保持在25度。腫瘤切除手術後,她的右側乳房和腋窩的淋巴組織被掏空,肋骨泛起,一條長長的傷疤像藤蔓一樣擁住她的身體。在手術很長時間以後,她才能直視鏡子裡的自己。
我們在遵義見面,鄧靜和何哲帶我去吃毛肚。“我已經好久沒有吃好吃的了。”鄧靜很期待,一定要吃比較辣的那家。打完藥以後,總有十天吃不下東西。剩下的十天,又是這不能吃,那不能吃。她連中藥都喝出了甜味。“哪一天吃飽飯,我就覺得我好開心。”
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這都是兩個嘴巴閒不住的人。兩口子沿路點評著街邊的店鋪,為此還難免一頓嘴鬥:“你看他們家好寬的……但是說實話我覺得他們家不太好吃。”鄧靜說。“好吃。”何哲不同意。“我說好吃就好吃。”“我說不好吃就不好吃。”說著說著,兩個人又達成共識:“那家的牛肉可以。”“牛肉可以,粉要吃老陳家的。”
他倆的相處方式一貫如此。即使是在面對鄧靜確診的訊息時,他們仍然把一切處理得像情景喜劇一樣輕快。2023年的情人節,他們在凌晨四點收到了檢查結果。鄧靜說:“給你講個好訊息,還有個壞訊息,你要聽哪個?”何哲說:“好訊息噻。”“好訊息安逸了噻,這次沒人管你了喲。”何哲嘿嘿嘿地笑了起來,問,“壞訊息呢?”“壞訊息啊?我得癌症了。”
詼諧的鏡頭剪輯外,何哲沉默半天,什麼話也沒說,站起身來抹一把臉,去了衛生間。鄧靜知道他在哭,她坐在床上也哭。她的腦子裡迴盪著一些問號:怎麼辦?孩子怎麼辦?父母怎麼辦?
2023年6月,鄧靜被推進手術室。從早上十點開始,手術持續了8個多小時。在那之前,鄧靜已經做了6次化療。到了第4次的時候,身體產生了劇烈的反應。全身像被打了“軟骨散”,連撐著坐起來都很難,躺著也是“昏天黑地的難受”。上吐下拉,一盆一盆拉血。但好在終於能做手術了。他們想,把腫瘤切掉,人就好了。結果,手術後兩個月,鄧靜複查時發現癌細胞已經肺轉移,她又哭了兩個小時。

“遭那麼多罪,以為自己會好,結果也並沒有好。”她悄悄在網上搜,看自己還能活多久?結果顯示:3-6個月。面對何哲,她扮演著一種樂觀的角色:“你看我能吃能睡的,根本死不了。”何哲笑笑不說話,他心裡很清楚,“肺沒辦法治,它是多發性的。(癌細胞)不是一點,滿肺都是,很多。”
手術後,鄧靜又經歷了25次放療,每天1次,每週5天。她的皮膚出現了嚴重潰爛,醫生判定達到了三級燒傷的程度,整個傷口被“烤脆了”,輕輕一摸就破皮,連帶著周圍的皮膚一同脫落。她在一次採訪裡形容過那時的感受:“這一年下來,沒有一天是好的。我躺在床上,每天這樣躺著,就覺得人活著沒意思,活著幹嘛?”
那種狀態持續了一年,直到現在都難以回想。他們的鄰床祁姐是個豁達的北京大姐,抗癌12年了,乳腺癌四期,有6處轉移。但總勸慰他們:“即便你明天真的沒了,在那之前,悲傷也是一天,快樂也是一天,為什麼不快樂呢?”
鄧靜想想覺得有道理。如果死亡是必然的,在它到來之前,人到底應該怎麼活?一定不是像現在這樣。“不曉得哪天都不在了,你要在乎有沒有錢,關係好不好?誰喜不喜歡我,有關係嗎?我再去糾結這個病對我傷害有多大,有用嗎?”
她強行把自己從病痛裡打撈出來,努力給自己找點事做。一個職高畢業就外出打工的人,決定在直播間讀書。開啟心靈雞湯,一行一行往下讀,鄧靜覺得自己的心靜了一些。賺到錢就更好了,能治病,給家裡減輕負擔。一個月後,她果然有了兩個固定的鐵粉,一個是老公,一個是兒子。有一天,兒子實在忍不下去,說:“媽,別播了,瞌睡都聽來了,還播啷個?”
鄧靜堅持每天出去走一走,到河邊散步,吃好一餐飯,讓自己的精神變得茁壯起來。何哲盡力陪她做每一件事。直到有一天,鄧靜宣佈,她要拍短影片,記錄自己的生活,給孩子留下點東西——“小兒子太小了,我怕他記不得媽媽的樣子。大兒子呢,我又怕他太記得我,會想念我。”

鄧靜和何哲在江邊散步©徐楊

我是一個從來不哭的人
鄧靜的“團隊”陣容無疑是個“草臺班子”:作為鄧靜閨蜜的兒子,小朱過去唯一和短影片有關的經歷是宣傳自己家的麻將室——那個麻將室最初是在鄧靜的建議下開起來的,裝修的時候,何哲還出了不少苦工,不小心把手弄傷了。另一名成員小龍是小朱拉來的好朋友。他們在川美學遊戲相關的專業,快畢業了,沒什麼課。他們週六週日跑到遵義來拍影片,週一又坐高鐵回學校上課,把這個賬號當畢設來做。小朱告訴我,當時鄧靜找他,僅僅是因為“我是她唯一認識的年輕人”。
在小朱的成長經歷裡,鄧靜一直扮演著一個“保護神”的角色。他幼年時父親去世,有親戚想分走家裡的房產,還霸佔了他們家的車。鄧靜帶著丈夫何哲跑到他們家,死死堵在門口。後來好幾年的時間裡他們住在一起,鄧靜照顧他,接他放學。小朱問鄧靜,到這個份上了,你還有什麼願望?就這樣,“遺願清單”,成為了鄧靜的影片主題。
沒有技巧,沒有角度,最初拍攝的裝置就是一臺舊手機。按照小朱的指導,“有什麼好玩的事,你們就拿著手機拍自己。”於是,鄧靜的影片裡常常是一張大臉懟上鏡頭。他們發過去的影片素材裡,有時候能“一鏡到底”半個小時。
無論如何,第一期影片總算發出去了。她平靜地講自己確診的經過。問大兒子:“有一天媽媽不在了,你啷個辦呢?”大兒子說:“我也不活了噻。”下一秒,鄧靜的手揪上了兒子的耳朵:“耶?以後不準像這種講,聽到沒得!”又問小兒子:“么兒,萬一媽媽有一天不在了,你會啷個辦?”小兒子那時不滿三歲,口水還滴溜在嘴邊,看著媽媽笑:“媽媽,媽媽。”鄧靜嘆口氣:“你不懂。”
她的每個影片開頭都會喊一句話:“有限的生命,無限的可能。”就是這樣幾個無比家常的粗糙鏡頭,突然在網路上“爆了”。一個社交平臺上一晚上蹭蹭蹭漲了10萬粉,另一個也是一天五六萬,普普通通的貴州嬢嬢鄧靜,成為了那個感動無數人的“鄧靜媽媽”。
他們總是把影片處理得無比歡樂,但傷痛的底色一直都在。小朱聽媽媽形容過,從前的鄧靜,不哭,也不笑,總是撇著嘴面無表情。拍影片以後,她嘗試去做很多事,也釋放了從前緊繃繃的自己。“做了這些事情之後,她才會去想、去感受。”小龍說,“我就天天看她哭,我喊她去寫個感想,邊寫邊哭。喊她去唸一下自己的遺願清單,邊念邊哭,或者跟大家談心,邊談邊哭。最後採訪的時候說,我是一個從來不哭的人。我每次都要翻白眼。”
母女關係是鄧靜影片裡反覆出現的主題。小朱說,有幾次,他們放下影片不拍,讓兩個人開誠佈公地聊從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鄧靜的母親是個老實本分、大字不識幾個的農村婦女,嘴硬,說話也不好聽。經歷過兩次婚姻,嫁給了兩個會打她的男人。鄧靜生孩子的時候,她打來電話,問:“我要來看你嗎?”

鄧靜和母親©徐楊
鄧靜的生父在她8歲那年早早去世,繼父在菜市場裡擺攤補皮鞋,母親是環衛工人。作為長女,母親沒把她當成孩子,她要洗衣服煮飯、收拾家務、照顧妹妹。那時候她最討厭週末,要從早上七八點鐘就起床洗全家人的衣服,一直洗到下午四五點。母親和繼父常因為錢大打出手。她不得不讓自己“兇點”,才能幫著母親幹架。
有一年,鄧靜跟繼父不記得是因為學費還是生活費的事情打架,母親叫她滾。鄧靜離家出走,跑到了同學家,跟著同學的姐姐到酒吧當服務員。洗盤子、擦桌子,幫別人買酒,從下午六七點上到凌晨一兩點。一個月沒回家,母親也沒有找她。這件事到現在仍是一個結。有一期影片裡,鄧靜故作輕鬆地提起這件事,她試探地問母親:“你搞忘了,找都沒找我。找我沒得?”母親沉默,看向了別處。
“後面都已經覺得和解了,其實是我自己跟自己和解了。”另一期影片裡,她錄了一卷錄音帶給母親,講那些說不出口的話,母親哭了。她想起坐月子的時候回到孃家,母親每天給她煮6個荷包蛋放在面前:“起來吃了,冷了。”去北京看病的時候,母親也曾悄悄塞給她一些錢,學會打影片和她聊天。後來,鄧靜給母親介紹了一種叫做短劇的東西,於是整個下午,他們家的小超市裡都回蕩著扇耳光的聲音:“敢打我?”“你是我養大的,我打你怎麼了?”

鄧靜和母親
對於媽媽拍影片這件事情,大兒子何子申起初不太理解。對於一個10歲的小男孩來說,“癌症”這個概念是如此遙遠,但媽媽生病這件事的影響又如此具體。上完課,老師特地把他留下來,對他說:“你媽媽生病了,不要惹媽媽生氣”,喊他好好學習。他很煩那種感覺,也害怕同學們也知道了,會看不起他。所以當媽媽在家裡宣佈要拍短影片的時候,他很反對:“不要拍。”
“他們怎麼看你,有什麼關係嗎?”鄧靜說,“你看我那麼痛苦都還想做事情,你沒有覺得這是一種精神嗎?”正好那時候,一個女孩給鄧靜發了一條長長的私信。她在信裡說,自己有雙向情感障礙,但是被鄧靜的精神感染,會好好活下去。鄧靜把這條私信念給何子申聽,“未來我不在了,除了可以給你們留下念想,我還去鼓勵了很多人。”
讓何子申沒想到的是,他的很多同學都成為了鄧靜的粉絲。他們打電話來告訴他,你媽媽好棒。“還有兩個人跟我成了很好的朋友。”

人到底要怎麼活?
那條決定放棄打藥的影片發出後,我問小龍,鄧靜現在是不是查不到癌細胞了?“查得到啊,只是她不想化療了。她覺得這樣子沒意思。”小龍說,“這是她的人生。我們做弟弟的只能支援她。”
幾天後,鄧靜一個人來北京複查,我去醫院看望她。午飯時間,她穿著寬寬大大的病號服,在病房門口買了一個菜糰子、一盒米飯。“他們不讓出去。所以辦好住院,我就去買了一些翅尖、豆腐皮。”她壓低聲音,偷偷向我傳達一些經驗:“他們的菜確實很難吃。”
即使在這樣的時刻,她也相當敬業,時刻保持著一個自媒體人的職業素養,“他們都習慣了我舉著手拍影片。”我來了以後,她終於不用再到哪兒都像打卡一樣自拍了。在進入CT室之前,她把手機遞給我:“待會我進去的時候你幫我拍一下,我出來的時候也可以拍一下。”面對如此重大的責任,我有些謹慎,問她,應該怎麼拍?用前景、中景還是遠景?她頭也不回:“隨便拍,我們都是隨便拍。”

三年前,鄧靜就是在這家醫院確診了乳腺癌。這是她第一次一個人來複查,以前這些瑣碎的事,都是何哲來操持。有時她覺得他過分焦慮。她去玩滑翔傘,何哲覺得不行,“這是適得其反。一定不能劇烈運動,不能累,會加速它(癌症)的程序。”鄧靜對此很不屑,“我做的好多事情,他都不敢。”
出發前,何哲不放心:“你搞得清楚不?”鄧靜嗆他:“我長了嘴,我可以問啊!”她想著,醫院不讓陪護,家屬來了也得住賓館。這兩個月沒有接到廣告,能省點是點。結果搞出好多烏龍。坐飛機忘了取票,被安檢攔了下來。嘴裡唱著“我是鄧靜,我是鄧靜,強強的鄧靜”,結果一進醫院又懵圈了。付完錢站在視窗,心裡想:“怎麼還不讓我走呢?”原來是忘了輸密碼。往那一坐,排號的紙就不見了,只好挨個求人家站起來,“讓我找一找我的號。”
打藥之後,她的身體發生了很多變化。眼睛裡像是蒙著薄薄的霧,看東西全是花的。記憶力也變得很差,一句商務廣告詞要拍二十遍,轉頭就忘得一乾二淨。“10天15天都躺在床上,我能陪孩子什麼?他來叫一聲媽我都冒火。”
鄧靜感覺這一切沒意思。為著打藥的事情,她不止一次和何哲生氣。這樣的對話反覆出現:鄧靜問:“能不能不打了?”何哲答:“不行。”勸她為孩子想想。起初,鄧靜只是答應“好”。後來,她忍不住了,問:“我能不能為我自己?”何哲說:“不行。”靶向藥進了醫保後,何哲說:“那麼貴的時候我們都打,現在進醫保你不打了,你不覺得虧嗎?”鄧靜想想是虧,那就打,至少每個月還有11天是好的。
起初,打一次藥,大概要恢復10天。剩下的11天,雖然身體還是發軟,但算是可以正常生活。後來,痛苦的時間被不斷拉長,她每天數著數過日子,3月份,大概有15天左右,還有“那種感覺”,嘴巴沒味道,想吐。4月,時間又變成了十七八天。沒好好過兩天日子,下一次打藥又來了。
“打完藥以後特別難受,我常常都跟他講,可不可以不打了嘛?”何哲不說話,“他沒有辦法答應我,但他深知我是多麼想不打藥。”在放棄打藥這個問題上,何哲一向態度強硬。為此,他們有過很多次爭吵。她有點生氣,“痛又不是你痛。”那幾天,何哲有點感冒,吞口水都吞不下去,鄧靜嗆他:“僅僅一天你就受不了了,我每個月、每天都這樣,你要我怎麼辦?”
但這次,何哲沒有反駁,他只是看著她:“你想好了?你都發影片了,你就肯定是要這樣幹了,是不是?”鄧靜說,是。“你不怕轉移很快嗎?”“你在想啥?”鄧靜打斷他,“不打藥了,我能吃能喝能睡,萬一出去遊一圈回來,我病就好了呢?你為什麼不想我好了呢?”丈夫嘆一口氣,好嘛,聽你的嘛。
這件事對何哲來說很難。談戀愛那年,鄧靜19歲,何哲20歲。像小孩一樣吵吵鬧鬧地,十幾年就過去了。他們都年幼喪父,用渾身的刺把自己包裹起來,直到對彼此袒露出柔軟的肚皮。有時,他寧願病的是自己。在鄧靜生病前,何哲本打算和別人合夥做高速公路養護維修,結果變故突如其來,他把自己撤了出來,“沒辦法,我要照顧她。”他沒想過失去了經濟來源該怎麼辦,“當時的想法是陪她走過最後的時光。”

鄧靜和何哲
在CT室門口等待檢查的空隙,鄧靜拿出手機,開始翻那條“放棄打藥”影片下的網友評論。有人祝福,有人共情,有人勸她堅持,她刷刷地略過那些,指著一條評論對我說:“你看,也有正常的。”那條評論寫道:我媽媽淋巴癌化療6次,最後一次結束之後我媽說我再讓化療她就死給我看,現在停了兩年了,她一切正常。
她一連說出很多理由:繼續打藥,可能真有治癒那一天,也可能在那天之前,就會把自己的五臟六腑打廢。不打藥,起碼還能吃得進去飯。萬一真的不再打藥,癌細胞瘋長怎麼辦?“我問過我自己,就算這個結果,你能不能接受?我覺得我可以的。”
她興奮地向我描述接下來的宏偉人生藍圖,她想去一直以來嚮往的床車旅行,從219國道、331國道、228國道三條線環遊中國。她設想得很好,“只要我不打藥,我至少可以吃得進去。吃得進去,每天開開心心的,我的身體是不是變好了?我覺得有種深刻的聲音告訴我,繼續打下去,你不是因為癌死的,是因為這些器官衰竭而死的。”她說,“萬一我真的好了呢?不是也有很多奇蹟嗎?”
“機率太低了。”我說。她看我一眼:“我就是那機率!”
“我問了我自己的內心,反正人都要死,最終都走了,我什麼時候死,那不是我能決定的,對不對?我能決定的是我怎麼活。”鄧靜說,“與其像這樣,還不如活得鮮活一點。這輩子我活到80歲,也才3萬多天,我每天都在這上面耽誤,每天病怏怏的,我覺得不值得。”

很遺憾,鄧靜日思夜想的床車旅行計劃再次流產了。和我分別第二天,她的老病友祁姐看見那條放棄打藥的影片,專門找到了她。“她現在的狀態非常不好,已經沒有任何藥物可以治療她的身體。她說,你現在至少還有藥可以打,還有希望。”
鄧靜哭了,“看到她癌後期發展很快,我就害怕了。”“我現在的課題就是打藥,怎麼打藥,能不能承受?其實也都是做自己,我也怕癌痛,我也怕很快(復發)。”現在,她的身體裡四處埋雷:肩膀上靠近甲狀腺的位置,有一個不明物體,查出了一點點血流訊號。子宮裡還有一個不知道是囊腫還是肌瘤的東西。它們會不會在停藥以後瘋長起來?一切都是未知數。
小朱告訴我,其實在最初,他問鄧靜有什麼願望的時候,她想了很久說,她想去西藏,想開車去自駕遊。“我覺得是離天最近的地方。”鄧靜說。離天最近幹嘛呢?“不知道幹嘛,我就想去。”然而,小朱說,“她的肺根本就不允許她上高原。”
見完祁姐,鄧靜哭得很兇。“不能完全做自己,也是好矛盾。”她後來告訴我,她的身體和精神在強烈地對撞。21天一次的治療,疲憊得隨時可能睡過去的身體,還有哇哇大哭的孩子,有父母、丈夫、姐妹,他們離不開她。“如果出去了,我肯定想毛豆(小兒子)的。如果孩子遇到了什麼事情,父母遇到了什麼事情,我肯定要回來。”
“所以本來我想好了,最後沒有走,我覺得我要去面對我的生活。”
從北京複查完回到遵義,幾天後,她走進醫院,第22次打DS-8201。長長的注射器刺破皮膚,身體的痛苦,精神的不自由,“習慣了也就沒那麼聲嘶力竭了。”她在影片裡寫,“只是偶爾看著窗外自由飛翔的鳥兒,心裡還是會泛起一絲漣漪。”

不過,野草一樣的鄧靜,仍然沒有放棄建立自己想要的生活。西藏去不了,她就在山裡找了個小院子,在那裡搭起帳篷,她決定先小範圍地為自己活一下。營地老闆慷慨地表示,土地和帳篷隨便用,收水電費就可以了。他們全家上陣,自己拿鐮刀鋤草,用鋤頭墾地,穿上雨衣和雨鞋冒雨清理礙事的石頭和雜物,何子申也來幫著清洗帳篷。
床墊、移動儲物櫃、桌椅板凳,暖黃色的檯燈,小院一點一點地被佈置起來。她白天在陽光下擦洗傢俱,中午到“鄰居”家蹭飯,再繼續回來釘好最後一塊樹皮圍欄,接上天然氣,通好電,高興地圍著它轉了好幾圈。坐在那兒發呆,聽見鳥叫的聲音,“好安逸哦,在這裡怕不會失眠都要給我治好哦。”

鄧靜說:“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都到這個時候了,還折騰什麼呢?”她的社交媒體簽名,是幾年前上綜藝時,詩人餘秀華寫給她的:“火焰一直在升騰,灰燼也是”。在“時間很珍貴,一天不浪費”的日子裡,她想繼續折騰,“我心裡頭那種想要為自己做點什麼的渴望變得特別強烈,像一團火在我心裡燒。現在,我不想再等了。”
在這之後,她撕掉了自己的“遺願清單”。她在影片裡說:“死之前要做了100件事不做,沒關係。理想中的樣子沒有成為,沒關係。一直向前奔跑,跑不動了,沒關係。”她決定放棄對不圓滿的恐懼,放棄打卡,放棄任務,放棄那些“精心策劃的表演”,放棄證明什麼。把自己扔回生活裡,“重要的是,我還在感受,我還在愛。”
 (來源:騰訊新聞)
(來源:騰訊新聞)

◦ 文中圖片除特殊標註均來自鄧靜抖音。
* 版權宣告:騰訊新聞出品內容,未經授權,不得複製和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
為了不錯過每一個故事,大家記得將穀雨實驗室設為星標🌟哦,期待每次第一時間與你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