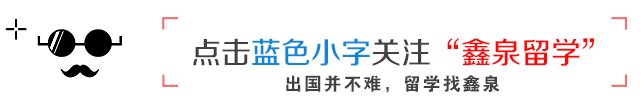"
在廣州工作的羅冬陽決定在30歲這年,帶智力殘障的妹妹逃婚。作為姐姐,她努力從山村考入大學,進入一線城市工作,擁有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自主生活;而與此同時,妹妹羅春月在父母收到彩禮後被嫁給同樣有殘疾的男人,在反覆出走的過程中遭遇多次性侵、生育孩子,最終,又被不願負擔的婆家退婚。

逃婚後這一年
數次參加心智障礙相關的講座,羅冬陽都發現自己是家長中唯一的姐姐。
“孩子不喝飲水機的水,去喝水龍頭的水,怎麼辦?”在廣州殘障家長們組織的專業交流會上,專家分析著案例,羅冬陽環顧幾百人的會場,到場的家長多是焦灼的母親們。8月,在一個有11個心智障礙孩子參與的職業培訓營上,羅冬陽去開家長會,發現其餘10個也是母親。
今年30歲的羅冬陽沒有結婚。她是為妹妹前來。一年前,羅冬陽帶著29歲的妹妹從贛南山區的農村老家逃婚,來到廣州生活。
站在人群中的姐妹倆長得不像。妹妹羅春月扎馬尾,臉龐黝黑,目光閃躲。她總弓著背,微縮著一米四幾的瘦小身體,說話時詞語在口中像老鼠模糊而倉皇地掠過。姐姐羅冬陽長得高些,披長髮,戴眼鏡,皮膚白皙。說話時她會直視對方的目光,語速平和聲音清晰。在羅冬陽身旁,羅春月看起來與孩童無異。

圖 | 冬陽給妹妹拍的照片
兩人的命運從出生那一刻開始分野。1994年,姐姐羅冬陽作為家中第一個孩子出生在醫院,身體健康、智力正常。兩年後,妹妹羅春月出生在父母打工的工地上,幾個月後還跟小貓一樣大,後被發現是二級智力殘疾。
姐姐一路升學,在2013年成了村裡第一個女大學生。妹妹在2015年嫁給一個患有罕見病、手臂腫脹如氣球的男人,在離家出走過程中兩次被性侵,生下一個男孩,打過一次胎,又在2023年被父親安排了第二次婚姻,彩禮加定金一共23萬元。姐姐羅冬陽感到無法忍受,決定帶妹妹逃離。
帶妹妹逃婚來到廣州生活的第一天,冬陽就拉黑了許多人。老家的“未婚夫”最先發資訊過來謾罵,“我和你妹的緣分是你拆散的,我恨你一輩子”“希望你妹下輩子不要有你這樣的姐姐”。父親在電話中怒吼著讓她們回來。母親的說法稍微委婉,“家裡要割稻子了,趕緊把妹妹帶回來。”
來廣州這一年,僅有6歲孩子智力的妹妹反覆向羅冬陽強調自己不要再回老家。連帶她出門時提起“回家”二字,妹妹都會變得警覺,問回哪個家?
新家是姐姐在廣州的出租屋。去年妹妹剛來時,羅冬陽還沒有搬家,姐妹倆擠在城中村冬陽自己租住的一個狹窄開間。書桌挨著床,沒有廚房。姐姐在自己的桌子旁添上一套小桌椅,又給29歲的妹妹買來兒童益智有聲書、塗鴉填色本和一些教材,教她認識數字。

圖 | 妹妹的塗色畫
冬陽當時在離出租屋不遠的一家傳媒公司上班,月薪7000元。給妹妹找到的那家心智障礙群體培訓基地離得不遠,從巷道中密密麻麻的點痣、10元理髮和港式燒鴨店中穿梭出去,步行20分鐘就能抵達一個沒有騷擾電話、櫥窗明亮的新世界。
基地由同為特殊孩子母親的歐陽秋月創辦,在一棟樓房中,設計成小餐廳的情景。孩子們在這裡將由老師帶領,在模擬餐廳中熟悉社會環境,學習擺盤、送餐、打掃、製作餐飲等工作技能,以期有朝一日融入社會。
明亮的落地窗將包含吧檯與餐廳的空間與露臺分隔。寬闊的露臺上花草蔥鬱,綠色的羅勒葉長得繁茂。妹妹春月和其它兩三位學員常用這些葉子製作檸檬茶,在老師的帶領下烤制餅乾和蛋黃酥。
窗中傾瀉的陽光,總是微笑的老師,自制糕點溫暖的甜香,兩隻肚皮柔軟的小貓,構成一個與姐妹倆的來處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基地的一年中,冬陽眼見著妹妹的狀態舒展開來,有了巨大的變化,從曾經“困住的、被壓抑”的狀態走出,開始“展露自我”。
在老家幾乎從不和家人說話的妹妹來這裡一週後就打開了話匣。出門時看見廣州的街景,她會跟冬陽說“這個氣球很漂亮”“花很漂亮”。回家後的她也有說不完的話,“今天我坐了電梯。”“店裡有人來了,開會,放電視。”有時,妹妹說著說著就睡著了。冬陽看見以前習慣縮成一團睡覺的她,現在肢體伸展開,“睡得四仰八叉的。”
基地的老師也透過微信群不斷向冬陽反饋妹妹的改變。“剛來的時候她眼睛都不敢抬,見到人就躲,像一隻小老鼠。”歐陽秋月老師說。後來,妹妹開始主動跟人說話。有一天,在廚房掌勺的師傅看見矮小的她走了過來,說了一句,“兩隻貓在打架。”

圖 | 妹妹在基地做檸檬茶,旁邊的同學不斷鼓勵她
今年2月,姐妹倆和三妹一起搬到一套二居室,冬陽不再和妹妹睡一個房間後,她發現春月又間歇性回到了從前的狀態。那些她一直不理解的特異行為又出現了。春月自16歲開始扔家裡的東西。家裡四個姊妹包括她自己的衣服,媽媽的衣服,都被春月偷走扔過,媽媽曾在一座山上發現了家裡所有人的衣服,只有父親的她不敢扔。冬陽猜想妹妹可能有強迫症。有時候,她看見妹妹會自己剪掉衣服上很小的線頭,或者一雙皮鞋、一件皮衣上破了一個很小的洞,妹妹就會把整個皮衣都摳禿掉。
在發現自己給妹妹買的八九雙新鞋都被全部扔掉後,冬陽曾短暫地情緒崩潰過。“你自己掙不到錢,我給你買鞋要花錢。鞋子明明還好好的,你幹嘛扔掉呢?”她如此問妹妹,只見春月像在老家時一樣拉著一張臉,沉默不語。和機構的老師交流,大家也沒什麼辦法。冬陽告訴自己不能生氣,改變不了的問題就只能接受。這一年她只給自己買過一雙新鞋。
更顯著的問題是經濟壓力。去年12月,冬陽遭遇裁員失去工作。她繼續找工作,面試了10次,都沒有後續訊息。Hr說最近找工作的人很多。她去面試超市揀貨員,對方說不要戴眼鏡的,容易起霧不好乾活。
裁員後的9個月,冬陽幾乎沒有收入,靠著零散的撰稿和存款,省吃儉用過活。搬家後的二居室月租1200元,冬陽和三妹分攤,自己出700元。村裡每月給予的700多元低保和200元殘疾補貼,基本能覆蓋妹妹每月的伙食費。在基地的每月5000元培訓費用是大頭,此前冬陽透過月捐的形式籌滿了一年,馬上要到期。基地老師提出之後減免一些春月上課的費用,只交每週四烘焙課的530元,每月交2120元。
冬陽希望透過基地的學習搭配各種機構的培訓課程,幫助妹妹提升工作與社交技能,在接下來的一年慢慢嘗試給她找到工作。
基地對於心智障礙青少年們的成長期許,不只是“走不丟、餓不死”,更要“在地球上有尊嚴地生活”——這符合羅冬陽對於妹妹未來的期望。

命運參照
冬陽曾覺得妹妹是自己命運的參照。作為家中第一個和第二個女孩,她們相繼出生在贛南山區一座只有二三十戶人的小村莊中,童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幹活。
想生男孩的父母生下春月後,就去廣東躲避計劃生育,一邊打工一邊繼續備孕。姐妹倆成了留守兒童,和奶奶一起住在一間沒有電燈的平房裡,睡在一張床上。晚上她們摸黑進去睡覺,早上一起起床去村小上學。冬陽負責給妹妹洗衣服、準備盒飯。相比姐姐,那時的她覺得自己更像妹妹的照顧者,幾乎沒有情感交流。
家裡五個孩子,除了四弟外都是女孩,冬陽一直都知道,智力殘疾的二妹春月是最不被待見的一個。二年級輟學後,春月在家幫忙種地、撿柴、餵鴨、洗衣,但衣服總洗不乾淨,柴火也只能撿兩三根。妹妹會被父母呵斥“沒用”。
姐姐冬陽相比妹妹遭遇的呵斥更少。對於妹妹遭受的偏見,還是孩子的冬陽感受模糊。更多時候,她覺得她們的身份接近,都是家中承擔家務的女孩。
10歲那年,妹妹春月開始離家出走,被找到的時候,她出現在鄰居家的閣樓、隔壁村的豬圈、危險的高速公路上甚至深山裡。冬陽認為很多時候,出走是妹妹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她在家幾乎不與家人說話,也不會主動溝通自己的想法,想吃什麼就自己去拿,也許不喜歡某件衣服的顏色、或者不喜歡上面的線頭,就直接扔掉。
冬陽幾乎能理解妹妹每次出走的原因:被父親責罵、感受到母親對她的偏見與不平等、畏懼結婚,或者有時只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人們都認為春月不明事理,但冬陽知道妹妹其實對情感很敏感。妹妹會在別人議論她時,在遠處偷聽,也會在跟姐姐交流時呢喃著分析,誰喜歡她,誰不喜歡她。
出走的習慣持續了十幾年。父親說,自己找春月找過不下百次,一次在高速公路找到她時,他想找警察拿副手銬鎖住她,警察不給。回家後,父親用牽狗的狗鏈改成腳鏈。他想讓春月走路的時候聽到腳上鍊條碰撞的響聲,從而不好意思出走。沒多久鎖鏈就被春月自己弄開了。
妹妹春月定下第一次婚約的2015年,冬陽剛讀大二。村裡有人做了媒,父親收了3萬彩禮,安排剛滿20歲的羅春月出嫁:丈夫是一位患有神經纖維瘤的男人,右手小臂腫脹成紫紅色,佈滿褐色的斑。春月看到那個男人就害怕。
出嫁前一個月,妹妹悄無聲息地出走了。被找回時,家人讓姑媽來勸說,反覆告訴妹妹,“那家人很好,不會欺負你,不會虐待你。”晚上姑媽跟妹妹睡在一起,防止她出走。春月在家人的監視下直至出嫁。
妹妹出嫁的一年前,冬陽考上省內一所大學的園林專業。大一時,她接觸到一家做口述史、劇場、攝影等人文故事記錄的公益機構,報名做了志願者。一次活動中,創始人邀請國外做戲劇的藝術家來學校做劇場,讓志願者們講述自己的故事。有人講自己出身農村又來到小城市的故事,有人講述農村的重男輕女、對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冬陽覺得很有力量。
這兩年寒暑假,她總帶著機構給的一臺攝影機回家,嘗試拍攝一些照片,許多是關於妹妹的:妹妹和媽媽一起摘菜、一個人待著摳手、發呆、在村裡遊蕩。有了攝影機,冬陽覺得自己有了一種新的視角,能夠重新觀察妹妹的境遇及她們身處的這座村莊。
知道妹妹要結婚的訊息後,冬陽舉起了DV,第一次想拍攝一部長紀錄片。婚禮當天,透過鏡頭,她看見20歲的妹妹的臉:一張抹上粉色眼影和腮紅後,仍然皺著眉頭、沉默不語的幼稚面龐。那一瞬間,她感覺這不是一個新婚少女,而是一個智力僅有6歲的孩童。
從老家的臥室出發,穿著白色抹胸婚紗的春月被丈夫背進院子,坐進轎車。鞭炮和禮花在她身後排排炸開,人群歡呼著一擁而上。妹妹從頭到尾沒有笑容。
冬陽覺得妹妹看起來像一隻受了驚的鵪鶉。在多年的相處中,她已經能透過妹妹的神情感知到她的心情:出嫁的一整天,春月一直都驚恐著。周圍有人指引著她完成那些步驟,她的行動緊張而拘謹,還有一些懵懂。她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只是別人讓她做什麼,她就做什麼。
拜高堂的時候,冬陽從圍觀的幾個嫂嫂、鄰居奶奶的臉上看出同情。這些都是從小看妹妹長大的人。有幾次,家裡失蹤的衣服出現在這位鄰居奶奶家,冬陽才知道妹妹並不是把衣服都丟了。還有一次她偷了家裡的豆子,送給這個奶奶吃,回家後解釋說,“她那麼老了,種不到菜吃。”
這些熟悉妹妹遭遇的人,都知道春月是心思細膩、善良的人,但實際心智只有六七歲。奶奶在春月出嫁的那一刻,突然哭得很厲害。冬陽感受到,那哭聲中擔心大於喜悅。春月出生幾個月時還像小貓一樣大,是奶奶堅持照顧,妹妹才得以存活。
冬陽惶然覺得這一切都很荒唐。大人們正做著一件愚昧的事,但他們沒有覺察。人心的善良、悲憫與醜惡在村莊中迸發,最終仍是醜惡佔了上風。整件事只能用殘忍去形容。
回家後,她將婚禮上拍攝的妹妹的照片發在朋友圈,配文“憂傷的新娘”。除了記錄,她不知道該怎麼辦。她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去對抗所有的親戚。只能記錄下一切的她心中決定,這部片子將以妹妹的名字去命名。

忍心的過程
第一次感知到行動的必要性,是冬陽知道妹妹被性侵時。婚後兩個月,婆家對產檢起疑時,母親把冬陽叫回了家。冬陽一個詞一個詞地與妹妹確認,最終勉強拼湊出事實:婚前出走的那一週,在山村裡的一條公路上,一個騎摩托的男人跟她搭話,而後將她拉去路口旁一間“破房子”實施了性侵。
第二天,冬陽在烈日下騎電動車帶妹妹重走那條公路,試圖收集證據。每隔一個路口,她都會停車和妹妹確認,從正午到天黑,也沒有找到那間破房子。由於沒有證據,妹妹又表達不清,冬陽沒有報警。
婆家知情後,還是決定讓妹妹把孩子生下:剛好他們擔心自己兒子的手臂疾病會遺傳,原本就有借精生子的打算。妹妹生育後,只勉強知道這個是自己的孩子。那段時間她再度離家,回來時,給還是嬰兒的孩子買了一根鉛筆、一塊橡皮擦。
2017年,妹妹婚後再次出走,被第二次性侵。這次出走時間是有史以來最長的,家人們找了她整半個月。4月,公公因為春月的反覆出走決定退婚,就在將春月送回孃家時買汽車票的間隙,轉頭她就不見了。媽媽打電話給冬陽,讓她回家幫忙找人。冬陽丟下畢業論文,坐火車回家。整個大學期間,有五六次家裡人找不到妹妹,都像這樣打電話叫冬陽回家。
最開始,家人們態度都很積極。父親請了假,每天一大早騎車出去找人,眼睛紅著,好像要哭一樣。奶奶說,這條命是我救回來的,不能出事,她拄著柺杖去鄰居家挨個問妹妹的動向。妹妹出走第九天,大家都開始覺得有些疲憊。那天冬陽找了一天後騎車回家,看見媽媽握著鋤頭站在水田中央微笑。媽媽眼睛不好,不能獨自出門。媽媽問冬陽找人的進展,“說話的力氣像是從她單薄的身子裡擠出來的。”說完,冬陽看見媽媽繼續翻田插秧,土翻得很淺。
在看到這個畫面前,冬陽曾在心裡責備媽媽把妹妹嫁掉。現在她感覺,在自己沒有能力肩負起妹妹的人生之前,她也沒有權力阻擋母親讓妹妹結婚。
冬陽的父母都是文盲,父親近年來流動在建築工地、傢俱廠和農田,母親一隻眼睛失明,另一隻眼睛二級視力殘疾,身體虛弱。兩人加一起幾乎沒有收入。三妹中專畢業後在廣州做服務員,四弟剛上大學,五妹讀著高中。長期養育智力殘疾的二妹,會給父母增加負擔。作為只大春月2歲的姐姐,還在讀大學的冬陽也不知道自己如何能為妹妹建立新的可能。
找人到後半程,所有人都放棄了。父親說要回縣城上班。奶奶急紅了眼,說春月會不會被拐賣到村裡給老頭當老婆了?會不會被挖了心肝?她想去算命問仙。
半個月後,只有冬陽還在堅持。她拿著妹妹的照片在每家商店、菜市場、小區打聽,騎電動車穿梭在村鎮之間,將尋人啟事貼遍每一根電線杆,最終在網上收到線索。妹妹獨自從村裡走到了縣城。
冬陽趕到的時候,看見她還穿著走時的衣服,卻沒有很髒。問話裡,春月模糊地告訴她,自己在“醫院走廊”“銀行取錢的地方”“別人家的樓上”都過了夜,但具體位置說不出來。一個月後,媽媽發現春月沒來例假,有了身孕。冬陽知道妹妹再次被侵犯了。
母親給了冬陽幾百塊錢,讓她帶著妹妹去鎮上的醫院打胎。妹妹進手術室時,兩邊的家人沒有一人在場。姐姐冬陽獨自站在走廊上,看見妹妹露出驚恐的表情。
做完手術後,妹妹遲遲不醒。驚懼的感覺傳遞向姐姐。半小時後,冬陽搖了幾下妹妹的頭,春月才睜開眼來。她們看著彼此,相對無言。
後來很多年裡,冬陽都想讓自己忘記這個場景。這種感覺像目睹戰爭在自己眼前發生,血腥、殘忍。“一件很嚴重的事情,我以前從來沒想過的事情在我眼前發生了,就在你很親近的人身上,我是那個見證者。”看見妹妹的生命反覆受到凌虐,冬陽覺得自己也在精神上被強姦了。
此時冬陽讀大四。在老家帶妹妹做完手術,回到學校後,她感覺自己仍整夜陷在恐慌與驚懼中。她的臉上冒出許多痘痘。一天晚上,床架緊鄰的那位室友說冬陽在睡夢中大喊大叫,抓她的頭髮。室友被嚇了一大跳,問她最近是不是太壓抑了。
妹妹做完流產手術那段時間,冬陽剛好來例假。生命中第一次,她看見自己流出了黑色的經血。
那次噩夢般的手術後,妹妹的公公給冬陽打來電話,責問她,為什麼急著打胎?冬陽幾乎用怒吼的語氣說,要不是你,我妹妹就不會落到現在這個地步。
回到學校已是六月,冬陽同學們的畢業論文實驗都結束了。她一個人來到實驗室,在培養基上做種子培養,觀察和記錄它的發芽。白天,實驗室的大窗戶外樹木蔥鬱,葉影搖動,夏日的陽光照射在桌面的玻璃器皿上。坐在窗前,冬陽感覺到一種和在老家狀態完全不同的、久違的寧靜。
她決定要做點什麼,再也不要讓妹妹重複這樣的生活。

逃離
畢業後,在冬陽的堅持下,被退婚回家的妹妹沒有再嫁,只是跟著媽媽幹些農活。冬陽也陸續在江西、 北京、深圳、廣州做了幾份工作,早已從家裡獨立出來自主生活。
這五年,冬陽幾乎要認為妹妹已經找到了最好的歸宿:留在老家父母身邊,不再在懵懂無知的情況下被介紹給各式男人結婚、生育,不再要用出走去表達拒絕,又在出走中被性侵。
直到2023年3月,家人打電話告訴冬陽,妹妹再次訂婚了。結婚的理由很簡單,“自古以來女的都沒有留在孃家養老的傳統,會壞了風水,影響弟弟結婚”,並且“嫁了人生了孩子,才有人給她養老”。父親的說法更為粗暴,“反正我的女兒大了就是要結婚,難道笨一點,就不用嫁?”尚未辦好離婚手續的春月,在家人安排下有了第二次婚約,婚期定在9月16日。
收到訂婚電話的那天,冬陽在午休時間到公司附近的小飯館,挨個給親戚們打影片電話。從中午到晚上十點,她從父母打到姨娘、舅媽、姑姑,甚至春月的媒婆。她想哪怕說動一個人去勸阻這場婚事。
沒有一個人站在她這邊。和父親通話時,她提起這些年妹妹和自己的遭遇,開始止不住地哭喊,哭得耳朵生疼、嗓子發啞,甚至被飯館老闆出聲喝止。她想也許是因為自己哭得太慘,最後父親才有了看似順應的表態。電話末尾,他對冬陽說,那就讓妹妹留在家裡,好吧?她感覺那語氣有些陰陽。
8月上旬,媽媽打來電話,說父親收了6萬多元定金,談好了17萬元彩禮,再次定下婚期,並且強調要低調辦事:不辦婚禮不擺酒席,一週後男方直接到家裡領人。
冬陽感覺自己的忍心已經被耗光。這次她沒有哭鬧,只是想好,如果再談不妥,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妹妹帶走。哪怕姐妹二人過得拮据,生活困難,哪怕自己可能要失去工作,要一輩子帶著妹妹生活,都沒關係。逃離是唯一的辦法。
此前,冬陽已經有好幾次產生要帶妹妹離開老家的想法。2015年,妹妹第一次結婚生下那個因性侵懷孕的孩子後,冬陽試圖帶她接觸村莊之外的世界。每逢學校寒暑假,她都帶妹妹離開家,去自己的大學玩。她也在網上查詢本地的特殊教育學校,發現對方只招收18歲以下的學生。冬陽曾跑到省會城市南昌打探,問學校是否招收妹妹這種情況的人,對方表示拒絕。
那段時間,冬陽只找到一個傳統文化的靈脩班,說妹妹可以參加。老師說,外面的世界太浮躁,工作生活情感遇到的各種問題,都需要修行。冬陽帶妹妹呆了一兩天,發現妹妹很牴觸就離開了。那時,還是大學生的冬陽覺得自己能力有限。
大學畢業後,冬陽找了一份北京公益機構的工作,給特殊兒童做就業輔導員。她想深入瞭解心智障礙孩子的世界,他們都在做什麼?他們的人生還有什麼樣的可能?在機構中,她看見很多和妹妹情況相似的孩子。有些女學員會在公眾場合脫衣服,老師解釋說這可能在表達對機構的抗拒。冬陽在這裡學習國際殘障法,學習如何與心智障礙群體交流,輔導孩子們學習就業技能。她也和同事們去企業裡宣講,科普殘保金和殘障人群工作的優勢,推薦自己的學員去就業。大學畢業後的這五年,冬陽靠自己的工資幫襯著一雙父母和四個姐妹弟弟,弟弟6000元每年的學費,每個月600到800元的生活費,都是冬陽支付。
這些年的她,已經不再是大學時期那個只能拍照片的學生。她成了家人中最瞭解妹妹處境的人,也逐漸探索出關於妹妹人生的新道路。她不再只有同情,還有了知識、能力、經濟儲蓄與社會經驗。她決定不再做妹妹處境的覺察者和記錄者,而是要行動,將妹妹從舊世界的泥淖中拔出。
9月9日,冬陽請了一週的假,坐火車回到老家。
到家第二天晚上九點,她就和父親大吵一架。“反正我的女兒大了就要嫁出去,誰都阻撓不了。”父親瞪著她。冬陽說他的行為就是在“賣女兒”。
父親憤怒到了極致,拿著玻璃杯衝到冬陽面前,好像眼珠子都要蹦出來。母親一把推開他,攔在中間。
又一次,父親將矛頭指向冬陽,“老大比老二還笨。讀那麼多書,沒一點用!”冬陽抄起一個裝瓜子的塑膠果盤往門外摔去,碎片散落一地。
冬陽來到所謂妹妹未婚夫的家裡。這是一個35歲的男人,在工地做日結工,有一個患有癲癇的前妻。聊天間,男人提起前妻有一個他接受不了的問題,“同房的時候(癲癇)更嚴重,會突然口吐白沫,翻著白眼。”冬陽趕緊說,妹妹也有這個問題。對方這才態度鬆動。
在場的記者們用錄音記錄下這一週的爭吵,羅冬陽幾次聲嘶力竭。父親的聲量比她更大。男人來索要6萬多定金的當天,父親衝著冬陽大吼,讓她寫一張保證書:如果弟弟妹妹在28歲之前沒結婚,冬陽要賠他60萬到100萬元,讓她“死也要死在外面”。冬陽向記者表態,“我要跟他抗爭到底。”她覺得如果不帶妹妹走,等自己離開,父親仍可能偷偷安排他們成婚。
2023年9月15日晚,冬陽問妹妹願不願意跟自己離開。春月毫不猶豫地點了頭。第二天一早,春月跑來冬陽的房間,說東西收拾好了。向村委會遞交完妹妹的低保材料後,下午,趁父親還沒下班回家,她們在五點多出發,穿過院子、菜園,跑上斜坡,坐上提前叫好的車。
在高鐵上的三個小時車程裡,冬陽看見春月緊盯著車廂的顯示屏,不停問她還有多久到站。確認已經遠離家鄉後,冬陽看見妹妹低著頭,偷笑了無數次。
到廣州開啟新生活的日期是9月16日,原定春月要第二次出嫁的日子。

圖 | 逃離老家後,姐姐帶春月去海洋館看海豚
到家的第三個晚上,母親就打來一個電話,讓冬陽國慶期間把妹妹帶回去。春月在旁邊聽著。冬陽看見妹妹縮成一團,躲在角落呢喃著說,不要回去。
隔天冬陽帶她出門,提起“回家”二字,妹妹再次變得警覺,回哪個家?我不要回老家。冬陽說,回我們住的地方。春月神色這才緩和下來。她說,你的房子好漂亮,沒有蜘蛛網。
那段時間,冬陽發現妹妹反覆透過話語將自己和過去的世界分割。“我跟老爸沒關係了,你呢?”“這個房子才是我家。”“我沒有老家,老爸才有老家。”

自由的重負
剛來到培訓基地的那幾天早上,冬陽都是被急著要出門的妹妹叫醒的,“太陽出來了,你怎麼還不帶我去?”
在這裡,冬陽聽到了有史以來對妹妹最多的肯定。創辦人歐陽秋月跟她說,自己從來沒有見過像春月這麼乖的孩子。冬陽聽說妹妹到基地後一直在自己找活幹,掃地、拖地、擦拭桌椅、收拾碗筷,給露臺的花草澆水,給貓添糧。來基地的第二天,春月甚至在沒有人安排的情況下自己將露臺大掃除了一遍,洗了一臺電風扇,用秋月給的鐵絲刷洗每個縫隙。
冬陽覺得妹妹甚至變得比自己話還多,還有活力。老師也說,她其實並不像父母想的那麼笨,“比任何人都聰明。”

圖 | 夕陽時分,妹妹給基地露臺上的植物澆水
在基地,妹妹的狀態一天天好起來,冬陽卻沒有。有半個月,她感覺上班都沒力氣說話,有一天連打字也沒力氣了。老家激烈的戰爭,父親對她的謾罵,如蜘蛛網般圍困住她的精神。事情向媒體曝光後,還有人對她發起責問。“有人責問我為何沒報警,為何沒有為她伸張正義,我也想知道,我也想知道,誰來幫幫我……”她在日記中寫。過去一年,冬陽努力推動性侵案的調查和妹妹離婚的進度,6月,警方通知她,性侵案中的一位嫌疑人已經被刑事拘留。
更現實的苦惱是生活的拮据。妹妹來後,為了控制成本,冬陽儘量自己做飯。一天中午,她下班後急忙跑回家給自己炒菜。給山藥削皮時,她知道要避免觸碰內瓤的黏液否則皮膚會發癢,但趕時間沒太注意。那天中午,她的手開始劇烈地發癢。
冬陽突然覺得好難過。她想到自己小時候住在村裡,也因為省錢要自己做飯,中午從學校回家在地裡摘菜後急急忙忙地炒,“現在長大了,怎麼還是這個樣子?”她忍不住想,難道自己一輩子,就要這樣生活下去?
30歲的她也幾乎沒有朋友。時常聊天的幾個好友都在外地,在廣州的社交生活則都圍繞妹妹展開。這一年的週末,除了陪伴妹妹,她大多時間都在參加殘障群體相關的培訓和活動,跟媽媽和老師們打交道。2022年,在妹妹來廣州前,冬陽曾買過一個單身青年週末出行的社群會員,想拓展一下社交圈,後來再也沒有去過,沒時間,也漸漸沒了想法。她不再對屬於自己的愛情抱有期望,秉持“不拒絕、不主動”的態度,有時覺得和妹妹在一起兩個人生活也挺好。面試找工作時,她會告訴hr,自己是“單身主義者”。
她發現自己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條圍著妹妹打轉的生活道路,但這並非她所想。最近一次蒸早餐,春月不小心摁到插座按鈕,蒸籠沒有通電。冬陽過去時,發現妹妹沉默地坐著。她問妹妹,怎麼還不吃早餐?對面仍然不語。她一摸蒸籠,是冷的,開始有點生氣。“你發現不通電,為什麼不跟我說?你跟我說,我就會過來看看情況。”妹妹始終拉著臉,悶不吭聲坐著。她感覺自己像在對著牆壁說話。
有時冬陽覺得,寧肯春月跟自己吵一架都好。一次情緒崩潰,她沒忍住大聲吼了妹妹,隨後馬上開始反思,告訴自己下次不要這樣。她甚至開始理解父母為什麼曾那樣對待妹妹。有段時間,她發現自己好像和父母也沒什麼區別,也是那樣不理智。
她意識到自己沒法像基地中的老師那樣,終日和顏悅色對著妹妹。帶妹妹逃離老家只是因為“看不下去、迫不得已”,她不想讓自己往後的生活都以妹妹為中心,也想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命的意義。
她想做點什麼,不要讓自己重複這樣的生活。和三妹一起合租後,三妹和春月住在主臥,冬陽自己住在6平米的次臥。她有了屬於自己的房間,買了紗簾,將自己參加活動時畫的版畫裝裱起來掛在牆上,嘗試重新建立和妹妹的關係,相互支援,也相互獨立。

圖 | 冬陽(左)和春月(右)在活動上畫的版畫
她也重新撿起7年前在妹妹婚禮上拍攝的那段影片,在朋友的幫助下嘗試剪輯、寫文案,提交了幾個電影節基金的申請。此外,她還想寫一些和妹妹無關的故事,備忘錄裡有一些電影劇本的場景和企劃,關於自己的童年回憶。
過去的經歷仍然鬱結在她心中。她暫時沒有經濟能力尋求心理諮詢的支援。廣州殘障家長組織曾給她介紹資源,提供了三次免費的心理資助。冬陽一說到自己的情況就哭,需要調整情緒,等一會兒才能繼續說。說不出來的時候,她讓諮詢師去看關於她們姐妹的報道。
在近年講述關於妹妹故事的時候,冬陽想起姐妹倆命運最重疊的地方,是老家的一條河流。在去小學的路上,她需要牽著妹妹的手,用十幾分鐘的時間,赤腳趟水渡河。
冬天河水冰冷,脫下鞋踩進水裡時,冬陽感覺河水冰得像刀在割腳,上岸時已凍得沒有知覺。夏天漲水,河流湍急。一天過河回家時,水漲到了冬陽的腰上。她一手拎著涼鞋,一手牽著妹妹,不小心被水流衝得跌倒下去。渾濁的河水漫上身體,恐怖襲來,她拼了命站起身來,確認自己和妹妹的安全。
一年四季,她們牽手一起過河,赤腳踩著河床的沙子,放學後,又翻過一座山回家。秋天時紅葉遍山,冬陽記得自己曾和妹妹並排躺在草地看天空,也在退潮後的淺灘上用木棍畫畫。那是她至今為數不多的快樂記憶。
有時她覺得自己的命運曾距離妹妹很近。鄉村醫療資源匱乏,小學二年級時,冬陽有一天發高燒,早上睜開眼就看見天花板在旋轉。奶奶叫醒六七歲的妹妹,讓她趕緊陪姐姐去找隔壁村的鄉村醫生。冬陽走在路上快要跌倒,一路走走停停很久才到。
後來,她在村裡每次遇到一位母親,對方都要跟她講:“要是我女兒沒有燒成這樣,她也跟你一樣考上大學,出來工作了。”她的女兒只比冬陽小一歲,小時候留守在家發高燒沒來得及趕到診所,後來變成聾啞加智力殘障人群。
冬陽從那時候開始感知到,自己和妹妹的區別並沒有那麼大,在意識與物質同樣貧瘠的鄉村,她行差踏錯一步,興許也要留在老家,無法過上和妹妹不同的生活。
和妹妹命運分岔的時刻,是三年級開學的那天。那天姐妹倆照常牽手過了河、翻了山,一起去村小上學。冬陽坐在靠窗的位置,窗戶靠著走廊,直對著校門口。她聽見外面下了大雨,轉頭看窗外,發現妹妹春月捧著盒飯,坐在校門口的前廊,頭髮淋溼了。
妹妹因為讀到二年級還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在開學當天被勸退,不能再進教室。上課鈴打響的時候,她曾看見那個教數學的校長從窗外路過。一瞬間,她想喊住他讓妹妹繼續上學。
她猶豫許久,沒有張口。妹妹從此再沒踏進過教室。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人物資訊有模糊。
– END-
關鍵詞
孩子
母親
父母
媽媽
心智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