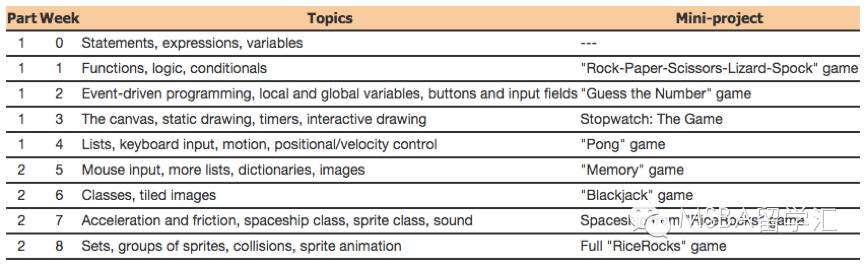鄭振鐸《最後一課》原文欣賞
口頭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見得便是殺身成仁的志士。無數的勇士,前仆後繼地倒下去,默默無言。
好幾個漢奸,都曾經做過抗日會的主席;首先變節的一個國文教師,卻是好使酒罵座,慣出什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類題目的東西;說是要在槍林彈雨裡上課,絕對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一個校長,卻是第一個屈膝於敵偽的教育界之蟊賊。
然而默默無言的人們,卻堅定地做著最後的打算,拋下了一切,千山萬水地,千辛萬苦地開始長征,絕不做什麼為國家儲存財產、文獻一類的藉口的話。
上海國軍撤退後,頭一批出來做漢奸的都是些無賴之徒,或愍不畏死的東西。其後,卻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維持地方的人物出來了。再其後,卻有以“救民”為幌子,而喊著同文同種的合作者出來。到了珍珠港的襲擊以後,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們相信著日本政策的改變,在做著“東亞人的東亞”的白日夢,吃盡了“獨苦”,反以為“同甘”,被人家拖著“共死”,卻糊塗到要掙扎著“同生”。其實,這類的東西也不太多。自命為聰明的人物,是一貫地料用時機,做著升官發財的計劃。其或早或遲的蛻變,乃是作惡的勇氣夠不夠,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問題。
默默無言的堅定的人們,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敵救國的問題,壓根兒不曾夢想到“環境”的如何變更,或敵人對華政策的如何變動、改革。
所以他們也有一貫的計劃,在最艱苦的情形之下奮鬥著,決對地不做“苟全”之夢;該犧牲的時機一到,便毫不躊躇地踏上應走的大道,義無反顧。
十二月八號是一塊試金石。
這一天的清晨,天色還不曾大亮,我在睡夢裡被電話的鈴聲驚醒。
“聽到了炮聲和機關槍聲沒有?”C在電話裡說。
“沒有聽見。發生了什麼事?”
“聽說日本人佔領租界,把英國兵繳了械,黃浦江上的一隻英國炮艦被轟沉,一隻美國炮艦投降了。”
接連的又來了幾個電話,有的是報館裡的朋友打來的。事實漸漸地明白。
英國軍艦被轟沉,官兵們鳧水上岸,卻遇到了岸上的機關槍的掃射,紛紛地死在水裡。
日本兵依照著預定的計劃,開始從虹口或郊外開進租界。
被認為孤島的最後一塊彈丸地,終於也淪陷於敵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腦脫路的暨大。
校長和許多重要的負責者們都已經到了。立刻舉行了一次會議,簡短而悲壯地,立刻議決了:
“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刻停課,將這大學關閉結束。”
太陽光很紅亮地曬著,街上依然地熙來攘往,沒有一點兒異樣。
我們依舊地搖鈴上課。
我授課的地方,在樓下臨街的一個課室,站在講臺上可以望得見街。
學生們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說道,“你們都已經知道了吧?”學生們都點點頭。“我們已經議決,一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立刻便停課,並且立即地將學校關閉結束。”
學生們的臉上都顯現著堅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沒有一句話。
“但是我這一門功課還要照常地講下去,一分一秒鐘也不停頓,直到看見了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為止。”
我不荒廢一秒鐘的工夫,開始照常地講下去。學生們照常地筆記著,默默無聲的。
這一課似乎講得格外地親切,格外地清朗,語音裡自己覺得有點兒異樣;似帶著堅毅的決心,最後的沉著;像殉難者的最後的晚餐,像衝鋒前計程車兵們的上了刺刀,“引滿待發”。
然而鎮定、安詳、沒有一絲的緊張的神色。該來的事變,一定會來的。一切都已準備好。
誰都明白這“最後一課”的意義。我願意講得愈多愈好;學生們願意筆記記得愈多愈好。
講下去,講下去,講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應該講授的東西,統統在這一課裡講完了它;學生們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記著。心無旁用,筆不停揮。
別的十幾個課室裡也都是這樣的情形。
對於要“辭別”的,要“離開”的東西,覺得格外的戀戀。黑板顯得格外地光亮,粉筆是分外地白而柔軟適用,小小的課桌,覺得十分地可愛;學生們靠在課椅的扶手上,撫摩著,也覺得十分的難分難捨。那晨夕與共的椅子,曾經在扶手上面用鋼筆、鉛筆或鉛筆刀,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塗寫著、刻劃著許多字或句的,如何捨得一旦離別了呢!
街上依然地平滑光鮮,小販們不時地走過,太陽光很有精神地曬著。
我的表在衣袋裡嘀嘀地嗒嗒地走著,那聲音彷彿聽得見。
沒有傷感,沒有悲哀,只有堅定的決心,沉毅異常地在等待著;等待著最後一刻的到來。
遠遠地有沉重的車輪碾地的聲音可聽到。
幾分鐘後,有幾輛滿載著日本兵的軍用車,經過校門口,由東向西,徐徐地走過,當頭一面旭日旗,血紅的一個圓圈,在迎風飄蕩著。
時間是上午十時三十分。
我一眼看見了這些車子走過去,立刻挺直了身體,做著立正的姿勢,沉毅地合上了書本,以堅決的口氣宣佈道:
“現在下課!”
學生們一致地立了起來,默默地不說一句話;有幾個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著。
沒有一個學生有什麼要問的,沒有遲疑,沒有躊躇,沒有彷徨,沒有顧慮。各個人都已決定了應該怎麼辦,應該向哪一個方面走去。
赤熱的心,像鋼鐵鑄成似的堅固,像走著鵝步的儀仗隊似的一致。
從來沒有那麼無紛紜地一致地堅決過,從校長到工役。
這樣地,光榮的國立暨南大學在上海暫時結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著遷校的工作。
最後一課 (法)都德
那天早晨上學,我去得很晚,心裡很怕韓麥爾先生罵我,況且他說過要問我們分詞,可是我連一個字也說不上來。我想就別上學了,到野外去玩玩吧。
天氣那麼暖和,那麼晴朗!
畫眉在樹林邊婉轉地唱歌;鋸木廠後邊草地上,普魯士兵正在操練。這些景象,比分詞用法有趣多了;可是我還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學校跑去。
我走過鎮公所的時候,看見許多人站在佈告牌前邊。最近兩年來,我們的一切壞訊息都是從那裡傳出來的:敗仗啦,徵發啦,司令部的各種命令啦──我也不停步,只在心裡思量:“又出了什麼事啦?”
鐵匠華希特帶著他的徒弟也擠在那裡看佈告,他看見我在廣場上跑過,就向我喊:“用不著那麼快呀,孩子,你反正是來得及趕到學校的!”
我想他在拿我開玩笑,就上氣不接下氣地趕到韓麥爾先生的小院子裡。
平常日子,學校開始上課的時候,總有一陣喧鬧,就是在街上也能聽到。開課桌啦,關課桌啦,大家怕吵捂著耳朵大聲背書啦……還有老師拿著大鐵戒尺在桌子上緊敲著,“靜一點兒,靜一點兒……”
我本來打算趁那一陣喧鬧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安安靜靜的,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樣。我從開著的窗子望進去,看見同學們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韓麥爾先生呢,踱來踱去,胳膊底下夾著那怕人的鐵戒尺。我只好推開門,當著大家的面走進靜悄悄的教室。你們可以想像,我那時臉多麼紅,心多麼慌!
可是一點兒也沒有什麼。韓麥爾先生見了我,很溫和地說:“快坐好,小弗郎士,我們就要開始上課,不等你了。”
我一縱身跨過板凳就坐下。我的心稍微平靜了一點兒,我才注意到,我們的老師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綠色禮服,打著皺邊的領結,戴著那頂繡邊的小黑絲帽。這套衣帽,他只在督學來視察或者發獎的日子才穿戴。而且整個教室有一種不平常的嚴肅的氣氛。最使我吃驚的是,後邊幾排一向空著的板凳上坐著好些鎮上的人,他們也跟我們一樣肅靜。其中有郝叟老頭兒,戴著他那頂三角帽,有從前的鎮長,從前的郵遞員,還有些旁的人。個個看來都很憂愁。郝叟還帶著一本書邊破了的初級讀本,他把書翻開,攤在膝頭上,書上橫放著他那副大眼鏡。
我看見這些情形,正在詫異,韓麥爾先生已經坐上椅子,像剛才對我說話那樣,又柔和又嚴肅地對我們說:“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最後一次給你們上課了。柏林已經來了命令,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學校只許教德語了。新老師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後一堂法語課,我希望你們多多用心學習。”
我聽了這幾句話,心裡萬分難過。啊,那些壞傢伙,他們貼在鎮公所佈告牌上的,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的最後一堂法語課!
我幾乎還不會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學法語了!難道這樣就算了嗎?我從前沒好好學習,曠了課去找鳥窩,到薩爾河上去溜冰……想起這些,我多麼懊悔!我這些課本,語法啦,歷史啦,剛才我還覺得那麼討厭,帶著又那麼沉重,現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捨不得跟它們分手了。還有韓麥爾先生也一樣。他就要離開了,我再也不能看見他了!想起這些,我忘了他給我的懲罰,忘了我挨的戒尺。
可憐的人!
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禮服,原來是為了紀念這最後一課!現在我明白了,鎮上那些老年人為什麼來坐在教室裡。這好像告訴我,他們也懊悔當初沒常到學校裡來。他們像是用這種方式來感謝我們老師四十年來忠誠的服務,來表示對就要失去的國土的敬意。
我正想著這些的時候,忽然聽見老師叫我的名字。輪到我背書了。天啊,如果我能把那條出名難學的分詞用法從頭到尾說出來,聲音響亮,口齒清楚,又沒有一點兒錯誤,那麼任何代價我都願意拿出來的。可能開頭幾個字我就弄糊塗了,我只好站在那裡搖搖晃晃,心裡挺難受,頭也不敢抬起來。我聽見韓麥爾先生對我說:
“我也不責備你,小弗郎士,你自己一定夠難受的了。這就是了。大家天天都這麼想:‘算了吧,時間有的是,明天再學也不遲。’現在看看我們的結果吧。唉,總要把學習拖到明天,這正是阿爾薩斯人最大的不幸。現在那些傢伙就有理由對我們說了:‘怎麼?你們還自己說是法國人呢,你們連自己的語言都不會說,不會寫!……’不過,可憐的小弗郎士,也並不是你一個人的過錯,我們大家都有許多地方應該責備自己呢。
“你們的爹媽對你們的學習不夠關心。他們為了多賺一點兒錢,寧可叫你們丟下書本到地裡,到紗廠裡去幹活兒。我呢,我難道就沒有應該責備自己的地方嗎?我不是常常讓你們丟下功課替我澆花嗎?我去釣魚的時候,不是乾脆就放你們一天假嗎?……”
接著,韓麥爾先生從這一件事談到那一件事,談到法國語言上來了。他說,法國語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最明白,最精確;又說,我們必須把它記在心裡,永遠別忘了它,亡了國當了奴隸的人民,只要牢牢記住他們的語言,就好像拿著一把開啟監獄大門的鑰匙。說到這裡,他就翻開書講語法。真奇怪,今天聽講,我全都懂。他講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我覺得我從來沒有這樣細心聽講過,他也從來沒有這樣耐心講解過。這可憐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東西在他離開之前全教給我們,一下子塞進我們的腦子裡去。
語法課完了,我們又上習字課。那一天,韓麥爾先生髮給我們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麗的圓體字:“法蘭西”“阿爾薩斯”“法蘭西”“阿爾薩斯”。這些字帖掛在我們課桌的鐵桿上,就好像許多面小國旗在教室裡飄揚。個個都那麼專心,教室裡那麼安靜!只聽見鋼筆在紙上沙沙地響。有時候一些金甲蟲飛進來,但是誰都不注意,連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他們正在專心畫“槓子”,好像那也算是法國字。屋頂上鴿子咕咕咕咕地低聲叫著,我心裡想:“他們該不會強迫這些鴿子也用德國話唱歌吧!”
我每次抬起頭來,總看見韓麥爾先生坐在椅子裡,一動也不動,瞪著眼看周圍的東西,好像要把這小教室裡的東西都裝在眼睛裡帶走似的。只要想想:四十年來,他一直在這裡,窗外是他的小院子,面前是他的學生;用了多年的課桌和椅子,擦光了,磨損了;院子裡的胡桃樹長高了;他親手栽的紫藤,如今也繞著視窗一直爬到屋頂了。可憐的人啊,現在要他跟這一切分手,叫他怎麼不傷心呢?何況又聽見他的妹妹在樓上走來走去收拾行李!──他們明天就要永遠離開這個地方了。
可是他有足夠的勇氣把今天的功課堅持到底。習字課完了,他又教了一堂歷史。接著又教初級班拼他們的ba,be,bi,bo,bu。在教室後排座位上,郝叟老頭兒已經戴上眼鏡,兩手捧著他那本初級讀本,跟他們一起拼這些字母。他感情激動,連聲音都發抖了。聽到他古怪的聲音,我們又想笑,又難過。啊!這最後一課,我真永遠忘不了!
忽然教堂的鐘敲了十二下。祈禱的鐘聲也響了。窗外又傳來普魯士兵的號聲──他們已經收操了。韓麥爾先生站起來,臉色慘白,我覺得他從來沒有這麼高大。
“我的朋友們啊,”他說,“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說不下去了。
他轉身朝著黑板,拿起一支粉筆,使出全身的力量,寫了幾個大字:
“法蘭西萬歲!”
然後他呆在那兒,頭靠著牆壁,話也不說,只向我們做了一個手勢:“放學了,──你們走吧。”
鄭振鐸(1898—1958),原文化部副部長。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訓詁家。
阿爾豐斯·都德(1840年—1897年),被譽為“法國的狄更斯”。一生共寫了13部長篇小說、1部劇本和4部短篇小說集。其中的《最後一課》和《柏林之圍》是世界公認的短篇小說傑作。
平臺原創文章均為作者授權微信首發,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與本平臺無關。



關鍵詞
法國
語言
韓麥爾先生
老師
教室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