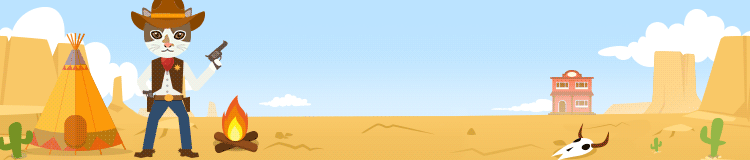繼湘菜成為全國爆款菜系後,今年打工人又愛上了江西小炒。
江西小炒不是一道菜名,也不是一個店名,而是江西特色菜的一種統稱。它通常是街邊小店或者大排檔,名為江西特色小炒、農家小炒、江西土菜館等等。儘管沒人能給它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不影響打工人對江西小炒的直觀感受——新鮮現炒、快速出餐、鍋氣滿滿,還特別下飯,當然最重要的是“辣”。
近二十年裡,辣菜似乎一直霸佔打工人的日常菜譜。無論是川菜的酸菜魚,還是湘菜的辣椒炒肉,又或者是如今的江西小炒等等。
窄門餐眼今年1月資料顯示,川菜與湘菜過去一年新開門店數分別為33964家、22910家,增速遠超魯菜、徽菜等其他菜系。一項來自抖音的資料也顯示,截止到2025年4月,圍繞“無辣不歡”的話題播放量,已經超過590億次。
中國打工人,為什麼越來越愛吃辣?

被辣菜硬控的打工人
在北京望京上班的陳晴,連早飯都離不開辣。這個春天她迷上了好適口的辣包子,“可好吃了,我最近天天吃。”午飯更不用提,翻看她最近三天的外賣訂單記錄,分別是爆炒牛肉麵、戰鬥雞拌麵、辣子雞,“都是辣的”。
陳晴是湖南人,最近剛做完近視眼手術,醫生要她忌口,但辣椒不在她忌口的範圍內。以前上中學得咽喉炎、流鼻血時,醫生也告訴她別吃辣,但她該吃還吃。
“我剛結婚那會兒,我爸去鄉下給我種了幾分地的辣椒,我跟他說我備孕不能吃辣椒,但我爸說不要聽他們的,什麼備孕不能吃辣椒,那湖南人的媳婦豈不是都不生孩子了?” 陳晴笑著說。
湖南嶽陽本地人曾豔,也是重度辣人。每週五下班,她都會和同事找家炸串店吃辣:“只要是下館子,就一定是重口,我們不會浪費錢點個清淡的菜吃,哪怕辣得拉肚子疼。”
但即使愛吃辣如她,在一次去同學家吃飯後,也被嚇到了:“她家每一道菜,都放大把大把的乾紅尖辣椒。辣到你要用開水去涮它,涮完之後還是很辣。連湯裡面都有辣椒。”
在深圳南山科興園寫字樓下,主打小炒黃牛肉的湘菜連鎖品牌辣可可,每到中午,都是人群最密集的時候。店內幾乎都設定成了2人桌和4人桌,很適合幾個同事一起用餐,“主要場景就是打工人一起幹飯,吃完就走,咵咵翻檯那種”,談起午飯情景,辣可可品牌負責人阿鹿這樣描述。
高翻檯率帶來了營收的增加。阿鹿坦言,今年總體營收一直很穩定,而且也沒有明顯的淡旺季之分。

● 辣可可深圳南山科興園寫字樓店日常店內等位
湘菜大廚出身的熊建,同樣感受了到大家對“辣”的熱情:“從這幾年湘菜的火爆度來說,門店數量在所有菜系裡面應該能排到第一了。”
開啟社交媒體,有標稱重辣愛好者的博主,專門發各種挑戰辣菜的影片,從變態辣牛蛙到龍息辣椒,在置頂的影片《挑戰50顆死神辣椒》下,有2.3萬人點贊。
而像《湖南人在北京吃些啥》《在通州吃到了好吃又超便宜的江西小炒!》等有關“城市吃辣攻略”的帖子更是鋪滿螢幕,點贊動輒過千。

● 圖片來自小紅書@神氣神奇七
這些網友基本都來自江西、四川、湖南等吃辣大省,他們自己不僅愛吃辣,還對自己家鄉的辣味有種護犢子的心理,以至於在業界形成了一個全國吃辣鄙視鏈:
“貴州人說自己喜歡吃辣,四川人第一個不服;四川人說自己無辣不歡,湖南人就要跳腳;湖南人說自己是吃辣界No.1;江西人就笑笑不說話。”
岳陽本地的曾豔,就認為湘菜是接受度最高的。她觀察到,這兩年經常有外地人專門到岳陽吃湘菜:“有武漢人過來吃,他們原本不怎麼能吃辣,但對這邊的菜評價還蠻高的。”
此外,她還經常能在B站、抖音上看到很多外國人吃湘菜的影片:“他們從一開始拒絕湘菜,慢慢接受湘菜,最後愛上湘菜。”


辣菜何以走紅?
正如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同樣是愛吃辣的人,喜歡辣的口味兒也不一樣。而在多數人的認知中,貴州人喜愛酸辣、四川以麻辣著稱、湖南以香辣聞名,而江西則是純粹的辣。但對打工人來說,無論哪種口味兒,都有一個共同點——下飯。

作為商家的阿鹿就發現,因為太下飯,辣菜甚至帶動了門店的米飯銷量,有客人吃完後,專門想去店裡購買大米,“當然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的米飯品質本身也很好”,她補充道。
打工人陳晴就說,自己長了一個吃米飯的胃:“無論是湘菜還是江西小炒,這類帶辣味的菜品能快速激發食慾,比起清淡的菜更下飯。可能我平時吃一碗飯就夠,但碰上香辣的湘菜連吃三碗都不在話下。”
但在陳晴看來,吃辣不只是為了下飯,還能獲得情緒價值。
她目前是一家新媒體公司的商務,在客戶的無理要求和公司業務人員的抱怨之間周旋,是她的日常操作,壓力也時常湧上心頭。去年她有個客戶,在臨近專案上線前瘋狂提修改意見,她一邊強忍憤怒,一邊安撫業務的同事,連續的熬夜讓她瀕臨崩潰,而正是一份辣椒炒肉,讓她在吃得滿頭大汗後恢復了穩定的情緒,“吃辣讓我感到特別解壓,那種暴汗的痛快感就像情緒宣洩一樣過癮。”

在北京打工的貴州人謝帆,也有類似的情緒體驗。
2016年高中畢業後,謝帆就離開貴州,先後去到南京和北京讀書、工作。現在的他,已經並不像以前那麼愛吃辣,加上他最近在健身,也減少了辣椒的攝入。但每當同事說要一起吃辣,他又總是忍不住參與。在他看來,吃辣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讓人顯得親近:“我和同事一起去吃辣,我吃得滿頭大汗,也覺得無所謂。而如果是情侶約會,雙方肯定還是想吃得體面一點。”
不過,對於湘菜、江西小炒等辣菜的流行,餐飲行業資深媒體人道哥,有著“吃”以外的觀察。
在合肥,他看到一家做得很成功的江西小炒店,而成功的原因就藏在了後廚,“四個師傅同時現炒,食材用標號的菜筐分類管理擺在身後,師傅不用走動轉身就能取料。反倒其他一些餐飲,過於注重產品品質和儀式感,而忽視了效率。”
效率同樣是熊建最在意的地方。去年年底,他在北京建國門的一個寫字樓二層,開了家名為瓏湘薈的湘菜館。為了保證出餐效率,他嚴格控制著廚師和桌臺數量的比例:“按照科學的廚師配比,1個炒菜廚師可以兼顧3到4桌,如果1個廚師管8桌,那就會跟不上。”
“對上班族來說,午休時間通常只有兩小時,這就要求餐廳必須做到上菜速度快、菜品口味好、價格還實惠。如果一家寫字樓餐館價格又貴上菜又慢,那就很難生存下去了”,他強調。

事實上,店面緊挨寫字樓,是絕大多數湘菜、江西小炒選址的共識。除了打工族午飯時間有限,也跟辣菜平價的價格定位有關。以江西小炒為例,人均四五十,兩個人吃飯,一份辣椒炒肉,一份蘿蔔乾炒臘肉,兩個肉菜不到100元,就能吃得很好。
“或許大家現在都沒錢了”,陳晴說,疫情之前她隨便一頓飯就七八十,一天光吃飯就要花費一百多。但這幾年她的收入減少,消費也降級了。
對此,曾豔也有同感。在岳陽一家連鎖超市上班的她,觀察到超市這兩年營收明顯下降,顧客消費也變得剋制,唯獨腐乳、豆瓣醬、剁辣椒等調味品一直賣得很好。
但她從不認為湖南人愛吃辣跟消費降級或者工作壓力有關,“湖南人就是愛吃,無辣不歡。這裡跟北上廣不一樣,那邊的人有房貸車貸,壓力比較大。而岳陽屬於宜居城市,到點就下班,沒什麼壓力,開心了就去吃。湖南人工資低但消費很高,大家好像都在及時行樂,200塊錢吃個飯都覺得很便宜了。”

曾豔的話並非炫耀。很多從吃辣大省走出去的打工人,都對家鄉的辣味有種執念。
在北京工作將近五年的謝帆,一直覺得北京的貴州菜和老家不一樣:“你很難說它是某一個因素造成的,可能製作流程一樣,但換了一種辣椒,味道就變了。”
在他的老家貴陽,辣椒品種很多,幹辣椒、煳辣椒、餈粑辣椒、糟辣椒,人們做菜有太多的選擇,“可能只有從小吃到大的人,才知道什麼辣椒是真香,什麼辣味是真正屬於辣椒的辣味”,謝帆感慨。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感受。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流動人口約為3.76億人,比2010年增長了69.73%。人口流出排名前8的省份,有6個都是吃辣大省,分別是四川、貴州、廣西、湖南、江西、湖北。
或許,對這些在陌生的城市中缺乏關係網的打工人來說,辣味不僅是一種味道,更是一種身份和地域認同。正如江西小炒會在浙江爆火,大概正因為有幾百萬江西人在浙江謀生,義烏的“江西小炒一條街”,既是這些人的生意,也是他們對家鄉的情懷。

一場關於中餐的
效率革命
事實上,自從400年前辣椒被引進明朝,中國人吃辣歷史已久,到今天,國人已經把辣椒吃出了一個巨大的產業。
早在2021年,中國吃辣人口就已經超過了5億。而全球著名增長諮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的研究資料進一步顯示,中國45歲以下的人群,喜歡吃辣的比例超過60%;其中,90後群體中吃辣人群佔比最高,約49%的人喜歡吃辣。
而巨大的市場需求,催生了各類辣菜的輪番爆火。2016年,麻辣小龍蝦最火的時候,門店總數是肯德基中國門店的三倍;到了2022年底,川菜又以超過32萬家的數量,位列全國各菜系門店數量第一,太二酸菜魚、眉州東坡還把店開到了海外;緊接著,湘菜品牌費大廚辣椒炒肉成了現象級的爆品,如今江西小炒的門店也超過了2萬家。

沒有無緣無故的流行。在道哥看來,湘菜和江西小炒既有鍋氣、又能快速出餐,看似如此自然的成功模式,並非一蹴而就:“它更像是中餐自2012年開始變革至今的一個結果。”
說起2012年,多數中餐從業者或許都印象深刻。那一年,比海底撈客單價還高出40元的巴奴毛肚火鍋,率先開啟了一系列減選單操作,隨後在全行業帶出了一波精簡選單的潮流。
巴奴的招牌產品是毛肚,為了進一步強化毛肚火鍋的定位,創始人杜中兵把選單裡的100多道菜,縮減到30多道,同時將毛肚重點展示,放在選單最顯眼的位置。這一策略,讓毛肚的點選率短期內飆升至139%,也讓提升效率成了所有中餐的共識——與其賣十個產品都很平庸,不如聚焦三四個產品。

“這帶來的就是效率,點餐的時候你不用再問你們家的爆品是什麼,推薦什麼菜”,道哥對此做過一個有趣的比喻:“之前所有菜品都是平頭老百姓,就像人都脫光了進澡堂,你看不出來誰傻。但改過之後相當於穿了衣服,你一看衣服就知道誰是皇帝,誰是小兵。”
事實上,如今的費大廚辣椒炒肉,正是這一變革的產物。費大廚的前身叫同新湖南菜,但很長時間裡由於菜品太多一直沒什麼特色,直到更名為費大廚,聚焦“辣椒炒肉”這一道湘菜,這才逐漸火了起來。
“一切向效率看齊”的理念,持續了10年左右的時間,直到在2023年左右,出現了新的問題——效率太快了,以至於出現了預製菜。
“那怎麼辦?慢點唄。搞鍋氣,所以現炒開始流行”,道哥一直認為,江西小炒的爆火應該感謝費大廚:
“今天做江西小炒的餐飲人,我很少看見新手,都是懂經營和管理的行業老手。他們既學會了費大廚那一套搞效率、推爆品的流程,又有意識做品牌、做私域、做短影片,這就讓江西小炒傳播開來,大家一看越做越好,就激發了更多人的跟進。”
“品類裡面有品牌,品牌提高了品類的能見度”,他把所有辣菜爆火的商業邏輯,都歸於這樣一句話。

辣菜這陣風
還能吹多久
當然,成熟的經營模式,並不意味著所有辣菜餐廳都能輕鬆躺賺。
在北京打工五年的河北人程鑫,每天的午飯,幾乎都在公司樓下一條小街的餐館裡解決。但就在近兩年時間裡,這裡超過一半的餐館已經換了名字。其中,就包括他之前最愛吃的一家蓋碼飯辣菜餐廳,不到30元的小炒肉蓋飯,吃得又飽又滿足,“可惜以後再也吃不到了”,他遺憾地說道。
網上,也有各種網友分享的閉店帖。比如,大連的網友@秋日又來賞楓葉,就發帖表示,大連羅斯福後順街的一家湘菜館,環境時尚,主打的小炒黃牛肉也量大實惠,但不到一年卻黃了,言語中滿是不解和失落。

事實上,餐飲行業向來利潤微薄,更不要說客單價本就較低的辣菜,“現在做親民餐廳的話,肯定是薄利多銷,翻一波臺、翻兩波臺都不一定能賺錢,可能翻到三波四波他才會賺錢”,熊建說。
從3月中旬開始,他在建國門的門店營收就出現下滑,單日營收平均少了大約4000元。他正努力尋找原因,同時也在想其他辦法增加營收,比如跟其他公司洽談商務套餐。他的門店之前接過這種合作,人均50元左右,最多的一次一天接了300份,營收一萬五。此外夏天就要到了,他準備做一波小龍蝦,“當然還是辣的”。
至於江西小炒這股風能吹多久,熊建表示:“短期內應該會冒出一些品牌。不過長遠來看,要像湘菜這樣持續火爆,還得看後續的產品創新和品質把控。”
餐飲從業者的權衡,並非沒有道理。尤其在大家消費趨於理性,收入普遍減少的當下。
曾經,在辣椒傳入中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因為用地少、產量高,也因為便宜、下飯而成了平民的恩賜,也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吃辣成了“窮”的表現。
直到近百年裡,一連串的社會變革刷掉了飲食的階級意味,這其中,辣椒的普及就是最好的體現。如今不僅普通老百姓喜歡吃辣,而中產、富人也都不能沒有辣椒。

談到國人吃辣的“窮歷史”,貴州人謝帆並沒有反駁:“雖然說出來不好聽,但一定程度上沒錯,比如在貴州,現在還有蹲在路邊接活兒的‘背篼’,重慶叫‘棒棒’,就是背個背篼幫你搬重物的人,他們經常吃的飯,就是饅頭和老乾媽。”
今天,辣菜的再次流行,或許和當初辣椒的普及有著相似的原因。當年輕人收入減少,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在飲食上對精緻的追求,必然讓步於吃好吃飽的底層需求。正如程鑫所說:“每次坐在桌前,看到剛出鍋的辣椒炒肉冒著熱氣的一刻,什麼煩惱都沒了。”
他從不擔心樓下的餐廳換來換去,“因為幾乎所有的菜館,都在賣辣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