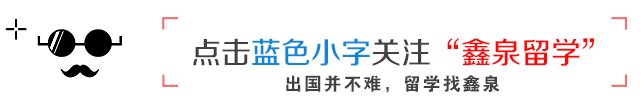中國歷史上曾有過門閥制度的時代,東晉尤為典型。那時,當官幾乎都是拼出身,是哪家子弟,祖上做過什麼官,直接決定你能不能入仕。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高位只給權貴子弟,底層人再有本事也上不去。
這種門閥壟斷帶來的後果就是社會活力的塌縮。人才選拔靠母嬰傳播,機會被少數人壟斷,普通人很難改變命運。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隋唐科舉制興起,才被慢慢打破。
最近發生的一些事,讓人看到,歷史上曾困擾中國社會許久的門閥制度,似乎正以另一種方式回潮。

1
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董小姐事件,讓協和“4+4”試點班走入了大眾視野。
這個原本借鑑國外、旨在拓寬醫學人才來源的制度設計,如今在現實中卻演變為某些特權子女規避競爭、繞開常規通道的便道。
有人本科唸的是經濟學,甚至是藝術、園藝、地質,結果四年後搖身一變成了“醫學博士”,在協和這樣的頂級醫院走上手術檯。更有甚者,論文只有十幾頁就能過關,規培只做一年就能上手術刀。這些看得人直發毛。
據媒體披露,這些人背景大都不一般,有的是央企高管的女兒,有的是體制內學閥的子弟。從讀書起就不靠高考拼殺,而是一路透過推薦、海外鍍金、內部轉錄,輕輕鬆鬆拿到名額。學歷履歷看上去找不出毛病,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種路徑是普通人根本無法複製的。
協和醫學院的“4+4”專案起初設立時門檻極高,明確只接收清華、北大、中科大這樣的頂尖學生。然而沒過幾年,標準便迅速放寬,發展到只要是“QS排名前80”的海外大學推薦的學生,便有資格入選。乍看之下,似乎合理,畢竟這些學校也算全球知名,但問題在於,很多這樣的海外學生,如果走國內高考路線,根本考不上協和醫學院。只不過他們家裡有資源、有規劃,提前鋪好路,先送去海外讀一個看上去不錯的大學,再透過4+4專案曲線救國回到協和。
有協和老師痛感生源質量一年不如一年,曾感慨:“不能再降了,再降分數線都快和清華一樣了。”
協和的分數線曾高於清北。那些去海外讀美本英本的學生,他們若參加高考,很多人都考不上清北,更別說協和了。他們就讀的院校雖然QS排名不低,但學生的基礎學力、科研素養和應試能力,與國內頂級高考生相比,差距肉眼可見。形式上看起來是精英迴流,實則是招生門檻在一點點向權貴和經過精細包裝的人傾斜。
協和4+4的醜聞再次證明,相對公平的高考制度,是中國普通人之福。它雖然也有種種問題,但好歹提供了一個憑實力一爭高下的機會。而源自西方的“推薦信+導師制”的路徑,在缺乏誠信體系、輿論監督和權力制約的土壤下,往往就變味了。打著國際接軌的旗號,最後對接的卻是中國的人情世故,上升通道拱手讓於熟人社會、關係社會,中下層民眾更看不到出頭的希望。
這種制度的變形並非空穴來風,現實中已有不少令人憤怒的案例佐證這一點。
近日有網友扒出,董小姐的博士論文,與北京科技大學一名殘疾學生的專利文章高度雷同。不僅選題一樣,連配圖都幾乎一致。令人心寒的是,這位殘疾學生疑似因為某些原因,被延遲畢業一年。更巧的是,這篇專利由四人聯合申請,除了那位學生,另外三人全是北京科技大學計算機學院的老師,其中一位班曉娟,不僅是殘疾學生的導師,還是董小姐的親姑姑。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主要研究工作肯定是那位學生完成的。現在不但成果被拿走,連畢業都被卡了一年。這副吃相,未免太難看了。
董小姐的背景關係,從這張圖就能窺見一二。圖片說明上,你能看出哪些資訊?不是行內人應該不懂。

2
這些年,大家對“拼爹”這詞已經訓練有素地迴避了,但現實並未變得更公平,只是遊戲規則更體面了些。
如今流行的是拼資源精細化隱蔽化。比如,早早去海外刷個聽起來高階的文憑,用人脈打通關節,繞過考試製度。形式上很好聽,國際視野、跨學科背景,實際上不過是特權換了個包裝。
這些人之間,彼此認識、互相扶持,自有一套遊戲規則。不是明著世襲,而是透過學歷、專案、身份,一層層把機會圈在一個小圈子裡。
這就是東晉門閥的那些套路。今天的門閥,只是換了馬甲,用更現代的方式包裝,比如名校、博士、精英專案。
其實任何社會,只要家庭制度還存在,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關係還存在,就很難徹底杜絕特權階層的存在。古今中外皆如此,區別只在於能否設立一套合理、公正的機制,把權力限制在規則內,而不是任其在灰色地帶裡生根發芽。
在多年前北大博士生馮軍旗調研撰寫的《中縣幹部》一文中,也曾揭示了類似的結構性問題。
他在某縣掛職時發現,看似制度完備的治理體系下,資源配置、幹部選拔和重點工程,實則牢牢掌握在幾個權勢家族手中,層層環節都有“自家人”把控,權力早已形成閉環。那一套熟人社會的執行邏輯,並沒有因為現代制度的引入而徹底瓦解,反而變得更隱蔽、更技術化。
協和4+4的問題,並不是孤例,而是這種門閥式結構,在醫療、教育、科研等很多領域的投影。
3
董小姐事件帶來最直接的衝擊,是普通人被邊緣化的挫敗感。
為何這件事激起這麼大波瀾,就是看到身邊越來越多這樣的事。很多年輕人開始意識到,機會正在以隱蔽的方式集中到少數人手裡。
更深層的,是整個社會對公平的信任感問題。一旦人們普遍認為拼學歷沒用,拼關係才有用,那麼真正用心讀書、腳踏實地做事的人,會越來越少。久而久之,這種環境會讓整個社會陷入一種無力感。看不到希望,就不會努力;看不到公正,就不會服從。
而當下的年輕人,很多已經處在極大的就業壓力之下。一邊是應屆生找不到工作、考公考研連年神仙打架,一邊是董小姐們輕而易舉拿到好工作、進名院實習,落差感之大,自然會引發情緒。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協和事件的輿論走向,也出現了明顯變化。輿論沒有停留在八卦或狗血情節,而是迅速轉向對社會不公的質疑。這說明當下很多年輕人其實非常清醒,他們關心的不是緋聞,而是自己的命運。他們需要一個出口,而這場風波,恰恰擊中了壓抑已久的情緒點。
這次輿情從發酵到擴散,有一種被默許的意味。微博給熱搜、自媒體大量相關文章沒有被刪,甚至在一些主流平臺上被轉發。這在以往是比較罕見的。有人猜測,這也許是上面藉機釋放訊號,想借助輿論的力量倒逼某些特權現象進行治理。因為有些事,國家層面心知肚明,但治理起來太難。那些盤根錯節的特權階層和利益集團,早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就像一臺服役多年的舊電腦,表面還能執行,後臺卻早已混亂不堪:系統負荷過重,垃圾堆積如山,風扇吵個不停,連打開個網頁都卡得發愁。防毒、清理、升級都試過,治標不治本。到頭來,不是邊換邊修、勉強維持,就是徹底關機重灌,甚至乾脆換新。
系統是不是穩定,取決於底層有沒有活力,而不是螢幕上的桌布是不是漂亮。
4
協和“4+4”只是一個縮影。
現在很多制度看著都挺好,檔案很漂亮,理念也夠先進。但真落實到地面上,很多時候就變了味。
比如有些地方搞公開招考,門檻設得特別細緻,學歷、經歷、年限、方向,一個不落。看上去很嚴格,但人家玩的其實是精準,精準到最後只有一個人能滿足。那個人是誰,大家基本都猜得到。
所以問題不是規則本身,而是誰能改規則,誰能提前知道規則。
有一次聽張雪峰接聽一個家長打來的電話,聊到孩子升學的路徑。他在直播裡不好講太明白,但反覆提到兩個詞:主觀標準和客觀標準。
比如高考分數,那是擺在明面上的客觀標準,多少分就能上什麼學校,誰都能查、誰都能比。你努力一分,就可能超越一千人。
可到了研究生、博士階段,規則就開始變了。你能不能被推薦,能不能進面試,導師喜不喜歡你,學校願不願給名額,這些就變成了主觀判斷。流程還在,檔案也都齊,就是標準變得模糊了。
這時候,那些有關係、有背景、懂得向上管理的人,就更容易獲得青睞。而那些單憑學習能力、出身普通的學生,就懸了。
媒體報道過,曾經的北大學霸陳如月,當年就是被協和4+4淘汰出局的。

社會穩定的前提,是要有向上的通道。如果階級開始板結,階層流動被堵死,社會就會積壓越來越多的不滿和擠壓感。這一點,歷史已經反覆證明。幾乎每一個王朝的終結,都伴隨著中下層上升通道的崩塌,最終走向暴力的爆發。現代社會當然不至於走到那一步,但若不能警惕特權擴張和機會分配的失衡,就可能為很多深層問題埋下伏筆。
要避免這種局面產生和進一步加劇,就得在制度設計上動腦筋,讓更多人相信努力是有用的,出身不能決定一切。
寫太多了,得收尾了。
宋冬野唱過: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個沒有故事的女同學。愛上一匹野馬,可我的家裡沒有草原,這讓我感到絕望。
當年聽著像情歌,如今回頭看,字字是隱喻。
董小姐確實不是一個沒有故事的女同學。
而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是董小姐。我們只是被允許在草原上跑一跑,好讓這套公平競爭的敘事,看上去完整一點。僅此而已。
這篇文章寫的是董小姐,想的是制度,指向的是我們大多數人的困境。歡迎來我的知識星球,一起討論董小姐的故事。

往期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