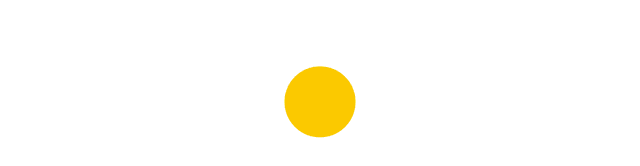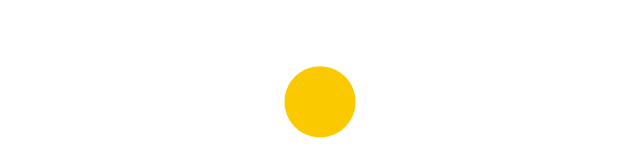非常建築於1993年由張永和與魯力佳在美國創立。在過去20多年中,非常建築從一個以研究、創新為特色的個人工作室,逐漸發展為國際知名的建築事務所。與此同時,張永和深耕建築教學領域,作為同濟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曾擔任麻省理工學院系主任,哈佛大學(GSD)丹下健三教授及任教多所大學,其思想理論及設計實踐多年來影響了無數建築學子。
前不久,張永和與魯力佳兩位老師來到紐約,為當地的建築師們分享了非常建築最新的專案成果。會後,ArchiDogs有幸對他們進行了專訪,就讀者非常關心的建築教育和職業發展等問題展開討論,並在本文中總結呈現。
注:以下問答中包含分享會中觀眾的部分提問,在此一併致以感謝。
採訪 | 汪澄波,馬元鳴,吳宇恆
作者 | 馬元鳴,李詩瑤,李夢倩
校對 | 汪澄波
編輯 | 藝夢
以下為正文
我感興趣的概念是離建築近一些的
ArchiDogs(以下簡稱A):非常建築以往的許多專案中,比如“垂直玻璃宅”和“後窗”等,我們都看到引人入勝的“概念”和“思辨”。這樣的設計思路影響了許多在校的學生。您認為對於一個好的建築專案,“概念”佔多大的比重?
非常建築(以下簡稱FCJZ): 我覺得概念在最終的產品裡非常不重要,但對設計過程可能是起重要作用的。我希望將我的興趣愛好帶到工作裡來,它們常常對我做選擇有所幫助。舉個例子,吃飯的時候酸甜苦辣的口味我都喜歡,導致選擇困難;但如果當天我的嗓子不好,理性就直接幫我排除了辣。這兩個過程非常相似。就像看電影,每個人對它的理解、個人的喜好和當下的心情都是相關的。



垂直玻璃宅概念圖紙
A: 因此建築師所構思的概念,和房子的使用者所理解的概念,可以有所偏差,這麼理解對嗎?
FCJZ: 這二者通常是非常不同的。其實理論也分離建築很遠的和離建築很近的。我感興趣的概念是離建築很近的。SanfordKwinter的理論討論到後結構主義和法國哲學,我不認為這和建築有很大關係。反之,一些理論家比如KennethFrampton和 Robin Evans,他們是做建築出身,反過來再用理論來解讀建築。這兩者的區別就非常大。

Frampton—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封面
美國東海岸是各種建築理論的“重災區”。記得我在MIT教書時,一個學生介紹完方案,兩個教授就開始爭論,結果我和那學生根本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那種風氣我個人認為對建築的發展是有一定影響的。
A: 八年前曾拜讀您的文章,有一個觀點是建議大家不要來美國讀建築,更推薦大家去歐洲留學。現在想再來問問您對歐洲教育體系是否仍然保持這個看法?
FCJZ: 這裡面是有一段歷史的。在70年代,美國學界出現了一些很重要的人物,比如Robert Venturi夫婦,他們開始對世界有一個新的認識,對資本主義、消費社會、大眾文化有一個不同的認識,也引起了一場偉大的後現代主義革命。那時現代建築越來越教條,後現代主義也向不同方向發展,波普藝術的幽默感又在復古潮流中消失了,結果美國建築就走向了比較特殊的發展之路,變得有些玩世不恭、犬儒主義。而在美國以外,包括西班牙、拉美國家的建築師,則越來越開始追求到底怎麼蓋房子,都發展得都很精彩。這個情況一直延續至今。
芝加哥建築師、時任耶魯院長的Thomas Beeby有一篇文章值得年輕人,尤其是想教書的年輕人讀一讀。他在文章中研究了建築老師這一角色,是這些人鞏固了建築學向非建築的轉變。他第一個研究的老師就是影響了一大批建築師的康。埃森曼的一句話可以作為總結:什麼是實踐?實踐是用來證明理論的,這完全是自上而下的。這就相當於說房子不能獨立存在,它的意義僅僅在於說明理論。這是個只存在於美國的現象。

芝加哥建築師、時任耶魯院長Thomas Beeby照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建築師,他們喜歡自己建構一個理論,比如黑川紀章的新陳代謝理論,可常常也做的不太好。但和美國不同,他們的理論往往基於個人對世界的觀察,而非基於純粹的哲學思想。相比而言,在美國越大牌的學校就越重理論,這就有點問題了。其他國家都沒有陷入美國這樣的困境。
出國留學是一種選擇,但不是必須
A:作為在中美兩國任教過的教授,您對建築領域出國留學持一種怎樣的態度?
FCJZ:留學現在正慢慢成為一種趨勢,很多國內的家長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選擇送他們出國讀書。我認為出國是一種選擇,但不是必須,其效果也因人而異。近幾年在事務所招人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現在國內院校畢業的建築學生專業能力並不差,其基礎甚至好於很多國外建築院校畢業的學生。因此是否有留學背景,對我們來說已沒有任何差異。因此,出國是一種選擇,一個經歷,而不是絕對優勢,也不會成為我們招聘時的一個評價標準。

非常建築工作室內工作場景
A:您剛才提到國內院校畢業的學生工作中表現更好,是否因為國內教育比國外大多數學校更偏向實踐?
FCJZ:並不完全是這樣。國內教育相比美國很多學校,尤其東岸一些學校確實要更偏實際一些。國內學生相對來講創造力會差一點,比較期待老師告訴你怎麼做。不過中國的國情不同,各個學校教學理念也有所差異,因此一個設計師成功與否更在於他個人的天分與努力。
A:根據您在MIT教書、擔任建築系主任的經驗,您認為MIT作為世界一流的學府,其建築學的教學體系是否在各方面達到了您認為的最高等級?
FCJZ:當下所謂的學校排名並不能夠完全反映建築教育的多樣性。麻省理工的一些資源,比如人才,是無法複製的。斯坦福大學有一個D School,借鑑了MITMedia Lab的形式。斯坦福大學作為以工程為背景的學府也有很多優秀的人才,但它卻沒有像MIT Media Lab一樣的跨學科人才。所以這兩者始終是不一樣的,沒有辦法做比較。

MIT Media Lab
在大家擇校時,排名只是參考的其中一個方面,但不應該是唯一的評價標準。如果現在讓我選我心目中最好的學校,可能一個是康奈爾大學,另外一個就是紐約的庫伯聯盟學院(The Cooper Union)。而我80年代初留學選學校的時候,就不可能會選擇庫伯聯盟,因為我對它不瞭解,對我自己也不瞭解。我現在做出的選擇則是依據我這麼多年的教書、做系主任的經歷,選擇一個更適合現在的我的學校。所以排名其實沒有那麼重要,前二三十名的學校區別也沒有很大,一個真正成熟的學生選學校時,其實是在選老師,認定一個老師就選這個學校跟著他學。每個學生都是不一樣的,沒有必要用同一套評價體系作為標準。
盲目追逐建築潮流不是一個好選擇
A:您如何看待當今建築領域的不同流派、發展方向及分支,年輕建築師該如何在各種潮流中做出合適的選擇?
FCJZ:當今世界沒有人可以預測未來的發展方向,年輕建築師更應該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做出選擇。如果單純追隨某種建築潮流,就個人發展與人生規劃而言,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潮流的東西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比如目前比較熱門的引數化設計,如果你數學不好,那就沒必要非要在這個領域與別人一決高下,因為很難做出成績。年輕建築師如果盲目地跟隨潮流,很容易會迷失自我,朝著不適合自身條件的方向發展。
A:近幾年的普利茲克獎評選結果出來後,有不少建築師評價該獎項越來越“政治正確”,偏向人文關懷、關注弱勢群體,而非有大量知名作品的明星建築師。這是否也是一種潮流?作為前幾屆的評委之一,您如何看待這些評論?

2018年普利茲克獎得主多西

Sangath Architects Studio.

印度學研究所
FCJZ:其實這是一般觀眾對於普利茲克獎獲得者這一群體的誤解,對明星建築師的誤解。普獎的重點不應在他們是否更注重人文關懷、關注弱勢群體等,而在於設計本身。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明星建築師的作品未必好。當今世界是市場加媒體的時代,一個建築師如果上了這條“明星”的軌道,就掌握了大量的機會,可是他未必有能力駕馭這些機會,很多時候做不好設計。同樣的,國際大牌產品的質量未必好,而一個沒有判斷力的消費者,很有可能就去買這些質量並不好卻很網紅的產品。
反過來,在印度、南美這些條件相對差的地方,比如烏拉圭,有些不那麼出名的建築師,卻在做真正好的建築。作為建築師,我們應當有自己的專業判斷力,應該關注這樣一些建築師。

烏拉圭聖工教堂照片
年輕建築師在不確定的時候一定要多實踐
A:您認為建築師、年輕學生該如何去發現自我,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道路?
FCJZ:年輕建築師在不確定的時候一定要多實踐。遇到自己感興趣的事,就繼續嘗試往下做,多花些時間,在這個過程中也許就能找到自己真正的興趣點。如果一段時間之後實在不喜歡,也可以再選擇其他的方向。
另外,年輕建築師一定要認清自己,要確定自己到底是否喜歡建築。建築這個行業是很艱難的。非常建築發展至今,我們仍然時時感受到困難的存在,從沒覺得事情越來越容易。如果確定了這條道路,就要多實踐,踏踏實實多幹活,只有實踐(Practice)才可以真正學到東西。


吉首藝術博物館圖紙、模型照片
A:實踐建築師面對甲方時,常常面對“話語權”的挑戰。您認為建築師在專案中有話語權嗎?
FCJZ: “話語權”在於“權”,而建築師是沒有這個權力的。與其說話語權,不如說建築師和業主之間是否有一個很好的對話,業主是否會很認真地聽取建築師的一個建議。很多業主在一開始並不願意聽建築師的,他們想要的是一個聽話的繪圖員。而作為一個接受過五年建築學教育的職業建築師,要把最真誠的意見告訴業主,而不能因為他是你的業主就可以犧牲建築學的原則。
版權宣告
版權歸作者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絡ArchiDogs或作者獲得授權
THE END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