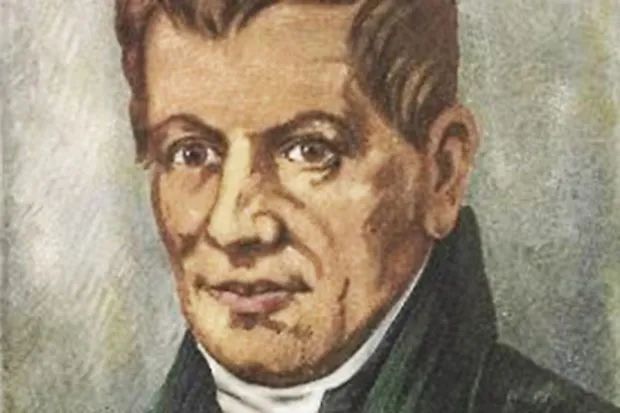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電影Ein ganzes Leben海報
文|沈衛榮(清華大學中文系)

沈衛榮(張子凌繪)
日前在從海口飛上海的飛機上,看了一部德語電影,名為Ein ganzes Leben,或譯《一個完整的人生》。本來只是隨意看看以打發時間,沒想到一下子竟就看了進去。電影講述的是上個世紀奧地利一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悲慘人生,但當他一生的經歷一幕幕地展示出來時,卻如史詩般地震撼人心。特別是片末主人公臨終前說的一段話,令我回味再三,卻始終感覺未得其甚解。他說:“我從來就不相信上帝,對死亡也無所畏懼。我不知道自己是從哪裡來的,也不知道要到哪裡去?而當我一生的經歷在眼前一幕幕回放時,我卻唯有驚愕!要不是我那麼累的話,我可以笑對純粹的幸福!”(Wenn ich nicht so müde wäre,könnte ich lachen vor reinem Glück)。這是這位無疾而終的老人處於“臨終中有”時的一段內心獨白,其人將死,其言也善,它應當很有分量,富有人生哲理。但是,我沒有明白於其臨終得見“光明”時,這位老人最終覺悟到的人生真理到底是什麼?德語畢竟不是我的母語,對他最後那句話的意思我不是那麼的確定。它的字面意思是說“要不是我那麼累的話,我是可以在純粹的幸福前笑的”,這是一個假設句,即是說他最終“沒有能夠在純粹的幸福前笑”出來就去世了。憑直覺我覺得他所謂“可以在純粹的幸福前笑”並不是說他至死終於可以笑對人間至福,而是說他終於明白所謂人間至福(純粹的歡樂)或是可笑的,他一生經歷的唯有無盡的苦難,或唯有即將降臨的死亡才是他的至福,只有當死神降臨時他才感受到這種純粹的幸福,可惜這時他已經累到連笑的力氣都沒有了。不過,我擔心我這樣的理解或又太平常和粗淺了,既缺少文學的審美,更沒有揭示任何哲學的勝意。難以置信,“一個完整的人生”留給我們世間有情的經驗和啟發,竟然就是佛家所說的人生即苦,人間至福其實就是死亡,這是人生最後的解脫!

小說Ein ganzes Leben封面

《大雪將至》,[奧地利] 羅伯特·澤塔勒著,劉秋葉譯,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6月版
《一個完整的人生》是根據羅伯特·塞瑟勒同名暢銷小說(國內譯本譯作“大雪將至”)改編而成的一部電影,敘述的是一位20世紀生活在阿爾卑斯深山老林中名叫安德列亞思·艾格爾的山民的人生故事。艾格爾是一名私生子,年幼失怙,被其叔叔接到地處偏遠山谷的農場,作為養子與叔叔一家同住,受盡了冷酷無情的叔叔的欺凌和摧殘,還曾被打瘸了一條腿。在他18歲那年,他終於逃離了叔父的魔爪,自立為一名樵夫。他在深山裡租了一間小屋,平日以出賣力氣,為他人幫工維持生計。於此,他遇見了他一生的生命之光——瑪麗,贏得了他隨後堅守了一生的愛情。可是,幸福的時光十分短暫,一次因建電纜線路實施爆破而引發的雪崩奪走了正孕育著一個新生命的瑪麗,同時也奪走了艾格爾一生的希望和幸福。從此,瘸著雙腿的他,日出日落,辛勤勞作,貧困而頑強地活著。二戰時,早已身心俱殘的他,依然被納粹政權強徵入伍,被派往高加索前線作戰,又很快遭隊友遺棄,獨自孤守山間戰場,直至神情迷惑,自投入敵方陣營,成了蘇聯紅軍的戰俘。八年之後,艾格爾得以生還故里,卻連一個棲身之地都無處可尋,但他一如既往地沉默、堅定、勤勞和倔強,不喜不悲,無慾無求,只是頑強地活著。電影中不時出現一個男人的背影,從孩童到少年,再從壯年到白髮蒼蒼的老年,他的背上出現過世間萬物:普通的揹包、沉重的稻草垛、槍桿和垂死的老者等等。艾格爾一生所受的苦難,無疑遠遠超過了一名苦行的僧侶,但他的愛情故事幾近童話:一生只動心一回,一生只愛一人,愛人逝去即封心鎖愛,心裡有話只願意向身在另一個世界的愛人訴說。世界待他如此薄情和殘酷,而他卻依然寬厚堅韌,善待世間有情,只是自己一個人苦苦地活著,從容地等待死亡。時光荏苒,當他終於成為一名步履蹣跚的老者時,他猛一抬頭即發現他居住的小鎮和整個世界都已經面目全非,不再是他熟悉的那個樣子,從未離開過小鎮的他感覺“對這個世界一無所知。”最後,他坐上鎮上一部環山遊覽的巴士,環山走了一圈,看了一路,體會了一下他身邊這個已經變化了的世界。此時,他一生悲歡離合的場景便像放電影一樣在他的意念中悠忽閃過,似漫長卻又短暫。他靜靜地躺在花草之中,無懼無畏地等待著“冷漠的老婦人”(死神)的召喚。最終,在他棲居的小屋中,他把他最後的人生體驗,向他的瑪麗一一訴說,這是他感覺人間至福終於來到了他的面前,然後一下撲倒在小桌子上,去另一個世界和瑪麗相會了。
無疑,艾格爾只是二十世紀歐洲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他的一生除了參與二戰的八年外都在深山老林中度過,除了飽受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無盡苦難外,沒有任何值得稱道的作為,他自己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在《一個完整的人生》這部小說問世之前,外面的世界對他自然更是一無所知。《一個完整的人生》這部電影是一部典型的歐洲小製作電影,它對艾格爾人生經歷的敘述和表達,採用的基本上是白描的手法,其中沒有什麼特別能刺激人感官的大場面,更沒有任何“宏大敘事”式的表達,也見不到政治正確的道德說教和對歷史是非的評判,但整部電影卻給人以史詩般的震撼力。但這種震撼力並不來自電影特具的表達力量,而是來自電影故事本身,它所敘述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人生經歷折射出了一部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時代歷史。有人說時代的每一粒塵埃落到個人的頭上都是一座大山,所以,落在個人頭上的每一粒時代的塵埃都可以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可以照見一個時代的歷史。
艾格爾雖然只是一個小人物,但他的每一段人生經歷都與那個時代歐洲的歷史和社會有著緊密的關聯。例如,他參與的阿爾卑斯山電纜車線路的建設,以及導致他失去了愛人的那場雪崩,表現的是歐洲工業化、現代化給世界帶來急速的變化和進步的同時,也對自然和人性造成了巨大的破壞;而身心殘疾的艾格爾的戰爭經歷,則凸顯出了那場由納粹政權挑起的世界大戰的荒誕和殘酷;戰爭對他的摧殘遠不止於奪走了他八年多的自由,並失去了棲身的家園,更是讓他失去了對物質和精神的一切追求;戰後歐洲的重建和復興,世界在急速的變化之中,而他卻在故土成了一個毫無用處的陌生人和遊離於人世之外的空心人,早在另外一個世界的瑪麗是他唯一的心靈寄託;他少年時代寄養在叔叔家中的苦難經歷,也典型地道出了人類天性本來就有善(老奶奶)與惡(叔叔)二面的道理,人類不能期待這個世界至善至美,想望人類永遠對你溫柔以待,但也不應當那麼容易就被人性的惡擊垮,要有脫離和戰勝惡的勇氣和能力。像艾格爾這樣一個小人物的經歷,單個看來確實微不足道,無足輕重,而若把它們放在那個時代的大歷史中來考察,則個人人生的每一個細節都具有時代的意義,都會令人驚心動魄!這大概就是為何當艾格爾臨終時在腦海中一幕幕地回放他的人生經歷時,他感受到的“唯有驚愕”,原以為平淡的苦難經歷,其實都是令人驚歎的時代歷史的細節。
近二十年前,我在美國偶然讀到了當年一位住在我隔壁宿舍的美國同學寫的一本書,書中描寫的就是我們南京大學歷史系七八級五位同學的人生故事,時間跨度歷五十年,始於1955年,止於2005年。這五位同學雖然不能說都微不足道,但至少沒有一位是家喻戶曉的知名人物,他們的那些故事放在今天也一定上不了“今日頭條”,可當我讀這本書,知道這些發生在我曾經熟識的同學們身上的故事時,卻常常驚訝得無以名狀!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常常會這樣想,我自己迄今的人生經歷平淡無奇,乏善可陳,但若要是也被人這樣寫下來的話,是否也會讓讀者感覺引人入勝,甚至驚心動魄呢?我感覺那五位同學的故事若要是沒被這樣放在大時代中貫穿起來敘述的話,也並不見得比我自己的故事精彩很多。我相信落到我們頭上的一粒時代的塵埃,不見得一定都會把我們徹底壓垮,但每一粒塵埃一定都能清楚地折射出這段大歷史的某個具體細節,它一定都是扣人心絃,令人動容的。
我之所以敢說《一個完整的人生》這部電影其實是一部歐洲二十世紀的時代史,這不僅是因為我對這部電影有上述這些粗淺的理解,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在現實中曾經遇到過一位與艾格爾的經歷非常相似的德國人,他是1990年代初年我在波恩留學客居Bad Godesberg鎮附近一座屋子達二年之久時的德國房東。這位老人與世紀同齡,我住進他房子時他已經是九十三歲的高齡,先後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二戰結束時,他被拋棄在波蘭的一個不知名的小地方,花了近一年的時間從那裡走回家鄉,一路歷盡艱辛,自不待言。待他回到家鄉時,發現一切都已面目全非,他已失去了過去所擁有的一切。於戰後重建時代,我房東的境遇看起來要好於艾格爾先生,他最終成了工廠中的一名技工,並建立了家庭,掙下了這一座不小的房子。在我與他同居一個屋簷下相處二年多的時間內,我很驚訝地發現他從來沒有真正走出青年時代戰爭給他留下的創傷,他一直活在對過去的回憶中,他對當下這個世界出奇的無知和漠然,過著一種十分單調和機械的生活。他每天同一時間起床、入睡,每天按既定的計劃做著同樣的事情,準備自己的一日三餐,和整理、打掃自己的小院和房子。起初他甚至要求我每週六早晨九點必須出門,由他來打掃和整理我的房間,換洗床單。我花了很多口舌才終於讓他同意我自己打掃房間,這樣週六早晨我可以睡個懶覺。他每日三餐吃的都是同樣的東西,千篇一律,日復一日。早餐是生雞蛋拌生牛肉片,再加上幾片生洋蔥,中餐和晚餐則從來都是煎炸的牛排或者豬排,還有油炸的土豆,從無變化。每次我炒個菠菜或者做個別樣的中式炒菜,請他和我一起享用時,他都會驚訝地問我你這是做的什麼東西,他連整棵的生菠菜都從來沒有見過,令我瞠目結舌!他年輕時一定有過美好的愛情,有次偶然在樓頂閣樓上見到一個塵封已久的紙箱,見裡面裝的是他和他太太年輕時的很多照片和來往書信,讓我驚訝年輕時他們曾是那麼的俊朗、美貌,他們的愛情也曾如此的熱烈和激情。在我搬進去住時,房東太太早已經被送進特殊的養老護理院了,但每隔兩週的週末,房東都會把他老伴接回家中住上兩天。其實,他太太早已處於失智狀態,看起來還有點躁鬱,每次她回來住時,這原本十分平靜有序的家中馬上就會亂成一團,常常在深夜還會聽到他們激烈地在爭吵,這狀況真的是如德語所說的Hoelle los,“地獄開張了”。每次送走他太太,房東都像剛下了戰場,疲憊不堪,對我說他再也無法忍受讓她回家來了,可二週後他照常又會將她接回家中,繼續忍受其折磨。比艾格爾更不幸的是,房東還有一位沒出息的兒子,他不但從不給予老父親任何的照顧,而且還時常要來向他索取財物。幾次我看到屋外有人探頭探腦,仔細打量著這座房子,一問才知道他們是房東兒子的債主,他們覺得要從他兒子那裡討回錢財是不可能的了,故期待房東百年之後他兒子或能夠繼承包括這座房子在內的鉅額遺產,以償還久借不歸的那些債務。或正如這些債主所願,平日身體健朗的房東一日竟一睡不起,無疾而終了。他常對我說:他九十歲時的身體狀況遠好於他六七十歲時,活到百歲估計是沒有問題的。也許他也和電影中的艾格爾一樣,突然覺得自己已是那麼的累了,完全可以笑對人間“至福”了。我德國房東的“一個完整的人生”,一樣是二十世紀歐洲的一部時代歷史!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責編:黃曉峰。
本期微信編輯:朱凡。
本文為思想市場原創內容,點選“閱讀原文”進入澎湃新聞網站閱讀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