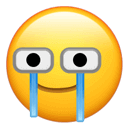文 |呂煦宬
剪輯 |張歆玥
編輯 | 陶若谷

“你訊號不好呀”
口吃是一種什麼感覺呢?
你試著完全不用氣息,憋著一口氣,用本身的力氣說話,會感到肺部脹開,渾身僵硬。這就是我遇上難發音的感受,即便很用力說出來,也會很糗。爆破音通常發不好,尤其緊張的時候,氣息弱,會更難。
比如“大家好”,這個“大”字,常卡住。不是大腦空白,而是我知道要說這個字,但怎麼用力都說不出來。小時候和班主任請假,嘴巴像抽筋一樣,不停眨眼,有時候會握拳、跺腳,其實是在用身體借力,想發出聲音,但發不出來。老師憋不住笑,給我批假,非常尷尬。
6月25日錄《喜劇之王單口季》那天,徐崢還有我很喜歡的幾個演員,全坐在下面。一緊張,不會說話了。說首字前,要在心裡打節拍,像跳長繩那樣,一下,一下,一下,打節奏,找準進去的點。(但)那天,很像幾年前口吃嚴重的狀態,每句開頭都卡了很久。
當時還沒有意識到講得那麼差,下了臺,其他演員提醒我,才發現連自我介紹都忘了說,我至今沒敢看回放。後面在Talking(和嘉賓交流)環節,我透過換字,繞過一些難發音,才順暢許多。但播出後,討論的重點全是,我是真的口吃,還是裝的。
我試著和朋友解釋,發現他們也不太能理解狀態(對口吃)的差異。其實平時演出,到大一些的劇場,臺子一高,我就會不適應。但這次彩排表現不錯,我就放鬆了。錄製的時候,卡頓太頻繁,破壞了表演節奏。
我接觸脫口秀的契機,得說回口才班。大概四年前,我想交朋友,報了個口才班,那裡會設定情景溝通。有次模擬相親,不知道該說什麼,聽到旁邊有人問,能不能接受歲數比你大的。我照著學,問一個女生,“你能不能接受”,卡住了很久,“歲數比你小的”。大家就笑了。我不知道笑點在哪兒,但看到大家笑,突然覺得自己很好。
班裡恰好有個脫口秀演員,說我的節奏很有趣,像馬三立。我開始對舞臺有了憧憬,後來那個演員弄了個培訓班,教一些基本技巧,我就去了。最開始像流水賬一樣,把好玩的事情說出來,什麼小孩摔倒了,小貓跳下去了。還有一些像網路笑話的,“我長得高,怕長到1米89,因為我恐高”,就那種。
反饋並不好,那個演員露出很微妙的表情,感覺他想說,很差,又不好打擊,就只是微笑。但當時我的關注點放在,我能不能說得流暢,沒有在意喜劇效果。

●子銘曾輾轉多地,參加口吃康復班。
第一個從生活中挖掘的段子是講我做銷售。文字沒有特殊設計,只是說我因為講話卡殼,客戶說:“你訊號不好呀。”講到這裡,臺下的人放聲大笑,還有鼓掌的。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笑。以前我說話卡殼,嘴巴抽搐,很好笑,但別人會憋著。
但這次我感到很自信。那是2021年4月,後來在朋友鼓勵下,開始去開放麥。很小的場子,觀眾20多個人,我排在靠後的位置。一上臺,腦子嗡一下,眼前全白了。我說不出來,心裡在數拍子,沒說話,臺下就開始笑,還給我掌聲。感覺被觀眾的善意接住,我慢慢放鬆,按自己的節奏走。下臺後,老闆很吃驚地看著我:“你也太好笑了”。其他演員也在給我肯定。那天晚上回家,我把演出影片反反覆覆地看。
以前我很想交朋友,放慢速度說話,卻把人嚇走。但在臺上,一下收穫那麼多人的喜歡,也沒把氣氛搞緊張,對我來說是很新鮮的體驗。那次我沒有袒露“口吃”的經歷,只說,我說話很慢,和小愛同學(智慧語音助手)溝通不暢。
兩三場開放麥後,有人約我商演。演員和廠牌老闆陪我聊稿子,讓我一上臺就說,“我是個有口吃的人。”我沒有很介意。
一直以來,我的羞恥感主要因為,說話時嘴巴抽搐的那種窘態。(早年)從康復班回來後,我就直接和別人說,“我有口吃,說的時間比較長,希望你不要著急。”
我想的簡單,這是錯位競爭,是條新賽道。隨著演出增多,我會注意到,哪些卡殼,會引發笑聲,之後就保持這種斷句。比如接過主持人遞來的話筒,我說“謝謝主持”,卡頓,“人”。觀眾就笑了。這不是我設計的,但我會記住這個節奏,在接下來的演出中,沿襲下來。

看上去失敗的人,讓我覺得親切
段子裡,我介紹自己是“停頓型口吃”,這是我糾正了發音方法後的狀態。以前,我是重複型的。
口吃的情況出現在小學一年級,老師叫我起來回答問題,站起來臉就紅了,出汗,瘋狂眨眼,嘴巴發抖,同學們都在笑,老師說,你還是坐下吧。
很多老師上課會避開我,不點我,他們好像知道我答不上來。我在段子裡說,“口吃是從小和別人學的,所以我學習能力比較強。”其實不是。我在學生時代是很邊緣的,好像無論老師說什麼,我都聽不懂,時刻很緊張,一直在出汗、臉紅。老師教寫田字格,我在田字格的四個小格子裡,各寫了四個字。
班上有個算校霸的人物,每次見到我,都會用力給我一拳。我想去找老師,但想到老師也不喜歡我,所以沒說過。我的同桌會把他叫住,說你以後不要欺負他了。但我也沒有想過要和她(同桌)成為朋友,我只敢和同樣邊緣的人玩。
有一個成天不洗頭,鬍子很長,衣服也髒,還有個比較胖。這些看上去失敗的人,讓我覺得親切。我們不交心,就是圖個伴。在操場上開早會的時候,有一兩個可以說話的人,顯得沒那麼奇怪。
父母對我也沒有期待,健健康康就行了。我是獨生子,我媽有點溺愛。小升初的時候,我隨口抱怨了一句,不想軍訓,我媽就給老師發簡訊,說我對青草過敏,真不讓我去了。我爸總跟她說:“你再這樣溺愛他就廢了。”我爸和我交流很少,感覺除了我媽,所有人都覺得我是垃圾。親戚聚會要發言,我就溜去上廁所,躲到房間,出來的時候發現他們吃完了,心裡會鬆口氣。
在正式進入工作前,我過得比較糊塗,沒有規劃,也沒認真想過怎麼對待口吃這件事。我的愛好都是為了逃避痛苦而培養的。畫畫,不用和人交流;唱歌有節拍,我不會卡殼。全民K歌剛出來時,我在家一個人唱,發現,誒,還挺好聽的。後來開了B站,有彈幕誇我聲音好聽,這種評價,以前從來沒有過。

●日常演出。
臨近大專畢業,父母讓我跟他們開個小店,幫人p圖。學校也來了家公司,招“家裝顧問”,底薪700,早九晚八,談成一單,有2%提成。和父母開店比較輕鬆,但我覺得“家裝顧問”是上門檢修、要進公司,算個正經工作。
進去才知道,這工作就是銷售,感覺天都塌了,怎麼找了份這樣的工作?又不敢提離職,我反覆想象那個畫面——某天開會,點到我發言,我支支吾吾,老闆問,這個人是什麼情況?接著我就會被開除。
辦公室四十多個人,一排排在格子間坐著,給客戶打電話。我總等其他人開始打了,再開始。如果周圍突然安靜下來,我會立刻把電話結束通話。頭埋得很低,這樣嘴巴抽搐,別人也看不出來。如果有人從我身後走過,或者周圍的人動一下,都會讓我驚一下。像個老鼠,想偷點米吃,就要擔驚受怕。
第一個電話,接通後是個阿姨,我什麼都說不出來,她以為這邊沒人,結束通話了。打了幾百個電話後,我才完整說出,“您好,我是xx裝飾的小劉”。我打電話的間隙不休息,別人是工作,我是排解焦慮,每次撥通一個,等待的同時撥好下一個。我想保持一種忙碌的狀態,別乾坐著,很尷尬。
也遇到過善良的人,不掛斷,鼓勵我慢慢說。工作了3個月後,狀況變好,老闆注意到了我,跟其他人說,“你們都跟子銘學學,他從來不休息。”
老闆人不壞,挺關心我的,但他潛意識裡還是把我當成弱勢群體。開晨會,老闆把我叫到100多位員工面前,指著我說:這位同事非常優秀,你們看,連他都可以。他還說:你們看得出來嗎?他是有點傻的。
我在這家公司工作了一年多,很欣賞經理,業務能力強,我會模仿他的語速。後來越想加快,就越著急,口吃失控了,卡殼變多,最嚴重的時候完全說不出話。
那時候是非常絕望的。我以為生活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又被打回原形。我父母在那時意識到了嚴重性。我跟他們說,因為說不出話,丟了好多客戶,說著說著情緒崩潰,開始摔東西,手上速度很快,但嘴巴跟不上。我父母站在一旁,看我在那裡哭。
正式開始和口吃的鬥爭就是在那一年,2018年,我辭掉銷售工作,從老家大連去了我媽給我找的口吃康復班,在山東。康復班牆上掛著個黑板,拉著橫幅:不斷地挑戰,口吃總會屈服。老師安排我每天按照固定路線,到小城的公園、學校、十字路口做戶外演講——“我是子銘,我有嚴重的口吃,我來勇敢地暴露自己!我相信我能勇敢地戰勝自己!我一定會好起來的!謝謝大家。”
就這麼每天衝著陌生人喊。公園裡的老人臉上不耐煩,但也聽我說完,還鼓掌。在公交車站講,被人罵是傳銷的。學校門口最尷尬,都是同齡人,他們在上學,我在口吃矯正。
三四十天後,口吃反倒更嚴重了。老師很嚴肅地說,只好用“沉默大法”了——30天不說話,如果沒有效果,就延長時間。我和我媽都覺得荒謬,但老師一本正經,我當時的狀態,不如不說話,就接受了。

停頓沒有那麼羞恥
沉默大法沒用,但我在這家康復班第一次學到了發音方法,用拖長音的方式,“比~如~像~這~樣~”。這樣說話,嘴巴不會抽搐,這是我最在意的,有尊嚴感。
那以後,我應對卡殼的方式從抽搐、重複變成了停頓,能正常說話,溝通流暢度提高了一些。第二年,又去了南京一家康復班,接觸到“順其自然、為所當為”的療法,學著接納口吃這件事。後來,結合各種康復方法,應付日常交流,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但那時候我已經幾乎沒有朋友了。“沉默大法”的時候,我跟朋友出去還要打字交流,他們可能覺得我太奇怪了,沒再聯絡。後來,我參加了很多活動。在口才班,我遇到了峰哥,他是做音樂心理諮詢的,說我唱歌好聽,還找來打鼓的人,叫來攝像,圍著我,讓我彈吉他,給我錄了一支影片,對我幫助很大。他還鼓勵我,把吉他拿上臺。
“慢語者俱樂部”也是他提議組建的,含義是,“口吃不是疾病,只是說話比較慢。”我們在朋友圈、B站發了邀請,最後有40多個志願者加入,圍著我一個口吃的,這個組織算是沒真正弄起來。

●峰哥給子銘辦的樂隊。
更多接觸到這個群體,是在去年,我發了一些口吃矯正的方法,收到不少私信。很多口吃的人還是很迷茫,像困在了一個無解的問題裡。我認識一些四五十歲口吃的人,一輩子在廠裡擰螺絲釘,沒有談過戀愛。說話都很困難的時候,你是沒有心思做別的事的。
口吃的痛苦是隱性的,大家普遍都經歷著挫敗和焦慮。我收到過一個求助問,“每天在人前大喊我不是口吃患者,我沒有病,有沒有用?”這種心理暗示我也試過,但只會讓人越走越偏——當你提醒自己不要想粉紅色的大象,腦子裡就會出現那隻粉紅色的大象。
我很幸運,認識了我的女朋友。我們倆同歲,相處起來很平等。剛開始,我沒有坦白口吃的事,開玩笑說,我是腦子有問題。坦白後,她說,其實挺可愛的。認識她以前,我覺得自己是在獨自挖一個筆直的隧道,沒有同伴。這種孤獨的感覺,現在基本消失了。有時我們吵架,嘴巴還是會抽,就會打字聊。
我其實很擔心,哪天口吃變嚴重了,會失去這段關係。但前幾天,女朋友看了節目,我問她,卡殼嚴不嚴重?她說,“還好,反正我笑得挺開心的。”也有口吃的朋友給我私信,說第一次感受到,停頓沒有那麼羞恥。
接觸脫口秀以後,口吃成了我的特點,讓我養活自己,我覺得是個天大的進步。有時還是避不開觀眾的同情,觀眾會說“加油”、“你很堅強”,還有人說“子銘給我看哭了”。你看得著急我可以理解,看哭就很奇怪了。
為了讓觀眾卸下顧慮,我通常一上臺就調侃口吃,說我去打架,一邊罵人,一邊被打,被打得斷斷續續的。這個梗放在開頭,觀眾會放鬆很多。有前輩提建議,說我已經能和口吃和平相處了,得寫點新東西。但問題也在這裡。
我的語速很慢,三四句就得有一個笑點,不然觀眾會走神,這意味著我很難講故事型的段子。我講過,銷售老闆說“連他都可以”的事,結果越說越激動,臺下完全不敢笑。把這些有情緒、有看法的事講得好笑,是需要水平的。我目前還沒有這個能力,有時寫著寫著就歪了。
我原本沒有計劃做全職脫口秀演員。在大連每週一場商演,掙200塊,很難養活自己。我找過畫畫老師的工作、培訓班帶小孩的工作,都沒有下文。
找工作不順利,“錯位競爭”這四個字不斷冒出來。我開始瘋狂寫段子,寫one liner,一句話抖一個包袱,不用太多鋪墊,用反轉製造笑點。這是朋友給我提意見,說我的停頓長於一般人,如果停頓後能有一個大反轉,效果會很好。
我的優點不多,這個舞臺讓我把缺點變成優點。也希望更多口吃的人看到我,給他們一點小的力量。父母的態度也變了,以前我是一大家子裡最差的小孩,現在能找到份餬口的工作,已經超出期待。我爸說,賺不賺大錢都沒關係,你去了那麼多城市,面對那麼多人演出,很有勇氣。放到以前,他不會說這些。
杭州今年夏天很熱,我給自己放了個假。每天看書、做飯,偶爾運動、唱歌,也幫一些口吃朋友做矯正。沒上臺的日子,有些平淡,我以後會繼續跑演出。現在已經不是“我喜不喜歡脫口秀”的問題了,是我需要它。
(文中圖片均由講述者提供。)
版權宣告:本文所有內容著作權歸屬極晝工作室,未經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宣告除外。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