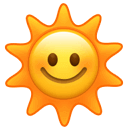▲ Photo by Pixabay
作者:陳功,諾友,現居日本東京。長期專注於職業規劃與人才招聘,致力於中日之間的人才交流與企業發展。
命運向我發起了一連串挑戰
回望 2024 年,那是一段灰暗而沉重的時光,彷彿命運在短短幾個月內密集地向我發出了一連串挑戰。
年初,我在上海的房產交易突遭變故。原本以為只是一個手續問題,結果卻牽扯出意想不到的複雜和反覆,甚至一度考慮聘請律師介入——雖然最終沒有真正啟用法律手段,結果也算圓滿,但整件事情帶來的精神消耗遠超想象。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體會到人性的出爾反爾,在利益面前的冷漠與算計,也讓我對所謂的“信任”有了更深的懷疑。這種帶著鋒利邊角的現實,深深割裂了我原本就不太穩固的情緒基礎。
而在此期間,我在東京投資的一家小店剛剛啟動,卻因為“人力荒”,沒幾個月便因為招不到服務員而倒閉,投入的資金在短時間內化為烏有。與此同時,剛來東京不久的我還在努力適應一個語言不通、文化陌生的環境。雖然並不是完全孤立無援,但與原本熟悉的環境抽離,仍讓我陷入一種持續性的情緒疲憊。
對我打擊最大的,是父親的突然離世。我們之間有太多未解的矛盾,也有剪不斷的情感。在複雜的愛與傷之間,他的離世讓我措手不及,也讓我陷入一種難以言說的情緒漩渦中。
房產的波折、投資的失敗、情感的隔閡、親人的離世——這一連串事件像一股股不留情面的暗流,輪番卷襲我尚未修復的內心。雖然從未正式被診斷為抑鬱,但我知道,那段時間的我,已經非常接近崩潰的邊緣。那或許就是人們常說的——中年危機。
用生命點亮生命
轉折發生在 2024 年 4月11日。
當我看到一諾主理的“東京文化教育考察團”的招生海報時,幾乎沒有猶豫就報了名。我是服務群裡的第七位成員,除了前六位是工作人員外,我是第一個報名的人,可見我當時的心情有多急迫,那不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而是一種幾近本能的回應:我需要一個出口,一個支點,一個重新出發的機會。(新一期的東京考察團正在招募中,可在文末海報報名)
讓我不假思索就決定加入的另一個原因,是李一諾這個名字。
幾年前,我就讀過邁克爾·辛格的著作《不羈的靈魂》,這本書對我影響極大。後來我又讀了他寫的《臣服實驗》,這本書的中文版序言的作者正是李一諾,她在其中提到這本書對她的巨大影響。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直覺告訴我:這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
於是去年五月,我在東京的遊學就這麼開始了。
據說好的電影不只是讓人當時感動,還“餘韻”悠長,即便是若干年後你再想起它,仍然值得回味,我想,一個好的遊學也是如此吧!雖然已經過去了一年, 但很多場景仍然讓我記憶猶新。
遊學的其中一個專案是,我們在一諾的安排下參訪她兒子就讀的學校。那所學校位於澀谷附近的一棟共享辦公樓裡,空間不大,約四十平方米,只有六個學生,由兩位耶魯畢業的外籍教師負責教學。
他們的教學理念是:教育的本質,不在於金錢和設施的堆砌,而在於激發學生的興趣和能力。透過專案驅動,孩子們可以圍繞自己感興趣的課題進行研究,再邀請外部專家提供視角支援。
當被問及這樣的教學模式是否“值得”時,老師說:“一個,也值得教。”

這句話深深打動了我:真正的教育,是人格的影響,是深度的陪伴,是你願不願意用你的人生去點亮另一個生命。
另一個場景,是在東京單向街書店的一場內部交流會上,我分享了作為中年人遠離家鄉、置身異國的種種複雜心情。
我說:“如果不是無可奈何,誰又願意背井離鄉?”當時我提出的問題是:人到中年,來到一個非中文國家,失去了原有身份定位,如何面對內心特別強的漂泊感?。
我講完之後,臺上的一諾已經淚流滿面,許多團友也都在默默拭淚。那是一次集體情緒的釋放與共鳴。
更巧的是,那天我也認識了東京單向街書店的向姐,她聽完我的發言後與我進一步交流,這之後又引導我參與到單向街東京職場系列活動中來,也因此認識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最讓我懷念的,還是每天晚上在居酒屋的暢談時光。不同背景的朋友們圍坐在一起,聊職場、聊教育、聊未來生活、聊彼此的不確定和各種破局的嘗試。
那些夜晚,沒有人設,沒有表演,只有中年人彼此之間的真實開啟。我們談自己的理想、掙扎和下一代的方向,偶爾也會吐槽,更多時候是相互鼓勵。
這種默契,是短暫營會難得留下的持久紐帶。

更多元的視角,更多維的連結
那之後,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
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行動上,我都開啟了一種新的可能:我從考察團的學員變成了“師兄”和分享者,參與到更多活動中,融入了“諾友”群體,也開啟了在東京的人才服務事業——幫助更多漂泊在日本的人重建事業與生活。

那次遊學其中一個關鍵詞叫“換個視角看東京”,對我而言更像是“多了個視角看東京”。那時,我雖然來日本也有一年多了,但日本的很多方面確實沒有深入瞭解。以我這樣的“懶人”性格來說,一來自己不知道怎麼去了解,更何況有些機構不對外公開,沒有特定預約,自己壓根就去不了;二來自己走馬觀花地去看,可能也看不到更多的本質和內涵。
直到參加了這次遊學,我才知道,原來國會是可以參觀甚至旁聽的,有的大學是沒有校門的,公立學校是不收費的,私立學校是真不貴的(相比北上深,歐美等),學生參觀是安靜整齊坐在牆邊排隊的,華人在東京是有越來越多聊天看書據點的……

曾經不止一位出海經驗豐富的朋友對我說:如果你想遊玩一個地方,應該先找當地的朋友;如果你想深入考察或者移居一個地方,應該先找到志同道合的組織,這兩者都是既快又有效的方式。
在參加了文化教育考察團之後,我就加入了 400 多人的東京諾友群,也算在東京找到了組織。群裡很多人都是在線上或線下有過交集的朋友。這一年,透過在東京不定期聚會、分享、吃飯喝茶,我也認識了不少有趣的朋友和合作夥伴。不僅是我,同期的其他學友詢問日本問題或者再來東京玩,幾乎都有熱心的諾友分享資訊和當面引導,這讓我感到既安心又親切。
過來人都知道,一個初到異國的中年人,想要在語言文化都不同的地方找到和自己原來職位匹配的工作機會有多不易,否則也不會出現“新移民三大行業”:民宿,餐飲,代購。
而我是幸運的,在那次單向街的發言,成了一個讓我連結機會的新起點,一諾和向姐之後又聯合在地專家團,在單向街書店舉行了多次廣受好評的東京職場分享活動,我也正是透過這些活動,認識了很多新諾友和現在的幾位合作伙伴,機會就像漣漪一樣慢慢展開……
時至今日,我應該是從中年危機的漩渦中游出來了吧。
其實這個過程中有意思的、讓人感動的故事還有很多,比如《力量從哪裡來》這本書帶給我的觸動,又比如和諾友俱樂部一起以球會友等等。
今天中午 12 點,我會和當年一起遊學的室友“魚骨頭”一起進行線上直播,重溫過去、碰撞現在,相信更多故事和感受會流淌出來。歡迎大家預約觀看~

5 月 29 日~6 月 3 日,一諾將組織新一期的遊學。在本次遊學中,會安排“孃家人見面會”,我和過往的一些學友,還有當地和從外地飛來的諾友,分享我們的心路歷程和親身故事,歡迎大家帶著好奇和問題相聚。
最後我想送給那些曾走過低潮的幽谷,不屈於命運的安排的朋友們一句祝福:“無論你身在何處,正經歷著什麼,都願你有人愛,有事做,有所期待。”
今天是考察團早鳥價最後一天,感興趣的夥伴可以趁優惠加入,詳情請看下方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