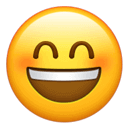華陽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美國新任國務卿魯比奧剛上任,就在南海問題上“出言不遜”。當地時間1月22日,魯比奧與菲律賓外長恩裡克·馬納洛首次通話,強調“美國根據《共同防禦條約》對菲律賓的堅定承諾”,並談及南海問題,為菲律賓撐腰“譴責”中國。
而就在通話兩天後,1月24日,菲律賓便“壯膽”付諸行動。菲3003號和3004號船未經中國政府允許,侵闖中國南沙群島鐵線礁附近海域,企圖非法登礁,中國海警船依法對菲船攔阻管制、警告驅離。
特朗普2.0時代,美菲會否在南海挑起更大風浪,是區域內國家、乃至全球關注的焦點之一。事實上,就在特朗普正式就職前,美國知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就摩拳擦掌,替菲律賓政府“出謀劃策”。


菲律賓登鐵線礁被我海警攔下 央視
1月10日,美國CSIS的東南亞專案和“亞洲海事透明倡議”(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AMTI)主任兼高階研究員格雷戈裡·B·波林(Gregory B.
Poling)在該中心官方網站發表了題為《如何“殺死巨人”:重拾南海仲裁》(How to Slay a Giant: Reviv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的文章。
該文中,波林的觀點思路清奇,其為菲律賓“量身定製”的策略“另闢蹊徑”,大有為菲總統小馬科斯當局充當“狗頭軍師”的意味,值得我國研究南海問題的學者及學界同仁關注、推敲、批判。

波林的這篇評論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跌宕起伏”地介紹了2016年7月12日所謂南海仲裁案的裁決作出以來,菲政府對待裁決的不同做法。波林指出,自2022年7月小馬科斯總統上臺以來,已一改此前杜特爾特總統執政六年間“冷處理”南海仲裁案裁決的做法,積極地同支持菲律賓立場的國家一起“敦促”中國“遵守裁決”。
兩年來,菲律賓一方面在南海海域加強了海軍巡邏,另一方面透過所謂的“透明度計劃”向世界“揭示”中國在相關海域的“非法活動”。此外,自2024年起菲律賓還積極醞釀提起“二次仲裁”的可能,並企圖透過聯合國大會等外交場合物色“支援”其立場的國家。
該文第二部分“他山之石”,以模里西斯和英國之間曠日持久的查戈斯群島領土主權爭端為例,講述東非小國模里西斯是如何透過國際仲裁和司法途徑獲取國際社會多數國家的支援,併成功於2017年藉由聯合國大會作出決議向國際法院請求作出諮詢意見。在2019年的諮詢意見中,模里西斯的立場得到了國際法院的支援。迫於國際輿論壓力,英國當局不得不同模里西斯就查戈斯群島的主權交接問題達成協議。
在波林看來,類似“小國扳倒大國”的先例還有不少,包括上世紀80年代尼加拉瓜訴美國,以及2014年荷蘭訴俄羅斯的“北極日出號”案等,因而值得菲律賓效仿。
在該文第三部分“勝券在握”中,波林透過分析涉及美國、英國和俄羅斯這些“大國”的聯合國大會決議投票情況的若干先例,得出“菲律賓有望在與南海有關的投票中至少以62比44的票數獲勝”的“論斷”。
最後,在題為“千刀萬剮”(Death by a Thousand
Cuts)的第四部分中,波林認為在國際平臺遭受一連串的“失利”將促使中國考慮向菲律賓做出妥協以“挽回顏面”。波林還建議菲律賓可運用聯合國大會的平臺向國際法院提起要求中國“遵守裁決”或認定中國的有關行為“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海上避碰規則公約》”的諮詢意見。他還樂觀預測一連串的“勝利”將使菲律賓積聚越來越多的他國支援。
雖然波林的文章看似環環相扣,有一定邏輯推理,也有若干耳熟能詳的國際例項,但仔細推敲不難發現其文章中存在各種各樣的瑕疵和謬誤,其核心觀點也是建立在諸多錯誤的前提之上的。
現一一指出,以正視聽,供學界同仁進一步批判該文時參考。
首先,波林在文中開篇即鼓吹“裁決”是菲律賓的“法律勝利”,為非法“裁決”背書。顯然,波林的文章通篇都是建立在南海仲裁案“裁決”“合法有效、必須遵守”這一錯誤的前提之上,屬於顛倒黑白。
在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的所謂“裁決”作出前後,我國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的涉海問題立場檔案,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菲律賓共和國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問題的立場檔案》(2014年12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於應菲律賓共和國請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關於管轄權和可受理性問題裁決的宣告》(2015年10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於堅持透過雙邊談判解決中國和菲律賓在南海有關爭議的宣告》(2016年6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於應菲律賓共和國請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決的宣告》(2016年7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宣告》(2016年7月12日)、《中國堅持透過談判解決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的有關爭議》(2016年7月13日)以及《中國致力於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與秩序》(2022年)等,有力揭示了南海仲裁案的本質是“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鬧劇”。
菲律賓單方面提起仲裁併不是為了善意地解決中菲之間存在的爭端,而是借仲裁這一法律手段來掩蓋其多年來非法侵佔我國南海部分島礁及侵犯我國在南海的海洋權利的違法行為。中國“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不執行”的立場恰恰是維護國際法治。
所謂“仲裁裁決”出爐後,國際社會的許多國家贊同中國政府透過堅持談判解決南海爭端的立場,而波林卻以美國智庫CSIS(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所謂“追蹤資料”作為立論依據,認為“只有7個聯合國會員國公開支援中國”,完全罔顧事實。
其次,波林偷換概念,混淆視聽。文章開篇提及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由在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的5位“法官”組成。這一表述用意明顯,存在混淆仲裁與司法以及刻意誇大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權威性”的目的。

位於海牙的常設仲裁庭
其一,波林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混淆了仲裁和司法這兩種不同的解決國際爭端的法律方法。
一般來說,仲裁由當事國就該案選任的仲裁員(而非法官)擔任,仲裁費用也由當事國承擔,且裁決作出後仲裁庭即告解散。但司法方式,如透過國際法院、國際海洋法法庭,由聯合國大會、《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大會選舉的法官(任期九年,可連選連任)審理案件,費用由相關機構而非案件當事國承擔(在相當程度上加強了公正性),且屬於常設性機構。
其二,波林強調位於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無非是想突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權威性”。但實際上常設仲裁法院既不“常設”也非“法院”,該機構唯二“常設”的崗位就是為仲裁服務的秘書處和一份仲裁員名單。
雖然常設仲裁法院的辦公地點和國際法院一樣位於海牙的和平宮,但該機構和聯合國沒有任何從屬關係,其作為平臺可為各類仲裁案件提供服務。簡言之,南海仲裁案仲裁庭選擇了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作為仲裁地點,本質上並沒有“加強”仲裁庭的“權威性”或其裁決的“合法性”,這與同樣在海牙和平宮辦公的國際法院以及位於漢堡的國際海洋法法庭作出的判決的性質是截然不同的。
第三,錯誤類比不同背景和性質的爭端。
波林在文章中用了一整個部分(篇幅實際上是全文四個部分中最長的)介紹了模里西斯與英國的查戈斯群島領土主權爭端的前因後果及2024年的最新進展,並提及了模里西斯訴英國的基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七的仲裁、聯合國大會的決議以及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
他試圖透過詳細介紹模里西斯“堅持不懈”以小博大,而沒有像菲律賓那樣“勝而輒止”,最終迫使英國回到妥協上來的成功例項,來勸菲律賓當局“重拾”南海仲裁的“勝利果實”並加以運用。
但事實上,模里西斯與英國的爭端同中菲爭端毫無可比性,將兩者等同或類比是對國際法治的極大的不尊重。
模里西斯與英國之間關於查戈斯群島領土主權的爭端,本質上是去殖民化時代的產物,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是英國在模里西斯獨立後仍將查戈斯群島租給美國作為軍事基地,從而造成查戈斯群島居民無法重歸故土。在別無他法的情況下,模里西斯透過訴諸法律的方式並在聯合國大會“維權”,其本身是符合國際法的正義之舉、正當之舉。

當地時間2024年10月3日,英國宣佈正式放棄位於印度洋一處群島查戈斯群島的主權,並將其歸還給模里西斯。不過雙方協議中還包括,英國未來至少99年內在島上設立軍事基地的權利。
而菲律賓自上世紀70年代初以來陸續非法侵佔中國南沙群島多個島礁,並在世紀之交透過坐灘軍艦非法佔據仁愛礁至今,其與中國的領土主權及衍生的海洋權利主張爭端,本質上源自菲律賓自身多項違反國際法的侵權行動。
菲律賓單方面提起仲裁也全然不顧《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透過友好磋商和談判”解決爭議的承諾,本質上屬於“惡意”挑起仲裁,更不用提其背後存在南海域外國家操弄的情況。簡言之,這兩起爭端毫無可比性,因而波林的舉例顯然缺乏信服力。
第四,波林作出的“菲律賓在聯大投票‘勝券在握’”的論斷,屬於用不科學統計得出的不可靠結論。
他首先指出聯合國大會決議的投票“向來不向大國服軟”,並列舉美國、英國和俄羅斯在聯合國大會決議投票中遭遇的“滑鐵盧”。鑑於波林意識到中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可能較其他大國要強,於是他試圖根據自己擔任主任的CSIS旗下“亞洲海事透明倡議”的“仲裁支援追蹤”(Arbitration
Support Tracker)的所謂統計資料來預判當菲律賓在聯合國大會提起事關南海的決議動議時,將得到多少支援票。
此外,波林還藉助美國國務院統計的聯合國大會投票中有多少國家基本同美國立場一致的情況,來預測菲律賓在得到美國支援的情況下會得到多少支援票。
不難發現,波林的方法論本身並不科學,且不說相關統計資料缺乏權威性,即便這些資料可靠,也完全不考慮聯合國大會的外交屬性而強行將某些西方國家的個別意見強加給其他聯合國會員國,這本身就不符合聯合國大會決議的初衷。
波林的觀點也讓人回想起2020年5月另一位美國學者喬納森·奧多姆(Jonathan G. Odom)在“法律事務”(Lawfare)部落格上發表的《在國際海洋法法庭保護基於規則的秩序》一文。
在那篇文章中,奧多姆曾鼓吹於當年6月召開的第30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大會上,各《公約》締約國(美國並非《公約》締約國)不要給參加競選的中國籍法官候選人段潔龍(時任中國駐匈牙利大使)投票。但事實是,在2020年8月24日的會議上,段潔龍在第一輪投票中就以147票高票當選國際海洋法法庭法官並任職至今(任期9年)。正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一投票結果是對奧多姆“高見”的巨大諷刺。
現如今波林再次拿投票做文章,且不說他預測的投票本身會不會出現,即便真搗鼓出這一投票,其結果恐怕也會向段潔龍法官參選時的情形那樣,與美國學者的“預測”截然相反。波林所謂的“馬尼拉的勝利程度會隨著每次投票而愈發擴大”的結論,恐怕最終也會成為奧多姆那樣的笑料。

2024年4月7日,美國人員從菲律賓的一架C-17A運輸機上卸下與“堤豐”武器系統相關的拖車式發射器。網路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波林在全文最後提到的一句話“美國應該準備好幫助煽動選票”,需要引起中國高度重視。
雖然波林全篇都以“客觀”的“第三方獨立學者”身份出現,但其文末終究暴露了寫作的真實目的,即借“好心勸說”菲律賓小馬科斯當局採取對中國的“外交戰”,實際上是鼓動美國政府在背後為菲律賓“造勢”,甚至建議特朗普新政府“直接下場”去為菲律賓“拉票”,其本質無非是用菲政府作為代理人來對抗中國,再借聯合國等國際平臺來兜售其“基於規則的秩序”等理論。
為此,中國相關部門特別應做好預案,在今年9月聯合國大會常會的開幕前做好充分準備,以防菲律賓勾連美國做出波林在其文章中“提議”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