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出門坐公交,突然發現公交站的奧運廣告牌換了,換成了公益廣告——
北京禁毒辦、北京團市委邀請您共同關注“防範青少年藥物濫用”。
???我當時就覺得有點不對勁。青少年嗑藥這麼嚴重了嗎?如果不是,國家是斷不會在受眾如此廣的公交廣告牌上宣傳呀!
不過,我當時匆匆忙忙的,也就沒有往深處想,直到昨天突然被一條新聞被刷屏——
東北14歲少年小聰在課堂上突然暈倒,被送到重症監護室,做了兩次血液迴圈,搶救47小時才救回來。

原來,小聰在課堂上服用了30多片卡馬西平!藥物中毒後,意識不清,並且伴隨著肺部感染、高乳酸血癥、血管舒張性休克、低鉀血性、肝功能異常等症狀。
小聰服用這些藥物,家長一點都不知情,更驚人的是,小聰說,學校裡還有好多同學在偷偷吃!
這些孩子為什麼要偷偷服用這些藥物?
據孩子們說,是緩解壓力,吃完了暈暈乎乎的,可以什麼都不用想了




。
看了這條新聞之後,我又搜尋了最近幾年青少年濫用藥物的相關報道,這才發現,為什麼青少年濫用藥物到了很嚴峻的局面——
偷偷服用藥物的十幾歲孩子很多,只是很多家長都不知道!

表面看是藥物濫用,本質是心理出現了問題
我查閱新聞才發現,其實這麼多年來,青少年濫用藥物的問題一直很常見!
只不過,這麼多年,孩子們濫用的藥物從止咳藥水、曲馬多、美沙芬到複方甘草片再,進化到現在的右美沙芬,卡馬西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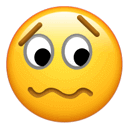
。

早在2007年, 我國第一家青少年成癮治療中心就成立於廣東武警醫院。
當時最早被列入管控的處方藥是止咳藥水,因為含“可待因”成份,被很多孩子濫用,被他們稱為“快樂水”、“神仙水”。
在當時,濫服止咳水的人群多為中專、中職類的低齡男生為主,農村鄉鎮的孩子居多。
很多人是在初中、中專時第一次濫用藥物,地點多在校園內或者周邊網咖等娛樂場所。
因為這個年齡的孩子,更容易存在慕強心理,很渴望得到群體認同,在同學或社會人員別有用心的慫恿下,知識有限的他們,不懂得濫用藥物的危害,在過量服用後,很容易成癮,最後精神恍惚,萎靡不振,甚至出現幻覺和被害妄想,不得不中斷學業。

甚至在濫用藥物成癮後,有些人開始轉向毒品。
2024年,我國對處方藥的管制越來越嚴格,但孩子們濫服藥物的現象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一種藥物被嚴格管制,孩子們就會去尋找下一種藥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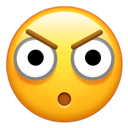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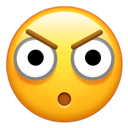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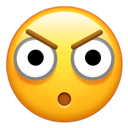
。
濫用藥物的青少年,也不再僅僅是中職學校的低齡男生了。
近些年,大城市中的中學生、 高中生這種現象也開始增加。怪不得北京都做到了公交廣告上!
並且不再只是男孩,女孩子也不少。
根據北京高新醫院戒毒科徐傑主任的統計資料,2017年,科室收治右美沙芬成癮的患者有50多人,2018年就翻了一倍,2021年已經突破400人!
而且,根據他的治療案例分析和追蹤,三分之二的病例都是故意濫用,一年後復吸率高達89%。
也就是說,一旦濫用藥物成癮,幾乎很難戒掉!
這也是國家在嚴厲管控這些藥物的原因,因為超劑量服用的危害真的是和毒品一樣啊。
如果說十幾年前,有相當大一部分孩子是在無知的情況下,被人慫恿和影響上癮,那麼現在的孩子則是明知其危害,也要超劑量服用。
十幾年前的那些孩子,一口氣喝掉好幾瓶止咳藥水,是為了追求超大劑量所帶來的欣快感。
而現在的孩子們服下10片,十幾片,甚至幾十片藥物,只是為了擺脫壓力,什麼都不用想。
查閱資料的過程中,我最不理解的是——
現在的孩子知識面很豐富,他們很清楚藥物的毒害和上癮危害性,但是,為什麼在明知危害的情況下,也要超劑量服用藥物呢?




甚至他們還會查詢、比較藥物對身體的危害成度,會去選擇相對傷害較小的一類!
《南風窗》報道,有一個14歲的女孩子蘭蘭長期服用右美多芬。曾擔任廣東青少年成癮治療中心主任6年的何日輝曾和這個女孩聊過,女孩說她知道止咳水有可待因成份會上癮,所以選擇了相對傷害較小的方案“右美沙芬”。
而另一個高一女孩默默,會在吃鹽酸美金剛(一種治療阿爾茨海默症的藥物)的同時,再吃一些保護胃的藥,因為這樣不會吐出來。
這都是啥邏輯???
是因為孩子們的壓力太大了。
很多精神類藥物,它們起作用的原理和毒品非常類似,會對大腦和神經進行藥物刺激,產生現實生活中無法擁有的快樂;

像蘭蘭說父母經常吵架,她的成績也不好,她很痛苦,但很多事也不知道跟誰說。蘭蘭說:我知道清醒以後這些問題都存在,什麼不會改變。但我更希望服藥以後,可以什麼都不用想。
而高一女生默默的最大壓力源同樣來自於父母,她父母天天在家吵架,父親常因為一點小事就吵起來,一吵架就摔東西。這些天天圍繞在她身邊的痛苦,她很難找到人訴說。
長期在這樣痛苦的環境下,前幾年,默默被確診為精神分裂,不得不休學進行治療。在休學的兩三年裡,無聊和痛苦幾乎就是她生活的全部。
偶然間,她在網上看到過有和她同樣疾病的人在服用右美沙芬。
也是那個時候,默默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od。所謂OD,是指英文overdose(過度服藥)。
默默找到了od群,她看到群裡很多人在分享od幾個小時後,人會有暈乎乎、飄飄然的感覺,那時的默默,由於病情非常痛苦,腦子裡會充滿“想死”的念頭,所以看到群裡有人分享od後的“興奮”和“幸福感”,對當時的默默來說,有著極大的誘惑力。
她也開始od之後,有了另一種途徑逃出現實的痛苦。
她說,右美沙芬很苦,但也比不上她心裡的苦。

孩子們不知道,濫用藥物沒有回頭路
我沉默的看著新聞,一種心痛的感覺襲來——
孩子們不知道,一旦開始濫用藥物,就很難再回頭了!
從超劑量服用藥物之後,就跨入了長期濫用藥物的門檻。一旦有了耐藥性之後,不可避免會加大劑量和成癮。
隨著而來的,將是伴隨一生的痛苦連鎖反應。
就過量服用精神類藥物的短期反應來看,孩子們過量服用精神類藥物,輕則頭暈、心慌,影響學習和生活;重則影響肝腎功能,損傷心肌,導致心悸、心電圖改變和心肌酶的異常升高。

甚至像新聞中的14歲的小聰一樣,危及生命。
長期的過量服用,則更加嚴重。
很多的精神類藥物都會產生藥物依賴,吃的時候感覺飄飄然,心情愉悅,但吃的時間長了,再停藥,就會情緒低落、抑鬱。
很多用藥的孩子,剛開始只吃幾片,後來越來越多,甚至一次超量吃十倍才能有效。

所以這些精神類藥物,也跟毒品一樣,讓孩子們很容易上癮,戒斷困難。
戒賭科徐主任所說,就算強制戒斷了,第二年百分之78%孩子還是會再次上癮。除非意志力非常堅定,否則孩子可能一輩子就毀在這些藥物上了。

除了對生活的毀滅性影響,精神類藥物的濫用,還會對孩子的身體產生破壞,比如不可逆的肝腎損傷;產生幻覺,甚至傷害孩子大腦等等。


那,這些孩子服用這些藥物,家長們知道嗎?
當然是不知道!
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
這些藥物成癮的孩子是這麼操作的:
-
購買之後直接撕掉包裝; -
把包裝扔在外面的垃圾筒裡,藏在家長髮現不了的地方。就算有家長髮現了,就說是囤的止咳藥,或者放在維生素盒子裡,家長根本不會注意到。 -
如果是像默默一樣,本身治療精神疾病就要服用各種藥物,更不容易被發現。
直到他們出現非常嚴重的症狀,需要馬上就醫,家長可能才會發現!

是什麼出了問題?
我國對這些“超劑量使用後可能成為毒品”的藥物,管制手段遠比一般國家嚴厲的多,但為啥這一現象這麼多年仍然存在呢?

一個禁了一個再找,孩子們在不斷去尋找下一種可替代的藥物。
這一切都指向整個社會背後的問題,這些青少年濫用藥物的背後,都是他們的心理和精神健康出了問題,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和痛苦。
我們普通人面對困難時,有三種解決途徑:
一是提高戰鬥力,勇闖難關;
二是降低預期,隨遇而安;
還有第三種,就是逃避。
能做到第一種的孩子,家長的鼓勵、陪伴,孩子自己的意志力和資質缺一不可。
第二種,如果家長幫不到孩子,那麼家長可以降低預期,接受和理解孩子的普通和平凡,這對已經處在崩潰邊緣的孩子,包容、理解和放鬆的環境無疑是給了他們一線生機,讓他們可以停下來,積攢夠能量,修復好信心之後再重新出發。
而處在第三種情況的孩子,往往無人訴說,無人理解,面對痛苦也根本無力解決。
又痛苦又看不到希望,如果在網際網路的滲透或者周圍一部分同學的影響之下,發現了藥物可以短暫讓自己解脫 ,獲得短暫的放鬆,從而一步步走向成癮。
像報道中默默那樣的孩子,用藥物來代替“想死”的痛苦,逃避無力解決的現實,實在是讓人痛心。
這也是我為什麼在上一篇《我們是最難的一屆父母,沒有之一》中提到,就算我們既不能給孩子攢資產,也沒太多錢投資他的教育,那至少保持家庭中溫馨和諧的家庭氛圍。
不要總是爭吵和冷戰,家人之間的陪伴、支援和樂觀向上,也足以保護好孩子的心靈,給孩子最大的支援和鼓勵。
這個時代,身體健康,心理健康,自食其力就已經是成功的教育了。
為什麼現在明明物質豐富,可孩子們卻如此痛苦,抑鬱高發?
我和朋友深入討論過這個問題,整個社會轉型和深度變革的時期,經濟下行,收入減少,失業增加,整體感受是痛苦的。
父母很痛苦,就很難去支援孩子。就連父母自己,都是需要社會支援和關愛的。
青少年的抑鬱,就是社會的某種“疾病”在最脆弱的這群人身上的爆發。
所以,我們大人,無論何時都要對現實有察覺,要自己保持樂觀、清醒和堅韌,才能給予孩子最大的支援,保護他們的身心,不讓他們墜入沉淵,成為社會轉型時期的那個“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