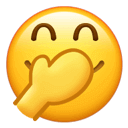*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蘇先生和賈女士夫婦曾在美國生活多年,2018年,他們帶著三個孩子回到國內,在深圳的國際學校就讀。今年,他們又面臨著回到美國的家庭轉折。趁著這個時機,他們做了一個有些大膽的決定:讓三個孩子休學一年,全家開啟一次以“二戰”為主題的遊學旅行。
蘇先生夫妻二人都是在大學本科以後出國留學的,如今三個孩子也分別輾轉在兩個國家求過學,這讓他們對中美兩國的教育體系,兩邊各自的優勢和侷限都有了深刻的感受。當越來越多的中產家庭被教育焦慮裹挾,他們希望找到一條真正適合自己孩子的成長路徑。於是,他們選擇按下暫停鍵,在自己的家庭內部,開展一次小小的教育實驗。
以下是他們的口述:
編輯|王海燕
賈女士:
我是在北京讀的本科,學法學,後來出國留學,畢業後在美國的一家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定居紐約。我家有三個孩子,大姐叫美美,今年14歲,妹妹叫麗麗,今年12歲,小兒子陽陽9歲,我們在美國一直生活到2018年。
出於對孩子的考慮,懷二女兒的時候,我們從曼哈頓搬去了紐約市以北開車大約半小時的西徹斯特縣(Westchester County)。
美國也有“學區房”的說法,美國住房每年會徵收房產稅,房產稅很大一部分就流向了學區內的公立學校。在學區內買房或租房,孩子都可以免費上學。一般房屋廣告的下面,都會寫上所屬學區,甚至還會加上專業機構評估出來的學區分數,這個分數會包含學術成績、家長評價、資金情況、學生文化背景等各種維度。
我們選擇的社群不大,但學區不錯。根據2023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這裡有6800人居住,60%以上就出生在美國,外國人群體中,亞裔佔到一半以上。社群裡的成年人,27%是本科學歷,碩士及以上學歷超過一半。
我的大女兒在這裡上學到小學二年級,二女兒上到學前班(kindergarten)。說實話,我和先生對美國的教育體系也不是很瞭解,都是邊看邊學。從學校和孩子的反饋來看,美國在孩子低幼階段的教育,更偏重讓孩子過得開心,學業並不是重點,孩子放學後,可能老師說,今天回去讀10分鐘的書,就算是作業了,沒有其他卷面作業。

到一二年級,學校很重視培養閱讀興趣,會有類似讀書筆記的東西。說讀書筆記都有點拔高了,就是給家長几個問題,讓孩子們讀完之後回答。一開始我也不理解,後來加入教師行業後,發現就是在鍛鍊孩子們的概括、分析和總結能力。至於數學作業,這個階段是完全沒有的,身邊的家長也不會在這個階段卷學習。
我先生到深圳上班時,我們考慮過,我和孩子繼續留在美國。但我們後來發現,從一個家庭的角度,這樣是不好的,我們也想讓孩子接觸真實的中國。有很多白人,在美國生活了一輩子,眼界狹小到坐井觀天,我們不希望孩子們成為這樣的人,所以我們決定回國。
蘇先生:
2018年決定回國,有我工作變動的原因,但也有對孩子的考慮。
美國的華裔二代經常會出現身份認同的問題,他們覺得自己是美國人,但美國人又把他們看作亞裔,最後,他們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我想,帶孩子們回國待一段時間,也許會對他們的身份認同更有幫助。
回國前,我在深圳考察了四所國際學校。有一所,我在宣講會上坐了五分鐘就走了,一開始,他們就講,如何超前學習兩年,會進行什麼考試。這所學校據說升學很好,在國內家長中挺火,但給我的感覺就好像,是一個“國際學校裡的衡水中學”。
最後為女兒選中的學校,我走進教學樓就知道是它了,走廊裡擺滿了小孩子做的手工,教室裡的佈局也很散漫,孩子們可以在地上隨便坐,有點接近她在美國上的學校。美式教育中,我比較認可的一點是,注意培養孩子的行為規範,不強調一二年級一定要學會什麼。
我相信,只要身心健康,建立了正確的價值觀,學會小學階段的知識,只是早晚問題。我的二女兒麗麗,小學三四年級還不太會乘法,甚至要掰著手指頭數,我當時其實是有點著急的,但我也告訴自己,她可能只是稍微慢一點。確實如此,她去年數學也考到了A。
我出生於一個教師家庭,爸媽都是中學教師。我本科在國內一所大學讀計算機專業,然後出國留學讀到博士,畢業後就一直在美國華爾街工作。在我的成長裡,中美教育都留下了痕跡。

坦白來說,美式教育並不完美。比如現在的美國學校裡,孩子們幾乎怎麼做都是對的,這跟家長有關,比如喜歡打電話投訴,導致老師不敢管孩子。這一方面,這當然會讓小孩子自信爆棚,但另一方面,也會導致自我認知不足,所以很多的美國中學生,閱讀和數學能力都嚴重落後,在這方面,中國教育也有自己的優點。
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教育,可能更符合我的預期,它尊重孩子的天性,也會給孩子適當的壓力。國內也一樣,我自己是80後,小時候讀書,9點就能上床睡覺,不像現在這樣緊張。所以現在中美教育都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的教育環境,對家長的要求更高了,你怎樣才能摸索出一條適合自己小孩的路?這其實挺難的。
在美國,雞娃也很普遍,尤其在東亞文化圈。現在的趨勢是,白人也開始卷,尤其是社會中上層,他們是另一種卷,可能練體育到七八點,再回家學習。所以現在的白人家長也感覺很累,他們叫微管理(micromanage),要深入去指導啟發孩子,給孩子打造完美簡歷。到處的社會都在變遷,可能美國的中產父母也意識到,如果孩子不努力,就過不上和自己一樣的生活了,這和鉅富階層是不一樣的。

賈女士:
在深圳,女兒讀的國際學校,走的是IB教育體系。在小學階段,IB課程的主要學習模式是,鼓勵孩子從興趣出發,進行探究式學習,每學期也沒有量化的成績單,而是老師的評語以及對孩子能力的評估。
到了中學階段,IB課程才開始考核學業水平。如果之前階段的能力,孩子都按部就班訓練了,這時候成績就不會特別差。而且孩子自己也會產生好勝心,想好好學習,想取得更好的成績。
除了各種各樣的體育班,我家的三個孩子,完全沒有在校外補過課。我們嘗試過各種運動,來找孩子們真正感興趣的東西。但我們並不想把體育當做升學途徑,因為選擇這條“捷徑”,你勢必需要付出比學習更多的努力。我們更希望孩子有健康的體魄,這也會帶動學習思維能力的提高。
現在我們家的三個孩子各有特點,姐姐勇於嘗試新鮮事物,她從5歲開始踢足球——她是真的很喜歡,哪怕到了深圳之後,找不到合適的女足隊,她就和男孩子一起踢,深圳夏天37度的高溫也不在話下。她現在是學校女足隊的隊長,還是每年的MVP。而且她從小學開始就是年級代表,上中學之後當上了學生會主席,每個月作為發起者組織各種學生活動。
妹妹就截然相反,是非常細膩敏感的孩子。她的運動能力也很強,但更喜歡個人運動,一直練習體操。我們也鼓勵她參加團隊活動,後來發現她並不享受,我們就反思,如果她性格內向,我們也應該尊重她,畢竟世界並不需要所有人都外向,對吧?
弟弟是個小暖男,同理心很強。我記得二年級的時候,給他讀了一本書,中間有一個情節是,小犀牛看到媽媽被動物販子槍殺,當時他痛哭流涕,這本書從此在我們家就被束之高閣,再也不敢拿出來。但他很聰明,學校的很多東西對他來說有些簡單,而且他很喜歡閱讀,經常會說一些超過他年齡範圍的話。

我們身邊也有專注“爬藤”的家長,很早就開始找升學顧問,計劃孩子的課程設定,安排孩子的課後活動。這些不一定是孩子喜歡的,但可能更容易出成績,會讓簡歷看起來很優秀。
但很多孩子即便進入了常青藤,也很痛苦。我先生看過一個數據,華裔上藤校的學生,只有75%左右是能畢業的。也就是說,你看到光鮮的例子背後,每四個,就有一個無法畢業的學生。這些孩子上大學後,失去了家長的託舉,甚至無法再往前走。
如果我們就是被這種越來越卷的浪潮裹挾著前行,那我們最終的出路又是什麼?
最近,大女兒即將升入高中,我先生再次工作調動,又到了我們需要回美國的時間,我先生說,要不大家一起休息一年,帶孩子們看看世界。
蘇先生:
我是個經常冒出稀奇古怪想法的人。我們很早就討論過回美國的事情,但某一天我就突然想到,從中國到美國,會有一個過渡的時間,可長可短,那何不乾脆長一點,做點不一樣的事。
當然,我也有私心。我知道小孩長大之後,就很難再和他們一起出去玩了,他們的學業會越來越繁重,也不一定想和家長一起出去。我也想趁這個機會,多跟他們相處。
我們最開始想得比較簡單,就是環球旅行,但從以前的經驗來看,小孩子對自然風光的興趣不大。這麼搞一年,對五個人都是折磨。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個新聞,法國會在諾曼底海灘舉行二戰期間諾曼底登陸的80週年慶典,邀請了各個國家的領導人。
我突然想到,2025年,距離二戰結束,也僅僅80年,為什麼人們對戰爭傷痛的記憶好像這麼快就抹去了?我和我的孩子,我們都成長在和平年代,對戰爭沒有切身的經歷和體驗。但去年我們決定休學時,俄羅斯和烏克蘭正在衝突中,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也戰火紛飛,世界的一些角落並不太平。
並且,我老家在湖南武岡,那裡有一個黃埔軍校的分校遺址。那個遺址上後來建了中學,我爸就在那當老師,我就在那裡度過童年。但我以前從來沒有意識到,我也算是在黃埔軍校里長大的。我愛人是衡陽人,1944年,這裡發生了衡陽保衛戰,是抗戰史上敵我雙方傷亡最多的一場戰役,極其慘烈。
從這個角度,我們家族的每一個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和二戰有著某種關聯。所以我就覺得,二戰或許是個不錯的主題。我們把這些背景講給孩子們,果然引起了他們的興趣。於是在六月的一次家庭會議後,就正式決定下來。二戰其實也是孩子感興趣的話題,他們之前也讀了不少有關的書籍。

賈女士:
最開始我先生提出全家gapyear的時候,我其實不太能接受。
這個點子當然很好,但我有很多憂慮。休學一年,會打斷孩子們的節奏,他們在家感到無聊怎麼辦?我也不知道如何規劃這一年,擔心操作不當或者方向錯誤,就耽誤了孩子。本質上,這相當於學校一年的教學任務,全落在了我們身上。
最終,我們花了幾個月,一次次散步,一次次探討,才讓整個想法真正成型,可以落地。我們決定把它做成一個專案制學習,用一年,完成主題遊學。由孩子們來做功課,做路線規劃,我和先生只負責機票和住宿。我們還討論了,如何呈現專案結果?
我們選擇了影片。因為孩子們經常在YouTube上看那些有名的影片博主,說也想做影片博主。那這次剛好就是一個機會,讓他們可以做影片,親自體驗這個事情的難度如何。我們建立了一個影片號,叫做《ZSU一家五口遊學足跡》,她們說,希望透過這個分享她們的發現和反思,也激勵其他同齡人珍視歷史的價值,共同努力實現一個更和平和公正的世界。我們很支援她們這種想法,雖然這個影片看的人估計不多,但至少她們想對這個世界做出一點影響和貢獻,哪怕很微小。
正式出發前的一個月,孩子們先在深圳海上世界做了一次“預演”,學習怎麼寫稿子、拍哪些景點、如何運鏡、怎麼剪輯。當姐姐匯出第一個影片的時候,我和先生都很詫異,問她是怎麼學會這些的,她告訴我們,在學校的學生會活動影片都是她剪的。

我們的第一站是俄羅斯,後來是歐洲部分,歐洲去了50天,包括7個國家,25個城市。後來我們還去了日本,最後的一站就是美國。到了當地,我和先生會發動朋友關係,給孩子們聯絡經歷過二戰的當地人,讓孩子們去採訪。
在俄羅斯,我聯絡到同事的婆婆,她的外公和爺爺都曾經參加過二戰,留下了不少資料。在法國,我們聯絡了孩子同學的爺爺,他所在的城市是納粹簽署投降書的地方。這些採訪物件並不好找,幸運的是,身邊的朋友、同學和家長都非常支援我們的專案,尤其是我們的朋友Sherry、Lannie和Jesse在各方面給予了我們極大的幫助,我們對此深表感激。
我們還去了國內的東北,湖南、上海、南京等等地方。因為我是衡陽人,說起來不怕笑話,我走到忠烈祠的時候,眼淚直接就流下來了。孩子們不明白為什麼,我告訴他們,你看,這裡本應刻上所有人的名字,但是太多了,寫不下了,只能用部隊番號。
在歐洲,我們去過一些美軍公墓,修得很氣派,去盧森堡看到了德軍的公墓,但因為是民間修建的,顯得比較寒酸,四個人共用一個墓碑,但這些都不及忠烈祠來得慘烈。
孩子們在國際學校,並沒有專門學習抗日戰爭有關的知識,只是隱約知道有這樣一個歷史事件。妹妹還問過我,為什麼她的一個韓國朋友很討厭日本同學?她們對侵略戰爭的理解僅限於課本,這和我們在現場的體驗是完全不同的。

南嶽衡山忠烈祠
蘇先生:
我能感受到,孩子們已經產生了很有價值的感悟,尤其是大女兒。在歐洲,我們和交戰雙方國家的當地人聊,他們每個人看待歷史的角度都是不一樣的。我在旅途問過大女兒,你覺得歷史是什麼?她對我說,她覺得事情本身是歷史,還有就是你如何去看待這個歷史,她自己提出來了角度(perspective)這個詞。
我們後來也去了日本,去了廣島的原子彈爆炸紀念館。走出來之後,女兒對我說,她覺得這個博物館做得不好,因為它只提到自己的悲慘,卻隻字不提為什麼會導致這個結果,和德國的博物館完全不一樣。她也明白日本的普通人也是戰爭的受害者,他們沒有能力阻止戰爭。我覺得她這個年紀能想到這些,已經非常好了。

我們在歐洲國家也看到了一些很好的歷史教育。我們去諾曼底海灘逛了幾天,那其實是一片很漂亮的海灘,但會突然看到德軍曾經修建的地堡,很厚的混凝土,大炮直直對著海灘,你可以身臨其境地想象到當時盟軍登陸面對炮火的情景。
我還記得,有一天,下著小雨,我們打著傘,看到一個巴士,老師帶著孩子們走到海灘上,淋著雨,孩子們湊成一圈圍在老師身邊,聽老師講諾曼底登陸的故事。在每個博物館,我也幾乎都能看到有成人團跟著講解學習。

賈女士:
我前面提到,在遊學的過程中,孩子們會用影片來呈現成果。最開始在俄羅斯,臺詞和稿件這些前期工作都是姐姐來做的,弟弟妹妹負責出鏡和講解。但去了歐洲之後,她沒辦法一個人完成這麼大的資訊量,於是三個孩子分工。
姐姐成了組長,他們現在會使用共享辦公軟體,三個人分別做成不同的資料夾,線上編輯整理資料。我先生說,他們有時候做事比他招的大學畢業生還有條理。這些都不是從課堂能夠學來的。
在整個旅行中,孩子都在成長。比如姐姐能作為一個“總導演”獨當一面,遇到不合理的規定,敢與成年人據理力爭,妹妹在我們的鼓勵下勇敢站在鏡頭面前,弟弟也能迅速掌握臺詞,侃侃而談。要說遺憾,可能是三個孩子都對藝術博物館不感興趣,甚至到了盧浮宮,他們都不想進去。後來我和先生也反思,他們不喜歡的事,我們何必硬要他們去做?

旅途中,孩子們在民宿中繼續做研究
在陪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我也改變了職業方向。妹妹出生後,我全職在家帶孩子,後來本來打算迴歸工作,結果又被弟弟出生打斷。
後來我發現,我花了很多精力研究教育,參加學校的資訊分享會,還申請了學校幼兒園階段的代課老師,我對這個行業很感興趣。於是,聽從校長的建議,我考了一個美國小學老師資格證。2020年開始,我開始在一所國際學校做老師。
以前我做法律,更多是跟文字和數字打交道,但有了孩子後,我真的不太喜歡這一行了。我現在覺得,和孩子在一起帶來的快樂才是無窮的。
回想我小時候,父母沒有給過我太大的壓力,一路順利成長。但是當我們家孩子問我,媽媽你小時候的理想是什麼?我突然發現,我那時候好像沒有什麼理想。我那時候學習的目的是什麼呢?好像也不知道。
那時候大家都對我說,要考上大學。可能直到高考後報專業的時候,我才去思考我喜歡什麼,我擅長什麼。所以我現在希望,我的孩子能儘早地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思考自己想做什麼。他們現在想的,不一定就是他們之後想做的事,但在樹立人生觀價值觀過程中,這很重要。
蘇先生:
有朋友問過我,你們的影片號,為什麼要用“遊學”這個詞,國內的機構都快用爛了。但這個詞確實最能概括我們家的狀態,一邊遊一邊學,大家一起度過一些時間。而且這大半年相處下來,我們的家庭關係也好了很多,我和愛人也有更多的時間,作為家長去反思自己的行為。
旅行期間我們經常會開“家庭會議”,我會問孩子們對我們有什麼意見。他們會說,媽媽容易急躁,急起來說話聲音都高了,而我容易抱怨。這確實是我們的缺點,但平時注意不到,或者夫妻之間說也起不到效果,反而孩子能夠幫助我們成長。
我並不指望孩子們學習一年,就脫胎換骨了。我更想給他們種下一顆種子,讓全家在一個輕鬆開放的情景下,去探索和討論一些問題。教育是細水長流的東西,並不會立竿見影,但做過的事情,一定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不經意地顯露出來。
我對孩子們現在的狀態還挺滿意的,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小問題,但他們很善良、純真、樂於助人,有主見有想法,不盲從於我們、也不盲從於老師。
不可否認,我們家在孩子身上投入了很多金錢和精力,但我告訴自己,要把教育當作一種消費,而不是投資。投資意味著執著於回報,而消費則是一種選擇。而對於孩子,我願意為他們付出,因為這不僅是我的責任,更是出於對他們的愛。
這次旅行中,他們用AI蒐集了很多資料,我女兒甚至會告訴我,哪種大模型的幻覺更嚴重。在這樣一個AI時代,他們要學習各種東西,簡直太方便了。所以對他們來說,終身學習的能力或許是第一位的。我希望他們對這個世界保持好奇心和同理心。
他們總有一天會比我們更瞭解這樣的世界。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詳細崗位要求點選跳轉:《三聯生活週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