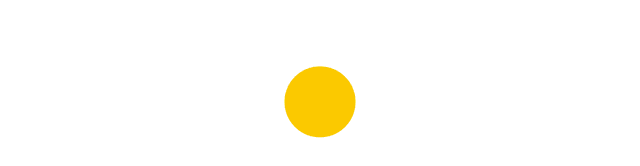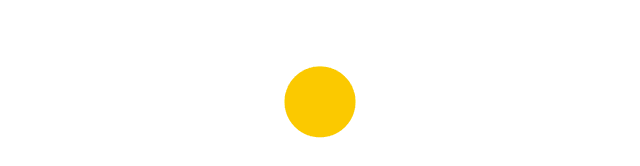他是學者,是《時代建築》雜誌的專欄主持人;
他是教育家,是在同濟大學注重學生思考而堅持不直接改圖的教授;
他是事務所創始人,是帶領致正建築以更開闊的視野和更多樣的方式同中國社會變遷互動的領導者;
他關注建築本身,堅持關注建築的空間和使用的問題;
他關注社會問題,關心當下建築師對社會的作用與多重角色的塑造;
他勤於思考設計,發出建築不僅要有建造層面更要有社會性思考的警示;
他就是我們本期採訪的建築師——張斌老師。
採訪人 | 李智 王梓童
編輯 | 靜儀
本期人物
張斌

1992年和1995年分別獲得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建築學學士和碩士學位
1995年至2002年期間在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任教
1999年至2000年期間入選中法文化交流專案《150位中國建築師在法國》赴法國巴黎Paris-Villemin建築學院進修,並在Architecture Studio事務所擔任訪問建築師
2001年起擔任《時代建築》雜誌專欄主持人
2002年創立致正建築工作室,並擔任主持建築師
2004年起受邀出任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客座評委
深圳雙年展—城市共生
A:您怎麼理解今年深雙城市共生的主題?
Z:今年“城市共生”主要關注城中村的議題。中國北上廣深這樣的特大城市有一個共性——很強的人口匯入性。深圳的城中村是承接了大量年輕人和外來服務人群的人口匯入區。在資源的佔有上,外來人口和本地人不在同一個平臺上,外來人會需要很多低成本的空間。劉曉都他們把城中村話題落在城市共生上實質是在應對中國特大一線城市的問題。而深圳對於這個問題的體現,就是城中村。

A:您理解的這個城市是市民的,遊客的,還是設計師的城市?UABB今年的展對南頭古鎮原住民的意義在哪裡?
Z:我只看了鹽田的分展場,間接地瞭解了主展場。我覺得不能簡單地判斷它的本意和最終狀態。雙年展有很強的政府推動和文化營銷背景,避免不了一些常見的問題,所以基本上採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處理——比如必須集中資源來做。由此產生了雙年展到底是為市民參與提供機會,還是為設計師展現理念提供機會的悖論。這要看個人如何理解。面對悖論要採取行動,但程度還看機緣。劉曉都可以義不容辭地去碰這個話題,這代表一種專業人士的態度。
A:您覺得策展人選擇練塘鎮政府專案參展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Z:馮路老師邀請我們參加他的板塊,請了國內的幾位一線的理論和評論專家來探討一個地方性的話題。練塘鎮政府專案早在10年的時候就建成了。他者南方的主題是在探討識別性——形式識別性和地方認同性。馮老師對這些房子到底有沒有地方性持疑問態度,他不認為當代建築還能創造某種真正的地方性。我把這個理解為“在地”而不是“地方”。“地方”最後又會講到很多像形式,符號,記憶的話題, “在地”卻不是一個時間維度上向從前看的話題,而是一個關於當下和未來的話題。我們在大梅沙做的建築也是一種在地,在於如何為這個地方的未來做出一點貢獻。


練塘鎮政府專案
A:您做過的工人新村研究是屬於上海的一種保障住房形式,和深圳的城中村相比較,是不是本質上一樣,只是不同地域的產物?
Z:對,本質都是城市的服務人群聚集區。城中村的原住民透過城中村擁有的物業早變得很富有,資源佔有並不公平。深圳的張宇星老師一直在探討城中村如何公共化——希望這些得益者能夠釋放一些利益。而上海的老工人新村沒那麼大矛盾,原住民也非得益者。因為上海的老工房不成套,在我們中國的產權改革當中不能成為一個獨立意義上的產權而只有一個可以繼承也可以交易的使用權。這導致我們研究的老工人新村裡面基本上一半外來人口,一半原住民,原住民也不是富有的那批。深圳有不一樣的形成原因。我們想在這樣一個表面上看起來髒亂差的社群環境探討空間怎麼運作。
關於專案和設計理念
A:您在分展上做了3號和8號分館的改造,想傳達什麼想法?它與城市共生主題又怎樣聯絡?
Z:我們鹽田的分展場是劉珩老師策劃的。大梅沙村旅遊區在深圳的一個偏角,沒有大的資源爭奪和空間爭奪,基本沒有 “高密度自發建造”現象,安靜地提供大梅沙旅遊景區服務酒店工作人員和部分原住民的生活。劉珩策劃的主題“村市(是)廚房”是在討論地方公共性重塑的問題。廚房的字面意思涉及到食物和共享,深層意思是把廚房比作公共的一個媒介。我們分到的這兩棟房子,一棟比較早,是七十年代的客家樓,另一棟是八十年代的。值得期待的是展會後這些村舍能可能發生的變化,這很難探討,需要長期觀察。
我作為建築師介入小小的空間,所能做的是在空間結構裡探討,引入“日常”和“事件”的並置。我們在這兩個地方創造了一點和日常不同的空間,有些是室內的,有些結合庭院屋頂及空間平臺,但都可以容納不同於日常生活的事情發生。我們還做了日常空間的整理,比如展會之間為藝術家駐場提供便利,展會後作為日常居家的狀態。我們希望兩個空間型別的並置可以為短期和長期的事情提供媒介。這個角度的切入給我們帶來平等的態度去看這個城中村的歷史,形成,現狀,族群,未來和以後新的外來力量,看他們在這個空間可能發生什麼。我們不太追求視覺衝擊力,而是追求如何探討兩種空間型別並置和矛盾的狀態。
這是中國當代城市發展的一個縮影,要在矛盾狀態中找到平衡——空間的改造會持續較長時間,但其中容納的事情與活動以及狀態在流變,存在著張力。穩定美好的空間缺乏彈性,混合並置的空間在流變中能容納更多利益糾葛。我覺得社會意義上的空間問題更多來自力量的妥協和共存,這是我們在小尺度空間中的回答。


上:八號館設計; 下:三號館設計;
A:日常空間,事件空間會和形式語言有對應嗎?
Z:並不是這樣。形式方面我們不追求新奇,不新增新材料,我們用的都是磚石木瓦等常見材料。我們希望用完全熟悉的材料卻形成有些陌生感的結果。


上:八號館內部;下:三號館鳥瞰;
A:您的兩個作品建在俞挺老師的作品旁邊。您怎麼評價這兩組在形式語言上完全不同的建築?
Z:我覺得最後的結果不同是由於介入方式的不同。我不關心這個房子最終的模樣,但我希望以專業的方式協調和參與這個過程。我關心空間和使用的問題,同時希望讓我們營造的空間起到一些積極作用。
俞老師一直強調農村和城中村的問題實質上是城市的投射,他更關心這兩個房子經過自己努力所形成的一種理想狀態。這要比單個去評價某個房子的好壞更重要。我不認為展場的改造是在檢驗建築師的終極形式能力,它更像一個當代藝術的操作,一個觀念和所在地資源的整合。在這當中,作為建築師應當有所追求,只是得放棄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們做的創造是為空間結構並置貢獻了一種最大可能性,使這個空間可以創造多樣的狀態。
A: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您釋出嬰戲屋的照片中,俞老師的房子顏色比較暗。而俞老師在釋出他的作品時,照片中房子的顏色變得非常絢麗。您怎麼看待傳播這件事情?
Z:現在是全數字時代,所有的影像都是有強烈的工業加工痕跡的。工業加工是一種媒介力量。建築師負責前半段建造,媒體負責後半段公共領域的傳播,二者永遠會結合在一起。
兩組照片算是同一位攝影師應對不同客戶需求所做的不同回答。我想更多去表達建造,希望它扔在這個城中村裡面會被淹沒。俞老師覺得色彩很重要,他們想做出一個摒棄掉所有具體環境的抽象層面上的作品。
這是對網路時代傳播方式的不同理解。建築師永遠要和攝影師打交道,和照片打交道,甚至於對於中國建築師來說由於現場無法把控,作品的最大傳播渠道是透過照片,建築師永遠要去面對攝影師的再創作。建築攝影領域的全數字化是比較晚出現的,但是在廣告時裝領域較早就普及了。我個人比較喜歡質感來自於直接的光學捕捉,而不完全依靠後期,具體還要看房子本身,不好一概而論。
A:您做過很多專案,有沒有一以貫之的核心概念或者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Z:其實一個作品最後如何表達更為關鍵。從國際經驗來說傳播得較好的事務所都有一種影像傳播意義上的識別性,這些作品往往影像意義上的識別性要大於現場的識別性。
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彼得卒姆託,他對於瑞士地方文化在環境當中的建造話題的探討,主要是靠影像傳播。因為材料質感構造透過影像傳播的可理解力要大一些。現場更多要去感受一些風土人文,而這些東西其實在影像層面上易被忽略掉。中國學生無非是看到他的精良的建造而並不關心房子在真實的社會環境當中如何運作。又比如SANNA是扁平化影像傳播的代表。它勝在對於當代文化和藝術以及日本社會的貢獻。我所關心的是傳播的差異性,這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定會存在的問題。
我並不太關心向大眾宣揚我的一以貫之的想法,因此我們的很多作品沒有固定的影像意義上的風格。當然,建築師不強調風格的做法逐漸變成某種主流——用研究型的方法工作,然後不設定特定的風格去介入某種具體的問題。
當然也有一些團隊比如OMA,不完全依靠單一的影像識別性來工作,而是一種工作方式的識別性以及它切入點的識別性,這一點也是我認同他們的地方。
我一直貫徹的是對空間和使用的思考。我們工作室剛成立時做的同濟C樓就是這樣的。C樓建成是04年,有很多人只關心它的材料和建造。我認為建築一定得有建造層面的思考,但還得有社會性上的一些思考。還有一點關於場所的問題——建築吸收環境的特徵,同時透過建築把環境的特質強化出來或者再定義這個環境。建築和場所的關係也是其社會性的一部分。這兩塊東西都可以跟建築的空間和使用一起探討。
我也會關心建築學話題在中國當代特殊性的回應,比如如何來認識中國當代條件下建築師能幹什麼?我們如何參與整個社會的運作?這個是我們現在更關心的——塑造建築師的多重角色,並不只是關注於狹義層面上的建築或者單純的物質建造。

同濟大學C樓
關於教育思考和職業經歷
A:您是六零後,您這一代建築師的教育環境是怎樣的?您如何回看大學求學的經歷?
Z:我87年就讀於同濟建築系,92年本科畢業念碩士後留校。我們讀書時是國外各種思潮引進最洶湧的時候。我們那一代人雖然很多是理科,但對於文科也有很多涉獵,課業負擔並不重。
80年代末的本科,很多東西老師是和學生一起學的。我跟著盧濟威老師學城市設計時經歷了盧老師建立自己的城市設計體系的過程,老師同學生一起面對未知的狀態。而現在整個大學學院的師承體系早已清楚。另外,我們結束教育後會面對特別直接的社會需求,92年之後的研究生宿舍像交易所般燈火通明,經常有人拿著錢來要圖。讀書時做的專案可能會落成。章明老師研究生階段就做完了二三十萬平方米的義烏小商品市場一期。而現在行業的體系化比較成熟,會帶來比較強的競爭狀態。我們當時是在嗆水中學游泳,在試錯中成長。
A:您後來留教任教的教學經歷,對您作為建築師的定位有什麼影響?
Z:我參與教學時為自己設定了一條紅線,不為同學改圖。我更關心思考層面的事情,交流時我永遠只會提出問題而非具體如何做。直到現在上實驗班的課,我們的教學像一種看專家門診的方式,一個老師對六七個學生,一對一或合在一起小組討論。
我們的工作團隊不是這種模式。一個專案由我到主管到專案建築師再到助理建築師的設定中逐層傳遞,我們共享價值層面或工作流程上的判斷。到具體每一個專案,專案越重要我個人的參與度會越高。一般團隊針對某個問題會給出多種答案由我來選擇,但是我們不太會採用完全開放的合作方式,這不太適合中國的職業環境——往往時間很緊任務很重,也沒有大的團隊。我們做不到讓每個小組去巨量討論,資源是不允許的。
我們需要很快速地直達設計訴求。工作團隊分層級,這個層級像是我手的一個延伸。工作中我們團隊的討論方式和教學有點像,是一種刨根問底的方式,不斷把淺層的東西和深層東西一起討論。這可能是我個人跟團隊之間的最大依託。
A:您在30歲時思考的建築學問題,對今天的實踐也一直有影響嗎?
Z:30歲之前並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麼,這也導致了我在99年停下工作去了巴黎。雖然我對教學有興趣,但我並不把教學作為我工作的一個特別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同濟教書時,有的老師會建立一些小的教學體系,從而調整體系和實踐的關係。我並不是,我自己的研究也還沒有完全和實踐直接掛鉤起來。對我來說有意義的是觀念或知識層面的探討,而不是實踐上的教學。但我們的田林新村研究也嘗試了延續到實驗班的教學,我們正在編這個專輯。
給青年建築師的建議
A:現在很多建築系的學生選擇留學深造,您對他們的求學或者職業發展有什麼建議?
Z:這個選擇不錯。現在年輕人有很好的機會去全世界最好的建築學院裡深造。在我們的時代不能想象有進入哈佛或MIT的機會。現在很多海外學校甚至50%以上是中國人,中國學生變成他們非常重要的一個群體——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歐洲米蘭理工的中國學生都超過50%。
我覺得年輕人海外留學重要的有兩點:一是如何選擇學校。美國的學校由於資源優勢可能更適合讀研究生,歐洲學校工學院體系和本科教學很強。二是最好能夠畢業後在當地展開一些職業工作,有利於學習與工作的轉換。
國內目前對頂尖建築學院畢業人才需求不大,更多人最終要進入大型商業機構設計機構或者大型國有設計院——這些機構的生產方式和所學東西不匹配,導致很多年輕人無法接受。我們這樣更關心設計思想的小事務所由於數量過少,在市場上無法佔據主流。而國外就算是大型商業公司,對於設計質量的訴求也和國內大公司不一樣。國內大公司大部分專案由於市場需求不得不快速進行,只有一些精品的專案做得比較有品質。而國際性大性商業機構基本上可以保證較多專案有品質,這對年輕人的職業成長更為有利。也有大量年輕人會因為找不到可以施展所學知識的地方而選擇創業,可是創業又是特別難的方向。
因此年輕人要有清醒的出國目的以及歸國志向。
A:這個年代的青年建築師面臨比老一輩嚴峻一些的生存環境,他們要努力平衡商業價值和人文思考。在這個過程中您對他們有什麼建議?
Z:我不太認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問題。但不同時代面對的基本問題都是一樣的。我們那時候面臨的嚴峻問題是剛工作的時候專案很多但質量不高。我前十年的工作就是在各種錯誤當中成長,沒有像樣的設計和好的機會。
不同時代的人面對的具體問題可能不一樣,但重點在如何適應這樣的環境並在其中較好的生存發展。你們的難處在於,這個行業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結構有些固化,在不復制前人設計取向、工作模式、成長軌跡的前提下如何突圍?在學科與專業都在快速變化的環境當中,如何去適應並抓住機會?這些可能是關鍵。
現在突圍的機會越來越多了。
版權宣告
版權歸作者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絡ArchiDogs或作者獲得授權
THE END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