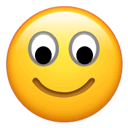【留美學子】第3615期
12年國際視角精選
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陳屹視線】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不想活了”
當我面對如此病人時

作者
楊軍,筆名楊伊德,安徽蕪湖人。安徽醫科大學神經藥理學博士,前安徽省醫學科學研究所正研究員,安徽省生物醫藥重點實驗室副主任。2000年赴美博士後留學,從事神經藥理學和動物行為神經影像學研究,後擔任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精神科學系助理教授。2007年進入美國西奈銀杉醫學中心(Cedars Sinai Medical Center),接受精神科住院醫生專業訓練。系美國精神神經委員會(ABPN)認證執業精神科醫生,現任美國洛杉磯郡精神衛生部主治醫生,阿罕布拉市心理精神諮詢中心主任。美國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我在美國當精神科醫生》,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洛城浮生》,安徽文藝出版社即將出版。


一
在精神科會診室
“我不想活了!”
在精神科會診時,這句看似沉重的主訴,並不罕見。它像是一把鈍刀,切入我們對“危險”的判斷,卻又往往缺乏清晰的邊界。是一次真正的求助,還是一種情緒表達?還是心理崩潰的前兆?
作為精神科醫生,我常會被其它科室醫生邀請評估病人是否“有自殺風險”。這些病人中,有些是常客,甚至是多次回訪的“老面孔”。但只要病人明確表露自殺的想法,醫院就必須邀請專科醫生啟動安全性評估。在美國的法律與醫療制度中,“自殺風險”是強制性住院的三大標準之一,醫護人員對安全性保持高度敏感。
然而,醫生面臨的難題在於:不是每一句“我不想活了”都意味著真正的自殺危險;也不是每一位有自殺主訴的病人,都需要強制性住院治療。
我們如何辨別真正的危險?當制度無法解決患者生存的問題時,醫生該如何在倫理與專業之間作出選擇?而我們是否真的有勇氣,在一個人人都想規避責任的系統中,承擔“安全處置病人”的責任?
二
這裡有個病人情緒不穩定
一天上午,我接到會診電話。急診科醫生聽上去語氣為難,“我這裡有個病人情緒不穩定,他不止一次流露自殺傾向,您能不能過來看看?”
這是一位四十來歲、身體肥胖、衣著凌亂的西裔男性病人。他坐在擔架床上,低頭擺弄著消毒紙巾,一邊擦拭指甲蓋,一邊小聲地喃喃:“我想死!”他的語氣單調冷淡,像在反覆背誦一句臺詞。
社工介紹說,這是一位高功能自閉症患者,長期生活在地區中心的寄養機構,接受24小時特殊照顧。地區中心是美國特有的醫療機構,專為自閉症、智障和癲癇病人提供診療服務。24小時寄養機構為每位病人配備專屬護理團隊。病人居住在政府資助的單人公寓,每天三班看護輪流上門,負責飲食、用藥、房間清潔、甚至洗衣。
從護理員的描述中我得知,眼前的病人生活能力尚可,但情緒極不穩定,時常在無預兆的情況下突然爆發自殺的負面言語。護理員不敢大意,每次都按照流程撥打911,將他送入急診室。
我問道:“他講這些話有多久了?”
“差不多三四年了吧。幾乎每三個月他就來一回急診室。”
我從電腦裡調出病人既往的治療紀錄,一看果然。他每年因“自殺”來急診四五次,但從未有過一次自殺行為。從前的精神科醫生會診都有相同結論:病人無自我傷害危險,建議病人出院,精神科門診定期隨訪。
我走進病房,坐下來與他開始交談。病人名叫荷西,他回話的方式極其刻板,每次回話前,他總要停頓五秒,像是在搜尋腦中的固定句式。
我問:“荷西,你說想自殺,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感覺不開心。”他回答。
“你打算怎麼做呢?”
“我想吃藥去死。”
“吃什麼藥?”
“我不知道。”
“你有藥嗎?”
“我沒有。”
“你想從哪裡拿到藥呢?”
“我不知道。”
從安全性評價角度上分析,這類回答屬於典型的“無計劃、無方法,無具體執行途徑”的自殺主訴,不構成實際自殺危險。
我繼續引導談話,試圖理解他為何不斷重複自殺言語。荷西雖然口頭表達能力有限,但在我幾次追問後,他話裡透露了一個重要資訊。
“我沒有朋友,每天只見到看護。爸媽太老了,他們也從不給我打電話。他們一年最多見我一次。”
我很明白,這是一種典型的注意力尋求行為。病人缺乏社交能力,不懂有效的社會互動,但他渴求關懷與回應。他可能發現:自殺的言語往往能得到更多人的重視,這也成了他尋求外界關注的有效手段。
評估之後,我按流程撰寫了完整的精神科會診報告。我的結論非常明確:病人雖有自殺主訴,但沒有執行的計劃和方法。他在地區中心有完善的社會支援,他返回原住處不會構成公共安全威脅或增加自我傷害的風險。
急診室醫生聽取我的會診意見,他頻頻點頭,但神色有些遲疑。
“我知道您說得對,”他說:“但我們的社工好像有些不放心。”
社工,這個在美國醫療系統中起到關鍵“中介”角色的群體,有時既是資源協調者,有時也不自覺成為了風險評估的次要把關者。當班社工堅持認為,病人有重複自殺想法,是“潛在危險”的訊號。
我用資料、臨床經驗、過往病史來解釋病人的“自殺主訴”,指出這不代表真正意義上的自殺風險。這位社工沉默許久,最後還是說:“我知道您是會診醫生,但我擔心一旦病人出院後,萬一真出事了怎麼辦?”
這句話我聽過太多次。
這是美國醫療系統中常見的“防禦性思維”——不敢對病人的真正需要來做決策,而是為了規避責任,整個機構的每一個環節都在儘可能“自保”。在這樣的機制下,真正專業的判斷被稀釋成“大家都同意最好”,即使那意味著更大的浪費和拖延。
“我建議病人出院,這代表我承擔對病人安全性的責任。”
“當然,急診室醫療團隊擁有最終決定權,但我提醒,病人不符合住院標準!”
我離開了急診室,腦中卻清楚地預見接下來的發展。
三
感到一種荒謬的無力
果然,幾天後我又收到急診室的會診請求。
“病人還在這裡,”當班醫生苦笑,“我們聯絡了好幾家精神病院,但沒有一家願意接受。您寫的那份評估,他們都看到了。”
我沒有幸災樂禍的感覺,反而感到一種荒謬的無力。病人夠不上精神病院入院標準,這意味他會被繼續留置在急診室觀察治療。
荷西舒服地住在急診室病房裡。輪班的醫生對他定時評估,護理員每日送餐,護士們監控生命體徵,社工們記錄他情緒波動。但是,沒人知道作這一切的實際意義?或者到底在“等”什麼?
從系統角度講,這樣的滯留是一種嚴重資源浪費。在急診室,每張床位都關乎生命救治的速度。荷西這樣一個沒有自殺風險的病人,卻滯留急診室整整七天。這不僅意味著其它急診病人需要等待,更是對醫護團隊士氣的持續消耗。
終於,在第八天,另一位精神科醫生受邀再次會診,他給出與我完全相同的結論。醫院別無選擇,將荷西送回原居所。為避免責任歸屬爭議,社工還特地通知地區中心主管和荷西家屬,要求他們進行安全性監護。
這一案例在醫院高層會議上被嚴肅提出,並進行“如何正確處理自殺主訴”的嚴肅討論。急診室主管坦言:“我們信任專科醫生的判斷,只是怕出事,怕媒體、怕官司。”
這句話點中了問題的核心。
在現代醫療體系中,“風險”已不再是一個臨床概念,而是一種法律焦慮的代名詞。 在這種焦慮之下,真正的判斷常常變得次要,取而代之的是——“安全性第一”。
而結果呢?是急診室七天無效的治療,一輪輪護理資源的耗費,一個被錯誤對待的病人,以及一群明知道不合理卻仍然沉默的醫護人員。
作為精神專科醫生,我們有時扮演著一個並不討喜的角色:指出現實的邊界,說出處置的理由。然後,就必須面對來自醫療團隊、甚至管理層的顧慮和質疑。我們不是不仁慈,而是希望在維護系統資源的基礎上,盡最大可能地去仁慈。
四
到另外一家醫院會診
此事過後不久,我被邀請去這家連鎖醫院的另一家醫院會診。會診醫院位於一個小城市,規模不大,只有兩百張床位,是一家非常普通的社群醫院。
病人是位六十歲的白人男性,患有長期精神分裂症,他的主要症狀為幻聽、妄想和躁動。他是個無家可歸者,生活在城市的街道上。這次,他因“有自殺想法”走進急診,幾天後被收治入院。
主管醫生告訴我:“病人已經穩定,也沒什麼行為問題,我們想讓他出院。但病人威脅醫護人員,說出院後就跳橋,所以我們需要您的專科會診意見。”
病人叫萊瑞,他在過去十多年中,多次入院治療,但沒有一次是被救護車送入急診室的。萊瑞每年冬天都會來急診室,主訴均為自殺,住院數日或數週後出院。
萊瑞衣著不整,髒兮兮的一張臉,他的鬚髮散發出異味。雖然護理人員已經安排他洗澡清潔,但成年累月遊蕩街頭,他身上那股怪味一時半會清除不掉。萊瑞思維略顯遲鈍紊亂,但基本能回答我的問題。
“你說要自殺,有什麼具體想法嗎?”
“如果你們讓我出院,我就從橋上跳下去。”萊瑞瞪我一眼。
“你之前跳過橋嗎?”
“沒有。”
“你打算什麼時候去?”
“我還沒決定。”
“你願意去庇護所嗎?”
“我不喜歡那些地方。髒、吵、不安全。”
“那你有沒有其他可以住的地方?”
“你們醫院不錯。”說這句話時,萊瑞笑了,他說話瘋癲,但掩不住臉上得意神情。
這不是“以死亡為目標”的主訴,而是一種“以死亡為工具”的表達。萊瑞知道“寒冷飢餓”不能打動人心,但“自殺”卻可以喚起系統的關注。
精神病人並不完全缺乏認知,他們能觀察、學習和總結——懂得某些表述的“效力”,哪些行為更能“獲得結果”。他們用自己掌握的方式,盡力爭取更多的生活資源。
我在會診報告中明確指出:病人雖有自殺主訴,但無具體計劃或執行能力。考慮其既往病史,判斷其自殺主訴含有次等動機。我建議病人出院。
主管醫生完全同意,他也看出自殺主訴下真實的心理動機。我的報告讓他鬆了口氣。
然而,問題再次出在社工環節。
醫院社工在交接會議上提出反對意見:“萊瑞沒有合適的去處。他拒絕去庇護所,也不配合去寄養機構的安排。如果我們強制把他趕出去,他真的自殺怎麼辦?”
我告訴社工:“你可以再做一次動員,看他是否願意接受庇護所的臨時安置。但從精神評估角度來看,他沒有住院必要。繼續住在普通內科病房,不僅無益,反而浪費醫院寶貴的治療資源。”
社工沉默了一下,“如果他在街頭自殺,那責任歸誰?”
這句話我們聽得太熟。它不是一個醫學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結構性難題被踢給醫院。這不是關心,而是對責任的恐懼。
我再次重申:“作為會診醫生,我給出我的專業判斷。你們出院流程和安置方案是系統性責任,不應由個別工作人員承擔處置的風險。”
我心理明白,這家社群醫院的醫護人員缺乏訓練,缺乏責任擔當。他們的不當處置給了萊瑞拒絕出院的膽氣。
五
一場鬧劇嗎
萊瑞從社工處得知“自己尚未有住處安排”,便壯膽拒絕配合醫院管理。他挑剔餐食,拒服藥物,有絲毫不如意處,便大聲辱罵,對某些護理人員表現言語威脅,並在房間內隨意大小便。
病房資源有限,萊瑞佔據著一個雙人大病房。主管醫生與他協商,問他是否願意搬去單人房,以騰出大病房給其它病人。
萊瑞斷然拒絕,“那是你們的問題。我就住這兒,誰也不能動我。”
醫療團隊感到挫敗。一些年輕護士不願接手他的看護,擔心被他肢體攻擊或言語辱罵。
我再次被邀請評估他的“行為風險”。
這已經不只是“要不要住院”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管理”。
我和醫院主管、護理長、值班保安一起到萊瑞的房間,清晰表明幾件事:
1. 醫院不是長期住宿機構;
2. 所有病人必須遵守基本規則;
3. 如果拒絕搬房且行為失控,我們將執行強制干預;
4. 必要時可依據5150規定進行藥物治療。
果不其然,病瑞開始高聲辱罵威脅“我要打死你們”,並抓起床頭櫃上的杯子朝門口砸去。在我的示意下,兩名保安進入病房,將其制服。護士給予他鎮靜藥物注射。幾分鐘後,萊瑞安靜下來,被強制搬離。
萊瑞換房後,他的問題依舊存在:他拒絕出院,拒絕安置。
管理層開始焦慮:萊瑞佔據床位已有兩個多月,他沒有保險,佔用病房,醫院不但沒有收入,而且要為他的治療護理吃住買單。護理團隊疲憊不堪,社工壓力山大,主管醫生每天都要向上彙報這個“懸而未決”的案子。
在這次安置討論中,我沒有談臨床治療,我只講資源、制度和醫療倫理。
“如果一個不合作、不接受任何安置的病人,能用一句‘自殺’就長期佔據床位,那你們未來會遇到更多類似病人,因為他們知道這家醫院根本不懂如何處置危機。”
醫院管理領導聽懂了,勒令社工主管聯絡庇護所,並制定轉診安排。最終,醫院安排救護車強制出院。萊瑞雖拒絕,但在保安的監控下,他未敢做出過激反抗。
萊瑞的案例給醫院帶來明顯的危機意識,最終他們對類似病例的治療安排形成一種安全性處置模式,全院醫護人員都被要求熟悉這一處置流程。
萊瑞沒有自殺,他甚至從頭至尾沒有顯示出任何自殺企圖。但他僅以口頭自殺要挾,便讓這家醫院管理人員疲於奔命了兩個多月,演出了一場鬧劇。
六
開啟正確的那扇門
兩個病人,兩種病情,一句相同的主訴——“我不想活了”。
從醫學角度來看,他們都不構成現實的自殺風險;從執行結果來看,他們造成醫療系統過度的防禦反應。醫療資源被嚴重浪費,醫護人員極度沮喪。
在現行美國醫療制度中,安全性的過度強調觸動了“責任恐懼”——醫生害怕錯放、社工害怕擔責、主管害怕媒體追責、系統害怕法律訴訟。於是,哪怕只有1%的機率,也會讓99%的資源被用來兜底。這種不對稱的代價結構,常常令整個系統疲憊不堪。而真正需要緊急干預的病人,反而被排在了“無法處置”的隊尾。
許多情況下,精神科醫生的角色往往被“技術化”,我們的評估建議並非最終決策。久而久之,精神科醫生成為了制度的顧問,而不再是臨床的主導。
這種錯位不僅影響醫療效率,也削弱了專業信任。它讓每一個決策都變成了妥協的結果,而非理性判斷的產物。
某些特別的病人利用醫療制度的缺陷,用“自殺“主訴作為通行證,來換取社會關注和衣食資源。這種制度適應是精神疾病與社會邊緣化交織的產物,當社會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後,他們反過來操控社會系統,找到了一種非語言的談判方式。
作為醫生,若只看到病人說了什麼,而不理解他們“為什麼這麼說”,那我們永遠無法真正判斷危險,也無法真正給出解決方案。
臨床上,到底由誰來定義“危險”?誰來決定一個人是否可以自由地離開醫院?誰來判斷“我不想活了”究竟意味著什麼?
自信的處置決定必須來自一個被信任的、有經驗的、在團隊中發揮核心判斷作用的醫生。
這才是精神科醫生在這個時代最大的價值:不是關掉所有的門,而是開啟正確的那一扇門。
延伸閱讀


近期發表
獨家| 她是搶救那段黑暗史的北大孤勇者
這裡的山光水色 讓我想歸隱出塵
美國公司CEO偷情後的代價
貝索斯再婚:一場現實的冷笑話
“隱藏”在城市中的世界
禁錮之戀| 一代大學生的情感史詩
從牛津到北大再回辛莊 黃土地的守望者
留下遺書·162天荒野徒步 華裔女孩挑戰極限
我在美國當精神科醫生
海外銷量百萬的華裔作家們
用100所大學鑄造的城市 魅力何在
名校之路-父母如何匹配兒女未來
訪談千位世界高人的她 收穫了什麼
留學安全須知·實用大全
名校之路-父母如何匹配兒女未來
訪談千位世界高人的她 收穫了什麼
留學安全須知·實用大全


【穿越訪談】世界華人系列
【行走如歌】100個國家·1000座城市
【王妃傳奇】皇冠越重 幸福感越輕
喜歡就點“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