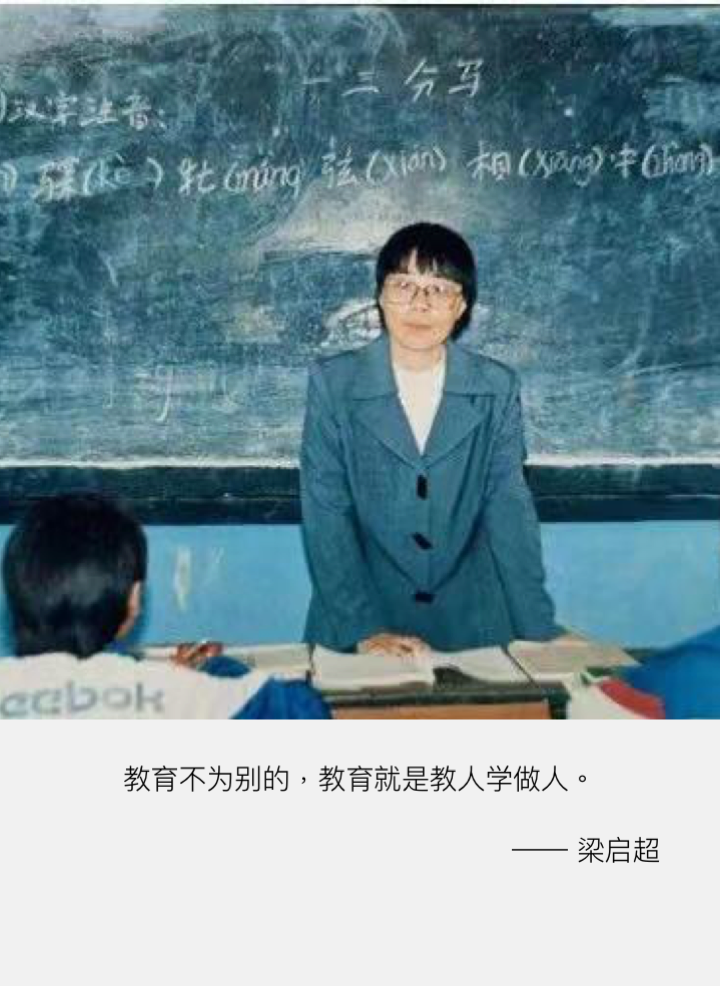【導讀】《山花爛漫時》喜獲第30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最佳導演獎”“最佳女主角”兩大獎項。《山花爛漫時》叫好又叫座,豆瓣上已有22萬人打出9.6的高分。本劇透過書寫張桂梅創辦華坪女高的過程,用開闊、溫和且節制的影像語言,打動了萬千觀眾,是當代主流文化的典範之作。
本文細緻討論了這部電視劇如何用影像語言復活了中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傳統。新中國成立時,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指導下,我們創作出了一大批極為優秀的電影作品。但後來,許多重要的創作原則和語法逐漸被逐利浪潮沖刷殆盡。在《山花爛漫時》中,我們能看見大量的“外景”“好天氣”,直接跳接革命樂觀主義現場,不再苦大仇深。我們還能看見鏡頭不再僅僅追逐明星、主角,即便張桂梅們離開了畫面,鏡頭還會在普通人或社會畫面上進行意味深長的停留,透過書寫群像,全面展開了劇中的人際關係、社會關係。我們還能看見張桂梅透過她的“行動”,串聯、帶動起了社會各階層,激活了所有人身上的社會主義性,“從一個人擴寫到無數人”。正因如此,從這部電視劇裡,我們收穫了無數感動,成為了當代主流文化的典範之作。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4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上要統戰天氣,下要統戰人民
《山花爛漫時》是我去年看過的最好的電視劇。人心荒蕪時代,此劇不僅重建信仰,而且用我們久違了的山河語法刻畫了信仰在一個整全社會的生長過程。電視劇取材於全國人民都知道的張桂梅事蹟:獻身中國赤貧地區的鄉村教育,憑信仰的力量把兩千多個大山裡的女孩送入高等教育的跑道,但張桂梅不是“燭光裡的媽媽”“最可愛的人”這類煽情形象,她是一個“通三統”人物。
張桂梅接受了全部的現代思想,會用紅歌鞭策學生,也會用一半的獎金給400多個姑娘買奶茶,為了讓從沒出過遠門的學生嘗一嘗“遠方的滋味”。這個人身上的張力相容了“黨的女兒”、浪漫主義詩歌以及部分的王朔。她信仰知識改變命運,信仰文化能使女子走出窮鄉僻壤,信仰共產主義,在辦學最困難時,張桂梅發現留下的教師中有六個黨員,於是組織他們重新宣誓,氣場直逼電視劇《潛伏》中餘則成宣誓入黨。她與學生互相成全的精氣神,既有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先鋒性,又有《死亡詩社》般的激情,同時還包含了最好意義上的保守主義。這是今年的影像新人。
這部劇最讓人振奮的,還不是對張桂梅的塑造。此劇天南地北讓無數觀眾虎軀一震,是因為它以失傳已久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語法重新建立了中國社會,雖然是在影像層面。
《山花爛漫時》用毛澤東詩詞的氣場統領全劇,也用毛主席開出的共和國氣候統領全劇。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電影迎來有史以來最好的銀幕天氣。《翠崗紅旗》(1951)開畫,山清水秀,勞動場面;《女籃五號》(1957)開畫,陽光燦爛,奔赴工作;《萬紫千紅總是春》(1959)開畫,陽光燦爛,各自出工;《李雙雙》(1962)開畫,山清水秀,集體出工;《女理髮師》(1962)開畫,陽光燦爛,準備上班。共和國早期電影,用絕對的好天氣來讚美新世界,也藉此和民國電影做出重大區隔,既告別靡靡之音,也告別黑燈瞎火。
這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天氣,源頭性地和蘇聯文藝、蘇聯電影相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藝創作法則,在蘇聯政治和文化最高層的強勢推動下,碩果累累。斯大林和高爾基組隊強調,藝術家要以辯證的唯物史觀武裝自己,用革命的社會主義把握未來,樂觀和朝氣因此構成當時文藝的主場特色,《新莫斯科》《前線來信》《清晨》就是代表作。這些影像中的天氣,明亮美好得無法用以往的形容詞來表達。天空、大地和空氣的這種肯定性抒情力量,被共和國早期電影接過來,我們的銀幕也大量使用正面的、歌頌的語法,既用好天氣表達一個嶄新的世界,也用這個新世界來鼓舞新人。
在這樣的美學組合裡,祖國山河成為人的形象,是“我見青山多嫵媚,青山見我也如是”的雙向奔赴。共和國的早期電影也就必然以白天和室外為主場,一直到《廬山戀》(1980),廬山有多美,我對你的愛就有多美。但“傷痕文藝”出場後,銀幕越來越把人物往房間裡趕。像《牧馬人》(1982),雖然主人公在抒情時還能說“祁連山你帶不走,大草原你帶不走”,但愛情已經需要一張床。到了吳天明的《人生》(1984),外部世界已經變成一個懲罰的空間。同期的《大橋下面》(1984)也一樣,外部空間的閒言碎語直接把男女主逼得不敢出門。外部世界如此危險,主人公只能在屋內握個小手,銀幕時空也再次向夜晚回落,“警察小偷妓女”重返銀幕,現代主義美學成為今日影像的主要語言。
《山花爛漫時》在這樣的語意環境裡出場。張桂梅騎著小電驢翻山越嶺挨家挨戶地把失學女孩帶回教室,生活的泥濘沒有降低電視劇的色調,張桂梅這個形象自帶的光亮,以及女高誓詞——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於群峰之巔俯視平庸的溝壑——攜帶的山河屬性,讓整部劇以天然的方式重返“正大仙容”的社會主義修辭法。其實《山花爛漫時》裡也有不少壞天氣戲和夜戲,開學就遇到大暴雨,一個學生都來不了,但這些暴雨不是賣慘,轉場直接跳接革命樂觀主義現場,就像燈火通明的教室,傳遞的是火種般的信念。所以,黑夜戲反而比白天戲更亮堂。而此劇做得最好的,是對信仰傳遞的刻畫,以及在刻畫中對中間鏡頭的徵用。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裡有一個經典的命題,就是需要儘量表現社會關係。表現社會關係,就需要有中間鏡頭。我們現在影視劇的鏡頭總是跟著明星走,明星到哪裡,鏡頭就到哪裡。所謂中間鏡頭,就是主演走了以後的銀幕時刻。《山花爛漫時》一個值得很多影像工作者學習的地方,就是場景中即便張桂梅們離開了畫面,鏡頭還會在普通人或社會畫面上進行意味深長的停留。如此,上到人民大會堂,下到販夫走卒,都有進入螢幕的權利和時刻,比如張桂梅和教育局長、縣長經常去吃滑肉的那家攤販,攤販的家庭狀況,包括廚師工作狀態都被我們看到。這種在新現實主義浪潮中被高舉但又很快被遺忘的鏡頭原則,在《山花爛漫時》中被有序地拿回。
細看《山花爛漫時》,它不僅表現了張桂梅和張桂梅的周邊,表現了群像,其中展開的人際關係、社會關係,更重建了影像層面的統合性整全社會。社會主義文藝作品其實一直鼓勵全景描寫,展現各行各業的聯動。所以,當年我們有很多尋人電影,無論是《五朵金花》還是《魔術師的奇遇》,發生在一個地點的一件小事,總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地召喚出社會大結構,所謂普遍聯絡。但這些年,尤其受現代主義的影響,這種包含社會各階級的作品明顯變少。《山花爛漫時》對這種普遍聯絡進行了漣漪式召喚,張桂梅這一人物也就不再是單體獨立,不是個體的好,而是周邊性的好,或者說,張桂梅的周邊都是“同類項”,不是對立面。比如,魏庭雲和姚小山的關係,他們既構成張桂梅的前史,也衍生為張桂梅的未來。雖然這兩個人物作為單體角色有敘事偏差,但他們統合在內部,彼此詮釋並保證對方的純潔性。他們在除夕確定關係時的場景,交織的多重話語就極有潛力,我們在裡面看到《柳堡的故事》,看到《早春二月》,看到《潛伏》,兩人的關係相容了《潛伏》餘則成和左藍、餘則成和晚秋、餘則成和翠萍的關係。他們補足了張桂梅個人情感的缺失,電視劇也由此完成對複數張桂梅的表現。
這種從一個人擴寫到無數人的方式,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常用手法,就像1955年的《董存瑞》,以國家英雄命名的電影,完全不是個人英雄主義敘事。影片最後,董存瑞犧牲,鏡頭沒有多作渲染,橫移過來,一個董存瑞倒下,千萬個董存瑞站起來。這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經典鏡頭表達,讓影片中的人物也好,走向也好,都帶上強烈的運動感。《山花爛漫時》完美復刻了這種鏡頭原理。
宋佳扮演的張桂梅,基本就像一個動詞活躍在文字中,她沒有休息的時刻,如同當年《今天我休息》(1959)中的人民警察馬天民,沒有休息日。作為動詞的張桂梅,串聯起社會各階層,也帶動了社會各階層,所有人身上的社會主義性,都獲得了啟用的可能,也在終極意義上,全國人民在活躍的聯動中,實現了“遍地英雄下夕煙”。由此,這部關於張桂梅的劇,不是個人英雄傳,不是個人史詩,她講的是,六億神州盡堯舜。《山花爛漫時》也因此和經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傑作《列寧在1918》(1939)一樣,我們在影像中看到的,不光是張桂梅辦學這件事,而是這件事牽動的社會形象。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這個戲裡基本沒有壞人,唯一有點壞的是有錢人。這麼多年來,我們影視劇裡的有錢人已經被資本洗白,不是情種,就是偶像,他們甚至在道德上也完勝窮人。而在《山花爛漫時》中,那些頭一天喝了酒答應給女高捐款的有錢人,一個個賴掉,這些人構成了劇中唯一的雖然稍顯粗糙的壞蛋。當然,這些壞蛋並不特別,他們賴賬的方式也不特別,但在這部沒有壞蛋的劇中,這些有錢壞蛋就顯得意味深長。很顯然,在這個上到人民代表、省委書記,下到賣豆花的阿姨,都同心同德的社會里,只有資本家對張桂梅的熱情無動於衷,或者說,只有資本家沒有被張桂梅啟蒙。有錢人置外於社會的情感系統,有錢人成為這個社會的“外人”。這是上世紀30年代左翼電影傳統裡的道德倫理法則,在一個有集體遠景的社會里,表現窮人的高貴和富人的無恥,或者說,表現當下中國社會的真實原理。
所以,用現實主義來定義《山花爛漫時》不夠準確,她對中國社會的把握需要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介面上去理解。劇集中常有一些超越現實的情節元件,包括縣長和教育局長為了幫張桂梅解決問題,開車到省委書記視察地獲得“最後一分鐘營救”的機會,但這個絕地反擊並不給人好萊塢感,就像《戰艦波將金號》最後的勝利,雖然和真實歷史完全相反,但觀眾接受這些,如同接受歷史的程序。這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題中之義:表現社會屬性和歷史箭頭。也因此,整個劇集的拍攝,鏡頭更注重角色的行為而不是表演,鏡頭裡的所有人物,一直在各忙各的,他們出畫就出畫,鏡頭很少跟拍窺視,重要角色離場就離場,我們在他們身後看到一整個忙碌的世界。
這種社會主義美學傳統,也是共和國早期電影的最大遺產。比如在《李雙雙》中,孫喜旺是一個思想落後、需要幫助的人,但不管怎麼樣,喜旺和李雙雙共享公共空間,共享花前月下、花好月圓的時刻;當雙雙最後幫助喜旺改正缺點後,他們不是在室內卿卿我我,而是讓兩個人在室外抒情,在大樹下面,光天化日之下,有群眾目睹。這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統戰能力和統合能力,這種明亮的、白天的、室外的社會主義性,就是上要統戰天氣,下要統戰人民的偉大魄力,我們在《山花爛漫時》中再次看到,因此熱淚盈眶。
編輯/Yudong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4年第6期,原題為《上要統戰天氣,下要統戰人民》。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訂閱服務熱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