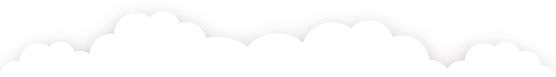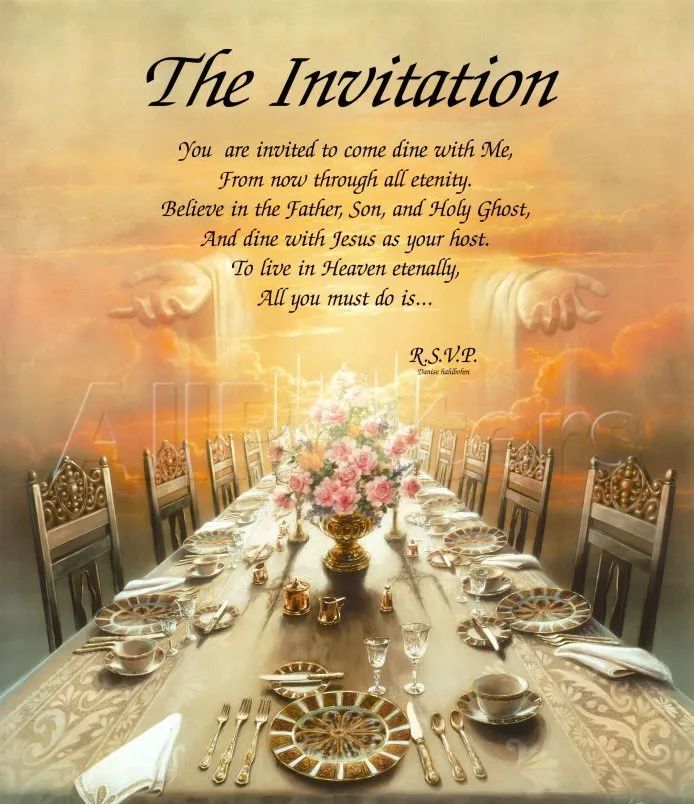在《宗教的陰霾依然籠罩著我們》這篇文章中我明確了以下觀點:一切宗教在唯物主義者眼中都是屑,而“亞伯拉罕一神教”——即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則是屑中之屑;沒有世俗化的佛教,比如舊社會藏傳佛教,也同樣很屑。
我專門寫過文章分析過這兩個問題:伊斯蘭教的現代化失敗以及為何成為了恐怖主義的溫床;佛教在中國的世俗化程序,以及沒有世俗化佛教的醜陋。今天再談一談基督教,就把三大教補齊了。
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很多老師、教授都是信基督教的,不過我遇到的所有老師都很有專業素養,從來沒有見到一個在課堂上宣傳自己信仰的(雖然我們私下都知道他們是虔誠的教徒)。不過在各學校舉辦的其他講座和交流會上,有些老師就控制不住自己加點“私貨”了,“私貨”最多的還都是政治性的東西,會陰陽怪氣一下“體制”,還有一次我還真遇到一個傳教的。
那次講座的主題本來是微軟併購諾基亞——當時全世界最火的話題甚至沒有之一,是一個純商科知識的講座,正好跟我專業契合,我就去聽了聽。結果這老師講到一半就是夾帶私貨,從跨國併購講到基督教的傳播,然後就講為什麼基督教是“歷史上最成功的企業擴張案例”。

他有一句話忽然啟發了我:“耶穌出生在以色列地區的一個猶太人聚居區……”我就產生了疑問,他出生在猶太人社群,基督教又是脫胎於猶太教,那耶穌按道理就是猶太人啊,之前怎麼從來沒聽人這麼說過麼?
於是這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在提問環節就問這位老師“耶穌是猶太人嗎?”這老師一副匪夷所思的表情,他說:耶穌是神,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他不屬於什麼民族或種族,彌賽亞是全人類的彌賽亞。
然後我就想問一句,那耶穌也可以是黑人咯?但是我當時畢竟是一個還在讀書的學生,沒有現在這麼無法無天,覺得這個問題攻擊性太強了,轉而就問“這麼說耶穌也可以是中國人?”,老師的回答是“我說了,基督是沒有民族、沒有人種甚至是沒有形象的,他在美國可以有美國人的形象,在中國可以有中國人的形象。”
其實這位老師雖然在講座上夾私貨傳教,但是態度真的挺好的,我如果再糾纏下去就顯得我沒素質了,其當他說“在中國有中國人的形象”時,我特別想拿手機搜一張洪秀全的照片——在中國耶穌一定是這個樣子啦,親兄弟嘛!

事後我查資料還發現了,羅馬人在釘死耶穌的十字架上,旁邊會寫犯人的姓名、民族和罪行,寫的內容就是“猶太人耶穌”。
後來我在北京工作,有次去北師大找朋友玩,他帶我順道聽了一次講座,是香港中文大學研究中東史的學者,主要講的是中東地緣政治。我聽了他的講座,忽然又想起了幾年前那個問題,這個老師不是傳教的,於是在講座的提問環節又問了一遍。
這位老師的回答很長、很專業,我以我有限的記憶總結一下要點:“第一,這個在學界是一個敏感話題,大家都不想去碰;第二,因為西方一直以來的排猶傳統,所以不可能承認耶穌是猶太人,反而要突出出賣耶穌的猶大是猶太人,作為反猶的依據;第三,猶太人群體都信仰猶太教,也不會承認更改了猶太教義的耶穌是猶太人。”

這位老師的回答給我很大的啟發,我去搜了搜相關的研究發現,不管宗教學還是歷史學,都沒有太多涉及這個問題了。畢竟基督教也不是乖乖小白兔,是真會把人燒死在十字架上或者送進宗教裁判所嚐遍人間酷刑的。
但有一點很有意思的是,二戰之後有了一大批世俗化的猶太人,他們走向世界各地,也不是猶太教原教旨主義者,所以喜歡宣傳耶穌是猶太人,可以給猶太人貼金,一如他們喜歡蹭歷史上所有的名人的一樣。但是猶太人對歷史上的名人是“一滴血原則”,拐彎抹角都想蹭到,而耶穌從歷史考據來看,確確實實是土生土長的猶太人,他既生在猶太人聚集區,又信仰猶太教,沒有比這個更純正的猶太人了。
為什麼我要糾結這一點?是為了證明西方歷史的不嚴謹與雙標。就是因為有基督教這個統治了歐洲一千餘年的意識形態存在,西方歷史被改得亂七八糟,一切以有利於基督教統治為目的。
最典型的,就是耶穌明明是根正苗紅板上釘釘的猶太人,但是長達千餘年的時間中他們可以忽略了這一點,然後強調“出賣耶穌的猶大是猶太人”,進行為排猶運動提供依據,豈不可笑?

我這次去義大利旅遊,深刻地感覺到了基督教對於古希臘、古羅馬歷史的玷汙。我對所謂的“西方偽史論”是不屑一顧的,因為我認為這是用一種反智主義去反對另一種反智主義,本質上還是“魔法對轟”。我們不能降低到他們那種層次去,而是客觀、理智、實事求是地看待西方歷史。
西方歷史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基督教對於歷史巨大的、全面的扭曲。他們沒有對歷史的敬畏與嚴謹,一切改成怎麼有利於傳教怎麼來。否則基督教怎麼能解釋,只有耶穌誕生之後才有上帝的神蹟,古希臘古羅馬獨立發展了那麼多年,跟上帝毫無關係呢?於是改吧,很多原始檔案被銷燬,歷史改得面目全非。
基督教最經典的改史,就是著名的《君士坦丁敕令》(注意跟著名的《米蘭敕令》區分開),這則檔案的內容是“賦予羅馬教皇及其拉丁教會以各種教俗特權以及整個西部帝國的全面統治權”,也就是說古羅馬帝國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釋出了一個命令,把帝國一半領土讓給了教皇和教會——是不是聽起來非常之匪夷所思?

然而這一份檔案實實在在為統治歐洲提供了法理依據,換句話說這叫羅馬認證的“正統”。直到公元十五世紀,在文藝復興的衝擊之下,教會喪失了巨大的思想領地。而天主教會的倒行逆施,也引發了全歐洲人民此起彼伏的反抗,此時正處於宗教改革戰爭的前夜。在思想解放和教廷失勢的雙重因素之下,德國語言學家尼古拉·庫薩才系統證偽了《君士坦丁敕令》。
尼古拉·庫薩用極其紮實的語言學功底證明,《君士坦丁敕令》中出現的諸多語法、詞彙,都是在公元八世紀才形成,不可能出現在公元四世紀的檔案之中。比如“塞特拉普”(satraps)、“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拜佔提亞”(Byzantia)等詞彙,在君士坦丁時代壓根就沒有這種說法。
檔案還有諸多史實性錯誤,比如提到“君士坦丁和加利卡努斯”一同任職執政官,但真實歷史中他們任職年代差了整整兩年。還有當時的教皇西爾維斯特為君士坦丁治癒麻風病、為羅馬城制服蟒蛇等等,壓根就是基督教為自己貼金凡的坊間傳說,就是模仿耶穌治療疾病的故事模板。這種傳說形成於君士坦丁去世一百年之後,然而卻光明正大寫進了檔案裡。
基督教改史是一個非常噁心的臭毛病,他們會把一眼假的傳說、神蹟、歌謠當成真實的歷史去玷汙史書——都有一個無所不能的上帝存在,如果不整出一點“神蹟”,來怎麼忽悠信眾呢?

我去梵蒂岡博物館參觀,最精華的兩個區域是西斯廷小堂和拉斐爾畫室。拉斐爾畫室第一間,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廳,四壁陳列著四幅作品:十字架顯聖(Vision of the Cross)、米爾維安橋戰役(Battle of
Milvian Bridge)、君士坦丁受洗(Baptism of Constantine)和君士坦丁獻禮(Donation of Rome)。
Milvian Bridge)、君士坦丁受洗(Baptism of Constantine)和君士坦丁獻禮(Donation of Rome)。
其中《君士坦丁獻禮》獻禮就是上文中所說的那個著名的偽史。《十字架顯聖》講的是君士坦丁大帝南征北戰中最重要的一個戰役之一:米爾維安大橋戰役。在這一場戰役中,上帝為了支援君士坦丁,用火焰在天空中畫出了一道十字架,並配上了一句拉丁文“你將克敵制勝”。看見了神蹟的己方士兵大受鼓舞,而敵人則聞風喪膽,君士坦丁一舉獲勝,成為了整個羅馬的主人。

另外一幅作品《米爾維安橋戰役》畫的是同一個戰役,但是傳說版本有所不同,講的是君士坦丁做夢夢見神蹟,於是要求戰士們在盔甲和盾牌上畫上十字架。果然在戰爭中天使顯靈了,手持利刃、弓箭、石索,在天空中打擊敵人,對方看到天空中出現了怪物,也士氣崩潰紛紛逃散。於是君士坦丁大帝獲得了最終勝利。
把一代南征北戰開疆擴土雄主的勝利,描繪成是上帝顯靈,這不就是“貪天之功,無恥之尤”嗎?基督教改史就喜歡搞這一套,什麼君士坦丁敕令我在場,米爾維安橋戰役我指揮……凡是重大歷史事件,都是它基督教的功勞。

這種靠迷信騙人的把戲以現代視角來看當然是匪夷所思的,但是在那個愚昧的年代確實有用。就比如耶穌各種神蹟,把水變成牛奶、讓池塘裡裝滿了魚等等,我們從張角到白蓮教、洪秀全都用過類似的套路。
“大賢良師”張角就號稱能撒土成糧、包治百病。現代史學研究,張角大機率是個自學成才的經驗主義土醫,確實是有點方子有用——尤其是對治療流行瘟疫,所以他確實能獲得一批信徒(種子使用者),然後才有資本去傳播。所以張角比耶穌還實在一點呢,人家多少是能治病,耶穌是純純靠騙。
就像君士坦丁最著名的米爾維安橋戰役一樣,整個西方歷史都被基督教改得面目全非。而且最關鍵的是,“上帝”和“耶穌”在一千餘年的歷史中,都是西方終極“政治正確”。這個政治正確可是真正的政治正確,LGBT跟基督教一比簡直就是幼兒園過家家。都不能把人架在十字架上燒烤,都不能組織十萬人跨越歐洲大陸進行遠征,還好意思叫政治正確呢(手動狗頭)。

正如開頭那位教授對我說的,“這在西方是一個敏感話題”,即便是專業歷史學者,可研究的東西那麼多,沒必要專門觸碰宗教這個黴頭,大學也是靠研究經費恰飯的嘛,不寒磣。
就比如對於真實的耶穌本人的歷史,有一個小方向供大家參考:耶穌是猶太民族大起義的領袖,代表著奴隸和破產農民的利益,所以享有崇高的威望,起義失敗後被羅馬總督處死。不過依然有些人利用耶穌廣播的名聲與威望,去發展組織,逐漸就變成了基督教,最後統治階級逐漸把符合自己利益的意識形態加進基督教之中,讓它變成了最有利於統治階級的思想工具。
當然我說的這個屬於野史的層面了,但是對於西方歷史的一切“野史”都要留個心眼,不怪他們野史太“野”,而是他們的正史太過於烏七八糟——甚至於自相矛盾、雙標。

上面這個故事倒是可以解釋一些基督教“雙標”。比如基督教最早能在羅馬帝國廣泛傳播,是因為它被稱為“窮人的宗教”:耶穌說“富人上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意思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眼頂針。而古羅馬正好貧富分化非常嚴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這就是基督教早起傳播的巨大土壤。
但是這也就是基督教最雙標之所在:它最後變成了統治階級鉗制人民思想精神的工具,所以必然要從“窮人的宗教”來一個180°大轉彎。比如《聖經·新約》中的故事:“在耶穌被釘十字架前,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瓶珍貴的香膏來澆在耶穌的頭上,香膏足足價值300迪納厄斯銀幣。耶穌的門徒認為這麼大一筆錢可以用來賑濟窮人,不該如此浪費,因此有些生氣。但耶穌則為她辯護,說道:‘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以;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所以看看雙不雙標?對別人就是勤儉節約,對自己就是“你們不常有我”。這種“雙標”和“擰巴”貫穿於基督教教義和整個西方歷史。不過我們還得深想一步:《聖經》中的“耶穌”,是真正的“耶穌”嗎?耶穌的擰巴是他本人的雙標,還是那些神父、聖徒、傳教士們所要創造出的“耶穌”呢?
想到這一步就很好理解了,為什麼神父、聖徒、傳教士們要創造出這樣一個“希望教徒為自己氪金”耶穌呢,因為他們自己也要賺錢的嘛,也要賣贖罪券的嘛,所以耶穌就必然要成為這樣一個“擰巴”的形象。歷史上真正的耶穌究竟是為窮人戰鬥,還是逼窮人氪金,已經不得而知了。還是那句話,西方正統的歷史研究都很忌諱這個話題,這方面沒有啥權威的成果。

耶穌本人是不是猶太人、是不是窮人領袖,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聖經》裡寫的那個耶穌,重要的是神父、聖徒、傳教士口中所描繪的那個耶穌,重要的是信徒心目中想象的那個耶穌。
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馬克思
我在羅馬旅遊,最大的感觸就是基督教玷汙了這座永恆之城。
比如這裡是位於古羅馬廣場中央的羅慕路斯神殿,大家看這個樣式,就是古羅馬的神殿後來改為了教堂。

羅慕路斯這個名字在羅馬意義非凡。是羅馬城的這個名字,就是來源於羅慕路斯,是整個羅馬城的老祖宗、創世王。羅馬狼喂的這兩個小人,就是羅慕路斯和他的弟弟。

結果基督教把名為羅慕路斯的神殿,改成了教堂,墳頭蹦迪了屬於是。
再看大競技場,一進門就是一個扎眼的十字架。

教會統治羅馬城時期,拆了好多大競技場的石料去修教堂,導致如此堅固的大競技場殘缺不堪,一邊拆還要到處立十字架,屬於夫目前の犯了有木有。
萬神殿,古羅馬建築的巔峰,一個巨大的混凝土穹頂,中間無樑無柱。萬神殿的正中央曾經有一個巨大的朱庇特(宙斯)神像,後來被基督教砸了,整個建築也被基督教霍霍得厲害,裡面也改成了各種禮拜堂、懺悔室、聖壇。

要不是基督教費拉不堪拆不動這個大穹頂,真有可能就被毀了拉去修教堂了。古羅馬競技場和大浴場的石料,就是又大又剛好能被拆動,慘遭毒手。
哈德良堡,古羅馬著名皇帝哈德良就葬在這裡,現在樓頂立了一個大十字架和天使雕像,這真是字面意義的“墳頭蹦迪”了。

圖拉真紀功柱,古羅馬浮雕的代表性建築,紀念古羅馬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圖拉真。結果最上邊圖拉真的雕像被砸了,換成了聖彼得的雕像。

黑暗的中世紀有一場漫長的“毀滅雕像運動”,因為古希臘古羅馬的雕像多是神話中的人物和歷史名人——比如宙斯、雅典娜、阿喀琉斯、古羅馬皇帝等等……但是這些人的雕像要麼是異教神祇,要麼是鎮壓過基督教的政治強人(和他們的前輩),於是被通通砸毀,大量珍貴的藝術珍品和寶貴文物都毀於此時。
還有一個原因是,基督教的教義,就有不進行具體的偶像崇拜的說法。上帝有說:“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象,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唯恐你們敗壞自己,雕刻偶像……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它。”——《聖經·舊約》
但是,這玩意又能看出基督教的雙標來,同樣是《聖經·舊約》裡的原話:“要用金子錘出兩個天使來,安在施恩座的兩頭”,“兩個天使要高張翅膀,遮掩施恩座”——這又是搞雕像了,聖經裡面都是各種自相矛盾的說法。
基督教總是標榜自己是“破壞聖像運動”的受害者,但是他們的“破壞雕像運動”持續時間之長、滅絕文化之狠、影響之深遠,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都是找不到第二例的,羅馬希臘遺產除了建築,幾乎相當於從歷史上抹去了。

除了一些海底出土的陶罐畫,古希臘繪畫全部失傳。古希臘最偉大的雕塑家波利克里託斯,他的所有作品全部毀於“破壞雕像運動”中,沒有一件傳世。但沒有傳世,為什麼說他是“古希臘最偉大的雕塑家”呢?
因為他有很多雕塑美學著作傳世,為雕塑藝術構建了堅實的基礎。比如波利克里託斯認為頭身比是7:1,現代理論精確了一些,是7.5:1,已經很接近了;波利克里託斯提出了美的對比原則——實和虛,重和輕,直和彎,所以雕塑應當把重心放在一隻腳上,另一隻腳虛站,然後手上拿著一個東西來進行平衡……
所以看到這些就很痛惜,基督教強盜打砸搶燒真是歷史傳統,從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古希臘古羅馬雕像,很多都是基督教沒那麼兇殘的時候從墓穴出土、從海底打撈,才能儲存下來。

也正因為此,古希臘羅馬的歷史變得亂七八糟,一部分被基督教毀掉了,一部分是文藝復興時期“假託”所做,給“偽史論”留下了巨大土壤。
偉大的文藝復興巨匠拉斐爾,因為其超越時代的藝術素養,一直都是教皇前炙手可熱的人物。拉斐爾擔任的最後一個職務是“羅馬古蹟保護官”,但是在那個時代,這個職位往往是無能為力,他只能眼睜睜看著一批又一批的古羅馬建築和藝術珍品被毀壞。
拉斐爾生命最後幾年的信件中,幾乎都在向朋友感慨自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大量古羅馬遺珍被毀壞,公開寫向教廷呼籲保護文物的檔案也石沉大海。1520年,37歲的拉斐爾離開了人世。
一些現代學者認為,拉斐爾作為偉大的藝術家,本身就有超於常人的敏感與細膩,他離世前那些感慨無能為力與表達痛苦的信件,很像抑鬱症患者的表徵,拉斐爾最終英年早逝,很大機率於此有關。

相關閱讀:文化革命的意義
◆ ◆ ◆ ◆ ◆
上一期內容的影片更新了,歡迎多多點贊:


第二本新書正式連載完畢:《資本囚籠》全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