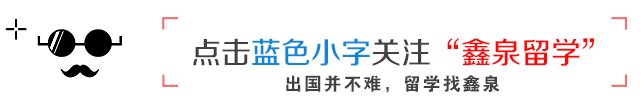作者:立正媽媽
轉載:藍橡樹

正文
鴉雀無聲的課堂,空洞無光的眼神,頹靡不振的軀體,一批又一批的天之驕子,在追逐多年的神聖大學殿堂裡,活成了“寂靜的一代”。
從小卷、各種卷、使勁卷,已經使本該朝氣蓬勃的他們,人生早早變了形。
《嚮往的生活》中有這樣一段,老狼問許光漢——“現在的年輕人都怎麼認識異性的?”許光漢笑而不語,舉起了手機。
老狼與黃磊都不由地感慨道,時代變了,當年民謠裡的校園愛情故事,已經離現在越來越遠了。

在《中國青年網》的一項大學生戀愛調查顯示:
近七成大學生單身,超五成大學生無戀愛經歷。如果你在大學談過超出1次的戀愛,很可能就已經擊敗了近9成的同齡人。
“戀愛不是洪水猛獸,有一天我們會發現,不會戀愛才是洪水猛獸。”
這是蔡興蓉老師在《高三的大姑娘》一文中提出的觀點。

我們的下一代,突然不會愛、不想愛、不屑愛了。在荷爾蒙最旺盛的年紀裡,變得沉默、寡淡、無慾,這是哪裡出問題了?
寂靜的一代:
不戀愛、不溝通、不發言
《三聯生活週刊》去年曾經做過一個主題——“寂靜的一代”。
“現在很多大學生不再熱衷於上課發言、和老師同學互動,也不再把談戀愛和交朋友當成大學生活的必需品,更不願意去揹負一份完整的情感。取而代之的是,跟虛擬人談戀愛,在網上徵集“搭子”等等功能性、碎片化的臨時關係。
面對和人建立更加親密、深度的聯結,他們並不想躬身入局。”

一所重點大學心理健康中心的負責人發現,大概從三年前開始,新一代的大學生對戀愛話題不感興趣了,甚至面對老師的詢問,會疑惑地問——“我能不談戀愛嗎?”
老師心裡一沉——“10年前,大學生對戀愛話題感興趣的程度是一騎絕塵。”
同樣有變化的,是大學的課堂。
博士生導師劉永謀在眾多高校講課中的最大感受——
“這幾屆的本科生,突然變得很呆,可以說是呆若木雞。”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看法,而是越來越多的高校老師感同身受。

“上課之前靜悄悄,沒人說話、搭訕,更別說追趕打鬧了。人人一臺筆記型電腦、iPad,或者乾脆是一部手機,眼睛直勾勾地望著它們,時不時手指劃一下,或者敲幾個字。上課的時候,也是悄無聲息,不打瞌睡,但也不抬頭,不參加討論,被點名了,就支支吾吾說兩句,隨即又沉默了。”
當老師忍不住發問——“怎麼現在大家越來越呆了。”
臺下的學生沒有反應,甚至連抬頭笑笑,回應老師調侃的人都沒有。
難怪有教授望著臺下的學子,忍不住痛心哀嘆——“我教了墳墓一樣的一個班級。”
鴉雀無聲的課堂,空洞無光的眼神,頹靡不振的軀體,一批又一批的天之驕子,在追逐多年的神聖大學殿堂裡,活成了“寂靜的一代”。

大學生“節能模式”背後,
是優績社會的反噬
“不談戀愛”、“不溝通和磨合人際關係”、“上課不發言”等沉默現象,大學生們自嘲這是“節能模式”。
精力有限,忙著績點、考研、考公、考編,忙著追求績效的大學生,變得越來越“功利”。把自己隱藏起來,減少不必要的社交消耗,只做“有價值”的事,“節能模式”只為了減少在“無謂”的事情上耗費力氣。
1、KPI考核下的高競爭感模式
從出生開始,這一代孩子就進入了一場無休止的KPI考核。
嬰兒時期每次喝多少毫升奶,幾個月會走路,幾歲開始繪本閱讀,上多少個培訓班,每次考試多少分,每天刷多少套題,考什麼學校,讀什麼專業,將來考公還是考研……
他們活在父母期待的數值裡,每一步成長都被參考在社會績效考核裡。
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管理學肖知興教授嘆息道——“這一代孩子身上的元氣、銳氣和內力好像越來越少了。每天各種KPI整來整去,‘外驅’變成‘他驅’,就沒有‘內驅’,沒有‘自驅’了。沒有內驅等於內心深處沒有發動機,不就是空心病嘛。我們的孩子都是被KPI操縱的空心人。”

高壓高競爭背後,總會被迫丟掉某些東西。
例如,情感。
從幼兒園開始,所有的同齡人就變成了競爭對手。害怕比別人學得少,學得慢,學得差,所以卯足勁了互相競爭。
當我們在問“偌大的小區裡,為什麼放學找不到一個玩伴”,那是因為現在的孩子已經不被允許自由玩耍了,為了所謂的KPI,幼兒園放學就開始奔波在各個培訓班之間。
那些“社交能力、團隊精神、同伴互助、玩耍享樂”等人際關係的建立,變得不值一提,卻不知埋下的,是教育系統裡最大最嚴重的坑。
在《寂靜的一代》一文中,有大學生就談到,“身邊很多同學都一邊努力做績點戰士,一邊打探其他同學的成績,一邊還要防範被打探甚至舉報。”同窗的情誼在考核、績點、排名面前,只剩下競爭。他們更加精細地規劃自己的生涯和利益得失,愛情和友情無法量化投入產出比,所以並不值得投入時間和精力。

有一位北大畢業去送外賣的年輕人,在接受採訪時就說,一直活在恐嚇中。“要不往上走就完了”,“這輩子就在同齡人裡混得最差了”正是這樣一句句的威脅裡,讓他們這一代“雖然沒有經歷過世界大戰,但活在心靈之戰中。”
人一旦屬於被衡量,被評價、被排名,就不得不被鞭策著去追求利益最大化、效率最大化、機能最大化。焦慮、不安甚至恐懼的狀態,就會讓他們始終活在巨大的疲倦感和緊張感中。
物質最好的一代,心卻最累。

執教於一所二本學校的黃燈老師,曾寫下一本書《我的二本學生》,她痛心地發現,越來越多大學生“像打溼了的火柴”,毫無活力:
“教育像一場慢性炎症,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抗生素、激素,到大學時代,終於結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惡果。學生內心的疲憊和大學時代的嚴苛壓力,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底色。 孩子們的個性、天性和生命活力,被磨滅得無影無蹤,他們的面目越來越相似,早已成為工廠的標準化構件。”
“那種對年輕生命力的確認、張揚”,早已喪失在學業功利化的各項KPI考核中。

2、習慣性自我壓抑帶來的社交無力
“節能模式”的消極社交,還來源於習慣性自我壓抑帶來的社交無能。
這一代的孩子或許上過很多學科培訓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擁有碾壓父輩的知識儲備,但卻缺了自我表達的一課。他們被父母和老師規訓成了“乖巧的綿羊”,學會了剋制自己的語言和表情,不敢表達情緒和慾望,習慣性地壓抑自己的感受。
“你只需要好好學習,別的不用管”的單一養育,讓他們連最簡單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欠缺;
“我都是為了你好,聽我的準沒錯”的洗腦下,他們已經失去了尋找自我興趣和追求的能力;
多年的埋頭苦讀,讓他們的生活被壓縮成三點一線,學校-培訓班-家;
課間連走廊都不許出的管制,讓他們的童年社交狹隘得連同班同學姓名都可能記不住;
“多考一分,幹倒一操場”,讓身邊的同伴全變成了競爭的對手,暗自都在較勁……

待到大學後,開始參與社團、交友、戀愛、校園活動和實習工作,從小在約束中長大,早已習慣自我壓抑的他們,就會對突如其來的自由感到無法適從。
在社交環境裡,尤其是需要表達自己的環境裡感覺到高度不適;
無法在別人面前生氣或難過,總是覺得自己的負面情緒是很糟糕的;
常常對於小事過度反應,卻又不讓別人知道;
即使很喜歡的東西也會表達出“無所謂”的態度,不喜歡的東西不知道如何拒絕;
心情不好時會依賴一些“逃避手段”,如:長時間泡在綜藝、電視劇、遊戲裡,或是睡很長時間;
習慣性地壓抑自己,其實就是在自己和他人之間主動地構築了一堵密不透風的牆,不僅自己出不去,美好和親密的感受也無法進來。

應試教育早已磨滅了他們對生活的期待,很少有時間做夢、發呆、思考。他們的時間是要計較成本的,要耗費太多時間精力去追求、曖昧、溝通、交流的磨合,他們談不來。
過分溺愛帶來的心靈脆弱,也使得他們在遇到摩擦時,更容易出現“應激式的對自我利益的關心”。
所以,相比起“不談戀愛、不交友”,大學裡很突出的一面是,同學之間的摩擦被放大,宿舍關係的複雜性尤其明顯:生活摩擦、觀念差異、經濟狀況差異、缺乏人際關係經驗、不良心理狀態帶來的問題、小團體排擠他人問題、保研評優帶來的不良競爭問題等等。
優績主義下成長起來的他們,習慣了無論交友、戀愛、工作、甚至婚姻,都是直接粗暴的,“合則聚,不合則分”,現實而冷漠。
那種“從前車馬慢”,用一生追求等待一個人的矢志不渝,是不符合價值理性的,有點小摩擦就分手了;
那種“朋友一生一起走”的同窗同宿舍情誼,一旦涉及績點、評比、名額、就業等考核,就變為彼此防備的競爭對手;
那種為了摯愛的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激情,在計算過價效比後,早早就被“更有前景”的未來所否決掉了。
“在應試教育的機制裡,他們在不知不覺中養成溫良、沉默、功利的性子……他們收縮起屬於青春年代的觸角和鋒芒,逼到絕境,唯一能夠下手的物件只有自己。”
在本該最張揚放肆、不計得失的年紀,他們早已成為了“一個世俗的冷漠的大人”。

3、網路發達,使人活在雲端裡
跟虛擬人談戀愛,在網上徵集“搭子”已經成為新一代年輕人的社交模式。
“搭子”的範圍非常廣,飯搭子、學習搭子、運動搭子、減肥搭子,甚至還有牌搭子、咖啡搭子、養貓搭子等,細分到方方面面,種類龐雜, 只有想不到,沒有“搭”不到。
這種更輕盈的社交形式,既不需要投入太多情感,也不會佔據生活空間和精力,又會在你需要的時候有人可伴,所以深受歡迎。
在大學生推崇的“節能模式”下,網路讓他們“以最低的精神治理成本得到一種高效的精神陪伴”,節省了和他人建立親密關係的時間和精力,個人的壁壘更加堅固,但也被迫失去了許多真實體驗——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不可或缺的重要體驗。

資訊時代帶來的新型社交工具,正在改變著人們的社交範圍、方式和結果。
網路看似提供了更廣泛的空間、更多樣化的人群,但“網上聊翻天,相對兩無言”的場景,越來越多的出現在正常的社交局中。
年輕人的聚會,已經從以前的暢聊天南海北、吐槽、八卦、共訴愁腸,變成如今的人手一杯奶茶、一部手機、一場遊戲局、一個朋友圈,比起面對面的聊天,他們更熱衷於給對方點個贊,評個論,發個表情包。
明明距離那麼近,卻心又相隔那麼遠。
越開放越封閉,越多元越孤立,是這個時代的悖論,也是當代年輕人社交的困局。

打破寂靜,拉近距離,
活在“現實世界”裡
牛津大學的社會人類學家項飆曾提到一個21世紀的新現象——“附近的消失”。
指的是,人們越來越不關注生活周邊的事物場景,在我們和真正觸手可及的世界之間,樹立起了一個看不見的隔離帶,讓我們產生了“真空感”。
尤其在在網際網路衝擊之下,“附近”會被摺疊,人們趨於凡事資訊化的同時,也在斬斷與“附近”的聯絡,愈發成為一座驕傲的孤島。
當我們的孩子成長過程中,被保護在一方書桌前,隔斷了與“附近”世界的情感交集,就會如同活在真空裡,越活越虛空,越活越冷漠。

有人說,今日的中國,正在重蹈美國幾十年前的覆轍。
美國的幾代人,經歷了從“迷惘的一代”到“沉默的一代”,再到“Z世代”,而在短期內迅猛發展起來的中國,一代人就濃縮了幾代人的特質。
出生在物質條件富裕,網際網路普及的這一代孩子,生逢其時,很難說幸運或不幸:
擁有了迅捷抵達知識的的速度,但對人生充滿迷茫和困惑;
得到了最多的關注和保護,卻喪失了自我探索的空間和能力;
強調“個性自我表達”,有多種渠道表達和溝通,卻找不到傾訴的慾望;
在迷惘中,愈發失去對生活的慾望,活得既豐富又匱乏。

王小波寫自己的21歲,曾這樣說道:
而我們太多的孩子,在人生的“黃金時代”裡卻垂垂老矣,失去了對生活的奢望。

《和心理醫生看電影》中有一句話特別打動人——
“真實的情感慰藉,還需要精神穹頂有意義感,需要回到真實的關係當中。”
增加與現實世界的聯結,需要讓溫室裡的花朵打破保護的罩子,走出教室那一小方天地,戳破資訊繭房,去感受世界的廣闊和多元,與不同的人群交往,見識人間百態,感受人情冷暖,在接地氣的生活中,體驗煙火氣,才能活得有“人氣”。
打破“寂靜的一代”的標籤,重在迴歸生活,活出真實感。
美本早申資料大揭秘

翠鹿升學榜2025早申資料報告如何領取?
點選下方名片
關注“視角學社”公眾號,
後臺對話方塊傳送“資料報告”(不是評論區哦~)
獲得完整版報告領取方式!
更多精彩
相關閱讀:
錢穎一:教育的三個基本問題——學什麼?怎麼學?為什麼學?
大學教育的價值被嚴重高估!是真的嗎?
牛津教授項飆:教育系統正在批次生產陪跑、韭菜、炮灰……
作者:立正媽媽,轉載:藍橡樹,本文經授權轉載。版權歸屬作者/原載媒體。
喜歡本文?歡迎掃碼加入視角&翠鹿公益交流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