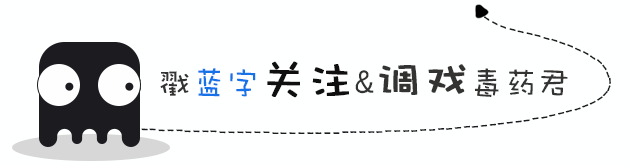你知道嗎?《三國志》《三國演義》中“三國”的說法,其實對三國之中的曹魏具有極大的殺傷力,因為這些說法把東漢和西晉之間的這個時代處理為“三國”時代,而非“曹魏王朝”時代,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曹魏王權正統性的否認。“三國”之說的背後,其實有著歷史書寫者的特定目的。
在《帶獻帝去旅行:歷史書寫的中古風景》一書中,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衝關注作為文字的“歷史”和作為事實的“歷史”之間的關係。他說,“後者一旦訴諸前者,就只能是帶有特定目的的歷史書寫,而前者卻是我們與後者之間唯一的橋樑。”
《帶獻帝去旅行:歷史書寫的中古風景》
徐衝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
他看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那位被“挾”的天子劉協,後來禪讓給了曹操的兒子魏王曹丕,曹魏王朝給他的諡號為“孝獻皇帝”,將他的陵墓命名為“禪陵”。諡號和陵墓的名字都有著明確的政治指向,以強調漢魏禪代的正當性。當人們念出“漢獻帝”三字時,曹魏王朝的權力來源的正當性再次得到了肯定。
歷史上活生生的漢獻帝是什麼樣?如今當我們翻閱史書,可以看到來自曹魏王朝立場的政治書寫,漢獻帝的一舉一動被拿來作為漢魏交替正當性的論證;也可以看到士人精英主導書寫的漢獻帝,與前述史書寫作保持距離,獻帝形象也絕非傀儡;此外還有曹魏敵國書寫的小道故事,借獻帝之口渲染曹魏王權的非正統……真實的獻帝,已被這些作品層層掩蓋。
“每部作品都有特定的書寫立場充盈其中,背後則是作者作為歷史參與者的特定時空經驗。換言之,這些作品又何嘗不能看成是作者帶著獻帝去經歷的一場時空之旅呢?”在這次採訪中,徐衝談到了“漢賊”曹操、五胡十六國等我們耳熟能詳的歷史形象或概念背後,有著歷史書寫怎樣的特定立場和目的,以及普通讀者在閱讀歷史時、在現實生活中應如何分辨和思考。
介面文化:我們要如何理解《帶獻帝去旅行:歷史書寫的中古風景》這個書名?
徐衝:這本來是書中一篇文章的題目,我覺得可以作為全書的一個思路提示。我們從當下出發,要想去接近“獻帝”,本身是很困難的。我在《自序》的結尾引用了一段書中的文字,寫獻帝當年在曹陽亭逃脫追兵、狼狽渡河的場景。那段描寫出自親歷者劉艾建安年間寫的《獻帝紀》,當時覺得是比後世材料更為接近真實歷史的。結果老友遊逸飛兄告知,其中最具現場感的描寫“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注:是指逃跑的時候先上船的急著要走,後來的抓住船不讓走,於是船上的人一通亂砍,船上被砍斷的手指多得可以捧起來),居然是化用了《左傳·宣公十二年》書寫晉楚邲之戰的典故。2019年底我在寫那段文字時,腦中迴盪的是剛看過的美劇《權力的遊戲》S5E8《艱難屯之戰》結尾瓊恩·雪諾帶領守夜人孤舟離岸、回望異鬼軍團的場景,不過大概沒有人讀出來吧。
根本上說,重返真實的過去看到鮮活歷史恐怕是不可能的。我們回望過去,就一定會有書寫者、敘述者以及我們作為觀者的濾鏡在內,我們看到的是他們呈現給我們的東西,也包括了我們希望看到的東西,我把這個叫作“風景”。濾鏡變形到什麼程度,我們又能意識到濾鏡變形到什麼程度,都是可以討論的。
歷史學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共通的規則,讓我們能夠在區分材料層次的基礎上,儘可能接近真相一點。但我想,歷史上不同時代的人們在不同的時空框架下對於歷史資源的利用,也都是有意義的。所以我在《自序》結尾說:“風景”無處不在,且聽風吟吧。
介面文化:書名中的“歷史書寫”是你一直以來關心的主題。
徐衝:我對“歷史書寫”的認識有一個發展過程。十幾年前寫博士論文時,我把它等同於政治權力的投射或者政治權力實現的方式。我考察的是紀傳體正史裡的幾種結構,認為它們是政治權力結構的投射,權力要實現,最後必然落實在史書上面。這種思路有制度史研究的巨大影響,主要的反思物件是常見的史學史研究思路,即強調歷史書寫是史家個人史學思想的反映,與政治權力發生關係的方式是所謂的“直書/曲筆”。我的思考落腳點則是希望揭示出一個時代中歷史書寫與政治權力、意識形態的合謀關係,是一種“贊成”的政治史,而不是“反抗”的政治史。
後來年齡漸長,經歷的也多了,尤其是2020年以來的這三四年,我逐漸認識到也體驗到,歷史書寫的滲透要廣泛得多。廣義的“歷史書寫”不只是有形的、寫出來的東西。我們對於過去的記憶、對於歷史的認知,都在規範我們的行為,構成了我們可以引用的資源。最後落實到書本上的,是前面無數次即時性的歷史書寫最後成形的部分。
可以說我們每個人都和歷史書寫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甚至是日常性的關係。每個人在做事情的時候,昨天發生的或者更久之前發生的事情,作為資源形成了正當性的支援。我們的頭腦在形成記憶的時候,也不斷受到對過去的認識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確實人人都在進行歷史書寫(廣義),而不僅僅只是擁有歷史書寫(狹義)權力的特定作者。
介面文化:你說不用“紀傳體斷代史”的概念,而是用“紀傳體王朝史”,是什麼意思?
徐衝:套用“理性經濟人”這個說法,“紀傳體斷代史”概念的背後對應著一種“理性史學家”的假設,是從特定的史學立場出發來寫作這一作品。但我認為這個假設抽離了太多參與到這個歷史過程中的要素,過於單調了。我用“紀傳體王朝史”這個概念,就是希望更多地提示與這種歷史書寫對應的政治權力方面的要素和群體,而不只是被限定的“史家”。
介面文化:不同的說法背後有著不同的目的,普通讀者應該如何面對這些概念和歷史書寫?
徐衝:不要不假思索地接受一個記載。想一想它是從哪裡來的?講述者是誰,書寫者是誰,受眾是誰?書寫的受益者是誰,受害者又是誰?這是我從歷史學家的職業習慣出發對普通讀者的建議。任何一種史料都包含著它特定的目的,所以我們使用史料的時候要審慎。其實,把它推廣到現實生活的其他方面,保持一種警惕而耐心的態度,也還是很有必要的。
介面文化:在《何以“漢賊”》一文中,你談到了曹魏王權的正當性被質疑、定格於“漢賊”的過程。《此處葬曹操》的作者唐際根則認為,曹操形象的奸雄化主要是在南宋以後,南宋的情結追溯到了東吳,敵對的金國追溯到了曹操。你是怎麼看待這種說法的?
徐衝:這是一種蠻有影響的說法。我在書中提到乾隆時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四庫館臣對習鑿齒《漢晉春秋》(注:東晉史學家習鑿齒撰寫史書,記述三國史事,以蜀漢為正統)的評價,也是將這本書貶低曹魏、推崇蜀漢的做法,歸因於東晉偏安政權對自身正統地位的維護。但我對這種解釋思路一直持保留態度。
一方面,像東晉並不把自己定位為江南的偏安政權,它的自我定位還是之前大一統王朝西晉正統的延續,只不過現在暫時“行在”江南,將來還是要重返中原、恢復神州的。從這一點來說,他們未必就需要推崇歷史上的偏安政權。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明確看到,在南朝劉宋初年范曄所撰《後漢書》中,曹魏或者曹操的形象就已經完成了“黑化”,成為了大漢的“賊臣”而非“功臣”。這個時間點顯然比南宋要早得多。
其實在漢末三國時期,如同曹魏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所取得的優勢一樣,曹操的“功臣”形象也還是相當主流的。將曹氏從“功臣”翻轉為“漢賊”,我認為西晉是重要推手。
西晉人的心態其實挺矛盾的。一方面他們在正統上繼承曹魏,兩個王朝的統治群體本身就有較強的延續性。但司馬氏先後消滅蜀、吳完成天下統一後,又覺得自己才是東漢正統最有資格的繼承者。如果可以直接繼承東漢,不必經過曹魏的中介,自己的歷史地位不是更高了嗎?所以滅吳之後,西晉人反而更容易接受、更樂意傳播以前吳人貶損曹操的的各種傳聞了。蜀人陳壽撰《三國志》,把東漢和西晉之間的這個時代處理為“三國”時代,而非“曹魏王朝”時代,在西晉當時能被接受且得到官方肯定,很說明問題。
徐衝:西晉對曹魏當然還沒有那麼貶低,但是至少沒有把它當成唯一的正統,所以當年曹操的敵對者寫的那些“小作文”慢慢就流行起來了。
關鍵的轉折點可能是南朝初年范曄編撰的《後漢書》。從傳統史學的角度來說,《後漢書》寫得很好,最終淘汰了之前所謂的八家“後漢書”(注:八家“後漢書”,是指《東觀漢記》、范曄《後漢書》以外,記載東漢歷史的八部紀傳體及編年體史書。其實不止八家,自《東觀漢記》之後,三國吳、晉之間人陸續撰寫後漢史者有十餘家)。而范曄“非曹”的立場非常鮮明,寫漢末歷史時用了不少孫吳給曹操寫的黑材料。因為大家對范曄《後漢書》的推崇,這些負面書寫就“正史化”了,這大大加快了曹操的“漢賊化”程序。
我在書中對比了《後漢書》和《三國演義》寫曹操派華歆入宮抓捕伏皇后的段落,發現這個故事的骨架在范曄《後漢書》裡已經完全成型了,《三國演義》只不過又添油加醋地進行了一些發揮。其實《後漢書》的這段故事,就是從孫吳人寫“小作文”的書裡面抄出來的,未必有切實的依據。
介面文化:在書中你還談到,諸葛丞相的聖化是遠遠滯後於曹丞相的黑化的。
徐衝:我們說諸葛亮的“聖化”,主要包括兩方面:一個是拔高他的“忠漢”立場,把他塑造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道德楷模;一個是賦予他各種超高的軍事甚至神異能力,用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裡的話說就是“多智而近妖”。其實,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諸葛亮都還是一個比較正常的傑出政治家形象,沒那麼悲情,打仗也沒那麼神奇。以上兩個方面的“聖化”,應該是唐宋以後的事情了,也未必是同步發生的。
“三國”這個歷史時期,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有什麼耀眼的特殊性,以至於讓曹操在後世變成奸雄的代表,諸葛亮成為忠臣的代表,關羽成為武將的代表,劉備成為好皇帝的代表?其實並沒有。曹操沒那麼壞,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也許真的跟《後漢書》裡東漢末年曆史寫得太好、太受推崇有關。否則,比如新莽末年也有很多英雄,劉秀和他們群雄爭霸,過程跌宕起伏,不亞於東漢末年到三國這段時間,但是為什麼就“三國”特別受歡迎,變成無數人甚至包括日本人都熱衷的歷史資源?
介面文化:這讓我想起作家唐諾提到過,司馬遷的《項羽本紀》把項羽寫得如此深入人心,在中國歷史百年千年中,“這樣一種人心為之顫抖的失敗,這樣一種幾乎已伸手摸到最高一點的墜落和毀滅,不是沒在其他人那裡發生過,但只有司馬遷寫到如此。一如海倫的絕世是因為荷馬的吟詠,項羽的無可比擬也是因為司馬遷的書寫。”
公眾一直在很積極地探討曹操究竟是奸雄、梟雄還是英雄,比如說易中天就說曹操是“可愛的奸雄”。你認為這樣的討論有意義嗎?還是說從不同歷史書寫的角度看,他的形象各不相同?
徐衝:當然不是說可以“戲說”歷史,但每個人都可以各取所需,從歷史資源中發掘自己想要的東西。就像易老師說曹操是“可愛的奸雄”,這當然也是可愛的說法,都是可以討論的話題。但我想強調的是,曹操反面形象的確定是一個後起的事情,在漢末三國相當長的時期內,他的形象都是非常正面的。不能說他想當皇帝就是壞人,這也不符合古人對於王朝更替的普遍認識。
北魏把自己寫成華夏文明正統繼承者
把五胡寫成野蠻人
介面文化:在書中你談到,北魏對之前政權用“五胡十六國”進行稱呼,意味著對他們自我定位的否定。為什麼曹魏的形象經歷過變化,五胡十六國的形象沒有過翻轉呢?
徐衝:我們今天已經習以為常地把“五胡十六國”作為對一個歷史時期的固定指稱了。但事實上“五胡”和“十六國”都是否定性概念,是帶有特定的歷史書寫目的和意識形態功能的詞彙。
“五胡”概念更早,大體成型於四、五世紀之交,是來自東晉南朝一方對華北敵對政權的貶稱。這大體還是尊重歷史事實的。在和東晉對峙的百年裡,華北確實先後存在過五六個相當強盛的王朝,其中後趙和前秦還一度完成過華北統一,歷史地位很高。建康一方雖然強調它們是僭偽政權,但也承認這種歷史地位。
“十六國”來自崔鴻編撰的《十六國春秋》,是北魏遷都洛陽後製造出來的概念。這種說法否定了之前“五胡”王朝的正統地位,把這些曾經佔據中原、稱皇帝稱天子的“天下國家”和割據地方的邊緣小政權一鍋燉,統稱為“十六國”。希望製造的印象就是,之前的歷史正統是西晉,分裂後變成了十六國時代,混戰百年,最後由我大魏來承接西晉的天命,結束分裂,完成統一。
因此,這兩個概念來源不同,達到的意識形態目的也不同,但相同之處就在於都不是“五胡”或者“十六國”自我立場的書寫,尤其對“五胡”王朝的地位是嚴重的貶低和失真。不幸的是,我們最後繼承的就是這樣一個扭曲的歷史認識。
主要問題在於“五胡”沒有留下合適的繼承者進行足夠的歷史書寫。北魏最後統一了華北,特別是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完成了自身的正統化。北魏對於之前這段歷史的書寫非常重視,顯然也是非常成功的。
更重要的是再之後接替南北朝的唐王朝是巨大而成功的帝國。唐代關於五胡十六國的書寫,大體繼承了北魏洛陽時代以降的成果和立場,體現為唐修《晉書》的三十卷《載記》。經此一役之後,“五胡十六國”的歷史形象大概就不可翻轉了。
介面文化:大家接受北魏的說法,或者對北魏印象比較好,是不是因為他們比五胡十六國更積極地接受漢化的結果?
徐衝:這是一個很傳統的印象,也是過去主流的關於五胡和北魏對比的思路,認為五胡沒有實現華北的統一,但北魏能夠完成,是因為北魏是一個比五胡更加接受“漢化”從而更加“文明”的政權。但事實上,近30年來的北朝史研究讓我們逐漸意識到,與五胡相比,北魏才是那個遊牧性、內亞性更強的群體。
站在華夏文明的立場來看,如果說五胡是站在門口,那北魏就是站在門外好遠的野地裡的陌生人。五胡是立足中原的“天下國家”,以漢晉以來的中原腹地為中心立國,但北魏和赫連夏的都城都在北方農牧交錯地帶,是華夏世界的邊緣。
誇張地說,如果以漢晉文明為尺度,北魏能完成統一併不是因為它“文明”,反而是因為它“野蠻”。以代北為中心的拓跋人融合當時草原遊牧世界和華北農耕定居世界兩種文明資源的能力非常之強,也迸發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如果站在更寬廣的文明程序裡,北魏的歷史地位應該是相當高的。不過,後來北魏自己又遷都到洛陽去,希望繼承西晉正統,就把自己寫得好像是一個漢晉文明的正統繼承者,把“五胡”寫成野蠻人,是西晉天下分崩離析的罪人。這裡面的歷史因緣有點複雜,經歷了好幾次翻轉。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採寫:潘文捷,編輯:黃月、潘文捷,未經介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