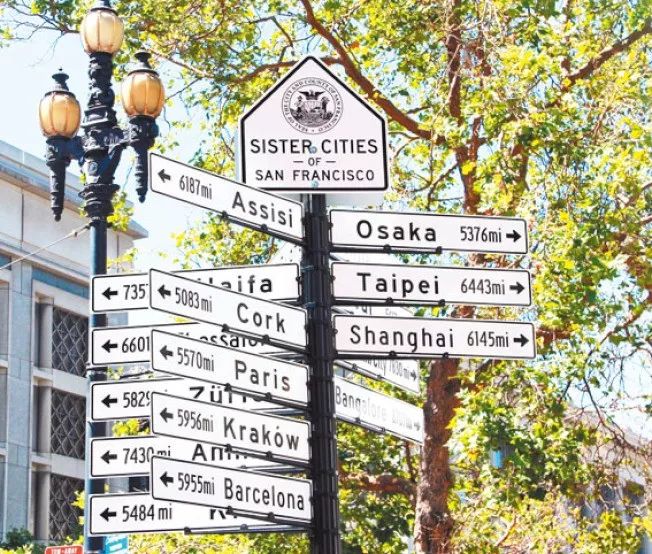蟄伏六年,李安終於決定迴歸。
與他一起出現在影壇的,還有兩個小孩子。
他們一個11歲,一個12歲,在美國西部沉默的山脈中行走、成長和謀生,偶遇水牛骨、虎爪印和乾涸的河床。
他們便是本次李安新片的主角:露西(Lucy)和薩姆(Sam)。
李安新作《舊金山》改編自90後華裔作家張辰極的作品《金山的成色》,預計將於今年8月在美國北加州開機拍攝,拍攝週期約為40天。

《金山的成色》(How much of these hills is gold)是張辰極的首部長篇小說,曾入圍2020年布克獎和美國海明威獎。
這部作品以19世紀美國淘金熱為背景,講述兩位華裔孤兒露西和薩姆在美國西部土地中流浪的歷程。
電影擁有豪華的主創班底,將由三次奧斯卡最佳攝影得主艾曼努爾·盧貝茲基擔任攝影指導,由韓裔編劇Hansol Jung擔任劇本改編。
據外媒報道,演員陳法拉有望參演重要角色。
年輕作家,首部作品,卻獲得國際知名導演青睞,《金山的成色》用什麼打動了李安,讓蟄伏六年的他重新接受創作的感召?


“這片土地,不是你的土地”
“爸夜裡死了,為此他們得去找兩塊銀圓。”
《金山的成色》開場冷峻且殘酷,正如它試圖去描繪的那段過往。這是一部關於華人移民遷徙和謀生的小說,它頗具力量感,討論歷史與記憶,歸屬和種族,家庭中不同代際成員間的矛盾,並借用自然元素將矛盾釋放。

《金山的成色》美籍華裔作家張辰極
作家張辰極出生於1990年。四歲時,她從北京移居美國,並在十八歲前搬了十次家。
移動之中,美國西部廣闊而壯麗的風景曾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暴風、流雲以及淹沒天和地的大雨。
她說:"對我來說,我對美國、對美國特質的體驗,是與旅行和某種程度的流離失所感有關的。"
這樣的過往讓張辰極的作品中既包含對身份認同的探尋,也湧動著沉鬱晦暗的情感勢能,這勢能來自於對土地的沉醉,像黑色的河水似有鎏金一閃。

張辰極的第二部小說《奶與蜜之地》,同樣討論了歸屬感的議題
主角露西和薩姆雖為亞裔,被當地白種人排擠和霸凌,卻從小生長在美國西部,熟悉並深深依戀著這片她們用身體丈量過的土地。
人種、國家的劃分沒有辦法概括她們矛盾的、模糊的處境,“我是誰”這個問題也變得格外困難。
正如作者所言,“我們要如何找到那種超越房產、超越出生地的歸屬感?”
她在小說中加入大量拼音的對話,以此模擬華人移民家庭英語和普通話混著說的語境;也描畫著女兒對父親的愛、怨恨和依賴,這是她私人情感的抒發,卻也符合華人重視家族,重視傳承的心態。


李安“父親三部曲”
作為同樣在美國進行創作的華人藝術家,李安自然也不會對這樣的作品無動於衷。
從“父親三部曲”出發,到在《臥虎藏龍》《色戒》中的打磨和圓融,李安本次迴歸華人題材,將挖掘歷史創傷,直面華人移民史這一原始、沉重、被主流敘事遮蔽的主題。而作品中年輕、銳利而洶湧的力量也將助推他再次出發,丈量電影這片土地。


解構西部精神
私人性是他們的抵抗
這並不是李安第一次將鏡頭轉向西部題材。
在2005年的作品《斷背山》中,他拍攝了壯麗山脈間性少數群體的愛戀,解構西部片的男性氣質與異性戀霸權,並因此斬獲第78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導演獎。


電影《斷背山》
而這一次,《舊金山》解構的是西部片的白人中心主義、英雄敘事與“成功者”神話。
這個關於淘金者的故事中,主角並不是白人男性,不是英雄,而是華人女性,是做家務的人和修建鐵路的人。他們不是征服者,而是逃亡者、求生者。
這片土地一直經歷著物種喪失和環境毀壞,也有華人移民曾喪命在修建鐵路的過程中。然而,這些故事卻少有記錄。
因此,張辰極沒有采用純粹的歷史紀實作品的寫法,不表明具體的年份和地理位置,而將敘述權把控在自己的手中,透過私人性的書寫,允許意識流淌,模糊歷史、記憶和幻想,用個人的情緒和記憶,抵抗歷史對少數族裔和邊緣群體的掩埋。

張辰極自述:“我寫了二十稿,決定將這本書重新構想為一種神話,而非歷史小說。”
她擇取許多神秘而奇異的意象,比如老虎爪印、水牛骨、乾涸的湖泊、乾燥的鹽床,用一種類似於瑪格麗特杜拉斯的語氣,冷峻而略感傷地回溯和講述,美國西部就像遠處群山的淡色陰影,隨著我們的接近,緩緩浮現。
同樣講述著流浪和生存,同樣模糊真實與幻想,也同樣展示著奇觀性的風景,李安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也質疑著講述和記憶的不可靠。
從大海到土地,李安的電影探索進入更加私人、內省和幽暗的領域,解構歷史、探索真實或許將成為這部電影的一大特色。


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蟄伏,是為了更好地迴歸
“
意識僅浮游于思緒的表層,潛意識則在底層波濤洶湧,是我無法明講的主流,只有在夢境或如夢幻的電影裡,自己去找尋解脫的出口。
”
——《十年一覺電影夢:李安傳》
自從2019年《雙子殺手》後,李安已經有六年沒有推出新作。但這並不是他的第一次“中場休息”。
從紐約大學畢業後,李安也曾經歷六年待業時間,在家煮飯、帶小孩,他雖不免自憐,卻一直堅持創作劇本,待在電影圈子裡等待機會,直到憑《推手》和《喜宴》從谷底翻紅。

李安年輕時
停滯帶來的痛苦是真實的,但如果身處困惑之中,急切也只會帶來疲憊和能量耗散,不如停下來蓄力,重新校準機會。
對李安來說,第一個六年是生存與技藝的磨礪期,第二個六年(《雙子殺手》後)更像是大師的困惑與再探索期。
蟄伏,是為了柳暗花明。

李安代表作《臥虎藏龍》
小說中,當主角露西遠離童年的丘陵,第一次回頭,她看見——
“雨後的丘陵像金錠一般閃亮,西邊地平線上盡是層層疊疊的金光。她感到喉嚨一緊。在她鼻子上方、眼睛後面的位置,一陣刺痛向她襲來。”
人們往往要出走後回看,具備一定的地理和情感距離後,才能捕捉一星半點來處的成色。拍攝電影的歷程也是一樣。
作為“東西方文化溝通的橋樑”,李安在電影之路上深耕幾十年,此時歸來“鍊金”,似乎既是休息後的一次回望,也是對拓展創作邊界的挑戰:
在更清晰的視角中,創作者個人的困惑將與歷史創傷相匯。

因此,與其說李安“選中”了《舊金山》,不如說這部小說憑藉其複雜的移民身份議題、沉重的歷史背景、強烈的逃亡與生存主題,以及潛在的視覺奇觀,“召喚”了蟄伏六年的李安,成為他再次出發,再次編織電影之夢的起點。
“我們要如何找到那種超越房產、超越出生地的歸屬感?”
或許,對於這個問題,有一部分的李安會回答:“電影是我的故鄉。”


文、編輯/外灘君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特別企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