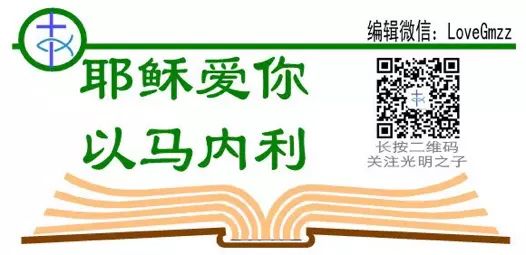當愛情的冒險歷程不再能吸引年輕人,他們又將在何處安放自我?應當如何理解年輕人的壓抑,以及情感的意義與價值?
在新近出版的《情感時代》一書中,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金雯透過研究興起於18世紀的情感小說,梳理了淚水、恐懼與憂鬱的意義與歷史,指出小說潮流的變遷正與時代情感潮流的變化吻合:在感傷文化氾濫時,人們會將熱淚盈眶視為自我標榜的方式,相信淚水能夠表達同情和善意,與他人形成心靈同盟;另一方面,淚水也成了失控的象徵,感傷文化因為可能助長人們——尤其是女性——的自憐自戀的病態而受到詬病。
金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和國際漢語文化學院聯聘教授,研究領域為18世紀英美文學、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受訪者供圖)
書中,金雯梳理了西方的兩類情感觀念史:一類認為情感是身體變化的直觀反應,另一類則認為情感是人們不能知曉、無法完全描繪的身體性力量,威脅著人的主體性與完整性。她指出,情感在啟蒙時期成為所謂“人性”的核心問題——正是因為人具有天然的利他情感,才能擁有強健的道德和審美判斷力,在形成個人主體性的同時維持社會和諧。
她以18世紀小說為例具體分析了啟蒙的情感史。斯特恩的《項狄傳》描寫了諸多憂鬱症狀,憂鬱(melancholy)一詞出現頻率很高,小說中發生的日常事件不斷將虛構人物推向憂鬱,這提示我們,憂鬱並不是這個時期的罕見病症,而是瀰漫於18世紀的英國日常生活的常見精神狀態。18世紀晚期,感傷小說與哥特小說盛極一時,憂鬱和恐懼成為小說傳遞的主要情感,這兩種情感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超出了啟蒙時代對掌握人類科學的樂觀信念。
呈現同情、憂鬱等情感的18世紀西方小說不僅促進了現代文學的形成,也與同時代的諸多歷史問題對話,對廢奴運動與女性地位提升等文化變革都產生了影響。情感對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生活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就像書中引言所論述的,“社會性依靠的不僅是意見,更多是結構和諧的感受。”
介面文化:在此前的一次活動上,你談到自己觀察到了年輕人情感恐懼的現象。你如何理解這個現象?
金雯:我在我的師門裡面的確發現,今天“90後”和更年輕的群體對於傳統模式的情感關係非常抗拒。他們在生活各個層面都追求穩定,儘量避免會對自己的生活帶來擾動、不可控的情感事件。這種傾向與經濟下行的壓力和社會上人們對穩定職業的普遍追求有關,也與年輕人在情感經驗和情感教育上的匱乏有關。對“70後”“80後”來說,追求偉大愛情的歷險有很強的吸引力,可今天的年輕人會嗤之以鼻。
今天的大眾文化內含一股強大的反浪漫主義潮流。我們過去幾代人心心念念保爾和冬妮婭的愛情,或者在金庸和瓊瑤描寫的純愛氛圍中長大,而如今,b站等媒體平臺中的許多內容致力於揭示意識形態對人們情感的操控,致力於批判新自由主義和自由市場的洗腦作用,拒絕透過私人情感得到生命救贖的幻覺,很多年輕人相信所謂浪漫愛情只不過是商業伎倆,或加強男權制的話語策略,屬於虛假意識形態的範疇。今天年輕人相信的情感雞湯文與他人的愛無關,崇尚的是無堅不摧的自我之愛。年輕人對愛的幻滅,或者對穩定的以浪漫愛為基礎的關係的幻滅,已經成為他們日常生活政治的一部分。對這個現象我是理解的,並不反對,但我也有些不同意見,希望以後有更多機會與年輕朋友們交流。
《情感時代》
金雯 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4-1
介面文化:這裡所說的年輕人求穩是一種自我壓抑的行為嗎?包括壓抑恐懼、憂鬱相關的負面情緒?
金雯:很多人看上去很超脫、很堅硬,看透了世間的情感謊言,但其實內心是軟的,非常需要光亮和愛的關注。很多人聲稱自己已經看淡一切:“已經沒有任何人能引發我的情緒,安穩地生活就可以了,不想每天處在巨大的壓力下,開開心心地就好。”但這種話語流露的是對獲得他人認可和理解的放棄。躺平不是思想上的鬆弛,而是內心恐懼和絕望的偽裝,當人們感覺無論如何努力也不可能達到“階層躍升”的夢想,不可能討得父母和長輩的歡心,這種錐心的痛感往往會以逃避和享樂主義的形式暫時地緩解自身。
很多人(不論是我這個年代的人還是今天的年輕人)都會出現“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狀態,這可以認為是對自己身體性需求——包括愛、興趣和其他情感滿足——的壓抑(repression)。不過,躺平和求穩都只是暫時的,有壓抑就會有反彈。
在19世紀,女性中常見的歇斯底里症,即瘋狂的情緒起伏,就是壓抑的症候,內心需求和身體需求長期被壓抑,在一定的時刻就會引發躁狂的行為。就像福樓拜《包法利夫人》裡追求浪漫愛的女人,身體不能得到愛情的滋養,只能透過讀小說來釋放最強烈的身體需求。20世紀的文壇充滿了創傷文學,告訴我們被壓抑的有關痛苦往事的記憶會以夢境和閃回的方式重現,在重現之時給人帶來巨大的負面情感。所以,一個普遍求穩的社會也一定是精神疾患比較普遍的時代,我們只能不斷透過社會層面的交流和對話來使之得到緩解。
介面文化:那麼恐懼呢?尤其是《情感時代》寫到的哥特小說傳遞的恐懼,是不是與今天的恐怖片有點類似?
金雯:恐懼跟壓抑不太一樣,是很容易診斷的情感,但它與恐懼也有共性,兩者都與壓抑有關。所謂哥特小說,的確可以認為是今天恐怖片的一個前奏。第一部哥特小說《奧特朗托城堡》建構了一個復古的場景:中世紀古堡中出現了一系列怪異現象,一個頭盔從天而降把繼承人壓在下面,鬼魂在四處出沒,好像過去累世的家族罪惡終於受到莫名力量的懲罰。
小說渲染的恐懼躍然紙上,但到底指向對什麼具體事物的恐懼卻是不清晰的。18世紀與後世讀者在閱讀時很可能把恐怖事件與自己的宗教體驗和日常經驗勾連,對小說描寫的恐懼做出具體的闡釋,藉此將小說的“無意識”和自己內心隱藏的恐懼揭示出來。這告訴我們,恐懼和壓抑一樣,不是一種直白的情感,源自我們被壓抑的憤懣和不滿,很少能被直接言說,也是經由小說和其它文化表達才得以顯現和成型的“不可名狀之物”。今天我們讀恐怖小說,實際上是在捕捉作者發出的“求救呼號”,嘗試理解文字隱含的深層恐懼,也同時理解自己的不安。
我在書裡想說,不論是憂鬱還是恐懼,18世紀的“否定性情感”指向了啟蒙這個自詡為進步的時代的軟肋。“理性時代”的文化精英投射著人們透過自己理性和思辨的力量構築和諧生活的願景,但哥特小說和各類情感小說就是來摧毀這種信念的。理性很難創造出令每個人安居樂業和諧的秩序。每個人都壓抑著對外在環境壓迫的不滿,長此以往,文化中便飄蕩著許多受害者的幽靈,恐懼和憂鬱言說的都是人對自己有限性和無助感的模糊體認。
金雯:恐懼的發生源於具有壓倒性優勢、隨時可以肢解你的外部力量——法國大革命就引發了許多歐洲人的恐懼,他們發現,當民眾的暴力狂潮襲來,個人會被撕碎。
憂鬱的生成需要更長的時間,常常像毒素一樣慢慢在人的體內積累,最終摧毀人的精神。《項狄傳》裡的叔叔託庇就是憂鬱的代表,他從九年戰爭(發生於1695年的戰爭,對壘雙方是法國與包括英國在內的反法同盟)退役,雖然受了傷,養了三四年,差不多也恢復了,但始終沒有從戰爭的陰影中走出來,卻又不知道是為什麼,於是他想,是不是多掌握一些軍事意識、在家做軍事演練,對戰爭就更有掌控感?但後來越學越迷糊,陷入了想要超越困境卻愈發無法自拔的迷霧。憂鬱的起因是駁雜的,往往由突發事件或長期精神虐待共同造成。
《項狄傳》
[英]勞倫斯·斯特恩 著 蒲隆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0-7
介面文化:剛才講到掌控和否定性情感之間的衝突,否定性的情感好像在提醒人們不可能完全獲得掌控感?
金雯:對,否定性情感否定的就是人的掌控力。一來,我們很難為這種情感命名,憂鬱和恐懼都只是大致的情感符號,說明人類語言無法揭示情感現象的具體物件或複雜維度。二來,這些晦澀情感的延續會持續削弱人們對自身和外界環境的掌控力。在18世紀哲學家和精英文人的想象中,情感是人之為人的理由,伏爾泰改寫《趙氏孤兒》就試圖說明反抗強權、維護個人尊嚴的情感是人性的普遍核心。不過,這個時代的人也已經發現,人之所以不能完全為人,也是因為情感。如果無助不會引發不可名狀的情感,人是不怕渺小的,我們對自己的無助是如此的敏感,這就是人的悲劇性之處。
介面文化:眼下,漠視個體無助的所謂“鈍感力”頗為流行,意思是隻要躺得夠平就沒有人能戰勝我。
金雯:這是一種自我療愈,但人真的能做到心如止水嗎?做不到的。如果能做得到,我們今天所有人都能靠自我暗示就健康起來。這是把診療神話化,診療只有配合社會結構的變化才能有效。
介面文化:情感不可能是完全是完全私人的,而是具有媒介性的。在這一點上,情感小說有點像今日的電視劇嗎?
金雯:有異曲同工之處,或者說情感小說是通俗劇集的前身。小說潮流的變遷跟情感的潮流變遷相吻合,也使得女性作者和讀者的數量大大增加。18世紀40-60年代這段時間,感傷小說開始興起,在60-80年代間蓬勃發展。惠海峰老師曾做過詞頻統計,在整個18世紀,60-80年代間“哭”這個詞出現的機率最高。
氾濫的眼淚似乎告訴我們,人們同情弱者和有道德操守的人,人們有天然的美德,正如亞當·斯密設想的那樣,人們可以達成情感共識,自發地構建有序社會。可18世紀的現實並非如此。18世紀末,哥特小說大行其道,說明此時恐懼已經成為更為強勢和顯像的情感,法國大革命及其催生的大規模暴力進一步加深了封建制度陰影以及性別政治、金融災難等社會因素已經催生的恐懼。一種小說型別的興起當然有偶然因素,但要引起風潮,還是需要有情感基礎。
介面文化:詞頻統計“哭”出現的機率最高,這個時代也因此被稱為“情感時代”,可是,淚水難道是這個時代發明出來的嗎?
金雯:淚水早就在文學中出現了。在古羅馬古希臘的史詩中,就有許多男性人物的淚水:阿喀琉斯為戰友帕特洛克羅斯之死流下熱淚,特洛伊王子赫克托爾去世後父王前來懇求阿喀琉斯歸還屍身,阿喀琉斯也因為想到自己的父親而抽泣。不過,這時候的熱淚——尤其是男性的淚水——並不被鼓勵,柏拉圖《理想國》對詩人的憎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像荷馬這樣的詩人會激發情感的外在顯現。
這個情況很快有所變化,古羅馬史詩《埃涅阿斯紀》就已經對埃涅阿斯的感物之淚做了正面描繪,中世紀詩歌和故事中的淚水就更為普遍。中世紀的人們生活在人類有罪觀念的陰影下,淚水被賦予了洗刷肉身和精神痼疾的神聖功能,基督教文化的情感世界為世俗的眼淚奠定了基礎。
到了17和18世紀,歐洲人對情感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相信自然情感是可以為理性和道德建設服務的,而圖書市場的擴大也為情感的構建、放大和傳播提供了便利。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狄更斯《老古玩店》中年幼的女孩小耐爾在去世前安慰其外祖父,這純真的一幕讓人們動容,同樣,美國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充斥著對奴隸悲慘境況的煽情式描寫。
19世紀的感傷小說仍然是社會變革和商業推廣的工具。這個情況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就消失了,作家、藝術家、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和早期神經科學家都更為集中地注重“否定性情感”,將隱秘心理動因的書寫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煽情和感傷開始與“經典文學”絕緣。總之,18世紀出現的煽情文學,不能說是歷史上唯一描寫和引發熱淚的文學,但這個時代對熱淚的態度的確與眾不同。
介面文化:熱淚文化、情感氾濫與社會變革之間的這種關係,也適用於中國嗎?
金雯:是的,清末民初的中國也出現了寫情文學,一類是“鴛鴦蝴蝶派”的因男女情愛引發的悲劇,比如《玉梨魂》《劫餘灰》,還有一類是有一定政治傾向的情感小說,比如林紓翻譯的《黑奴籲天錄》(即《湯姆叔叔的小屋》)。林紓在這部譯作的序言中表示了對中國政府漠視在美華工悲慘遭遇的不滿,希望自己的譯文具有激發中國讀者與非洲奴隸同仇敵愾之情的功能。在其影響下,後來出現了一批反映華工境遇、具有鮮明政治訴求的感傷小說。
《黑奴籲天錄》
[美]斯土活 著 林紓 譯
商務印書館 1981-11
寫情小說與媒介文化的發展相連,與此時大眾文化的勃興互為因果,也與具有變革抱負的仁人志士使用大眾媒介實現政治訴求的意圖相關,這與18和19世紀英語世界及法國很相近。19世紀的日本也有類似現象,森鷗外等浪漫主義小說作者同樣引發了大量的哭泣和文化反思。
介面文化:講到情感和媒介的關係,有時候也會驚訝於當下人們的情感需求之強,這會表現在影片的彈幕裡,即使是看吃播也會發出尋求同好的彈幕。
金雯:大眾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試圖滿足人們自戀的情感,以此轉化為成功的商業模式。18世紀感傷小說氾濫時,人們以流淚標榜自身的道德水準——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用善心來感動自己。事實上,當時就有人意識到這點,批評仁慈之舉和熱淚。
18世紀初法國作家馬裡沃有一部小說叫《同情的奇怪效應》,專門設計暴力色情和悲情的段落,用來刺激讀者的情感,並反諷他們同情中內含的自戀。不過,話說回來,大眾媒介也可以被創造性地使用,促進每一位觀眾梳理、挖掘自身被掩蓋和偽裝的晦暗情感。
我不久前在一次飛行旅途中終於看了賈玲編劇的《你好,李煥英》,印象中這很可能是一部庸俗的煽情電影,但看了以後我覺得其中煽情的點其實非常高階,觀眾很難知道自己為什麼流淚,在反思淚水的過程中會有很大的智識滿足,也會因為更透徹地瞭解自身情感而疏通內心。電影中有一個舞臺表演場景,沈騰扮演的廠長兒子和賈玲扮演的穿越到媽媽年輕時代的女兒表演二人轉,試圖引發觀眾的歡笑,兩人出盡洋相還是遭遇冷場,卻在狼狽不堪顏面盡失的那一刻突然達成了自己的願望,臺下爆發出鬨堂大笑,賈玲在影片中的媽媽也開懷起來。然而,此刻電影的觀眾卻只想流淚,被自己這突如其來的淚水驚訝。
這個場景內外的情感深邃複雜極了,這兩個人物勉強出醜的羞恥之情和不惜折損尊嚴只為博所愛之人一笑的無私情感互相交織,既猥瑣又崇高,喜劇在這一節點無聲地向悲劇轉折。這樣的大眾文化我不反對,反而很欽佩。
介面文化:你在《情感時代》裡寫道,啟蒙時代一方面承認情感的重要性,構建以身心關係為基礎的普遍人性,另一方面也滑向了為人類劃分等級的理論工程。可以再講述一下情感與啟蒙的關係嗎?
金雯:現代社會的誕生一定會伴隨情感地位的提升。人們要自主地構建美好的生活,就必須要使得情感為改善社會秩序所用。啟蒙時期的情感理論試圖挖掘和肯定人的普遍善意,以此為人類社會奠基。亞當·斯密認為,同情是人共有的情感,是人類所有情感的基底,所謂同情就是透過觀察想象再現他人的能力,也同時是與他人保持情感強度一致的天然傾向,同情是“道德情操”的最根本體現,是普遍道德觀念的前提。斯密的情感理論與他的自由市場理論一致,正如市場被不可見的手調控,人和人之間也被不可見的天然傾向調控。
另一方面,雖然啟蒙思想構建了普遍人性,卻也不得不面對全球文化的多元性,在文化多元性的語境中重新審視普遍人性理論。在康德早期的《關於美感與崇高感的觀察》中,康德對不同民族的情感和審美稟賦做出了區分,這種思想在他後續的著述中被大大弱化,但仍然留下了許多痕跡,也使得康德不僅成為啟蒙普遍主義——為人類社會整體制定規範性的道德、審美和法權觀念——的旗幟,也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現代種族思想。
當然,18世紀對各民族文化多元性的解釋並不單一,法國的孟德斯鳩認為民族差異主要與政治、法律制度差異有關,不能被歸結於某種自然的情感稟賦。但是,無論怎麼說,18世紀的普遍主義和民族差異論之爭與情感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採寫:董子琪,編輯:黃月、潘文捷,未經介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