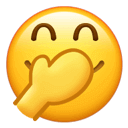新刊出爐!點選上圖,一鍵下單↑↑↑
「沒有朋友的青春期」
2024年底,我們的《少年新知》雜誌收到一則中學生投稿,標題叫《原來我是“人機”啊?》。作者是一位初中生,她講述了自己在班級裡的人際交往情況:她從初一開始就沿用了一種“低耗能”的社交模式,像遊戲裡的NPC(非玩家角色)一樣,不融入任何小團體,選擇和班裡的所有人保持點頭之交。
她在文章裡引用了一條影片“教你在學校如何變人機”,我找到了那條影片,同時在留言區找到了更多和她一樣認為自己是“校園人機”的孩子。他們的處境大都與投稿者類似,有人在學校的11個小時裡,除了上課回答問題,幾乎不主動和人說話,全班48個同學,唯一可以算朋友的人是個“體育課搭子”,上課自由分組的時候他們可以一起練習。除此之外,她可以整天都待在座位上,一言不發。
根據發展心理學的理論,處於青春期的中學生,正是最需要友誼和同伴關係的階段。可是為什麼這些孩子主動退出了校園社交圈,甚至甘心做一個沒有感情的“非玩家角色”?

但這種略顯極端的選擇,似乎又帶有某種合理性。2024年,我們做過兩期封面,一期是討論大學生人際交往狀態的《寂靜的一代》,一期是研究小學生卡牌遊戲的《小學生如何社交》。在當時的採訪中,我們已經隱隱感覺到,孩子們的校園生活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小學生們傳統遊戲的時間、空間都被大大壓縮,不得不選擇安靜的桌面遊戲,作為自我發展受限的代償。而到了大學階段,很多本科生不願意與人建立真實的社交聯絡,他們不熱衷談戀愛和結交摯友,在課堂上也不願跟老師互動,寧願在虛擬人和“搭子”身上尋找情感滿足,看似自由、自主,但也孤獨、隔離。
那麼,在處於這二者之間的中學校園裡,究竟在發生著什麼樣的變化?如今這些處於青春期的孩子們,正在如何度過這個“自我同一性發展”的關鍵階段,在如何與同伴交往,如何去建立友情,乃至去探索正在萌芽中的愛情?
令我意外的是,在前期採訪中,當我向許多相熟的教師、班主任和家長提出這個問題時,他們最初的反應常常是茫然的。比起孩子們的社交生活,他們更關心班級的學習氛圍、教學質量和考試排名,如果一定要聊聊這個年紀學生的自我發展、情感需求和同伴關係,他們有時會不知不覺繞回幾個常用的詞彙:“攀比”“網癮”“搞小團體”……
但在學生那裡,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個未曾體驗過的世界。我的同事駁靜花了不少時間和孩子們聊天,發現作為真正的“網際網路原住民”,他們已經自然地習慣了在虛擬空間尋找友情的替代品。他們打遊戲,寫作業要“連麥”,實在找不到人就在B站找一間正在直播的虛擬自習室作背景。他們透過喜歡的遊戲、明星、電影、綜藝,在網路上結成各種“同好”,還在網際網路上共同創作、彼此分享、互相點贊,甚至可以與遠隔千里,素未謀面的朋友“官宣閨蜜”。

家長和老師眼中現實的校園生活,似乎正在和孩子們感受到的世界發生脫離。
也有敏銳的教師感受到了這一點。江蘇省崑山市葛江中學的教師於潔是一位從教33年的“老班主任”,去年剛剛獲得中宣部和教育部評選的全國“最美教師”稱號。她常常在自己的微信公號裡為老師們答疑,2024年,她給一位回信老師:“如今的學生和之前的不一樣了,他們很多時候生活在虛擬世界,在那裡,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人際交流和生活方式……教育變得越來越艱難,這是很多老師的共識。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學生和老師生活在了兩個世界。”

那麼,在數字分身之外,孩子們肉身所處的那個世界是什麼樣的呢?於潔也向我分享了一個觀察。這些年每接一個新班級,她都會給孩子們每人發一本名叫“家校之橋”的小冊子,在裡面每天給同學們寫信,再請他們回信給自己。也是在這些回信日記裡,她發現,孩子們最常提到的詞是“孤獨”。
孤獨感的來源是多種多樣的。首先是校園環境的變化。採訪中,一位正在讀高一的學生告訴我,從初中開始,他們學校的教學樓外牆上就懸掛著一條紅色橫幅:“入校即靜,入座即學”。操場上空空蕩蕩,走廊不允許隨意駐足,教室裡的桌子彼此分離,孩子們沒有同桌,在教室裡很少交談,即使有聊天,話題也大都圍繞學習展開。
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副教授徐凱文接觸過大量休學的孩子,他的一位諮詢者向他描述過一個場景,說每到午飯時間,自己打了飯,就會找一個沒人的地方獨自進餐,有時甚至要在樓梯的角落裡才能吃得下飯。徐凱文問他為什麼不在食堂裡好好吃飯,他說,在食堂裡吃飯所有人都在說學習的事,他聽了特別難受。有一次他和同學聊天聊到各自的生日,對方瞭解到他比自己大幾個月時,第一反應卻是:“你比我大這麼多,怎麼學習成績還不如我?”

我的同事王怡然也採訪了許多一線的老師,她發現,高強度的學習與激烈競爭使一些學校的教育維度趨向單一,一些少年們自由生長和產生聯結的時間與空間也隨之被高度擠壓。同齡人本該在校園裡建立的友善夥伴關係,被互相競爭所取代。
單一的評價體系也影響到了學生的社交環境,一位在初中兼任心理教師的班主任向我描述,幾乎每個班級都存在一個“社交生態位”,“或許在小學的時候,孩子們這方面的概念還不強烈,但只要在初中的班級裡待上一週,你是班幹部,我是‘平頭百姓’,你是‘好學生’,我是‘拖後腿的’,你受同學喜歡,我是‘小透明’,各自在什麼位置,清清楚楚”。固定的生態位,意味著固定的社交表現,很多感受到自己“透明狀態”的孩子,也會隨之出現角色賦予他/她的行為。
更重要的是,我的很多受訪者都談到,在高壓力、強監管的現實與網際網路資訊對撞之下,許多青春期的孩子都陷入了“意義危機”。他們無法認同父母和老師許諾的“吃苦學習,改變命運”的價值觀念,又無法獨自處理成長和發展中面對的現實問題,因而陷入難解的困境。比如有老師提到,當學生問他,“這樣拼命努力,考上大學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嗎?”“人工智慧已經可以做這麼多事情了,我們這樣早出晚歸、死記硬背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時,老師也很難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我們是不是正在用指向過去的方法,教育著指向未來的孩子?
這種感受是我在去年參與《寂靜的一代》封面時開始出現的。那時一群“00後”的大學生告訴我,他們的初戀很多都發生在高中階段。而在我的青春回憶裡,想在高中談戀愛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只要回到家,男生想再約我出門就必須撥打家裡的座機,父母一接電話,邀約就很難實現了。但“00後”是在青春期就擁有個人手機和微信的一代人,即使離開學校,也能和朋友們24小時保持聯絡,“10後”接觸網際網路的社交方式就更早了,很多孩子從出生開始,就已經開始與螢幕互動,與網際網路上的朋友建立連線,在他們那裡,交往中的距離、時間、陌生與否、線上線下的定義是完全不同的。
這也是這次採訪中屢次突破我們“認知邊界”的事情。就像駁靜在採訪中發現的,被上一代人定義為“虛擬”的網路空間裡,青春期的孩子們獲得的是一種真實的從屬於某個共同體的愉悅,這些基於興趣的虛擬社交,也並不像我們“大人”想象中那樣浮於表面。當現實生活中的同伴關係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時,孩子們仍在另外的空間尋找連線、自我成長的可能性。
不過,這種看似自由自主,不受監管和限制的情感連線中,也隱藏著相當大的風險。尚未成熟的孩子們對隱私和自我保護的意識往往不夠清晰,與同伴交往的能力也仍需要練習,青春期的特質疊加特殊的環境,讓他們的網際網路交友“來得快,去得快”,嚴重的時候也會影響個人自我認知的成長和完善。
一位高中語文老師告訴我,她發現,當社交媒體加入後,校園霸凌的範圍也擴充套件到了網路上,“現在我們講霸凌,不只是我在學校裡邊欺負你,說你的壞話,給你起外號。有時候可能我們全年級的學生都在一個群裡,如果我在這裡釋出一些負面的霸凌性的言語,其影響力也會變得更廣。因為孩子們是要把影響加之於‘我在乎,對方也在乎’的人身上,這種跨越線上線下的霸凌傷害性也會更大。”

成人與青少年、線下與線上、校園與網路,逆向而行的世界之間需要溝通和對話的橋樑。談到校園生活的種種壓力,我們很多人都會聊到給孩子適當“鬆綁”、提供更多的活動和交友空間。這次的採訪卻讓我意識到,在“鬆綁”之外,一個值得信任且負責任的成人,能夠為青春期的孩子提供相當重要的情感支援。這個人可以是父母,也可以是老師,當這種連線被建立起來,孩子們正在形成中的自我才能發展得更加穩定和強大,正如我們的約稿作者訾非老師在文章中所說,青少年發展就像火箭發射的過程一樣,最先起到推進作用也是最先被拋下的是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然後是與老師的關係,然後是與同伴的關係……最終留下這顆“衛星”,憑著自己的動力飛翔。

「沒有朋友的青春期 」
點選下圖,一鍵下單
本期更多精彩
| 封面故事 |
-
沒有朋友的青春期(魏倩) -
教師眼中:青春共同體如何消逝(王怡然) -
學生自觀:線上線下交友生態(駁靜) -
在網上交朋友,會讓我更快樂嗎?(魏倩) -
“我是如何熬過初中三年的”(駁靜) -
“10後”戀情:不親密、不激情的“科學戀愛”(吳麗瑋) -
“獨自玩耍”的想象力(段弄玉) -
“男孩文化”下,那些被壓抑的渴望(段弄玉) -
子厭父業未嘗不是好事(訾非)
| 經濟 |
-
市場分析:房租持續下降,會帶來怎樣的影響?(謝九)
| 社會 |
-
時事:加沙停火與人質交換:和平遠未到來(程靖) -
調查:被撞沉的客船(覃思 彭麗)
-
看展:馬可·波羅的見證(蒲實) -
文史:盛京之閣(卜鍵)
| 專欄 |
-
邢海洋:機器人的腳與手
-
袁越:多動症的新研究 -
張斌:運動員需要全新安全觀 -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