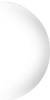1973年,我們一家從綠意盎然的Glen Iris搬到了Burwood,那時候我們沒意識到房地產風潮會發生多麼劇烈的變化,這個決定在當時看起來再合理不過。
我父母當時是為了換一套三居室、維護成本低的磚瓦外牆住宅,才放棄了我們那棟老舊的加州式木板平房。
儘管我一開始還挺興奮,但我們的新家從來就不是中世紀風格的高光代表。那幾盞1964年仿金葉吊燈、帶金屬斑點的浴室梳妝檯、滿牆的碎花桌布,都只是繁複審美的落後象徵。
相比之下,我舅舅後來在Vermont South買的房子看起來時髦多了:高聳的拱形天花板、樸素大地色調、仿鄉村風的吊燈,還有一大片蓬鬆的橘色地毯。

實際上,和那些依靠傳統魅力維持身價的成熟社群不同,Burwood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所謂“最新最棒”的東西來者不拒——儘管這些潮流往往曇花一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Burwood Skyline——澳洲第一家汽車影院,於1954年建成,位置就在如今迪肯大學那座現代教育大教堂的斜對面。在1983年之前,你都可以沿著Burwood Highway開車去看場合家歡電影。那時正值嬰兒潮,這座能容納600多輛車的影院生意紅火。

而如今,那片地已經變成了Suburban Rail Loop的施工現場。
我來自一個保守的移民家庭,從未去過汽車影院,但幸運的是,附近的Kmart成了另一處地標——也是澳洲的第一家。

這家Kmart於1969年開業,建築低矮、線條簡潔,是當年零售業的一張名片。我在那裡買過人生中第一張唱片。在被講究的咖啡文化“逼退”之前,Kmart還有一家名叫Holly’s的自助餐廳,配著美式餐廳風格的卡座,曾是本地的一道風景。

隨著地價飆升,這家Kmart如今已被大規模翻修。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Kmart門前那片戶外停車場,在夏天被太陽曬得滾燙,冬天則是風沙肆虐,遼闊得彷彿沒有盡頭。

對沒車接送的孩子來說,更近的“冒險地”是對面RSPCA旁的本地商鋪街。那時候,一分錢可以買兩顆糖,像現在看來“政治不正確”的Big Boss雪茄糖,或者叫Fags的模擬香菸糖,都能買到。那時還可以買到鞭炮,小孩們沒事就往彼此的口袋裡塞著玩。
不過,Burwood也確實有不少限制。沒有公共圖書館,沒有酒吧,一家人很容易在這裡“住到膩”。要想購物,就得擠上晃來晃去的公交,前往附近的Box Hill。儘管那時的Box Hill還不是如今這個迷你CBD,但在當年,那裡就是我們“普通郊區生活”的中心。

1980年之前,我一直得穿那種在折扣店買的無名牛仔褲,心裡特別不服氣。但在1980年,我終於朝聖般地去了Box Hill Plaza,在Just Jeans那間幽暗、有著毛絨地毯試衣間的店裡,買下了人生第一條夢寐以求的棕色燈芯絨Levis牛仔褲。當它和一雙麂皮沙漠靴搭配在一起的那一刻,我花了23澳元,終於收穫了少年身份認同的入場券。
然而在回家的路上,我也為離開Burwood這個“安全區”付出了代價。在地面公交總站等車時,一個面帶兇相的人突然朝我臉上揮了一巴掌。他穿著緊身、高腰的牛仔褲和一件貼身的開衫,逼我把手裡的土豆餅讓出來,而我拒絕了。
多年後,我在紐約街頭都沒遇到過類似的事,每次想起這段經歷,都覺得諷刺得很。坐在母親家飯廳的靜謐之中,我不禁反思:像“dormitory suburb”(宿舍型郊區、睡城)這種說法,就是為Burwood量身定做的。而我,也確實快睡著了。

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在悄然影響著這裡。曾經充滿孩子喧鬧聲的街道,如今成了若隱若現的記憶。許多當年的學校早已關閉,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不斷湧現的聯排公寓和被忽視的老舊合租屋,擠滿了迪肯大學的學生。
多年後,隨著旅程的結束,我對Burwood的安靜與平淡產生了新的理解與欣賞。
當母親搬進養老院後,留給我的,是她那個樸素老家的回憶,還有我對這個默默無聞郊區的點滴印象。儘管家裡後來也曾短暫經歷過80年代的粉色裝修潮,但大部分老式裝潢都還保留著,滿滿是她珍視一生的物件。
如今她已年過九旬,仍常常說:“那房子還在那裡,等我回去。”
以上這篇文章來自《The Age》的專欄:我的郊區生活系列,邀請墨爾本各個郊區的普通人講述自己所在郊區的生活。
此前我們已經先後分享過Box Hill、Glen Waverley、Doncaster、Mt Waverley的生活。
大家還想看哪個郊區的生活,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來源:The Age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閒話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