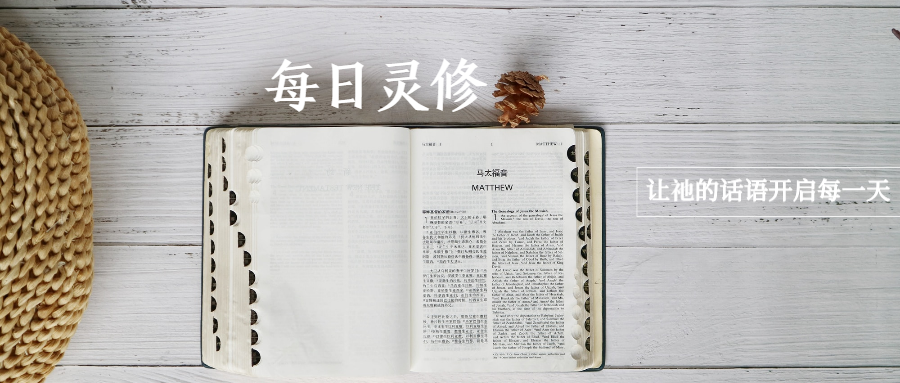梁文鋒:舊世界分崩離析,新時代正在光速到來
來源/中制智庫、王育琨頻道
2025年2月9日


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的60條思考:
1.我們做大模型,跟量化和金融都沒有直接關係。我們要做的是通用人工智慧,也就是AGI。
2.語言大模型是通往AGI的必經之路,並且初步具備了AGI的特徵,所以我們從這裡開始。
3.我們不會過早設計基於模型的一些應用,會專注在大模型上。從長期看,大模型應用門檻會越來越低,初創公司在未來20年任何時候下場,也都有機會。我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不做垂類和應用,而是做研究,做探索。
4.我們理解人類智慧的本質就是語言,人的思維就是一個語言的過程。你以為你在思考,其實可能是你在腦子裡編織語言。這意味著,在語言大模型上可能誕生出類人的人工智慧(AGI)。
5.只做復刻的話,可以在公開論文或開原始碼基礎上,只需訓練很少次數,甚至只需finetune(微調)一下,成本很低。而做研究,要做各種實驗和對比,需要更多算力,對人員要求也更高,所以成本更高。
6.我們希望更多人,哪怕一個小App都可以低成本去用上大模型,而不是技術只掌握在一部分人和公司手中,形成壟斷。大廠的模型,可能會和他們的平臺或生態捆綁,而我們是完全自由的。
7.從商業角度來講,基礎研究是投入回報比很低的。我們比較確定的是,既然我們想做這個事,又有這個能力,這個時間點上,我們就是最合適人選之一。
8.從最早的1張卡,到2015年的100張卡、2019年的1000張卡,再到一萬張,這個過程是逐步發生的。很多人會以為這裡邊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商業邏輯,但其實,主要是好奇心驅動,對AI能力邊界的好奇。
9.對很多行外人來說,ChatGPT這波浪潮衝擊特別大;但對行內人來說,2012年AlexNet帶來的衝擊已經引領一個新的時代。AlexNet的錯誤率遠低於當時其他模型,復甦了沉睡幾十年的神經網路研究。雖然具體技術方向一直在變,但模型、資料和算力這三者的組合是不變的,特別是當2020年OpenAI釋出GPT3後,方向很清楚,需要大量算力。那之後,我們有意識地去部署儘可能多的算力。
10.一件激動人心的事,不能單純用錢衡量。就像家裡買鋼琴,一來買得起,二來是因為有一群急於在上面彈奏樂曲的人。
11.人工成本是對未來的投資,是公司最大的資產。我們選的人相對樸實一點,有好奇心,來我們這裡有機會去做研究。大廠很難單純去做研究,做訓練,它更多會是業務需求驅動。如果不能很快應用,大廠不一定能持續堅持,因為它更需要看到結果。
12.我們招人有條原則是,看能力,而不是看經驗。如果追求短期目標,找現成有經驗的人是對的。但如果看長遠,經驗就沒那麼重要,基礎能力、創造性與熱愛等更重要。
13.我們的核心技術崗位,基本以應屆和畢業一兩年的人為主。做一件事,有經驗的人會不假思索告訴你,應該這樣做,但沒有經驗的人,會反覆摸索、很認真去想應該怎麼做,然後找到一個符合當前實際情況的解決辦法。
14.我們招人的條件是熱愛,這些人的熱情通常會表現出來,因為他真的很想做這件事,所以這些人往往同時也在找你。
15.我們的考核標準和一般公司不太一樣。我們沒有KPI,也沒有所謂的任務。
16.創新需要儘可能少的干預和管理,讓每個人有自由發揮的空間和試錯機會。創新往往都是自己產生的,不是刻意安排的,更不是教出來的。我們交給員工重要的事,並且不干預他。讓他自己想辦法,自己發揮。
17.招人時確保價值觀一致,然後透過企業文化來確保步調一致。當然,我們並沒有一個成文的企業文化,因為所有成文的東西,又會阻礙創新。更多時候,是管理者的以身示範,遇到一件事,你如何做決策,會成為一種準則。
18.按照教科書的方法論來推導創業公司,在當下,他們做的事,都是活不下來的。但市場是變化的,真正的決定力量往往不是一些現成的規則和條件,而是一種適應和調整變化的能力。很多大公司的組織結構已經不能快速響應和快速做事,而且他們很容易讓之前的經驗和慣性成為束縛,而這波AI新浪潮之下,一定會有一批新公司誕生。
19.最讓我們興奮的是去搞清我們的猜想是不是事實,如果是對的,就會很興奮了。
20.信仰者會之前就在這裡,之後也在這裡。他們更會去批次買卡,或者跟雲廠商籤長協議,而不是短期去租。
21.創新是昂貴且低效的,有時候伴隨著浪費。所以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才能夠出現創新。很窮的時候,或者不是創新驅動的行業,成本和效率非常關鍵。OpenAI也是燒了很多錢才出來的。
22.這個世界存在很多無法用邏輯解釋的事,就像很多程式設計師,也是開源社群的瘋狂貢獻者,一天很累了,還要去貢獻程式碼。類似你徒步50公里,整個身體是癱掉的,但精神很滿足。
23.不是所有人都能瘋狂一輩子,但大部分人,在他年輕的那些年,可以完全沒有功利目的,投入地去做一件事。
24.我們的大模型服務降價只是按照自己的步調來做事,然後核算成本定價。我們的原則是不貼錢,也不賺取暴利,在成本之上稍微有點利潤。
25.搶使用者並不是我們的主要目的。我們降價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探索下一代模型的結構中,成本先降下來了,另一方面也覺得無論API,還是AI,都應該是普惠的、人人可以用得起的東西。
26.如果目標是做應用,那沿用Llama結構,短平快上產品也是合理選擇。但我們的目的地是AGI,這意味著我們需要研究新的模型結構,在有限資源下,實現更強的模型能力。這是scale up到更大模型所需要做的基礎研究之一。除了模型結構,我們還做了大量其他的研究,包括怎麼構造資料,如何讓模型更像人類等,這都體現在我們釋出的模型裡。
27.最重要的是參與到全球創新的浪潮裡去。過去很多年,中國公司習慣了別人做技術創新,我們拿過來做應用變現,但這並非是一種理所當然。這一波浪潮裡,我們的出發點,就不是趁機賺一筆,而是走到技術的前沿,去推動整個生態發展。
28.隨著經濟發展,中國也要逐步成為貢獻者,而不是一直搭便車。過去三十多年IT浪潮裡,我們基本沒有參與到真正的技術創新裡。我們已經習慣摩爾定律從天而降,躺在家裡18個月就會出來更好的硬體和軟體。但其實,這是西方主導的技術社群一代代孜孜不倦創造出來的,只因為之前我們沒有參與這個過程,以至於忽視了它的存在。
29.大部分中國公司習慣follow,而不是創新。
30.創新的成本肯定不低,過去那種拿來主義的慣例和過去的國情有關。但現在,無論中國的經濟體量,還是位元組、騰訊這些大廠的利潤,放在全球都不低。我們創新缺的不是資本,而是缺乏信心以及不知道怎麼組織高密度的人才實現有效的創新。
31.過去三十年,我們都只強調賺錢,對創新是忽視的。創新不完全是商業驅動的,還需要好奇心和創造欲。我們只是被過去那種慣性束縛了,但它也是階段性的。
32.在顛覆性的技術面前,閉源形成的護城河是短暫的。即使OpenAI閉源,也無法阻止被別人趕超。所以我們把價值沉澱在團隊上,我們的同事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成長,積累很多know-how,形成可以創新的組織和文化,這就是我們的護城河。
33.開源,發論文,並沒有失去什麼。對於技術人員來說,被follow是很有成就感的事。開源更像一個文化行為,而非商業行為。給予是一種額外的榮譽,一個公司這麼做也會有文化的吸引力。
34.美國最賺錢的公司,都是厚積薄發的高科技公司。
35.中國AI和美國真實的gap是原創和模仿的差距。如果這個不改變,中國永遠只能是追隨者,所以有些探索也是逃不掉的。
36.英偉達的領先,不只是一個公司的努力,而是整個西方技術社群和產業共同努力的結果。他們能看到下一代的技術趨勢,手裡有路線圖。中國AI的發展,同樣需要這樣的生態。很多國產晶片發展不起來,是因為缺乏配套的技術社群,只有第二手訊息,所以中國必然需要有人站到技術的前沿。
37.我們不會閉源,我們認為先有一個強大的技術生態更重要。
38.我們短期內沒有融資計劃,我們面臨的問題從來不是錢,而是高階晶片被禁運。
39.更多的投入並不一定產生更多的創新,否則大廠可以把所有的創新包攬了。
40.我們認為當前階段是技術創新的爆發期,而不是應用的爆發期。長遠來說,我們希望形成一種生態,就是業界直接使用我們的技術和產出,我們只負責基礎模型和前沿的創新,然後其它公司在DeepSeek的基礎上構建toB、toC的業務。如果能形成完整的產業上下游,我們就沒必要自己做應用。
41.如果需要,我們做應用也沒障礙,但研究和技術創新永遠是我們第一優先順序。
42.技術沒有秘密,但重置需要時間和成本。英偉達的顯示卡,理論上沒有任何技術秘密,很容易複製,但重新組織團隊以及追趕下一代技術都需要時間,所以實際的護城河還是很寬。
43.提供雲服務不是我們的主要目標,我們的目標是去實現AGI。
44.大廠有現成的使用者,但它的現金流業務也是它的包袱,也會讓它成為隨時被顛覆的物件。
45.大模型創業公司可能活下來2到3家。現在都還處在燒錢階段,那些自我定位清晰、更能精細化運營的,更有機會活下來。其它公司可能會脫胎換骨。有價值的東西不會煙消雲散,但會換一種方式。
46.我經常思考的是,一個東西能不能讓社會的執行效率變高,以及你能否在它的產業分工鏈條上找到擅長的位置。只要終局是讓社會效率更高,就是成立的。中間很多都是階段性的,過度關注必然眼花繚亂。
47.我們釋出的V2模型沒有海外回來的人,都是本土的。前50名頂尖人才可能不在中國,但我們能自己打造這樣的人。
48.DeepSeek也全是自下而上的。而且我們一般不前置分工,而是自然分工。每個人有自己獨特的成長經歷,都是自帶想法的,不需要push他。探索過程中,他遇到問題,自己就會拉人討論。不過當一個idea顯示出潛力,我們也會自上而下地去調配資源。
49.我們每個人對於卡和人的調動是不設上限的。如果有想法,每個人隨時可以呼叫訓練叢集的卡無需審批,同時因為不存在層級和跨部門,也可以靈活呼叫所有人,只要對方也有興趣。
50.我們選人的標準一直都是熱愛和好奇心,所以很多人會有一些奇特的經歷,很有意思。很多人對做研究的渴望,遠超對錢的在意。
51.創新首先是一個信念問題。為什麼矽谷那麼有創新精神?首先是敢。Chatgpt出來時,整個國內對做前沿創新都缺乏信心,從投資人到大廠,都覺得差距太大了,還是做應用吧。但創新首先需要自信,這種信心通常在年輕人身上更明顯。
52.我們在做最難的事。對頂級人才吸引最大的,肯定是去解決世界上最難的問題。其實,頂尖人才在中國是被低估的。因為整個社會層面的硬核創新太少了,使得他們沒有機會被識別出來。我們在做最難的事,對他們是有吸引力的。
53.OpenAI不是神,不可能一直衝在前面。
54.AGI可能是2年、5年或者10年,總之會在我們有生之年實現。至於路線圖,即使在我們公司內部,也沒有統一意見。但我們確實押注了三個方向:一是數學和程式碼,二是多模態,三是自然語言本身。數學和程式碼是AGI天然的試驗場,有點像圍棋,是一個封閉的、可驗證的系統,有可能透過自我學習就能實現很高的智慧。另一方面,多模態、參與到人類的真實世界裡學習,對AGI也是必要的。我們對一切可能性都保持開放。
55.未來會有專門公司提供基礎模型和基礎服務,會有很長鏈條的專業分工。更多人在之上去滿足整個社會多樣化的需求。
56.我主要的精力在研究下一代的大模型,還有很多未解決的問題。
57.所有的套路都是上一代的產物,未來不一定成立。拿網際網路的商業邏輯去討論未來AI的盈利模式,就像馬化騰創業時,你去討論通用電氣和可口可樂一樣,很可能是一種刻舟求劍。
58.我們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積累過程,外部看到的是幻方2015年後的部分,但其實我們做了16年。
59.未來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會更依賴硬核技術的創新。當很多人發現過去賺快錢很可能來自時代運氣,就會更願意俯身去做真正的創新。
60.未來硬核創新會越來越多,現在還不容易被理解,是因為整個社會群體需要被事實教育。當這個社會讓硬核創新的人功成名就,群體性想法就會改變,我們只是還需要一堆事實和一個過程。

梁文鋒為文藝復興科技公司創始人、“量化之王”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的傳記《征服市場的人:西蒙斯傳》一書寫過序言。序言的最末寫著,“每當在工作中遇到困難的時候,我會想起西蒙斯的話:‘一定有辦法對價格建模。’”
文/梁文鋒 幻方量化創始人
詹姆斯·西蒙斯是量化投資領域的泰斗。一直以來,外界對西蒙斯和他所建立的文藝復興科技公司所知不多。但這絲毫不影響無數年輕人在西蒙斯的故事的激勵下,進入這個神秘的行業。和很多新技術一樣,量化投資剛出現的時候也是被嘲笑的物件,沒有人相信計算機可以像人類一樣進行投資。但西蒙斯卻敏銳地預見到,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終有一天“不可能”將會變成現實。西蒙斯在早期做了諸多嘗試,都不太成功,但他並未放棄,他相信時間是站在他這邊的。
西蒙斯是幸運的,他遇到了好的時代。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計算機軟硬體的發展到達了一個臨界點,人們開始構建真正實用的模型,並在某些投資細分領域取得了初步成功。
在1988年西蒙斯設立大獎章基金時,他已經50歲了,在投資上經歷了10餘年的挫折,但這一次他抓住了機會,登上了通往新時代的列車。
如今華爾街很多量化巨頭的崛起,都可以追溯至這一時期。西蒙斯和其他先驅者,使用現在看起來並不複雜的技術,迅速摘掉了市場上最低垂的果實,積累了第一桶資金。
這只是開始,在之後的30餘年裡,計算機技術繼續發展,量化投資正逐漸發展成資本市場中的一個新寵,不斷有新的模型被開發出來,更多的“不可能”變成了現實,最終使量化投資在21世紀成為金融領域發展的大勢所趨。
在這個過程中,文藝復興科技公司在西蒙斯的帶領下,始終站在時代的潮頭,成為行業的標杆。
文藝復興科技公司輝煌的30餘年,同時也是金融市場監管愈發嚴格、透明化的30餘年。很早的時候,基金經理可以從公司管理層獲得更多資訊,從而取得交易優勢。但諸如此類的不公平問題在過去30餘年逐步得到了解決。
在資訊化時代,金融市場是公平和透明的,人類基金經理和計算機模型站在同樣的起跑線上,這進一步為量化投資的大範圍成功掃清了障礙。
為何恰好是這30餘年,金融變得公平和透明瞭呢?這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得益於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在西蒙斯即將退休之際,本書的出版,為我們揭開了很多之前未解的疑團,也為我們帶來了豐富的可供借鑑的經驗。
國外的模式未必能照搬到中國,但閱讀本書,可以讓我們收穫很多的思考和啟發。是什麼樣的特質和機遇,使西蒙斯成為歷史的幸運兒?如何管理一支優秀的團隊,使之30餘年立於不敗之地?為什麼科技會使金融市場產生如此深刻的變化?讀者可以從本書中尋找答案。作為後輩,能為西蒙斯的中文版傳記作序,我感到十分榮幸。每當在工作中遇到困難的時候,我會想起西蒙斯的話:“一定有辦法對價格建模。”

(這是一本為美好社會理想構建政治地基的探索之作)
推薦閱讀
十點公社
一個時代的記錄
自由評論


只為蒼生說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