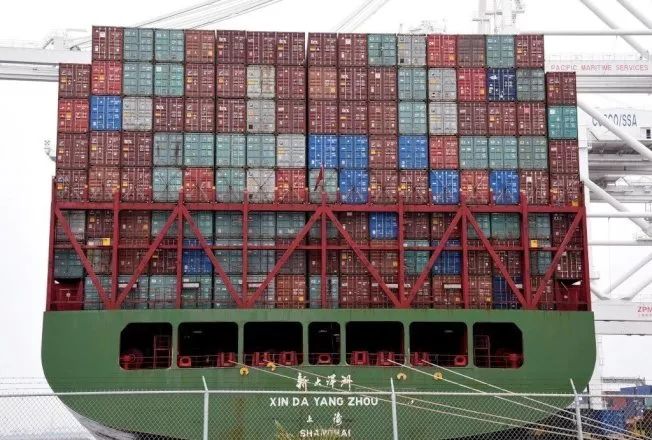作者在2024年9月的文章《再全球化下的通脹與通縮》中,首次提到了Robert Lighthizer(萊特希澤)在2023年出版的No Trade Is Free。川普第二任期開始後,由於Lighthizer沒有獲得任何職位,使得外界普遍認為他已經被邊緣化。他的著作再度無人問津,他的觀點也再次無人提及,他本人也徹底銷聲匿跡。直到2025年3月20日,Lighthizer高調參加Tucker Carlson的訪談,將他在No Trade Is Free中的觀點再行普及。
當時外界應該還不明白他為什麼會突然出現。
直到,川普對等關稅的出臺。
人們從Carlson對Lighthizer的訪談中,瞭解到原來巴菲特早在2003年就在Fortune雜誌上撰文(America's Growing Trade Deficit Is Selling the Nation Out From Under US. Here's a Way to Fix the Problem-And We Need to Do It Now),表達過對貿易逆差問題的擔憂,巴菲特當時還提出Import Certificates(ICs,進口許可證)方案。簡言之,巴菲特當時認為,想要彌補貿易赤字,美國可以發行ICs給所有美國本土的出口商,其數量按照其出口金額計算,這些美國出口商可以將ICs轉賣給美國本土的進口商,美國進口商可根據獲得的ICs額度來進口海外商品並銷售到美國本土。如此一來,美國的出口金額等於進口金額,逆差就消失了。
其實,Lighthizer在2023出版的No Trade Is Free中就提到過上述巴菲特方案。除巴菲特的ICs方案外,Lighthizer在書中還提出另兩個方案:
一是對流入美國的外國投資徵收附加費(put a surcharge on inward investment),目的是壓低美元幣值(以利美國出口);
二是加關稅,關稅比例取決於美國貿易逆差的規模(tariffs could come or go depending on the size of the deficit)。
換言之,那個被稱為“草臺班子力作”的川普關稅計算公式,其實就是Lighthizer最早建議的。很顯然,Lighthizer自認為,並經Carlson訪談一宣傳,如今無論是美國的populist,還是華街分析師,甚至連中國大陸的經濟學者,都開始認為,Lighthizer方案是十分接近巴菲特ICs方案實質的。
於是,4月4日開始,在川普親自轉發一個“巴菲特認可”的短影片後,美國網路瘋傳巴菲特支援川普的經濟政策。如果不是巴菲特和Berkshire Hathaway出來緊急闢謠,這個段子很有可能演變為,川普關稅政策其實是巴菲特二十多年前提出的


巴菲特表示,在2025年5月3日Berkshire Hathaway的年度股東大會前,他不會對市場或關稅發表任何評論。所以,下個月,人們就能知道巴菲特如何評價自己2003年的觀點了。希望巴菲特繼續健康。
在2024年10月《川普關稅的底氣與中國大陸的內需》一文中,作者詳述並推測,川普之所以鍾愛關稅總統William Mckinley,很可能是因為受到Lighthizer的影響。事實證明,這個影響不是一般的大。至於今天這個世界的貿易結構與Mckinley所處19世紀末的區別,看起來並不在Lighthizer和川普的考慮之內。
作者認為,要了解川普關稅政策的由來,只需認真閱讀Lighthizer的No Trade Is Free以及Micheal Pettis的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就夠了。這兩本書在過去兩年,作者都多次提及。如今市面上各種紛擾的資訊,基本都是在拾人牙慧的基礎上,再行自由發揮。
回到川普關稅的萊特希澤方案,並且站在今天的時點,再去回溯巴菲特2003年的ICs方案,不禁有一種垂垂老者憶往昔的感覺。
2003年,中國大陸才剛剛加入WTO一年多一點,當時的全球化與今天截然不同。當時的世界,產業鏈雖然已經向東亞轉移,但中國大陸這個後來最龐大的世界工廠和需求地才剛剛準備啟動。彼時,生產總體上還是可以按照國家進行地域區分的,你生產飛機、電腦,我生產毛毯、襯衣,各自分工是明確的。在國家分工明確的前提下,無論是以ICs還是以關稅,來實現貿易逆差縮減的可能性都要比今天大得多得多。時至今日,雖然僅僅離2003年只有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但人類世界已天翻地覆。
邏輯上看,美國今天要解決貿易逆差問題,只有兩個辦法:
一是美國下定決心開始自力更生。把全球化後紛繁複雜的國際產業鏈打破並在美國國內進行重建,讓織機、紐扣、拉鍊、線頭全部都在美國生產,進而能夠生產出一件完整的襯衣。否則,一旦需要進口襯衣上任何一個“零件”,關稅都擺在面前。最終有無利潤,都是問號。
二是美國人民開始節衣縮食,沒有進口就沒有傷害。對美國而言,在去工業化後,出口增加難度很大,所以進口就是逆差之源。透過關稅強行縮減貿易逆差的結果,不太可能是靜態地獲得關稅收益,很可能是進口的大幅下降。因為,進口產品越來越貴,又不能像當年日美貿易戰那樣,用不加稅的韓國產品替代加稅的日本產品,那美國本土需求就會自然收縮。從出口國的角度,既然在美國掙不到錢,那也只有兩個選擇:一是轉向海外其他市場或者大力振興內需,二是在全球需求整體收縮的時候,選擇規模化的去產能。
巴菲特提出ICs的2003年,儘管美國的去工業化已經開始,但美國仍然保有足夠的製造業優勢。然而,放到今天來看,ICs方案與萊特希澤方案一樣,最終都只能是一個需求收縮的結局。
這是因為,美國持續性的超大規模貿易逆差,源於美元是世界儲備貨幣,而美元之所以成為世界儲備貨幣,是因為各國對美元的需求。時至今日,沒有一個國家願意主動而完全地拋棄美元儲備。這導致美國可以不停用印出的綠幣去購買實體的世界。所謂“鑄幣稅”,是各國基於認同而對發鈔國形成的“信仰”。曾經,世界對美元的信仰主要基於以下原因:
一是戰後尤其是美蘇爭霸結束後美國科技實力的一枝獨秀和產業盡皆優勢的現實;
二是戰後美國作為“世界警察”形成的歐亞美三洲和平環境;
三是石油等大宗商品國主動與美元的捆綁;
四是基於上述形成的美國軟實力。
如今,原因一開始消散,原因二逐漸被川普團隊放棄,原因三尚在,原因四已經崩壞。
作者在此要提及一篇八年前的譯文(《金融資本主義(1850-1931年)》),如果讀者能夠讀懂這篇Carrol Quigley寫於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前的晦澀文字,大致就能瞭解,美國今天強行用關稅消滅逆差,等同於追求恢復金本位,而金本位在現實世界則意味著走向大幅通縮。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今天美元的地位。當一個國家可貿易部門的產業實力不足以維持基本的貿易平衡時,鑄幣稅優勢仍可能源於不可貿易的領域,例如為全球提供一個整體的“生存性公共產品”,只是,這個公共產品的價格是難以量化的。但如果發鈔國自己並不認為這個公共產品是其幣值的基礎(例如歐日韓澳的防務不應由美國來支付),加之由於自身債務約束能力太差導致債務利息一次次難以被償還,反而硬要追求傳統的貿易順差,那結局就如今天一般——全球通縮共識快速達成。
如果川普真是在採用Lighthizer方案,那幾乎等同於一個金本位方案。相當於在一個產業鏈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透過關稅虛擬出金本位的效果,來實現貿易平衡。由此帶來的結果,只能是美國通縮預期導致的全球通縮預期。
如果川普只是虛晃一槍,只是想強迫各國回到談判桌,那麼故事還有其他可能。但問題是,談判的目標到底是什麼呢?如果是追求大幅縮減逆差,那結局仍然是一樣的。如果不追求大幅縮減逆差,又該追求什麼呢?
無非只有兩種可能:
要麼,是川普團隊深思熟慮多年,正在下一盤人人都看不懂的大棋;
要麼,是川普團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下一盤什麼樣的棋。
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