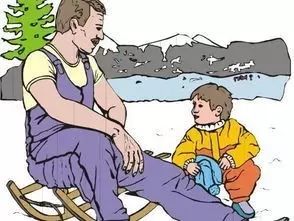偶然看到清華大學清影工作室拍的紀錄片《風起前的蒲公英》上映,還是比較少見的初中生群像,就火速去最近的電影院看了。
看完哭得稀里嘩啦。這麼好的片子居然0宣發,錯過實在太可惜了。

北京大興,藏著一所特殊的學校,蒲公英中學。它是北京第一座經過政府批准的專門為農民工子女創辦的中學。
要不是有鏡頭記錄,真的難以想像北京還有這樣一群孩子。
他們住的是擁擠的待拆遷房,一家三口轉個身都要颳著對方;睡的地方是敘利亞風格,像難民窟,牆上是抹不掉的汙漬;穿的是愛心人士捐贈的衣服……

生活條件差還只是表面的。這部片子的導演是清華大學傳播學院博導、副教授梁君健,他的視角帶著深厚的人類學思考。
他在“一席”演講時說,本來是想拍一部底層學生逆襲,大圓滿的紀錄片。但隨著深入瞭解孩子的生活,發現根本不是這樣。

他們甚至連影片中的“主線人物”都找不到,每當開始熟悉一個孩子時,他就轉學離開。好不容易篩選出“小主角”,他們也為了美好的未來奮鬥過,可沒多久又被摁滅了“希望之光”。
最後幾個小主角在追求自己夢想的道路上紛紛“團滅”,原因可能來自家庭、社會、甚至只是老師的一句話。

這部電影讓我想起《跋山涉水上學路》,不過,這條難走的路是他們的人生路。
但電影的可貴也在於它100%的真實,看完才知道這個世界的參差以及我們生活中擁有了多少的幸福。

蒲公英中學是怎麼樣的一座中學呢?帶大家瞭解一下下背後的故事。
紀錄片中出現的中學老校區,它前身是一座村辦工廠,教室是老廠房改裝成的,冬天連供暖都沒有。

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卻出過一個極為優異的畢業生——段孟宇。
她從蒲公英中學畢業後考上了世界聯合學院,又在美國路德學院讀了本科,最終讀到了哈佛教育學院的研究生。
她從哈佛畢業後,又回到了蒲公英中學擔任教職。當年還有不少她的新聞。

不過段夢宇的經歷僅僅是一個個例,大部分學生的命運和蒲公英一樣,由於家庭不穩定,還沒畢業,就被吹到了各地。
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家庭,這些學生的家長為了生計疲於奔命,爸爸一般幹都是建築裝修,而媽媽們則在菜場做些零散的活計。

生活已然是不堪重負,還有更多的突如其來和“雪上加霜”:比如有的孩子家庭單親,有的孩子父母都患重病,還有的孩子甚至要面對酗酒後的家暴……厄運專找苦命人,麻繩偏挑細處斷。
也許對於這些孩子來說,在蒲公英上學的日子,就是他們疲憊生活中最佳的避風港。
學校為了讓學生安心學習,特地採取了住宿制,這樣就能遠離家庭的嘈雜。
因為會受到社會的關注,他們的生活不乏“高光時刻”,在中網開幕式上獻過唱,也在慈善晚會上和黃曉明合過影。
但他們註定只是這種場面的過客,甚至連這些場合也不歡迎真實的他們。
開幕式排練時,工作人員怕搞砸直播,讓他們“假唱”;慈善晚會上,名流穿著定製禮服推杯換盞,他們在後臺吃著統一發放的炸雞。
距離雖近在咫尺,但中間卻隔著一個世界。

同樣的這種割裂感,還體現在他們平時聚在一起討論的話題上。
比如兩個女孩聊到想去北京哪裡玩,其中一個說想去迪斯尼和日本。另一位很驚訝的說,“可日本不在北京呀。”


紀錄片中有段讓人印象深刻的對話。
每個人都是好苗子,有的人栽進了黑土地裡,有的人栽進了紅土地裡,有的栽在了沙漠裡。最苦的就是那些栽在沙漠裡邊的。
這話幾乎成了這些孩子命運的讖語。
紀錄片是圍繞學校的一個合唱團展開的。學校開合唱團的初衷是為了補上孩子成長過程中缺失的音樂教育。

帶了八年合唱團的教師袁小燕發現,學生不只是學到了相關的知識,有的被音樂點燃了夢想,有的在參與團體事務中得到了成長,有的還頗有天賦,透過藝考說不定可以得到一個翻身的機會。
對音樂有熱情的孩子中間,有四個特別值得一說的名字:張展豪、權煜飛、王路遙、馮小云。

張展豪是四個人中年齡最大的,身材已經長得比較魁梧,但他卻有個文藝夢,彈的一首好吉他,還會打非洲鼓。
張展豪的夢想是長大了當一個歌手。不過,教室裡寫著夢想的紙飛機卻被他劃了三道。因為他特別懂事,知道爸媽工作不易,自己的夢想沒有物質支撐。
他成了紀錄片中第一位離開合唱團的學生。

權煜飛是男生中不多數對合唱團有感情的。在參與排練時,他甚至還發現了一個老師都忽視的錯誤,也是有一定個業務能力的。
不過由於老師想組建一個只有女生的合唱團,權煜飛不得不離開。被通知到後,權煜飛還想再爭取爭取,可“旁聽”了幾堂課後最終也離開了。
他們的人生中,總是被選擇。

王路遙可能是對合唱團感情最深的學生。初一還沒自信展示聲音,但到了初二,她卻成了合唱團的靈魂人物,不僅聲音大了,還主動當了老師的代班,老師不在時,她就帶著同學練習。
但路遙的爸爸堅決不同意她學習音樂。他的理由是,“我們家裡沒有搞這個的,我不想你受委屈,那滋味不好受。”
聽完爸爸的道理,路遙哭了。新學期,路遙沒再來合唱團。

可能會有人覺得這位爸爸在誇大其詞,可事實上,這位爸爸是未卜先知。蒲公英中學再開學時,來了一個頗有音樂天賦的新生,馮小云。
她的音域很廣,能唱到c3,是學校裡少見的好苗子。
更難得的是,她的父親非常開明。紀錄片中,別的家長都覺得孩子學音樂是不務正業,只有小云的家長表示,不管女兒想幹什麼他們都支援。
社會也為他們打開了綠色通道,只要透過篩選,他們就有進入知名音樂學院免費學習的機會。
天時地利人和都有了。連導演都說,這看上去是個很有信心的故事。

可希望剛剛燃起,就熄滅了。小云是進入了選拔環節,但還是被淘汰了。
原因並不是業務能力的問題,而是因為她不守“規矩”。在等待面試時,小云彈了學院的鋼琴,碰巧被老師撞見,“禮貌”一欄就被評了“D”,這直接導致她落選。
小云是有些冤枉的,第一,她動鋼琴前,有個“小姐姐”說可以彈;第二,一個篩選音樂人才的面試居然把規矩看的更重要,實在有些本末倒置。

影片剪好後,導演邀請孩子們先看了成片。小云說,她很理解路遙的爸爸。就算沒動鋼琴,要走這條“星光路”,等待她的困難也是難以計數的。
他們的經歷是這個團體的縮影,充分說明沙漠裡小苗成長的艱難,僅僅是有夢想和熱愛,還是遠遠不夠的。

不由想起何炅寫的一篇小作文。他記錄了這樣一則故事:
有位學生吹牛說“何炅是我哥”,為了不在同學面前丟面子,他找到何炅,請求何炅能在班裡露下臉。
何炅當然不同意這個無理的請求,一來沒時間,二來覺得把自己當成賭約,有些不尊重人。
可那學生依然不依不饒,一問才知,他竟然用“1000塊錢”作為賭注!
聽到數字何炅都嚇出一身汗。但那學生卻不在意,“沒什麼大不了的,不就1000塊錢嘛。”何炅被這位“弟弟”花錢的大手大腳震驚到了。
何炅擔心小男孩為這筆“鉅款”做傻事,勉強答應。但也“約法三章”,第一,同學的錢不能收,第二,希望他以後不要再“賭”。臨了,何炅給這位“弟弟”寫了封信,信的結尾這麼寫到:
“我目前正為把系裡讀不起書的貧困生留在校園而忙碌,當你們一擲千金的時候,請想想他們。”
溫室裡的花朵把現成的美好生活想的過於理所應當了,沒有切身經歷過拒絕,可能真的沒法感知到那條一出生,就為他們敞開的無形的道路。
感知到這世界客觀存在著不同,我們平常的生活或許正是有些人一直努力奮鬥的目標,這麼想來,心態也平和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