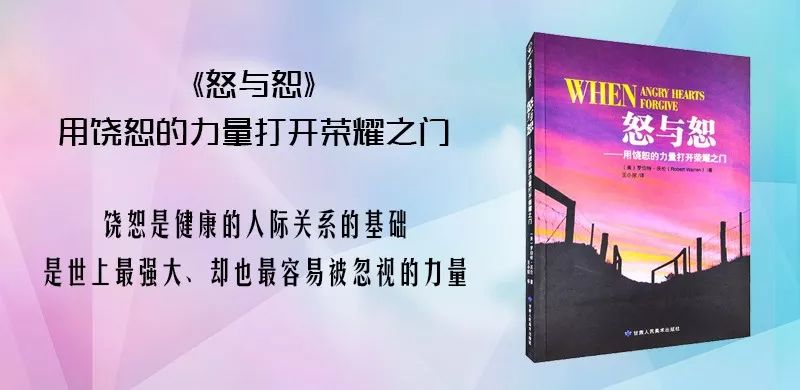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王逸舟,黃希林
自從兩位以自由主義政治立場而在媒體界知名的作家埃澤拉·克萊因(Ezra Klein)與德雷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的著作Abundance(《豐饒》,也譯作《富足》《豐裕》)於2025初年問世以來,其提出的“豐饒議程”理論已成為2025年美國民主黨政治中除了“對抗寡頭”(Fight Oligarchy)這一反擊現任共和黨總統特朗普和他的政治經濟支援核心以外的另一重要議題。隨著2024年選舉週期中慘敗帶來的重創,民主黨關於如何重新定義自身的內部政治辯論愈演愈烈,“豐饒議程”一詞已成為該黨內自由派和左翼陣營中許多人爭論不休的熱點議題:未來政治成功的關鍵是否取決於對經濟投資並推動更多專案建設的積極倡導?
在紐約市長選舉的民主黨黨內初選中,困擾居民許久的住房問題,已然成為主要候選人的核心關注點;其中,豐饒議程的理論及其相關的新城市主義思潮對這些候選人產生了顯著影響。來自布魯克林的紐約州議會參議員澤爾諾·麥瑞(Zellnor Myrie)由於明確支援增加住房供應而被視為最為支援豐饒議程的候選人,而民調領先,並最終在初選中勝出的民主社會主義候選人卓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則明確表示,他政治立場的重大轉變之一是認識到市場在住房建設中的重要性,而這顯然受到了豐饒議程相關思潮的影響。
豐饒議程的核心主張是“稀缺是一種選擇”;克萊因和湯普森認為,美國在21世紀面臨的許多危機,例如住房危機、氣候危機、醫療危機等,其本質上是供給不足的結果,而這種供給不足並非不可避免,而是政策選擇和制度設計的產物。在這種政治立法和態度所約束的環境中,政治環境陷入到了自相矛盾的境地:政客們一方面說要解決住房可負擔性問題,卻在最富有的城市透過法律限制使建造新住房變得極其困難;一方面聲稱要拯救地球免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卻在自由派州關閉零碳核電站並抗議太陽能專案對於環境的“潛在影響”。

這種矛盾的根源在於,美國過往的汙染讓當時的政治體制創造了一個全面的管理系統,而這一系統其中的程序正義常常阻礙了實質性結果的實現。豐饒議程提出了一種經濟和政治上放鬆約束的框架,強調增加關鍵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並消除阻礙建設和創新的制度性障礙。
“稀缺是一種選擇”:豐饒議程能否超越傳統左右分歧
儘管豐饒議程迅速成為民主黨一大政治主軸,但來自黨內外左翼的批評聲仍不絕於耳。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有人認為豐饒議程本質上是“包裝更精美的新自由主義”,因為其在住房領域強調“去監管”,這讓人聯想到里根-撒切爾時代的政策及其導致的貧富差距擴大;其次,批評者擔憂豐饒議程過於關注“做大蛋糕”而忽視分配問題;第三,有人質疑其對技術解決方案的樂觀態度低估了生態極限。
然而,豐饒議程與傳統新自由主義有本質區別。新自由主義主張政府全面退出,而豐饒議程強調政府作為市場建構者的積極角色;新自由主義以減稅為核心,而豐饒議程強調公共投資和制度改革;新自由主義關注一般性經濟增長,而豐饒議程特別關注住房、能源、醫療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最重要的是,豐饒議程所謂的"去監管"並非無差別地放松管制,而是有針對性地改革那些阻礙公共利益實現的具體規定。
所謂“豐饒議程”,並非某種完整意識形態或抽象綱領,而更像是一系列聚焦於基礎設施、住房、交通、能源等領域的具體政策組合。其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正如曼達尼所說,是它把關注點落在了官僚體制的具體細節之上,而不是隻做宏大敘事。換句話說,豐饒議程關注的不是空洞的“去監管”,而是“為什麼這些具體規定反而阻礙了公共利益的實現”。它的許多主張正是從效率、公平、生活質量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了那些歷史遺留、與現實脫節甚至有歧視色彩的城市法規。正如曼達尼自己在接受湯普森的採訪中強調的那樣,“這些常被忽視的細節,實則對專案能否順利實施產生著巨大影響”。
讓我們以住房安全和房屋建設管理作為一個“具體規定阻礙公共利益”的範例。美國一些沿用數十年的防火規定要求單樓梯住宅的最高層數不得超過三層,這一規定導致大量低矮密度公寓因需配備兩套樓梯而無法建設,因為這種要求對於成本和地塊的要求往往超過地產商的預算。而另一方面,現代的防火理念更強調源頭防控與火勢遏制;相比之下,那種傳統的帶多樓梯的“五帶一(5-over-1)”美式連廊式建築,則反而容易因走廊連通在火災中迅速蔓延。
對此,部分城市如西雅圖已經放開了類似監管,並透過配套改革成為受住房危機衝擊最小的民主黨執政城市之一。在這裡,豐饒議程強調的,恰恰是那些在現實中影響深遠、卻常被忽視的具體操作問題:比如一座樓究竟需配幾套樓梯、哪些防火規範在當今環境下已不合時宜、如何最佳化審批流程、怎樣簡化小型公寓建設的繁瑣門檻等。透過這種微觀改革,可以在不犧牲安全的前提下,顯著提高住房供應和可負擔性。
除了對於房屋建設的觀念調整之外,豐饒議程也對美國政府決策和執行過程中的“程式主義”問題提出了深刻批判。在美國,環境影響評估(EIA)等制度最初設計用於保護環境,但如今卻常常成為阻礙清潔能源專案的主要障礙。為了保護20世紀的自然環境而設計的法律,如今反而阻礙了21世紀拯救地球所需的清潔能源專案。
單個審批程式可能合理,但疊加在一起形成了幾乎不可逾越的障礙。克萊因和湯普森在書中以舊金山的Tahanan住房專案為例,這一專案透過繞過政府資金(及其附帶的繁瑣要求),專案得以更快、更便宜地建成。這種現象反映了一個“絕對瘋狂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確保程式公正的努力由於過於繁瑣,反而阻礙了改變住房危機的實質性結果能夠成為現實。
在思維上,豐饒議程主張重新平衡程式與結果,簡化政府決策和執行流程,減少不必要的程式性障礙,同時保持必要的監督和問責。這不是對監管的全面否定,而是對監管質量和效果的重新思考。
相比於僅是陳舊規定的防火政策和建設規劃要求,某些區劃法規對於社會不同群體的影響,則甚至可以直接視為一種制度性不公。例如獨棟住宅區劃(single-family zoning)。雖然美式獨棟屋出現早於二戰,但在二戰後種族隔離結束時,許多無法接受多元社群的種族主義白人遷往郊區,重建“純白社群”,並利用高門檻的純獨棟住宅分割槽來阻止經濟條件較差的黑人搬入。
這種排斥機制的另一個方式是依賴汽車出行,由此產生了一系列製造“汽車社會”而歧視其他出行方式的法規,如在住房和其他建築單位中強制規定的最低停車位要求導致預算和規劃面積的顯著增加;這些政策不僅加劇了住房危機,還帶來了難以想象的生活成本負擔。在密蘇里州,當地慈善機構的廣告宣傳“必須在給汽車加油和購買食物之間做出選擇”,而這對於習慣無車生活的全球大多數地區的人來說是難以想象的。
從管理層面來看,豐饒議程主張重新審視這些帶有歷史歧視色彩的區劃法規,不僅從效率角度,更從社會公平和包容性角度進行改革,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完全可以被視作具有積極改革思想的政治運動。正如美國城市可持續更新倡導組織Strong Towns創始人查克·馬龍(Chuck Marohn)所言,城鎮為對抗住房危機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除對於獨棟住宅區劃的繫結。
豐饒需要國家能力:“有效”政府究竟有多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豐饒》一書除第一章外,很少提及簡單的“去監管”,而是大量討論了“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關鍵作用。兩位作者透過青黴素的大規模工業化生產和曼哈頓計劃等歷史案例,展示了強大的政府執行力對於重大專案成功的決定性影響。這種國家能力不僅指政府規模,更指其有效執行復雜任務的能力:一個強有力的、得到經濟支援的、能夠把事情做成的公共部門。
國家能力,或更準確地說是國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以及有能力的公營機構的缺失,與公共住房息息相關。以聖路易斯和芝加哥為例,政府治理不善和維護不力導致當地公共住房淪為犯罪滋生的溫床,最終難逃被拆除和紳士化的命運,以至於自1998年後美國政府幾乎停止了新建公共住房。然而,公共部門實際上有能力提供或儲存公共/低租金住房,例如芝加哥住房局就透過一系列法律手段保留了Millers River的公屋社群。
正是這種能力(包括低價大量建設高質量公共住房的能力)的缺乏,使得政府在降低房租方面缺乏有力的手段。例如,紐約市由於存在大量私人持有的租金管制房屋,市政府每年都需要努力平衡房東和租客之間的利益。如果紐約市擁有大量公共部門持有的住房,並且有能力建設更多此類住房,那麼這方面的壓力自然會小得多。
在這一點上,國家能力與豐饒議程形成了恰當的互補:前者確保政府能有效執行關鍵專案和政策,後者則確保這些干預是針對供給約束的。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MTA)幾乎是一個完美的新自由主義對於公營機構戕害的例子。在書中,兩位作者特別著重提到了紐約第二大道地鐵規劃的超支問題,而MTA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源於工程外包導致的軟成本(Soft Costs)飆升。這有一部分是MTA內部工程師裁員導致的內部工程能力缺乏、過度依賴外部顧問而雙方溝通不暢導致工期拖沓、需求得不到傳遞造成的。

這一裁員的原因在於時任紐約州州長,後來因為醜聞被迫辭職的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在公開場合以MTA效率低下為名削減其預算並砍掉了他認為不重要的部門,甚至將資金挪用於補貼紐約上州的滑雪場來換取他們對自己的政治支援。這些資金削減,最終導致MTA缺乏優秀的內部工程能力,建設成本隨之飆升。這是一個典型的惡性迴圈:政客聲稱公共機構不夠高效→公共機構的資金減少→公共機構交付能力變差→公共機構真的不夠高效→政客繼續批評公共機構。
從豐饒議程的角度來說,它的目的就是打破這一惡性迴圈,以積極設想來去重建公共部門的技術能力和執行力,從而使政府能夠有效履行其在關鍵領域的職責。這不是簡單地擴大政府規模,而是提高政府質量和效能。為了做到這一點,國家或者地方政府的辦事能力應當和對供給的擴張相結合:前者確保政府能有效執行關鍵專案和政策,後者則確保這些干預是針對供給約束的。提升國家能力需要多方面改革:重建政府內部技術專業能力,避免過度依賴外包;改革公共部門人才招聘和薪酬體系,吸引頂尖人才;簡化決策鏈和問責機制,提高執行效率;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打破“筒倉效應”。只有將監管改革與國家能力建設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豐饒議程的願景。
回應批評:豐饒議程的公平與可持續性
豐饒議程常被批評為過於關注在經濟規劃上“做大蛋糕”而忽視分配問題。然而,這種批評忽略了供給約束本身對分配正義的重要影響。當住房、醫療、教育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供應不足時,最終受害最深的往往是最弱勢群體,而當“擴大住房”的危害仍然停留在假設之中時,舊金山隨處可見的街頭帳篷正在告訴我們,住房危機所導致的社會問題已經明顯地無法再被忽視。
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上說,增加住房供給並不必然導致所有新增住房都被富人佔用。相反,研究表明,即使是市場價格的新建住房也能透過"過濾效應"(filtering)最終增加整體住房可負擔性。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不需要針對性的可負擔住房政策,但這些政策在供給充足的環境中會更加有效。用實用的眼光來看,豐饒議程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所支援的“財產再分配”並不存在本質上的衝突,而是兩種可以互補的思路:前者關注增加供給,後者確保收益廣泛分享。這種“包容性豐饒”的框架可以兼顧效率與公平,避免陷入零和思維。
另一常見批評是豐饒議程對技術解決方案過於樂觀,低估了生態系統的物理極限。在《外交政策》雜誌中,馬薩諸塞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伊莎貝拉·韋伯(Isabella Weber)表示,豐饒議程的核心缺陷在於其對技術解決方案的過度信任,忽視了資本主義增長邏輯與生態可持續性之間的結構性衝突。在她看來,僅靠供給側改革無法解決資源有限性的根本約束,也無法應對無限增長與有限資源之間的內在矛盾。在以韋伯為代表的評論者看來,豐饒議程未能充分認識到氣候危機的系統性本質,過於依賴市場機制和技術創新來解決深層次的生態問題。
從運用角度上說,豐饒議程並非主張無限制增長,而是強調更高效、更可持續的增長。支援提高生產和供給不是簡單的增長崇拜,因為豐饒議程本身關注的應該是如何重塑生產方式,使其更加可持續和包容。在氣候變化領域,豐饒議程則主張透過清潔能源轉型、電氣化和能效提升等技術路徑實現脫碳,而非用“去增長”等強行限制的路徑來去單純限制經濟發展的規模。在西方國家的政治體系之中,這種方法更具政治可行性,因為它能夠有效地建立包括關注就業和經濟機會的選民群體在內的廣泛聯盟,而純粹的生態主義立場難以形成足夠廣泛的政治基礎。
從這一角度來說,豐饒議程並非“技術樂觀主義”,而是一種“技術現實主義”:既不同於傳統生態主義對技術本身的懷疑,也不同於技術萬能論的盲目信仰,而是在承認生態約束的前提下,尋求技術創新、制度變革和行為調整的最佳組合,以實現更可持續、更包容的繁榮模式。
不過,如果想要豐饒議程利用增加建設而推進的改革變得“順其自然”,那麼這一理論必須需要從最需要得到幫助的社群開始做起。以清潔能源為例,透過拜登總統時期透過的一系列法案,美國環境保護署可以使用自己70億美元的“全民太陽能”基金將為超過90萬弱勢家庭提供屋頂或社群太陽能,而財政部的低收入社群獎金信貸將第一年的稅收優惠政策引向49000個小型清潔能源專案,其中包括社會福利住房綜合體的800個陣列,預計每年可為居民節省約2.7億美元。

除了聯邦政府之外,一些州和地方的實驗正在填補地區此前對於清潔能源的空白:加利福尼亞州的多家庭社會福利住房太陽能專案已經回收了約 34 兆瓦的租戶服務光伏;丹佛房屋管理局的2兆瓦社群太陽能花園為數百套太陽谷公寓供電;納瓦霍族的部落所有的卡耶塔太陽能農場已經擴充套件到55兆瓦,展示了收入共享的可再生能源如何取代退役的煤炭。這些專案共同展示了豐饒議程的劇本,將原本的標語轉化為更直觀的政策、更便宜的賬單、更清潔的空氣和最需要它們的家庭自建工作崗位。
儘管如此,豐饒議程的支持者們也需要承認技術解決方案的侷限性,需要配套的行為改變和制度創新。例如,僅靠電動汽車無法解決城市擁堵問題,還需要更好的公共交通和城市設計;僅靠可再生能源無法解決能源系統的所有挑戰,還需要儲能技術和智慧電網。從美國曆史沿革的經驗教訓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技術創新必須與制度變革相結合,才能真正實現系統性轉型,但這一點在豐饒議程的實踐中尚未得到充分體現。
這些缺陷是“豐饒”這一概念至今在民調中仍然未能產生積極影響的原因之一。在5月進行的一項民調中,當被問及在“豐饒議程”與“經濟民粹主義議程”之間做出選擇時,超過56%的民主黨受訪者選擇了經濟民粹主義議程而非豐饒議程。然而,正如我們的討論透過例項所示,經濟民粹主義與豐饒議程並不必然對立:當豐饒議程能夠將重點和優先事項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群身上,幫助他們擺脫貧困和缺乏流動性的迴圈時,它將成為一個長期惠及所有人的規劃方案。
尾聲:豐饒議程的未來在於實踐和細節
正如前文所論,豐饒議程之所以與傳統新自由主義有根本性區別,恰恰在於其關注那些在現實生活中真正決定成敗的細節。從防火規範中的樓梯數,到審批流程的微小障礙,這些看似瑣碎的政策設計,往往決定了城市能否容納更多居民、工薪階層能否享有更高的生活質量。豐饒議程並不是抽象的意識形態爭論,而是一套具體、面向現實的改革方案,強調將目光投向“那些常被忽視的細節”。豐饒議程的未來取決於其能否建立更廣泛的政治聯盟。這需要超越傳統的意識形態標籤,關注具體問題和實際效果,尋找共同利益和價值觀的交集。
展望未來,豐饒議程的發展需要在三個方面取得突破:首先,需要更系統地整合公平與效率,發展“包容性豐饒”的理論框架,確保供給擴張的收益能夠廣泛分享;其次,需要深化國家能力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如何在保持市場活力的同時提升政府執行力;最後,需要將豐饒理念擴充套件到更多領域,從住房、能源擴充套件到教育、醫療、養老等全方位民生問題。
豐饒議程的理論意義在於,它提供了一種超越傳統左右分歧的新政治經濟學框架,重新定義了政府角色,強調增加關鍵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其政策啟示是,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那些看似合理但實際阻礙進步的具體規定,透過微觀改革釋放巨大潛力。只有將理想主義的願景與務實主義的細節結合起來,我們才能真正實現一個更加豐饒、可持續和公平的未來。
歸根結底,豐饒議程對於美國政治生態可能產生的影響,就如曼達尼在競選時所表示的那樣:
“我認為,左派本應關注的諸多議題,卻往往被右派佔據:官僚體制、民主、效率、浪費。若真正關切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則必須將這些問題置於首要地位,因為任何效率低下的跡象都可能成為削弱公共部門的理由。同樣,若審視'生活質量'一詞,其常被視為保守派所關注的範疇,但事實上,這是每個工人階級最基本的需求。他們皆渴望擁有良好的生活質量,而這些關切並非與我們的原則相悖,恰恰是這些原則的具體體現。”
豐饒議程的核心價值,正是將這種對細節的關注、對效率的追求與對公平的堅持有機結合,形成一種真正能夠改變人們生活的務實改革路徑。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責編:朱凡。本期微信編輯:朱凡。本文為思想市場原創內容,點選“閱讀原文”進入澎湃新聞網站閱讀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