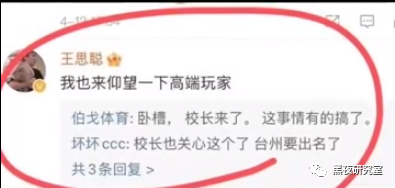作者按:本文原作於2019年,文中出現的資訊和資料均僅代表當時的情況。回頭看來,雖然世界變了很多,但是本文講的道理應該大致還是成立的吧?因此再發一遍,供大家參考指正。
本怪盜團團長讀初中一年級時,學的第一篇文言文課文叫《論語六則》,裡面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後來又有一篇文言文課文叫《勸學》,裡面我最讚賞的一句話是“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孔子是聖人,荀子是半個聖人,他們這樣說,肯定是有論據的。這些年來,我越來越贊成上面兩句話了,也越來越意識到了為什麼人家是聖人,我們只是凡人。
十幾年前,我以為世上最缺的是思考;只要肯思考,就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現在,我覺得世上最不缺的就是思考,太多的思考會把事情越搞越亂,而且絕大部分思考是錯誤的、毫無價值的。與其閉門造車式的“思考”,不如起而學習。我們需要的是90%的學習加上10%的思考,可惜很多人把比例弄反了。
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我一直以為這句話是米蘭·昆德拉說的,剛才查了一下,發現竟然真的是米蘭·昆德拉說的。
我覺得,上面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如果我們不學習,就去“盲目思考”,那麼不但上帝會發笑,路人甲乙丙丁也會發笑。全世界都會發笑。
2016年,本怪盜團團長還沒認真研究過網際網路行業。有一次,我去一家創業公司調研,對方給我講了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隨著移動網際網路的興起,百度等傳統流量入口正在衰落。現在,流量入口呈現高度分散化,哪怕你做一個休閒遊戲,也很可能吸引足夠的流量,在內部玩導流和變現的套路。對小公司來說,真是特別好的時代啊。這就是我們的商業邏輯:在流量分配高度分散化的時代,成為垂直、有特色的流量變現平臺。”
我聽了驚為天人,仔細一想好像都對:移動網際網路確實在崛起,各種垂直App大行其道, 百度在PC端的流量分發能力沒有全面轉移到移動端,垂直特色平臺好像也符合當前的使用者分層趨勢。接下來大半年時間,圍繞著上述邏輯,我思考了很多、很多,甚至形成了一套“流量從集中到分散”的理論,這套理論可以幫我們做投資,甚至還能指導做業務。我就這麼坐在辦公室裡,用投行和諮詢公司慣用的方式畫資訊圖、做PPT,把自己感動的熱淚盈眶。我還真的拿著這套理論去忽悠了一些機構投資者,其中一部分還真上當了,另一部分禮貌的表示“真有趣”。
直到2017年3月,我跟一個出身網際網路行業、又跳槽到投資行業、在兩邊都混跡多年的老朋友打電話,聊起我的“流量分散化理論”,對方毫不客氣地回答:“錯的。”
我大驚失色:“啊?什麼意思?”
對方直截了當地說:“全錯了。第一,隨著移動流量紅利耗盡,使用者在集中化而不是分散化。第二,使用者越來越懶,越來越不願意安裝使用你說的那些小型App(除非確實很有特色)。第三,你只看到了百度在移動端的統治力下降,卻沒看到騰訊、阿里的統治力有增無減,更別說還有正在崛起的今日頭條。回憶一下,過去一個月你開啟過多少個App?你有多少時間是花在微信、微博、淘寶等頭部App裡的?”
這位朋友在我剛開始研究網際網路的時期,給予了我極大的幫助。每當我產生什麼奇思妙想,他就會怒吼:“去學習!去調查!去找個真正懂行的人聊聊!坐在安樂椅上向壁虛構,會讓你越來越蠢!”
我發現自己需要重新學會“學習”。在學生時代,我們學習的方法是死記硬背、題海戰術、跟著教科書走。在工作中,沒有什麼教科書,也沒有習題課和補習班。我們經常會混淆“獨立思考”和“胡思亂想”的界限。比如說,2017年10月以前,我曾經一口咬定FGO是一款刷榜遊戲(對不起,我真心對B站和型月致歉)。為什麼呢?
因為有人教過我一個判斷遊戲刷榜的方法:開啟App Store頁面,檢視這款遊戲的“暢銷物品排名”。一般而言,玩家單次充值金額呈金字塔型分佈,最暢銷的是6元包或30元包,648元的超大包一般是賣的最少的。但是,刷榜者會選擇拼命買648元包,因為可以最快地刷出排名。我發現:FGO最暢銷的竟然是648元包,而且它的暢銷榜排名極不穩定,大部分時候前30名都進不了,偶爾卻能拿第一名!這不是刷榜的鐵證嘛?
直到2017年10月,我把上述“FGO刷榜理論”講給一位二次元遊戲行業前輩聽,對方盯著我看了半天,確認我沒在開玩笑,然後慢悠悠地說:“我發現,有時候你也挺幼稚的,不過也挺可愛就是了……”
原來,FGO是一款抽卡遊戲,而且新卡上線節奏與劇情密切相關。一旦有熱門新卡上線,Fate廚就會狠狠砸一波648抽卡,在一瞬間衝到暢銷榜榜首;等到Fate廚都抽到卡了,排名當然就降下去了。為什麼抽新卡的時候要買648包呢?因為優惠幅度最大,而且Fate廚也不缺錢啊。附帶說一句,後來我也玩了幾個月的FGO,總共只充了300多元。

2019年,本怪盜團決定集中精力研究網際網路廣告行業。眾所周知,增長最快的網際網路廣告平臺是字節跳動(頭條系);網際網路媒體廣告被打的落花流水,客戶預算大量轉移到效果廣告那邊。但是,我發現了一個矛盾:人人都說“抖音/頭條的廣告效果好”,我把“效果好”理解為“較高的價效比”;可是,看看抖音的廣告成交價,按照CPM結算明明比微博、入口網站更高呀!再說,既然抖音/頭條是效果廣告的大本營,為什麼還採取CPM(而不是CPA,CPL或CPS)結算呢?我坐在家裡冥思苦想了一個週末,毫無頭緒,只好去找一位頭條廣告的朋友喝茶。
這位朋友在五分鐘內解決了我遇到的難題:“是這樣的,廣告主交給抖音或類似平臺的需求,是以CPA或ROI方式呈現的。以遊戲買量為例,廣告主會提出‘我的目標獲客成本是120元,也就是一次有效下載120元’。廣告平臺會把這個CPA/ROI翻譯成CPM——假設每3000次觀看會產生一次有效下載,那麼‘CPA 120元’就會被翻譯成‘CPM 40元’。廣告平臺會代客戶為CPM 40元以下的觀看出價,並且根據實際轉化率隨時調整CPM。所以,在客戶那邊是按照CPA/ROI結算的,在廣告平臺這邊顯示為按CPM結算。”
在廣告行業,上述知識可能只是常識。可是對我來說,這知識太寶貴啦!順著這個話題,我們討論了“流量窪地”的概念:假設有一種遊戲,展示轉化率特別高,它就能開出遠高於競爭對手的CPM出價,從而以最快的速度拿到最大的量;假設有一家廣告主的目標使用者恰好不受同類廣告主歡迎,面臨的競價環境比較寬鬆,它就有可能以較低的出價獲客。“當然,在自動化報價的條件下,任何實質性的‘流量窪地’皆會在不太長的時間內被填平。不過這個填平的過程可能就足夠幾個產品異軍突起了。”朋友如是說。
說到遊戲買量廣告,我還請教過一位遊戲行業的老朋友:“現在各類遊戲的實際買量成本是多少?未來的趨勢是什麼?”
對方以一種關愛傻瓜的眼光看著我:“啥?我沒聽懂,這算什麼問題?”
我重複了一遍問題,對方“哦”了一聲,說:“有兩個答案。簡短的答案是:你可以以任意低的價格買到量,只要你不在乎時間。”
我更不理解了。他接著解釋:“每天,在抖音、頭條、微信朋友圈、百度這樣的流量平臺上都有無數的流量產生。你無論報一個什麼價,都能拿到一些量。但是,報價高了,你就更有競爭力,拿量更快;報價低了,你就沒啥競爭力,拿量很慢。”
原來如此,很有道理啊!我繼續追問:“那麼,長一點的答案呢?”
朋友說:“沒有長一點的答案,只有更簡短的答案:如果你是投資人,那麼你沒必要關心這個問題。”
什麼?搞了半天,我這麼多天的苦心思考全是白費嗎?對方耐心地解釋:“近年來,遊戲買量行為越來越標準化、工業化了。有經驗的買量公司會有一個詳細的方案,並與廣告平臺商定一個投放框架,從而達到一個目標ROI。頭條系的廣告銷售甚至可以做到按付費使用者結算,也就是儘可能讓‘最終效果’透明化。所以,如果你是投資人,或者是站在戰略角度看問題,應該更關注產品和整體營銷策略(例如目標使用者群、產品生命週期等),而不是買量價格這樣的微觀問題。”
本怪盜團團長就是這樣反覆因為“只思考,不學習”而被專業人士教育。但是,偶爾也有我教育別人的時候,因為世上有的是太愛思考、太不愛學習的人。
例如,當Google Stadia推出時,很多人興奮地問我,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在手機上玩3A大作了,包括在地鐵上刷《荒野大鏢客2》、在上班午休時間刷《怪物獵人世界》(其實在中國很少有人真玩過上述遊戲,只是聽人吹的心癢癢罷了)。我不想糾纏於延遲時間、付費模式和5G之類的話題,只是簡單地反問:“用觸控式螢幕怎麼玩《大鏢客》?還是單獨開發一個觸屏版?”
對方仍然很興奮地說:“外接一個手柄不就完事了,我看到好多外設公司都在強推移動手柄呢!”
我說:“我有一個問題,你試過帶移動手柄出門嗎?”
對方顯然沒有。我接著說:“我試過。有一陣子我還帶著Switch出門呢。重量是個大問題。想想看,手機廠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就為了減去那麼十幾克、幾十克的重量;你倒好,直接建議使用者隨身攜帶幾百克的手柄。我覺得絕大部分使用者會選擇繼續玩《王者榮耀》或《刺激戰場》。
這就是“學習”的好處——無論以什麼方式“學習”,它都在擴充我們的知識,讓我們接觸到全新的邊疆,不斷遠離自己的舒適區。一想到“學習”我就熱血沸騰,就像一個只玩過馬里奧的玩家決定嘗試《只狼》,或者一個從來只玩中單的召喚師開始嘗試刺客。如果我開的是坦克,我希望在一望無際的雪原上劃出全新的履帶痕跡;如果我開的是戰艦,我希望在從未有人抵達的七海之上留下第一道航跡。
人生苦短,少年/少女啊,趁著我們的心還火熱,趁著我們尚有無處發洩的求知慾,去學習吧!而思考,那應該是在經歷很長時間的學習之後,躺在沙發裡給自己的犒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