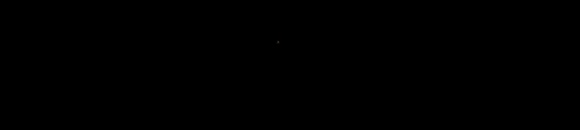5歲的女兒和姥姥一起洗澡,女兒主動提出給姥姥洗內衣,不然媽媽就要洗了,她不想讓媽媽累著。16歲的女兒一個人去異國,從來不跟媽媽說自己的辛苦。25歲的女兒如果每天不給爸媽打電話就會愧疚,她覺得自己不孝順,她隱瞞著乖巧聽話以外的所有面向,她努力讓自己成為媽媽喜歡的孩子。
不把這些故事綴以各自的姓名是因為雖然她們是完全不同的個體,但是你看,她們的經歷驚人地相似,都被同樣的詞彙描述——“懂事體貼”。《是女兒是媽媽》這四對母女關係各有不同,但沒有一個女兒不是乖巧的。

女兒不是作為一個人被教養長大,而是作為一個女性被培養長大,她們被教導怎麼說話、行事,比如要溫柔、乖巧、為他人考慮、有羞恥心,這種要求削弱了女孩說“不”的力量,常常讓女兒讓位自己的感受和需要,為別人服務,這個別人是母親、父親或是其他任何人,母親不會控制兒子的身體,卻會控制女兒的身體,因為她們擁有著相似的身體和命運,共享著很多身體的感受,比如月經和生育。這種支配從身體到精神,影響著女兒的命運,常常讓母女關係有著錯綜複雜、難以剝離的交織性。
女兒們當然不是一出生就乖巧懂事。媽媽們總是習慣指出女兒的毛病,她們要求自己,也要求女兒,退讓、壓抑、犧牲,就像陳夢媽媽對她說,讓別人先選,我們要最後一個選房。陳夢說自己小時候跟媽媽去超市,她要什麼,媽媽就不買什麼。媽媽給出的解釋是,因為她怕陳夢跟著別人去超市也這樣,於是後來陳夢跟著親戚們逛超市,什麼都不要,大家誇她懂事。

黃聖依也是一個聽話的女兒,母親鄧傳理在接受採訪時,對方問,做決定時有沒有考慮過女兒是否喜歡,她說:“興趣是可以培養的。”“有沒有想過黃聖依能不能接受呢?”她沒有任何猶豫地說:“她不接受也得接受,決定權在我。”
觀察鄧傳理和黃聖依的相處時,李嘉格說:“因為黃聖依習慣了強勢的母親,所以她在往後的日子裡也很習慣和強勢的人相處。”我們都知道,她說的是楊子。
結婚時黃聖依沒告訴家裡,鄧傳理說自己是從電視上得知的,“我就很驚訝,她為什麼要選擇那麼樣一個人”。黃聖依的解釋很清晰,楊子是她在權衡中最合適的選擇,這當然是理性的考量,但在外界看來,黃聖依雖然獨立,但她總要給自己找個權威的角色,這個角色以前是母親,後來是丈夫。

黃聖依描述母親和描述楊子時有著高度相似的地方。她描述母親——媽媽幾乎拿了她所在領域的所有榮譽,媽媽就是人生指南針,一筆一劃地構建了我的人生方向。她描述楊子——小時候我覺得他是萬能的、值得託付的,他對待我有一種長者、父親的角色,希望能夠按照他的指令去行事,我總是接到通知的角色。

錄製《是女兒是媽媽》期間,李嘉格幾乎每天都在哭。媽媽薄永霞在接受節目組採訪時說她知道自己總是否定李嘉格,而且也知道她會不舒服,但她覺得女兒沒有達到她的期待。
其她三對母女關係裡雖然各自都有心結,但只有李嘉格和母親薄永霞是如此地糾纏複雜,夾雜著細細密密的尖刺,讓人疼痛,在母親的面前,李嘉格是如此的不開心。

她們之間的拉扯和痛苦,讓人想到學者上野千鶴子對母女關係的經典分析:“無論是回應母親的期待,還是背叛母親的期待,只要母親還活著,女兒就不可能逃離母親的束縛。無論女兒是順從還是叛逆,母親都想一直支配著女兒的人生,哪怕在自己死後。女兒對母親的怨恨,表現為自責和自我厭惡。女兒無法喜歡不能愛上母親的自己,因為母親和女兒互為分身。對於女兒來說,厭女症常是對帶有母親影子的自己的厭惡。 有解決辦法嗎?正如信田所言,母親向女兒,女兒向母親,相互告訴對方:‘我不是你。’我們只能從這裡開始。”
看到李嘉格和媽媽薄永霞的關係時,讓人忍不住會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是愛?控制是愛嗎?貶損是愛嗎?如果愛裡有控制、貶損、打壓、否定,那這還是愛嗎?我們總是談論愛,但是很少去辨認愛裡的侵犯性。
薄永霞總是指責女兒“沒耐性”,脾氣差,對她說話大聲,看上去好像是這樣,但李嘉格說了那些沒有被看到的東西,她曾晚上三四個小時不睡覺陪媽媽說話,哄她。

薄永霞要求李嘉格要獨立、有自己的事業、在上海買房,這看上去沒錯,但是李嘉格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很辛苦,無法承受母親的這些期待,但母親也只是一邊繼續督促她,一邊讓她不要太辛苦,李嘉格被夾雜在這矛盾的要求裡,勉力支撐。
她們之間很大的心結是薄永霞認為李嘉格婆婆不好,婆婆第一次見面就跟她說:“這個家以後做主的是我兒子,你女兒不好使,我沒看好。”此後8年薄永霞不跟女兒的婆婆來往,女兒想說和,薄永霞就更加生氣。為了薄永霞的感受,李嘉格連續五年回孃家過年陪媽媽,有一年婆婆和媽媽都在三亞過年,李嘉格每天通勤一個小時跟老公見面。對於這些付出,薄永霞說,“這是他們兩口子商量的,跟我沒關係”。

媽媽總是跟李嘉格說,你婆婆看不上你,你可得自己爭氣。李嘉格非常直接地跟媽媽說,“你不覺得你跟我說這些話,你傷害的是我嗎?”“媽媽,你想過我很無助嗎?”
薄永霞無法接住女兒的痛苦,她依舊選擇刺痛李嘉格:“我哪裡傷著你了?”“那是你的事。”

相較於其他母女關係,程瀟與母親梁愛群顯得很客氣、很陌生也很有距離感,她們不太像一對母女,像是兩個懂事的女兒,互相為對方考慮,於是常常出現的問題是,這個家庭有太多的秘密,爸媽離婚,她們避而不談,媽媽生病也不告訴女兒,女兒遇到困難也不說。她們都想不困擾對方,可這種隱瞞也只是把對方推的更遠,就像梁愛群來參加節目的願望是,希望和程瀟吵架。“她只給我展現她好的一面,她不想讓我看到她脆弱。”

幾年前,梁愛群患乳腺癌,中晚期,當時妹妹準備高考,梁愛群考慮大女兒的工作,二女兒的學業,選擇隱瞞這件事,只是吃藥,等二女兒高考完才做手術。
知道媽媽生病的事情後,程瀟打電話罵她,梁愛群說,“罵得我很開心”。媽媽其實非常需要女兒的關心,哪怕是責怪,她也喜歡,可是即使這麼需要家人的關心,她也要忍受。就像在平時,她很關心女兒,但是她知道程瀟工作忙,從不主動去打擾,在網上關注女兒的行程動態。
程瀟在說起媽媽生病的事情時,有著很重的自責,不停地哭,“家裡所有人都知道我媽生病了,就是我不知道,她到動手術都沒有告訴我”。

其實程瀟也像這樣,她很小就去韓國做練習生,遇到很多困難但她也不說,最困難的時候,她給母親打電話,說得很簡單,“媽媽,我想回家。”當她回國之後,她把去韓國積攢的花銷小票給媽媽說自己一定會十倍百倍回報她。
這像極了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裡的一種情緒,雖然已經是極為理想的親子關係,但是愛裡仍然混雜著自責、犧牲和隱忍,總是讓離開家庭的孩子充滿著愧疚。IU飾演的女兒這樣說過:“我討厭媽媽這麼窮,更討厭因為我媽媽才變得這麼窮。”這種愧疚不只是因為錢,就像程瀟很介意梁愛群沒有更早離婚,是因為顧慮她們,於是才隱忍那麼多年。
這也像張泉靈在追溯薄永霞和李嘉格的矛盾時,她指出薄永霞之所以對女兒的依賴感這麼強,是因為她同時遭遇三重打擊:“母親去世”“丈夫偏癱”“女兒結婚”,於是她總想著把女兒捆綁在自己身邊,讓她支撐自己,不要拋棄自己。
張泉靈對李嘉格說:“你結婚把她的希望抽掉”,而這又讓李嘉格更自責了,“我其實以為我完成了,我才去奔著自己想過的人生走的,後來發現好像不是,是沒完成。”



談論女兒的痛苦時,外界總是習慣性地把矛頭對準了母親。可是不要忘了,母親也是這個社會結構的弱者,社會神話母職,這讓母親投入巨大的、過度的育兒成本,這注定導致她們緊緊抓住孩子,不肯也不敢放開。所以母親給出的愛,常常充滿著控制、犧牲和情感綁架,讓孩子特別是女兒充滿內疚、恐懼和責任感。
如果母女關係裡充滿著控制和傷害,那一定存在另一個問題——父親是隱身的。
在李嘉格和薄永霞起衝突時,她爸爸躲在廚房不出聲。李嘉格形容自己“有點給媽媽做老公的感覺”,“我覺得對於保護她這件事,我做得比他好”。小時候李嘉格的父親常以令人不適的方式貶低她,但媽媽薄永霞會給她很多心理安慰,每次爸爸說她不行,媽媽都會說你是最棒的,在她離家出走時,也是媽媽安慰她,把她找回來。當李嘉格因媽媽的壞情緒而崩潰,黃聖依建議她與父親傾訴時,她說,“我爸情緒還不如我媽穩定。”

薄永霞在養育女兒時承擔了比丈夫多更多的情感勞動,在愛情裡她也給丈夫當“媽媽”,她負責丈夫的情緒、身體健康、賺錢,丈夫很少給她情緒價值。在女兒的慶功宴上,丈夫連喝三天,突然中風偏癱,脾氣驟變,薄永霞照顧了他十年的生活起居。
程瀟在形容父親時也是說,父親從未參加過家長會,也從不關心她和妹妹的生活,從小她們就不跟爸爸聊天,不聯絡,父親對家庭淡漠,沒有家庭觀念。媽媽覺得丈夫的冷暴力給孩子造成很大的傷害,“我記得小時候瀟瀟跟在他背後喊他二十幾聲爸爸,他都不會回頭看一眼孩子。”

在旅途中期,節目開始展開媽媽們的人生,她們堅韌、勇敢,一直為家人付出,有的辭去穩定工作,獨自南下打拼,一邊抱著小孩子一邊創業。有的放棄留在國外的機會,回家照顧生病的媽媽,有的因為原生家庭的經濟,放棄了熱愛的乒乓球,從此她的人生就是照顧媽媽和照顧女兒,退休了也不願意出去玩,因為媽媽93歲了,沒多少時間了。
即使存在那些愧疚、自責、痛苦和傷害,我們也仍然會被一些時刻戳中,我們看到了愛。梁愛群說:“我想給女兒一個身體健康的媽媽,讓她更加沒有後顧之憂,沒有任何負擔的前行。”一直否認女兒的薄永霞在旅途中有了一些變化,她終於對李嘉格說:“你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很好,我很滿意。”李嘉格被媽媽困擾,可她也得到過很多支援和愛,她對媽媽說,“我很多的堅強和勇敢,是你給予了我非常多的信心勇氣,這支撐我走到今天,給了我很多力量。”

編輯:Tristan
撰文:周取
設計:小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