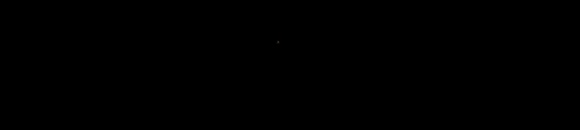作者 | 李沁予 編輯 | 範志輝
虛擬偶像,已經進化出“純血”AI藝人了。
最近,美國著名製作人Timbaland提出了一種新的音樂概念A-Pop,並宣佈推出首位AI偶像TaTa,並宣佈首張單曲《Her》即將發行。

按照Timbaland的說法,“A-Pop”被其定義為一個新的音樂流派,類似於以往的 J-Pop日流、K-Pop韓流。不同的是,它不是以國家為核心,而是以“AI創作能力”為核心。TaTa 則被Timbaland設定為這一新流派的第一個代表藝人。
那麼,當AI全面驅動虛擬偶像的創作與表現後,將如何影響當下的虛擬偶像生態,並與人類藝人競爭或共生?其全AI創作模式又給音樂行業帶來哪些影響?

首位“純血”AI偶像誕生
今年6月,Timbaland與知名電影製片人Rocky Mudaliar、AI音樂顧問Zayd Portillo共同推出了AI音樂公司Stage Zero,並宣佈首位AI藝人TaTa即將出道。
值得注意的是,Portillo不僅是AI科技工作室Light Energy Labs的聯合創始人,還擔任AI音樂平臺Suno的顧問,協助平臺進行AI音樂技術的整合。同時,Timbaland也在Suno擔任戰略顧問。

據介紹,Stage Zero的創作流程依賴於Suno的協作。具體來說,團隊會先上傳Demo音訊,接著Suno會對Demo進行處理,利用AI技術生成新的音效、調整聲音,甚至可能根據Demo的內容,來幫助確定音樂的風格或情感。然後,團隊會結合由人類創作的歌詞,最終完成整首歌曲。
而TaTa 的聲音正是在一次AI音樂生成過程中引起了Timbaland的注意。他表示:“那一刻我意識到,這個聲音令人驚豔。”
在Timbaland眼中,TaTa 並非虛擬形象的再版,也不是二次元的對映,或3D建模的幻想角色,而是由AI構建、具備學習能力、能夠獨立發展的真實藝術家,更像是AI生長出來的。

Timbaland認為,未來的藝術家將不再僅僅是人類,他們將成為完全自主的智慧財產權、程式碼和機器人。他表示,Stage Zero正在打造的正是這樣的未來。TaTa只是一個起點,也是“A-Pop”文化演進的重要標誌。
雖然,目前TaTa的首張單曲的發行日期仍處於保密狀態,但Stage Zero團隊已經在打造她作為完全實現的數字藝術家的身份。
從目前官方釋出的形象來看,TaTa呈現出一種濃烈的新朋克加Y2K混合風格穿搭,熒光粉紅挑染頭髮極具辨識度,配合黑色髮根,整體氣質有種叛逆卻精緻的視覺衝突。穿著方面,紅色亮麵皮衣、金屬疊鏈的整體視覺與背景略顯未來感,相比以往的虛擬形象多了一絲真實溫度。

顯然,Timbaland對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十分有信心,他表示:“我不再只是製作歌曲。我正在從零開始製造系統、敘事和明星。”
不過,仍有網友指出,曾經的嘻哈教父Timbaland如今已經失去了當年銳度。他不僅更看重商業,而且在直播中常常批評“現在的音樂太沒水準”、“聽不懂在唱什麼”,但自己卻始終無法提供令人信服的新作品,喜歡搞一些充滿營銷噱頭的新物種,目的是為賺錢或維持公眾關注。
比如Timbaland所推出的TaTa,給人一種為了迎合市場需求而失去藝術價值的感覺,甚至讓人覺得有些“尷尬”。
然而,無論外界如何解讀,TaTa的誕生本身已經是不可逆的現實。在技術革命的產業現實中,這種新形態正在悄然逼近主流文化視野。

“虛擬偶像101”
“虛擬偶像”並非一個新鮮概念,在不同歷史節點上,虛擬偶像作為技術發展、娛樂工業與文化想象交匯的產物,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
深挖的話,虛擬偶像可追溯至上世紀50年代。1958年,美國演員Ross Bagdasarian打造虛擬樂隊Alvin and the Chipmunks,憑單曲《Christmas Don't Be Late》兩登Billboard冠軍,獲五項格萊美,唱片銷量達500萬。

1967年,美國製作人Don Kirshner推出虛擬樂隊The Archies,其首次亮相於漫畫書《Life with Archie》的第60回,一經推出便迅速吸引了大眾的目光。

這一時期的虛擬角色由製作人主導。虛擬角色依附於劇本和動漫框架,由幕後製作人操盤,透過電視傳播,形成“動畫+音樂”驅動的虛擬偶像雛形。儘管這兩個IP後續都推出了真人影視改編作品,其核心形象依然侷限於媒介載體之中。
這一階段的虛擬偶像,更多是“媒介奇觀”,扮演著技術展示視窗或品牌附屬形象的角色,本質上缺乏內容的自主性和人格的連續性,形象生命力多依附於外部敘事。

從近30年來看,虛擬偶像的演化路徑可粗略劃分為三個階段:技術文化探索階段、擬人化階段、多元化階段。每一階段的關鍵差異,不全在於視覺呈現的升級,而在於內容主權的歸屬變更,從由人賦形,到共創互動,再到AI驅動的自主生成。
1990年代初,日本Visual Science Laboratory推出了伊達杏子(Kyoko Date),被稱為首個CG虛擬偶像。當時,其製作團隊採用三維建模和運動捕捉技術,模擬人類歌手的表演形態,嘗試在廣告、音樂與綜藝中滲透傳播。

同一時期,韓國娛樂界開始嘗試製作虛擬偶像。韓國娛樂公司Adamsoft推出了虛擬歌手Adam併發布新專輯《Genesis Adam》,他也曾登上電視廣告、音樂節目舞臺等,以“數字藝人”的身份參與商業活動。

然而,技術侷限令它們的外觀質感與表現力難以與三次元美學競爭,美學不成熟、表演過於機械,更像一個試驗性專案,而非真正的文化符號。
直到2000年,英倫樂隊Blur主唱Damon Albarn與漫畫家Jamie Hewlett共同創造的英國虛擬樂隊Gorillaz,併發行首張EP《Tomorrow Comes Today》正式出道,才為虛擬偶像的演進帶來了關鍵的轉折點。
雖然音樂完全由真人創作,但演出形象、專輯視覺和MV敘事均由四位虛擬角色構成,真正將“偶像即角色”的理念推至主流舞臺,開啟了“虛擬形象即品牌人格”先河。此時,虛擬偶像不再是單純的皮囊,而成為具象的文化介面,可承載理念、風格與敘事。

後來,相繼登場的日本的初音未來、國內的洛天依等虛擬偶像,則進一步深化虛擬偶像的“工具角色”雙重性。
在語音合成軟體Vocaloid支援下,使用者可將語言拆解為最小音素單位,不僅創作音樂、影片和故事,還共同塑造虛擬偶像的人格設定與情感認同。在這一機制下,虛擬形象不再依賴單一創作者,而是由社群不斷注入意義與生命力,內容生態呈現出顯著的去中心化趨勢。

此外,當年爆火的“萌系少女”這一設定,也為商業化鋪平道路:代言、插畫競賽、粉絲活動與演唱會遍地開花,Cosplay、二創內容與周邊經濟形成完整的文化經濟閉環。
這一階段的虛擬偶像雖高度擬人化,但創作主導權仍掌握在人類手中。它們擁有“角色生命”,具備穩定的性格設定與情感投射通道,但行為邏輯與內容生成仍依附於人類的設定與策劃。
行至2020年代,伴隨生成式AI模型、元宇宙概念進入大眾視野,虛擬偶像開始出現本質躍遷。這個階段的重要標誌,是虛擬藝人開始具備一定程度的內容自生成能力,並在音色建模、歌詞生成、形象驅動等多個維度擺脫人類主導。
以AI說唱偶像FN Meka為例,其音樂和歌詞部分由AI生成,人物形象則結合街頭文化、科技審美進行視覺塑造。這種嘗試雖引發文化挪用、種族立場上的爭議,但確立了AI內容主導型偶像的雛形。

在虛擬偶像的迭代演化中,“人類表演”與“虛擬身份”之間的關係也逐漸鬆動。比如,SM娛樂推出的首個系統性引入“虛擬孿生體”(AE)概念的女子組合aespa,每位現實成員均配備一個虛擬分身,兩者共同存在於一個名為“Kwangya”的敘事宇宙中。
虛擬成員不僅參與MV與視覺內容,亦在社交媒體、虛擬舞臺中進行即時互動,成為偶像生態中不可替代的一環。虛擬身份在此不再是技術展示,而是世界觀敘事的結構支點。

相較之下,虛擬男團PLAVE採用了真人即時驅動的虛擬形象系統,既保留了人類情感表達的真實溫度,又賦予了虛擬形象高度的可延展性與穩定性。他們並不試圖走向逼真的真人復刻,而是以誇張化、風格化的二次元形象切入,與年輕使用者的審美共識構建更強的認同橋樑。

回看如今Timbaland推出的 TaTa,從聲音、形象到音樂都由AI生成,似乎標誌著真正意義上“純血AI藝人”的落地,具備一定程度的表達自主權與動態創作和表達能力。她是創作者,也是內容本身。

將不同階段的虛擬偶像進行橫向比較,可以發現,過去,虛擬偶像是人類敘事的延伸,而現在,它們逐漸成為一種技術自組織的表達主體。這不僅改變了偶像產業的運作模式,更將重塑內容創作的現實基礎。
換言之,虛擬偶像的核心變數,正從“它是誰”逐步過渡到“它能做什麼?”,可以預測,在TaTa之後,虛擬偶像將正式進入到生成化階段。

虛擬偶像,真實衝擊
過去,我們認為偶像是一種“真實的投射”,有血有肉,有成長曲線,有情緒波動。但今天,虛擬偶像所掀起的浪潮,正在悄悄向行業逼近。
根據Metastat報告,全球虛擬偶像市場正在世界各個地區迅速擴張。到2025年,北美地區佔全球虛擬偶像市場的24%。而亞太地區是虛擬偶像市場領先且最具活力的地區,由中國、日本、韓國和印度等國家和地區組成。

而據 QYResearch 釋出的《全球虛擬偶像市場報告2024-2030》顯示,預計到2030年,全球虛擬偶像市場規模將突破50.3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高達18.8%。而在更廣義的虛擬網紅(Virtual Influencer)市場,Grand View Research 資料指出,2024年市場已達 60.6 億美元,且預計2025至2030年將維持 40.8% 的驚人增速。
尤其在日本,虛擬主播公司Hololive旗下藝人與各種公司甚至東京都政府展開了廣泛合作,使Vtuber(虛擬主播)文化越來越走入主流。不少成員已成為真正的網路明星,甚至頻頻出現在現實世界中。

Hololive母公司Cover創始人兼CEO谷郷元昭曾表示,3D、Vtubing(虛擬主播)相關的內容只會越來越大。曾是2010年代的小眾文化,如今在日本已成長為一個到2033年預計市值將達80億美元的產業。
在全球範圍內,虛擬偶像的演化趨勢也正在顯現,隨著 AI 技術的融入,它們正逐步迭代出AI基因。相比傳統偶像的依賴團隊包裝、市場運營、慢速成長的路徑,虛擬偶像從一開始就擁有可控的設定,從外貌、聲音、性格到價值觀、成長軌跡都可以被預設、修改甚至迭代。
它們不再受限於肉身的疲憊與邊界,而成為操盤者完全可控的內容資產。

虛擬偶像天生具備的穩定性,也讓它們無塌房之虞、無輿論反噬之累、無違約風險之憂。這一點,對於品牌方或平臺來說,幾乎等於穩賺不賠。在風險控制愈發重要的時代背景下,數字構造的“非人”反而顯得更可控、更可靠,甚至更“人性”。
從內容製作的角度來看,隨著虛擬偶像逐漸朝著AI偶像迭代,其也打破傳統音樂製作的分工體系,詞曲創作、編曲製作、演唱表達、形象包裝、內容發行,這一套線性流程正逐步被模型生成、資料驅動所滲透與重組。
正如Timbaland所說,“如今的技術簡直是為音樂製作量身打造的。以前需要我花三個月完成的工作,現在只需兩天。”這也正是虛擬偶像開始替代真人藝人的關鍵原因之一,它不僅能做,而且能快、能穩,還能無限複製。

在變現機制上,虛擬偶像也展現出更高的靈活性與可延展性。無論是虛擬演唱會、社交平臺IP聯動、時尚代言,還是與NFT、元宇宙場景整合的沉浸式商業空間,虛擬偶像可以輕鬆穿梭於不同的媒介架構與消費語境,形成全域營銷的動態節點。
然而,效率提升與結構最佳化的背後,也埋下了深層次的行業震盪。
目前,三大唱片與AI音樂公司Suno、Udio的談判仍在繼續。音樂公司希望對其作品的使用擁有更大的控制權,而AI平臺則希望保留更多的靈活性來探索和創新,同時希望協議的價格能夠適應初創公司的需求。

若訓練資料含有受版權保護的作品,生成結果是否構成侵權?演算法是否可視為創作主體?這些問題尚無明確法律先例可循,成為音樂產業在AI時代最尖銳的法律衝突之一。
不難看出,效率與情感之間、在商業與文化之間,AI虛擬偶像的衝擊遠未到達終點,但顯然,它已經成為音樂行業無法忽視的變數。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粉絲將真實情感投注於“演算法人格”時,背後的公司或平臺是否應承擔起內容與倫理邊界設定的責任?
又或者說,若一個虛擬偶像的“人格”由AI生成而來,其價值觀、情感表達、審美趨向均可由程式碼迭代,我們是否願意將“藝術家”這一稱謂賦予其身?
先聲話題
話題內容:你認為,AI偶像會是走出下一個“初音未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