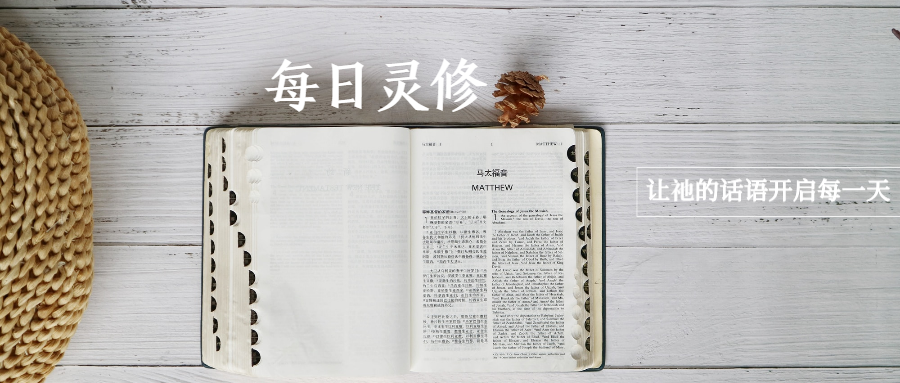上週六,我們在忽冷忽熱的上海舉辦了第127場一席演講,以下是本次活動的幕後花絮和精彩片段。
花絮
花絮導演 / 大凱
攝像 / 大凱 Chaos
演講
01.
陳小雨在生命的河流中坐上自己的船

在那部紀錄片裡,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的好朋友大米。她是一家青年旅舍的老闆,她說:“其實我來大理尋找的是一種生活,是一種故鄉的感覺。”
這句話給我一種朦朧又強烈的共鳴,因為我好像也一直在異鄉尋找故鄉的感覺。我們期望當中的故鄉,應該是可以給我們一種非常簡單、安定的港灣的感覺。但是由於迅猛的城鄉變化,農村的人口結構變化,你回到那個村子裡面,它好像變得不是港灣,所以你要向外面去找。
大理的安定和自由其實也沒有給我一個答案,然後我就開始想:是不是其實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所以就病急亂投醫找了“夢想”這樣一個東西,覺得在這個快速變化世界裡有屬於自己的一份篤定?但現在我的夢想到底是什麼?它變得越來越虛幻。

02.
蔣政宇 每個人都會跟麻醉醫生打交道

相比於專長某種疾病或某類人群的內外科醫生,麻醉醫生的工作貫穿了一個人從嬰兒至暮年的所有階段,也囊括了婦、兒或危重症者等不同人群。我在手術室裡聽到過新生兒的第一聲啼哭,也送走過器官捐獻患者的最後一聲心跳。從這個角度來說,麻醉醫生守護了生命的每個時刻。
我想告訴大家,如果某一天不幸在看病治療的時候需要沉沉睡去一會,請大家放心,會有一個人在離你最近的地方守著你。這是麻醉醫生給你的承諾。

03.
周軼君 教育的細節

也有人問我,看過這些案例後對我有什麼影響。非常坦誠地說,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孩子的成長有他們自己的軌跡。他們生來就有自己的特點和個性,不可能按照家長既定的目標,或者有什麼樣的期待去成長。和他們相處的過程,我原來以為是我每天在對他們施加影響,其實呢,是我每天在改良我的認識。教育中,需要改變的不是孩子,是成年人。

04.
李昀鋆隱藏的哀傷
在我的研究中,很難說有誰真的接受了“為什麼”的答案,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想通了”。慢慢地,我意識到,對年輕子女來說,父母為什麼會在他們還年輕的時候死亡,“這一問題的答案就是無解”。很多苦難之所以苦,也正是因為無解。到最後,很多年輕子女與這份認知失序和解的方式,並不是找到答案,而是接受了自己被改變了的認知結構。
這些用年輕子女的話來說“很喪”的認知重建,與一些西方研究結果相呼應:經歷過父母離世的年輕人,比起對照組的同齡人,更難相信這是一個有意義的世界,更傾向於認為世界是隨機且不可控的。當年輕子女將“經歷父母離世”理解為一個認識世界,或者生命本相的過程時,似乎那些痛苦沒有那麼難以承受了,但他們所交的學費,實在太過於沉重了。

05.
宋明蔚比山更高
如果他們因意外離開這個世界,痛苦會落在那些最愛他們的人身上。是盡情追求自己的攀登理想與自由意志,卻要刺痛家人;還是遠離曠野與高山、帶有遺憾地過此一生?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生觀的博弈。對自由攀登者而言,他們沒有中間地帶,必須選擇其中一個。這成了他們內心中最掙扎、最撕裂、最矛盾的地方,也似乎成為了他們永遠無法與自己和解的原罪。
大多數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不會迴避、漠視這份原罪的存在。他們就像揹負荊棘一樣,清醒、痛苦地揹負著它一起攀登。有人說這是自私,然而我卻覺得這也是一種勇氣。

06.
張沁文從親歷疾病到創造迴響

也有的患者會問我:“我是不是得了進食障礙?我最近總是控制不住地吃東西,然後又偷偷地吐掉。”有的患者則會傾訴:“我好害怕別人知道我有這個病,我覺得自己好丟臉,不知道該怎麼辦。”還有的患者會向我求助:“我已經嘗試了很多種治療方法,但都沒有效果,我是不是沒救了?”
我想,我在上海的就醫之路已經如此曲折,更何況其它地區的他們呢?如果當時被社會看見的我,不多說幾句,那他們要花多少時間才能知道自己的痛苦究竟叫什麼名字呢?於是,我自然而然地開始了健康傳播的旅程,在網際網路上不斷分享進食障礙的科普短片。

07.
姚璐看不見的中東
旅行不僅讓我看見了中東女性,也讓中東女性看見了我,看見了女性的另一種可能性。
在那些保守地區,我的女性沙發主對我的經歷和見聞很感興趣。我作為一個活人出現在她們眼前,讓她們真實地看到了女性未必只能過一種被禁錮在家庭中的生活。女性可以去登山、去徒步、去旅行,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當你相信你可以做到,並勇敢地付諸實踐後,你或許就真的可以做到。

現場 & 幕後





▲ 沈辛成老師(演講《幸福村為什麼沒有抽水馬桶》永珍《博物館裡的美國》)


▲ 感謝牛童老師的攝影(演講《短暫的認同,漫長的流動》)
籤售現場

▲ 周軼君《走出中東》《中東死生門》

▲ 蔣政宇《深呼吸,開始麻醉了》

▲ 李昀鋆《與哀傷共處》




▲ 感謝大家支援小微企業 ⬅️⬅️ 一起來做好事,做大做強
感謝@俊豪.Archie現場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