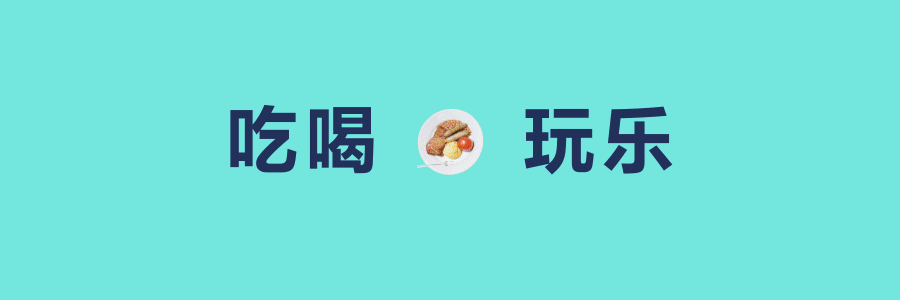外賣平臺的高抽成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網路上經常有小餐飲店老闆發帖,抱怨做外賣根本賺不到多少錢。前陣子微博曾經有個熱轉的截圖,顯示顧客實際支付40.8元,而商家到手的只有25.02元,平臺提成15.78元,抽成比例是38.7%。
顧客支付的40.8元裡,有34.5元是食物和包裝費用,另外還有6.3元的配送費(不知道這6.3元是不是全部給外賣小哥)。姑且把這6.3元從我們的計算裡刨去,這單外賣的總金額按照34.5元計算,那麼商家收到25.02元,平臺提成9.48元,提成比例是27.5%。
這麼一看好像合理一點了,但其實27.5這個比例還是有點高的。我看到有餐飲行業協會分析,10-15個點是一般餐飲企業可以接受的合理抽傭,超過這個範圍商家就很難實現盈利。開餐館畢竟是薄利行業,賣出去10塊錢,要給第三方交2.75元,剩下的還要交房租水電發工資買食材,利潤確實所剩無幾。
當然,僅僅是這一單外賣的個例沒有太大的說服力,不能說明普遍的情況,有些外賣單的抽成可能並沒有這麼高,當然也可能比這個更高,但具體這個比例是多少,很難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外賣平臺通常會設定一套複雜的計算體系,每一單外賣的提成金額受到距離、時間、總價等等因素的影響。即使它們公佈了計算公式,也很難讓外界對佣金比例有一個清晰的瞭解。
但是,我看那條微博下的討論,真是叫苦連天,所謂“天下苦平臺久矣”的說法顯然不是空穴來風。
其實同樣的故事也正在美國發生。
紐約剛剛透過一項法案,規定外賣抽成不能超過15%,美國三大外賣巨頭反手就把紐約市告到了法院。現在官司還沒有開庭,但更多的美國城市已經在考慮跟進紐約的措施,可以說一場針對外賣平臺的戰爭正在很多城市悄悄地打響。
先簡單介紹下美國外賣市場的情況。中國的外賣市場主要是美團和餓了麼的黃藍天下,美國市場的競爭要更加激烈一點,主要有三大巨頭——DoorDash,Grubhub,以及Uber旗下的Uber Eats。此外美國還有十多個區域性或者針對細分市場的小平臺,像我在紐約時就用過一個以服務中國移民為主的APP,上面大部分是中餐館,全中文介面,風格和餓了麼有點像。
總部在舊金山的DoorDash是後起之秀,成立最晚但是發展特別迅猛,去年底DoorDash在紐交所上市,當天股價暴漲85%,所有人都看好它們長成另一個網際網路巨無霸。值得一提的是這家公司的創始人是斯坦福大學畢業的三名華人,從左到右分別是香港人Stanley Tang,5歲隨父母從南京移民到美國的Tony Xu,和在加州長大的第二代移民Andy Fang。

從全美來看,DoorDash佔57%的市場份額,Uber佔26%,總部在芝加哥的Grubhub佔16%,三大巨頭瓜分了99%的市場。紐約的情況則比較特殊,DoorDash 36%,Grubhub 34%,Uber 30%,三家基本打了個平手。
和中國相比,美國的線上外賣市場規模原本不是很大,但是受益於疫情,各家公司的業務在去年都出現了爆發式增長。查了下資料,2020年全美各外賣平臺總營收506億美元,約相當於人民幣3260億元,是前一年的兩倍還多,是僅次於中國的全球第二大外賣市場。
作為參考,同年中國的外賣市場規模是6600億元。考慮到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但同時美國物價貴很多,一單一個人吃的外賣少則十幾美金多則幾十美金,綜合這些因素,我們可以對美國外賣的滲透率有一個大致的瞭解——雖然可能不像中國這樣街頭隨處可見外賣小哥,但也算是非常普及了。
美國外賣平臺的抽成大致在15%-30%之間。和中國一樣,美國各城市的餐飲從業者對平臺的高抽成也是怨聲載道。
早在2019年,紐約市議會的小商業委員會就注意到了很多餐館的抱怨,開始著手研究措施,舉辦了一系列調研和聽證會。紐約市議會的網站上有非常詳細的文件記錄,聽證會上每個人說的每句話都能查到。
我看到其中有一份調查,在接受調查的300家餐館裡有90%都表示外賣平臺的佣金高得離譜(unreasonable),還有60%表示他們在外賣平臺接的訂單幾乎沒有利潤勉強保本(barely profitable)。
一位餐館老闆說,自己就是在給這些平臺免費打工(working for free);另一位說,感覺自己累死累活卻是在給平臺賺錢(it seems like we’re making food to make them profitable)。
中英文翻譯一下,簡直可以說和中國餐飲從業者說的話一模一樣。世界是如此相似。

去年的疫情讓美國餐飲行業舉步維艱,因為不能開放堂食,餐館只能透過外賣平臺接單。於是紐約順勢推出一項臨時措施,規定外賣平臺收取的抽成比例不能超過訂單總金額的15%,其他諸如廣告展示、排位之類的費用不得超過訂單總額的5%。兩項加在一起20%,應該說這已經是一個對平臺比較仁慈的數字。
除了紐約,還有舊金山、芝加哥、西雅圖等十多個大中城市都做了類似的規定。
今年疫情漸退,餐廳的堂食開始恢復。8月底,紐約市議會透過法案,把之前對外賣平臺15%+5%的限制變成了永久規定。在紐約之前,舊金山市議會在6月同樣全體通過了類似的法案,直接把平臺的抽成比例封死在15%,成為全美第一個對此地方立法的城市。
這下三大外賣巨頭就急了,它們怕從此就永遠只能收15%的租,更怕其他的城市也會跟進。DoorDash、Grubhub和Uber Eats迅速作出反應,聯合起來起訴舊金山和紐約市政府,它們認為這些規定違反了美國憲法,是越權管控。
這兩個案子的走向會比較有意思,不知道法院接下來會如何判決。
三家公司起訴時還附帶了經濟賠償的訴求,也就是說兩地政府如果敗訴,恐怕還得支付一筆不菲的賠償金。反過來如果三家公司敗訴,那將是紐約24000家餐館、舊金山4400家餐館的福音。
《紐約時報》在2019年時有篇報道的標題比較有意思,“New York vs. Grubhub”。我是看到這篇報道才突然意識到,原來這不只是餐飲從業者以及政府監管部門與外賣APP之間的角力,對紐約人來說這是一場全紐約和外賣巨頭之間的爭奪。
仔細想想,不難理解這樣的視角。我一直講紐約人的觀念裡有一樣讓我很受啟發,就是他們特別注重保護那些“小店”——小餐館,小咖啡館,小雜貨店,小麵包房。無論是都市更新、建新高樓,抑或是新的連鎖商業開店、新的商業巨頭進駐,紐約人一定會評估的就是這些這些建設專案帶來的地價上升和商業競爭會不會讓周邊原來的小店開不下去;如果是,那這個專案就會被否決。
沃爾瑪在全美國有5000多家大賣場,唯獨紐約是他們幾十年來一直無法進入的止步之地。街頭那些紮根於社群的小店,才是一個城市最獨特最珍貴的組成,至於那些在全世界複製貼上的連鎖商業,多一個少一個也沒有什麼不同。
外賣平臺收高額佣金,受影響最大的一定是那些利潤最微薄的中小餐館。如果佣金不降低,餐館要想活下去,要麼只能漲價,要麼只能偷工減料用更便宜質量更差的食材——無論哪種做法,最終還是會讓餐館開不下去,進而破壞改變這個城市原本的商業生態和社群文化。
所以,外賣平臺收餐館多少佣金,並不只是政府監管和餐飲行業的事,其實也影響著普通人。
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個人一直下意識地避免使用這些網際網路平臺,還有另外一個小小的原因,就是我不是太喜歡我的生活被一個個平臺完全接管的那種感覺。
我們常常說網際網路是“造神運動”,原來的意思大概是說網際網路行業裡有很多白手起家成為億萬富豪的創業神話,可是我越來越覺得這個詞還有另外一種更加字面意義上的理解——一個個巨大的連線一切的網際網路平臺,正在成為數字時代的一尊尊真神,它們高居雲端,有著無所不能的神力,可以透過演算法肆意地影響凡人的生活。這種神力總是讓我覺得略為惶恐。
我承認它們確實給生活帶來了很多便利,但是在不忙的時候,我總是儘量多走幾步路直接去餐館裡吃飯,我買單的錢全部都交給了餐館,不會被平臺抽走20%甚至更多。
我很少用那些生鮮電商平臺,儘量每天去線下買菜,一般的日用品也儘量不用電商網站而是直接去超市買。因為我不希望未來線下商業逐漸消失,變成想要買菜買日用品只能透過手機電腦下單的狀況。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公眾討論完全交給了社交媒體平臺,它的好處和壞處現在都已經顯露無疑,但我們再也無法掙脫。我實在是不希望未來,我們會把吃飯和其他的事也同樣完全交給一個個平臺。如果這個趨勢不可避免,我希望至少它可以來得稍微晚一點。
———
上一篇


看完請點在看 | 歡迎轉發朋友圈 | 長按上圖二維碼關注
關鍵詞
外賣平臺
餐館
外賣市場
美國外賣
佣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