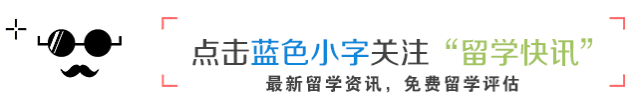一
當古老東方神話遇上現代新聞語境,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讓《華爾街日報》來報道“大鬧天宮”的這個想法源於我多年前看的一本書:《劍橋倚天屠龍史》。
作者新垣平創造性地用劍橋嚴肅歷史著作的風格來重新解構金庸的武俠經典,裡邊的目錄是這樣的——
“第五章:明教的復興與武術界的分裂”、“第九章:武當的崛起及其與少林的衝突”。
裡邊的正文是這樣的——
“每一次華山論劍都反映出武林中的權力分配關係,以“五絕”為名號的高手名單實際上映射出武林中權力秩序的現實邏輯。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稱之為江湖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正是這次論劍確定了此後大半個世紀的武林秩序。”
這種嚴肅的筆調和娛樂的內容所形成的奇妙反差當年曾給我帶來相當愉悅的閱讀體驗,以至於有時候我也會萌生創作類似作品的衝動。
但遺憾的是,我彼時有限的輸入和訓練並不足以讓我遊刃有餘地駕馭兩種截然不同的寫作風格。
然而,大模型的到來改變了一切,其海量語料的預訓練在理論上可以高度抽象出任何文字的內在特徵,同時還能流暢地風格化生成。
需要說明的是,不同模型的能力差異是非常大的,為了實現更好的效果,我選擇了AI圈在創作領域口碑出色的Claude,具體模型是Claude 3.5 Sonnet。
在我看來Anthropic公司是一家在AI世界聲量和實力嚴重不匹配的公司。
事實上,該公司出品的Claude已經在多個例子中被證明了在創作層面有著驚豔的表現,我稱之為“最強創作型AI”。
山姆*奧特曼2年前之所以讓ChatGPT匆忙提前上線,就是害怕被Anthropic搶先發布奪走了“第一個預訓練大模型產品”的心智。
二
廢話少說,我們直接看結果:如果讓《華爾街日報》來報道西遊記重要戲份:“大鬧天宮”,它最終的呈現會是怎麼樣的?
以下是Claude輸出的全文,提示詞相對複雜,我放到了後邊的篇幅中——
《仙猴衝突升級,天庭安全體系被攻破》
昨日,自稱齊天大聖的孫悟空闖入了玉皇大帝的天庭,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安全漏洞,動搖了天庭的行政核心,標誌著天庭權威與日益叛逆的猴群之間持續的緊張關係在顯著升級。
這一事件對天庭財產造成了廣泛的破壞,並擾亂了天庭的正常運轉,引發了人們對天庭維持其塵世臣民秩序能力的日益擔憂。
“這是對我們天庭治理模式的根本挑戰。”天庭行政部長李天蓋說,由於此事的敏感性,他要求匿名。“我們正在與一個在無監督情況下掌握修仙技術的實體打交道。”
知情人士稱,在將自己的名字從生死薄中抹去後聲名狼藉的孫悟空此前曾拒絕擔任弼馬溫一職——分析人士將此舉解讀為對天庭傳統等級結構的直接蔑視。
這次危機在天庭官僚機構中引發了衝擊波,幾個部門報告了嚴重的運營延誤。雲管理部報告稱,在關鍵基礎設施受損後,效率降低了 40%。
事件發生後,天庭武器製造商的股價飆升,Phoenix Feather Armaments (PFA) 在早盤交易中上漲了 15%。“我們看到所有天庭各部門對加強安全措施的需求都在增加。” 永生證券首席分析師張嫻說。
對於此次事件在經濟層面的後續影響,天庭經濟學家張雲子分析認為:“短期內天庭GDP或將受到衝擊,特別是在仙丹、蟠桃等高階消費品領域。但從長期來看,這或將推動天庭加大在安保科技領域的投資。”
此次危機引發了對天庭當前安全協議的嚴重質疑。據報道,孫悟空揮舞著從東海龍王那裡獲得的金箍棒,成功突破了多層天庭防禦體系。
“我們現在的安全框架是針對傳統威脅設計的,而不是為已經掌握了 72 種變身的挑戰者設計的。”天兵天將司令託塔李天王說。此後,軍方宣佈對其防禦戰略進行全面審查。
接近玉皇大帝的訊息人士透露,幕後談判正在進行中,如來佛被作為潛在的調解人進行接觸。然而,孫悟空作為白手起家的草根挑戰者的獨特身份讓形勢變得撲朔迷離。
“在與一個從根本上拒絕現有天庭秩序的實體打交道時,傳統的外交方法可能被證明是無效的,”神治研究所(Institute of Divine Governance)的著名政治學者袁博士指出。
在天庭努力應對這場前所未有的危機之際,許多觀察家認為,這一事件可能會迫使公眾從根本上重新評估天體當局如何處理與強大的地球實體的關係。
“簡單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時代可能已經結束了。”一位要求匿名的高階官員說。“我們需要制定新的框架,與不適合我們傳統類別的新興大國進行接觸。”
玉皇大帝辦公室已宣佈召開天庭議會緊急會議以解決這些問題,同時堅稱局勢仍“可控”。
本報將持續關注事態發展。
可以看到,Claude完美復刻了《華爾街日報》的寫作風格——直觀、專業、嚴謹、維度多、資訊密度大。
當這些新聞專業主義的詞彙和古老東方神話結合時,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化學反應,花果山叛逆妖猴的逆天舉動被其處理成一個關於治理、安全和制度改革的嚴肅議題,讓人忍俊不禁。
(大模型也不是完全沒有Bug,比如報道中把要求匿名人士的職位和姓名都爆出來了,這在現實中《華爾街日報》是看不到的。)
儘管這些年在網際網路的衝擊下,《華爾街日報》作為媒體的影響力在客觀上有所下降,其政治傾向等多個方面也屢遭公眾質疑,但其長期構建的簡潔、嚴謹、專業風格的確對全球新聞業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我們之所以看上面的文字熟悉,並不是我們真正看過《華爾街日報》,核心在於我們曾經接觸到不少國內嚴肅報道其實就有著《華爾街日報》的許多烙印。
這時候或許有人會問:潘寒,你到底寫了什麼提示詞,讓Claude能如此嚴絲合縫地輸出超預期的結果?
三
咱們先不著急揭曉答案,我量大管飽地讓大家看一看AI創作的表現,既然《西遊記》可以寫,那麼《紅樓夢》可以不可以?
當然可以!
讓我們來看一看《華爾街日報》是如何將《紅樓夢》第13章——“秦可卿死封龍禁尉,王熙鳳協理寧國府”,轉化成一篇關於京城家族企業人事重組的專業報道的——
賈氏家族核心高管意外離世,寧國府人事重組引發關注
北京訊 – 賈氏家族旗下寧國府分部營運總監秦可卿女士日前意外離世,終年24歲。知情人士透露,秦女士是在其私人居所遇難,具體細節尚未對外公佈。賈氏家族發言人拒絕就此事發表評論。
人事變動引發連鎖反應
秦可卿女士生前擔任寧國府營運總監一職,與寧國府當家賈珍私下關係密切。其突然離世不僅給寧國府日常運營帶來衝擊,更牽動了整個賈氏家族的神經。據悉,榮國府當家賈政已臨時任命其弟媳王熙鳳女士兼任寧國府營運協理一職。
"這一任命顯示了賈氏對於穩定寧國府局勢的決心。"企業管理專家表示,"王熙鳳作為榮國府的資深管理者,具備豐富的運營經驗。"
皇室褒獎雪中送炭
與此同時,皇室方面已批准由賈珍接任龍禁尉一職,此舉被解讀為對賈氏家族的支援。分析人士認為,這一任命將有助於穩定賈氏家族的社會地位,緩解當前的危機。
"龍禁尉雖為虛銜,但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政經觀察家指出,"這表明皇室仍對賈氏保持信任。"
財務狀況引發關注
然而,有市場觀察家對寧國府的財務狀況表示擔憂。據瞭解,近年來寧國府奢靡之風盛行,開支巨大。一位不願具名的前僱員透露,府中日常開銷已遠超正常水平。
王熙鳳此番就任協理,除穩定人心外,相信還肩負著理順財務的重任。有分析認為,這可能預示著寧國府將開啟新一輪的成本控制。
根據本報獲得的多份內部檔案顯示,王熙鳳在寧國府的降本增效計劃會在本月下旬陸續執行,部分高管已提前結束休假返回集團金陵總部。
市場反應與展望
訊息傳出後,與賈氏有業務往來的多家商號反應謹慎。對此,經濟學家表示:"賈氏家族作為帝都四大家族之一,其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市場走向。短期內,市場或將持觀望態度。"
截止到3月5日收盤,賈氏控股和賈氏地產分別微跌0.7%和03%。
至於寧國府未來發展,業內普遍認為王熙鳳的管理能力將受到考驗。有專家指出:"接下來的三到六個月將是關鍵期,王熙鳳能否帶領寧國府渡過難關,值得關注。"
不知道大夥看的感覺如何,我反正在震驚的同時多次笑出了聲。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Claude不但在語言風格上還原了《華爾街日報》的神韻,同時對《紅樓夢》本身的事實和邏輯關係理解異常準確,其解讀的層次也非常多元。
比如《紅樓夢》原著中沒有明說但暗示了賈珍和兒媳秦可卿不可描述的關係,在報道中文字體現為“與寧國府當家賈珍私下關係密切”,其用詞謹慎、準確、意味深長,確實很難相信這是AI寫出來的文字。
(當然還是有一個小Bug,開頭的“北京訊”表明大模型還是沒搞清楚金陵、京城和北京之間的關係,同時封龍禁尉的並非賈珍)
四
好了,接下來說一下我是如何寫這段創作的提示詞的——
要想讓AI寫出原汁原味的華爾街日報的Style,我們首先得搞清楚“華爾街日報風格”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風格?
要將這份創辦於1889年的古老報紙的寫作風格總結起來其實並不容易,遠非我們上面所說的“直觀、嚴謹、多維度、資訊密度大”等幾個簡單的詞可以概況。
因此,我們需要組織一個維度足夠豐富的框架來將《華爾街日報》日常報道最核心的特徵囊括起來,這個框架應該既有表層特徵,也有裡層內涵。
經過大量的閱讀與研究,我選取“皮、肉、骨、魂”這個由淺入深的框架,即“表徵句式、語言特點、行文邏輯、價值取向”這四個維度來定義其寫作風格。
最終輸出XML格式的提示詞如下——
<WSJ_Style_Guide>
<Prompt>
請以《華爾街日報》嚴謹專業的新聞報道風格,撰寫一篇關於孫悟空大鬧天宮事件的深度報道。需要包含事件背景、衝突經過、損失評估、各方反應及影響分析。
</Prompt>
<Character_Sentences>
– "XX對本報詢問未予置評。"
– "據接近XX的訊息人士稱…"
– "鑑於此事的敏感性,該人士要求匿名。"
– "根據本報獲得的多份內部檔案顯示…"
</Character_Sentences>
<Language_Features>
– 使用客觀、專業的措辭,避免情緒化表達
– 行文使用商業和政經專業術語
– 多角度引用各方觀點,語氣剋制、平實
– 重視資料支撐和事實依據
– 透過細節描寫提升真實感和可信度
</Language_Features>
<Narrative_Logic>
<結構>倒金字塔結構,核心資訊前置</結構>
<發展>層層遞進,由表及裡</發展>
<論證>多方引證,平衡各方觀點</論證>
<深度>注重挖掘事件背後的意義</深度>
<聯絡>善於將個案與宏觀趨勢相連線</聯絡>
<完整性>保持背景資訊和歷史的完整</完整性>
</Narrative_Logic>
<Value_Orientation>
<經濟理念>
<觀點>倡導自由市場經濟</觀點>
<觀點>強調企業效率和市場競爭</觀點>
</經濟理念>
<政治立場>
<觀點>偏向保守主義</觀點>
<觀點>對政府幹預持謹慎態度</觀點>
</政治立場>
</Value_Orientation>
</WSJ_Style_Guide>
好了,如果你這個時候正在仔細研究我以上提示詞中的技巧和邏輯,在琢磨我為什麼這麼寫,甚至準備複製、收藏以便趕緊去試一試,那麼請先停一停。
事實上,以上並不是我真正的提示詞,我真正的提示詞如下——
1.請用《華爾街日報》的風格給“大鬧天宮”寫一篇報道
2.請用《華爾街日報》的風格重寫紅樓夢的其中一章——“秦可卿死封龍禁尉,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這個Case裡的輸出為中英混排,我修改了個別翻譯不地道的詞彙

沒錯,我真正輸入的提示詞確實就是上面這一句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自然語言,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了。
少,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多;
簡潔,有時候比複雜更有力量;
五
我們中的不少人看到優秀的輸出本能會認為它的提示詞一定很複雜,即便不復雜,也一定很精妙。
甚至我將上面的輸出效果發給好基友看的時候,他判斷我一定是給Claude餵了一個《華爾街日報》新聞源的長文件。
沒錯,當三天前我隨手將這個創意丟給Claude的時候,我其實沒抱什麼希望,我當時的預期是:這種級別的提示詞要想達到理想狀態,怎麼著也得迭代個十幾遍吧。
然而,Claude以其強悍的實力打了我的臉。
這對於我而言是一個驚喜的Case,但對於如何更好地與AI對話的“提示工程”而言,它有著多種令人深思的啟示——
第一、深刻地理解簡單與複雜之間的關係;
對於效能強大的大模型而言,當你輸入“華爾街日報的風格”這個詞的時候,在它的向量空間中,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東西。
它意味著極其豐富的內涵,海量的語料預訓練的大模型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它不僅知道,而且它對這個詞的理解比你的描述要深刻的多。
所以,此時任何額外的描述都可能因為大模型的“注意力機制”偏離“華爾街日報的風格”這一本身的需求。
沒錯,用簡單幾個詞、十幾個詞甚至幾十個詞顯然無法描述偉大的莎士比亞、偉大的馬爾克斯、偉大的劉慈欣殿堂級的寫作風格,怎麼可能呢,這顯然是無法實現的妄念。
但神奇而又合情合理的是:“莎士比亞風格”、“馬爾克斯風格”、“劉慈欣風格”這三詞在大模型居然可以。
複雜和簡單的轉換就是如此神奇而微妙。
一個真正簡潔而直擊需求的提示詞最終的效果就是——“一支穿雲箭,千軍萬馬來相見”。
那支箭就是那一個或幾個準確命中靶心的詞,而千軍萬馬則是那些原本散落在浩瀚語料中飄散的詞,它們會如聽到遙遠的召喚一般:整齊出列、眾神歸位。
從這個意義上,語言學中的分支——語義學、語用學和計算語言學這三個子學科大機率會成為提示詞工程師們可以高度參考的領域。
六
第二、提高信噪比是寫提示詞的核心目標
如果看了上面這一段,你認為我推崇極簡的提示詞,那麼,你就錯了。
事實上,我認為提示詞該簡單的時候應該簡單,該複雜的時候應該複雜。
讓我從資訊理論的角度來解釋這一點——
我們如何寫提示詞,簡單或者複雜,用自然語言或者程式碼風格,本質上意味著我們如何對自己的需求和想法進行編碼。
有人用長的編碼,有人用短的編碼,從資訊理論告訴我們,如果表述足夠準確,長編碼和短編碼在數學上是等價的。
但現實的問題在於,自然語言本身的特點容易讓長的編碼產生冗餘和噪音,這就降低了提示詞的信噪比。
什麼意思?
比如,你要描述一個物體,你可以用形狀、大小、顏色、密度來描述,這些不同維度在資訊理論上都是正交的,即一個維度和另一個維度沒有任何關係。
但我們用自然語言描述的時候,往往很難做到正交。
比如我們經常寫的提示詞是這樣的——
“請創作一篇關於AI的賽博朋克風格的科幻小說,要求簡潔、明快、溫暖。”
事實上“賽博朋克”本身就代表了一種符號化的風格,這種風格或許可以簡潔、明快,但它內涵中“反烏托邦”的精神是不包含“溫暖”這一取向的。
如果這樣輸入,資訊不正交,就會產生噪音,降低提示詞的信噪比,AI遇到這樣不正交的提示詞就會疑惑、懵B,最終輸出的結果大機率會變成四不像。
因此,並不是一定要將提示詞寫短或寫長,也並不是一定要用結構化或程式碼的方式,而是你的提示詞的資訊維度要儘量做到正交。
當我們輸入“寫一篇賽博朋克的小說”時,我們其實已經規定了主題傾向和風格。
那麼額外的描述我們可以補充小說的“節奏”、“結構”、“人物關係”、“篇幅”等其他與“賽博朋克”正交的資訊,這樣的輸入才是真正有效的輸入。
關於這一點,從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圖畫論”也可以理解,他認為語言就是將世界的實際場景描繪出來的一幅畫,語言是世界的對映。
同樣,提示詞也是一幅畫,你可以畫的簡單、也可以畫得複雜,但不能畫成“五彩斑斕的黑”。
所以,重要的是用正交的資訊編碼來高信噪比地表達自己的需求:需求複雜,提示詞維度就多一些,需求簡單,提示詞維度就少一些。
永遠不要讓形式大於內容。
七
第三、對一件事理解的深度是提示詞效果的上限;
什麼意思?
我們就以上面的例子作為說明,如果你是一位新聞學科班出身的同學,你大機率會在讀到上面的文字時跳出來說——
“你這根本就不是華爾街日報的新聞報道風格,"華爾街日報體"作為一種新聞教科書中固定的文體早就已經是新聞學中的顯學了。
它的基本特徵是:首先以一個具體的事例(小故事、小人物、小細節)開頭,然後自然過渡新聞主體部分,接著展開交待主題背景、深層邏輯,結尾再呼應開頭,迴歸到開頭的人物身上。
你上面的文字大概只能叫“倒金字塔”體,你明顯是外行。”
(“倒金字塔體”據傳源自南北戰爭電報經常斷的時代,即把重要事實放前面,次要資訊和細節依次放後邊,這樣電報在任何節點斷掉都不太影響新聞效率。)

讓我們來仔細討論一下到底誰是外行?
的確,早在遙遠的2013年,遠沒有今天火的馬伯庸老師在知乎回答過一個問題——“什麼叫做新聞寫作中的「華爾街日報體」和「倒金字塔體」?”
(原貼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834756/answer/20410958 )
馬親王分別用“華爾街日報體”、“倒金字塔體”和“新華體”重新報道了“鴻門宴”這一歷史事件。(本文創意的來源除了《劍橋倚天屠龍史》,另一個源頭就是馬親王的這個無比驚豔的回答。)
其中“華爾街日報體”的開頭是這樣的——
“樊噲闖進鴻門宴會的時候,他的雙手緊握著短劍和盾牌,頭髮直豎,眼角幾乎要裂開。守門的持戟衛士試圖要阻止他,但失敗了。這位年輕時在沛縣從事狗類屠宰業的的平民,此時正面對著天下最有權勢的貴族項羽,高聲發出嚴厲的指責,整個宴會現場鴉雀無聲。”
沒錯,這樣的文風確實是中國新聞教材中的“華爾街日報體”,但問題是——現實中的《華爾街日報》日常真的是這樣報道新聞的嗎?
當然不是!
事實上,上述原教旨主義的“華爾街日報體”一般只應用在非事件新聞的趨勢特稿裡,而現實中《華爾街日報》超過90%的日常報道依然像上面Claude輸出的文字一樣遵循簡潔風。
我們用常識思考也會明白:一個正常的事件新聞,如果全都按以小見大的複雜套路來報道,而不是快速交待5W1H,那黃花菜都涼了,讀者早跑光了。
馬親王當年精彩的回答只是示範不同文體在風格上的差異,在鴻門宴這個例子中,仔細閱讀我們也會發現以小見大、細節頗多的“華爾街日報體”確實並不適合報道事件型新聞,其作可讀性和效率遠不如核心要素先行的“倒金字塔體”。
今天,我們《華爾街日報》的官網上看一看,通篇都是這樣簡潔、嚴謹符合“標題、導語、主體、結尾”這樣主流格式的新聞。


真實《華爾街日報》日常新聞都是將最重要的資訊放最前面
沒錯,我們如果只是拿著教科書上標籤化的理論去套,那隻在理解事物第一層,而理論和真實世界到底是如何對映的,這是理解事物第二層;
對於寫提示詞而言,其實還有第三層,那就是深刻理解目標任務和大模型訓練邏輯之間的關係。
Claude理解中文語境中的“華爾街日報體”嗎?
其實,並不理解。
我用“華爾街日報體”替代“《華爾街日報》風格”提問,出來的結果在風格上無差異,都是倒金字塔結構。

這背後的原因在於,中國新聞圈流行說的“華爾街日報體”其實國外討論熱度遠不及國內。
以“Wall Street Journal Formula”、“Wall Street Journal Style”等相關關鍵詞去Google搜尋,結果並不算太多,而且英文語境中對這個詞理解也不太一樣,它們甚至給它取了另一個名字——鑽石結構。

事實上,新聞領域著名的《華爾街日報如何講故事》這本書中,也並沒有公式化“華爾街日報體”這一概念,而是非常立體地講述如何做採訪、如何組織材料、如何讓故事更具可讀性。
但有一點,我們幾乎可以肯定,Claude的訓練語料中一定會有《華爾街日報》原始語料的。
作為在英語世界已經出版超過130年的報紙,Anthropic這樣級別的公司大機率有100種方法繞過《華爾街日報》的版權限制,從而獲得部分原汁原味的華氏語料,不然效果絕不會如此絲滑。
再回到本身的需求,在上面的Case中,我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事實上,我非常清楚我想要什麼,我當然不是想要原教旨主義的“華爾街日報體”。
這種文體除了不適合“大鬧天宮”這種事件型大新聞外,例子篇幅太長也不符合本文“以小見大、一葉知秋”的初衷,我要的只是“雙重陌生化”帶來的反差感。
再思考一個問題:四大名著我為什麼不選《水滸傳》和《三國演義》?
這背後的原因在於:以《華爾街日報》動不動上價值的尿性,《水滸傳》那些名場面生成的內容都會讓我這篇文章分分鐘過不了審。(不信你去試試)
而《三國演義》本身就屬於政治領域,出來的反差感遠不如前兩者;我為什麼不選擇《西遊記》、《紅樓夢》中的其他章節?(留一道小小的思考題)
所以,在寫任何一個提示詞之前,我們應該問自己一句:我對這件事的理解足夠深嗎?
提示詞真正的功夫,在提示詞之外。
八
第四、模型比提示詞重要100倍;
這其實用不著解釋,我試過上述的“大鬧天宮”的提示詞,無論是簡潔版還是專業版,輸入到豆*、文*言、Ki*、元*、通*等其他模型,你都得不到上面高質量的效果。(大夥可以試一試)
輸入簡潔版本提示詞,輸出在文風和用詞上非常浮誇,而輸入專業版提示詞,輸出在“形”上有所改善,但在“神”上差之千里。
所以,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至少在這個任務中,國內的大模型和Claude還有不小的差距。
當然,也必須客觀說明的是,我猜測出現這種結果大機率和訓練語料相關,事實上,在其他文字創作層面,國內模型和Claude差距就明顯縮小,比如創作“古龍”小說風格的文字。
我前些天聽了李繼剛老師的一次分享,他在分享中列了一個公式——
輸出效果=模型✖️(任務+提示詞)
沒錯,我非常認可繼剛老師對於模型和提示詞在效果權重中的深刻洞察,這個公式最大的價值在於,它清晰地告訴我們獲得理想輸出效果的最佳化要素。
同時我也想在此基礎上補充一點,從個人體驗上看,在效果方差極大的文字創作領域,這個公式或許可以修改成——
輸出效果=模型²✖️(任務+提示詞)
所以,如果你想用AI創作出超預期的內容,請確保你所用模型的先進性;
在AI創作的世界,選擇,真的遠遠大於努力。
九
到這裡,既展示了有反差感強烈的例子,又挖掘了提示詞背後的邏輯,文章本來可以結束了,但最後我還想引申出一個重要的推論——
AI的“消費型內容時代”已經來了!
什麼意思?
在ChatGPT誕生後的兩年,除了極少數AI極客群體,對於大部分人而言,至少在文字內容生產這一塊,90%輸出的是“應付型”內容。
單位要寫一個通知、找AI;老闆要求寫一篇讀後感、找AI;總結一個文件,找AI;這些內容的共同特徵就是,它是“應付型”內容,它大部分只需要60分就行。
然而要做到“消費型內容”,即人們願意花時間並且樂在其中的內容,60分是遠遠不夠的,沒有人願意消費“首先…..其次…..總而言之”這種“AI味”撲面而來的、永遠政治正確的文字。
而今天,無數傳播甚廣的案例表明,以Claude為代表的領先AI,在內容創作層面已經接近透過“藝術家圖靈測試”。
即人們已經區分不了這些文字到底是AI生成的還是藝術家創作的,這就是標誌著“消費型內容時代”到來。(當然,我指的是文字創造層面,影像領域早就做到了,但文字是遠比影像要宏大得多的創作形式,篇幅原因不展開,有機會專門寫長文章聊一聊這個。)
“AI消費型內容時代”意味著很多,意味著文藝逐漸進入“亂紀元”的新階段,意味著舊的創意體系和生產結構會逐步瓦解,意味著內容領域依賴人“原創+優質+高頻”的不可能三角開始鬆動,意味著複合科技和人文的“π”型人才可能比單一的“T”型人才擁有更多的結構性優勢,意味著很多很多…..
但無論如何,人和人的創意,依然是一切內容生產的起點。
“降維實驗室”這個賬號建立的核心價值就在於:發掘AI創作的上限,用聽得懂的語言和大家一起跟上AI的節奏,從容迎接“AI消費型內容時代”。
結語
塔西姆·辛是一位風格獨特的電影導演,在電影之外,他拍廣告片的開價也極高 。一次,一位廣告主問他:你就拍一個30秒的廣告 ,卻要收超百萬美元,是不是太貴了?
塔西姆·辛說——
“你花錢買到的不只是我做導演的這段時間,還有我喝過的每一口酒,品過的每一杯咖啡,吃過的每一頓美食,讀過的每一本書,坐過的每一把椅子,談過的每一次戀愛,去過的每一個地方,你買的是我全部生命的精華轉化成的30秒,怎麼會不貴?”
對於機率分佈並不均勻的未來,我只有一句話——擁抱AI、擁抱生活!
—完—
作者:“降維實驗室”主創潘寒,《三體》死忠,野生AI創作者,挑戰AI的各種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