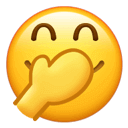在一次關於“女性身份感”的訪談調研中,心理學家提出一個令人不安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女性,正在失去自己的名字。她們在公司被叫“X經理”,在家庭被叫“媽媽”,在社交場合被叫“誰的太太”……但很少有人,真正喊她一聲“你自己”。
城市中產女性的“身份消耗”正在加劇。資料顯示,近67%的28-40歲女性表示:在忙碌與期待之間,她們“越來越不像自己了”。2024年,《第一財經》釋出了一份針對中國城市女性的生活狀態調研報告:超過72%的職場女性表示“經常感到情緒疲憊”;48.6%的女性有過“自我價值感缺失”的感受;而在社交平臺,“情緒穩定”甚至被視為一種“奢侈的能力”。

與此同時,#悅己主義# #女性情緒價值#等話題在社交平臺的瀏覽量突破30億次——這些數字所透露的,是一個正在悄然崛起的社會現象:越來越多的女性,正在從“取悅他人”走向“迴歸自己”。
在以快節奏與高期待為底色的都市生活中,女性常被裹挾於多重角色之間:是職場裡的高效執行者,是家庭中的情緒中介,是社交場上的精緻人設維持者。
但很少有人問:她們自己呢?

當“悅己”成為越來越多女性的生活關鍵詞,它早已超越了簡單的消費升級,變成一場關乎精神自洽的意識覺醒。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萃雅發起了“覓境尋真·以花悅己”的玫瑰溯源之旅。這不僅是一場護膚品牌的原料溯源,更是一次關於現代女性“如何與自己相處”的深度對話。
參與者從繁忙的都市抽身,走入四川綿竹萬畝玫瑰花田之間,在自然與芳香之中,完成一次“從外在護膚到內心自愈”的身心轉向。她們不是為了逃離生活而來,而是為了重新找回生活的節奏。
這一次,我們不只是講述玫瑰的芬芳,也講述在這芬芳之中,那些重新學會“好好生活”的女性故事。

女性的名字總是最先被犧牲掉的。
當“母親”“職員”“伴侶”這些角色一層層疊加,真正的自我,往往在無聲中被擠壓至邊緣。
35歲的王娟(化名)就是這樣慢慢丟失自己的。
凌晨四點,王娟又一次在黑暗中睜開了眼睛。這已經是她這周第三次失眠,手機螢幕的藍光映照著她疲憊的面容。作為某網際網路公司的市場總監,35歲的她正處在所謂的“黃金年齡”——事業上升期,家庭穩定,孩子乖巧。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這份“完美人生”背後是怎樣的代價。
她翻開備忘錄,上面密密麻麻記著:早上七點送孩子上學,九點半部門例會,中午約見客戶,下午三點產品評審會,六點家長會……在每一個身份標籤背後,真實的王娟正在一點點消失。
這種狀態並非個例。資料顯示,超過70%的30-40歲職場女性表示“經常感到自我認同模糊”。社會學家將這種現象稱為“身份超載”——當一個人同時承載過多社會角色時,核心自我反而會被擠壓得支離破碎。王娟的故事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代女性的集體困境:她們可以完美扮演每一個角色,卻唯獨忘記了如何做自己。

直到在四川綿竹的萬畝玫瑰谷,王娟第一次感受到了久違的“存在感”。
晨霧中的大馬士革玫瑰沾著露水,空氣中瀰漫著清甜的香氣。花農告訴她,採摘玫瑰必須在日出前完成,因為這是花朵香氣最濃郁的時刻。“我突然意識到,原來生命中最美好的東西都是有‘時限’的,”王娟後來回憶道,“就像我的自我認同,如果再不抓住,可能就永遠錯過了。”
這個頓悟並非偶然。萃雅品牌設計的這場玫瑰溯源之旅,本質上是一次精心策劃的“自我喚醒”實驗。透過剝離日常身份、迴歸自然場域、專注當下體驗,參與者得以暫時逃離社會規訓的牢籠。
“我們不是在販賣逃避主義,而是在創造一種可能性——讓女性重新獲得定義自我的權力。”

同樣在活動現場,主持人梁田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作為知名主持人,梁田曾長期活躍在鏡頭前,對外界評價格外在意,總想做到別人眼中的完美。“這其實是一種對自己非常不友好的鞭策方式。”在玫瑰谷的分享會上,梁田坦言道,“人生是用來體驗的,方向盤應該掌握在自己手上。”
她說,外界總有太多聲音告訴女性“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但她相信,每個女性都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樣。就像盛放的玫瑰,各有各的生命力與美麗,沒有固定的標準,也無需迎合任何期待。
她的坦誠引發了在場女性的強烈共鳴,許多人流下了感同身受的淚水。

這種集體性的情緒釋放,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社會問題:在女性賦權話語盛行的今天,“做自己”反而成了最奢侈的事。
心理學家指出,當“獨立女性”“職場媽媽”等標籤成為新的社會期待時,它們同樣會變成另一種形式的束縛。而萃雅透過玫瑰採摘、手工製作等體驗設計,恰恰在試圖解構這種束縛。就像他們嚴格挑選在特定時辰綻放的玫瑰一樣,品牌想傳遞的資訊是:真正的自我認同,應該建立在個體感受而非社會期待之上。
活動結束時,王娟在留言簿上寫下一段話:“真正的悅己,不是偶爾放鬆的下午茶,而是每天都要記得,在成為別人的某某之前,我首先是我自己。就像人生不必時時刻刻都開花結果,但永遠不能忘記自己是一株會開花的植物。這個領悟,比任何護膚品都更能撫平歲月的痕跡。因為它治癒的不僅是肌膚,更是那些被忙碌生活擦傷的靈魂。”

玫瑰谷的溯源之旅,於是成為了一種隱喻。從城市奔赴花海,不是為了逃離,而是為了“退出、觀察、重啟”。在晨霧中採摘大馬士革玫瑰,在手作香囊時靜默縫製,在無數次的彎腰與抬頭之間,這些女性逐漸意識到,悅己,不是一種自私的權利,而是最基本的自我修復。
萃雅提出的“覓境-尋真-悅己”三重節奏,正是為這些在生活中迷失了名字的女性,搭建了一個無評判的空間。在這裡,她們可以卸下“優秀母親”“完美職業人”的標籤,只需要以一個簡單的名字——“我”,去感受一朵玫瑰的綻放,一陣風的流動,一場真正屬於自己的對話。

“悅己,從來不是對責任的逃避,而是對自我的一次重新負責。”
因為只有當一個人,學會好好照顧自己,學會允許自己脆弱、坦然、自由地呼吸時,才有力量去承擔更多,也才有能力去愛得更深、走得更遠。
王娟說:“在花海的那天早晨,我突然覺得,原來活著並不是要完成什麼KPI。我只是想,好好活著,像一朵自然開的花,足夠了。”
王娟回到城市的那一天,早高峰的地鐵依然擁擠,手機的訊息提示也從未停止。
但她知道,自己已經變了。
她學會了在忙碌之間,留下一點空白給自己。學會了在壓力來襲時,像那天在花田邊一樣,深呼吸,閉眼,告訴自己:
“我不是誰的誰,我是我。”

學會放慢腳步,聽見自己的聲音,對很多人來說,或許已經足夠。可也有一些人,需要走得更遠一些。需要在更深的寂靜裡,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
46歲的於果(化名),就是在這樣的沉默中,走進了綿竹玫瑰谷。
成為外企高管的那些年,她早已習慣了將自己歸納進一張又一張精確的資料表格裡。工作業績、年度升遷、孩子的獎狀、家庭的經濟支撐……她把自己安放在一個個可以量化的位置上,彷彿這樣就能證明自己的價值。
直到一次突如其來的身體不適,將她從慣性裡拽了出來。

住院的最初幾天,她本能地抱著筆記型電腦試圖繼續工作。可身體的疼痛和倦怠,讓她再也支撐不下去。病休期間,於果翻出塵封的《道德經》,讀到“致虛極,守靜篤”六個字時,讓她想起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的警告:當“積極生活”變成暴力,自我剝削比外在壓迫更具摧毀性。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很難過,那些年拼命追逐的所謂成功,不過是將‘自我價值’典當給了永無止境的外部肯定。”
當身體開始抗議,當那些光鮮的頭銜突然變得蒼白,一個被忽視已久的問題浮現在她腦海裡:“如果剝離所有社會角色,我究竟是誰?”這個疑問像一粒種子,最終將她帶到了四川綿竹的玫瑰谷。
在玫瑰谷的第一晚,於果躺在床上,聽見遠處山融水撞擊卵石的聲響,忽然她淚流滿面——那是她二十年來,第一次聽見自然的聲音蓋過腦內的待辦事項提醒。

第二天清晨,川西平原風微涼,成片的大馬士革玫瑰在薄霧中搖曳,露水滾落在花瓣上,反射出碎金一樣的光。在花農的指導下,於果小心翼翼地摘下第一朵玫瑰。花瓣的溫柔質感從指尖傳來,像久別重逢的觸感,讓她怔了怔。
“植物表皮細微的絨毛,讓我想起女兒嬰兒時期的胎髮。原來真正的觸碰需要這麼慢。”她低聲說。
一旁的花農笑了笑:“玫瑰最懂時辰。清晨五點到七點,香氣最純,活性最高。摘早了,香氣未成;摘晚了,陽光一曬,精華就散了。”花農指向遠處的工人,她們彎腰在花田間移動,“玫瑰清晨的香氣最為純正,這是自然與時間的默契。萃雅堅持在清晨5-7點間手工採摘,只取玫瑰初綻時最飽滿的香氣,每一瓶玫瑰精華油,凝聚著18朵花初綻時最純粹的能量。”
於果望著掌心的玫瑰,“其實,真正值得守護的,不是標籤,不是功成名就,而是這種與萬物同頻的感知力。”
直到午後的音療體驗,她才真正理解這句話的分量。

蒲團鋪滿草地,東方頌缽聲在空氣中緩緩盪開,像一圈圈無聲的漣漪。於果閉上眼,最初腦海仍是未完成的郵件、孩子的課業、未來的焦慮,密密麻麻地湧動著。
但隨著音波一圈圈滲透,她感到自己身體最外層的緊繃在慢慢鬆動。眉心舒展,呼吸變得深長,某種久違的柔軟感在骨骼深處甦醒。
頌缽的震動從尾椎骨直竄天靈蓋。閉眼的一瞬間,於果彷彿看見了三十五歲的自己——在上海交易所敲鐘時,高跟鞋裡藏著磨破的血泡;女兒肺炎住院時,她一邊輸液,一邊開越洋會議。
“人是根弦,拉得太緊,彈回來的就不是音,是傷。”
音療師辜蘭的聲音在空氣中迴響:“現代社會用‘效率’獎賞女性的一心多用,卻悄悄偷走了她們專注自我的時間。”

後來於果在交談中,談起音療環節時,突然哭了。“自己以為的成長,是被動適應;自己以為的成熟,是麻木忍耐;而真正的成長,是有勇氣重新傾聽內心。現代女性的困境在於,我們獲得了定義自己的權利,卻還在用舊世界的語法。”
在品牌工程師的展示環節,“黃金油水配比”的實驗意外成了於果的人生隱喻。當50%的大馬士革玫瑰精油遇上50%的三箭泉雪水,在38℃的恆溫中緩慢交融,原本分離的液體逐漸呈現出琥珀色光澤。
“這需要整整72小時,”工程師指著試管說,“就像真正的改變,急不得。”
於果輕笑。
她想起自己曾經用Excel表格規劃人生,卻忘了生命本就不是可以Ctrl+C複製的模板。

在最後的分享環節,於果說:“家庭是土壤,給我們紮根的力量;事業是陽光,促進我們向上生長;而財富是水分,太多會溺死,太少會乾枯。”她停頓了一下,又補充道:“但最重要的是中間那個‘我’,就像玫瑰的莖稈,如果它不夠強韌,再好的土壤和陽光也開不出花來。內調外養,不是虛詞,而是一次可被感知的慢生活切面。”
返程前,於果特意帶回一罐玫瑰精油,這趟旅行讓她明白,真正的悅己,不是暫時喘息,而是奪回定義自己的主權。
“在這個以角色定義女性的時代,每一個為自己命名的人,都是在默默拓寬世界的邊界。迴歸生活,依然會有壓力,有期待,有失落。但我再也不會把自己交出去。不是春天成就了玫瑰,而是玫瑰決定了怎樣去迎接春天。”

如果說。
王娟的困境,是角色撕扯。她在工作和家庭之間疲於奔命,最後明白了,真正的力量不是承擔一切,而是允許自己需要支援。
梁田的困境,是完美主義的枷鎖。她在不斷證明和取悅中漸漸失聲,最終學會接受不完美,允許自己從緊繃中鬆弛下來。
於果的困境,是身心的斷裂。她在多重身份壓迫下崩潰,直到身體出了狀況,才明白,人真正的存在感,不在於角色,而在於和自己重新連結。
她們面對的是情緒,是關係,是生活方式的疲憊與破碎。她們用“聽見自己”“放下標準”“重拾身體感知”來完成自我修復。
那麼,陳潔(化名)的困境,卻藏得更深。她的問題,不是情緒崩塌,也不是角色失衡,而是根本性的認知誤區:她把幸福/悅己誤解為一種可以透過目標打卡和成就疊加來量化的東西。
在綿竹玫瑰谷,她第一次直面這個隱秘的悖論。

不同於急於逃離的人,40歲以前的陳潔,想要的是接管自己的人生藍圖。
她總是比別人更早地為未來做打算。小學時,她就用一本小本子列出人生流程圖:高中留學、28歲升中層、30歲買下第一套公寓……每一個節點都有明確的時間軸,人生在她眼中,是可以精確拆解和執行的專案。
到40歲之前,她的人生履歷無可挑剔:世界一流大學畢業,就職於頂級諮詢公司,實現財富自由。在客戶眼裡,她總能將最複雜的問題梳理得明明白白;在朋友看來,她是個把自律刻進骨子裡的完美主義者。在外人看來,她是標準的“掌控型女性”:理性、自律、沉穩,像一臺運轉高效的儀器。
可只有陳潔自己知道,表面上的精密秩序,掩蓋著一種漸漸蔓延的失重感。“每當一個目標完成,我短暫地感到滿足,卻又很快陷入更深的空虛。幸福,似乎總是緊隨而來的一個新KPI,永遠在下一階段的待辦清單上,而非當下可感。”
“那麼,如果人生只剩下打卡式完成,那我到底在體驗什麼?”一次質問,像一粒微小但頑固的砂礫,開始在她心中不斷打磨、刺痛。

不惑之年,她決定暫停一次。但不是放棄掌控,而是想弄清楚:“幸福,到底是不是也可以被理性定義?或者說,悅己可以被量化嗎?”
陳潔第一次對這個問題的答案產生動搖,是在玫瑰谷的手作香囊工作坊。她習慣性地拿起筆,準備記錄香料的配比,卻被老師輕輕按住手腕:“先別急著記,閉上眼睛,聞一聞。”
她愣了一下,下意識反駁:“如果不記下來,怎麼確保下次還能配出一模一樣的味道?”
老師笑了:“可如果只是為了‘複製’,那香氣就只是資料,不是感受。” 這句話像一根針,輕輕扎進她的思維慣性裡。
“自己過去的人生,就像一臺精準執行的機器。計算卡路里,計算投資回報率,甚至計算戀愛的最佳時機等等,卻唯獨忘了計算‘此刻是否快樂’”。
在她過往的人生裡,大部分成就感,是被“加”上去的——證書、績效、標籤、光環。真正從心裡自然生長出來的東西,少得可憐。
幸福,難道也可以不靠加速,不靠打卡,而是自己慢慢長出來的嗎?

當天的交流分享,陳潔第一次沒有拿出PPT式的總結。她靜靜地聽著別人分享,腦子裡卻在悄悄推演一個新的公式。
直到輪到她時,她輕輕開口:“幸福 = 事業是否促成長 + 人際關係是否讓人放鬆 + 自我是否誠實清醒。”
有人問她:“事業不是為了賺錢嗎?成長又算什麼?”
她回答:“如果快樂只是逃避痛苦,那只是止痛劑。但如果能在事業中感受到自我擴充套件,在關係中保有鬆弛,在內心深處持續對自己誠實,那才是不會被奪走的幸福感。”

誠然,在現代社會中,“幸福”早已被市場化敘事重新包裝。特別是對女性而言,幸福似乎必須繫結一整套外部指標:漂亮的簡歷、精緻的生活、穩定的關係、得體的情緒,好像只有一切完美對齊,才配得上說自己幸福。
這種隱性的社會劇本,裹挾著無數女性拼命“修煉”,卻把真正的自我感知,壓縮得越來越細小。
“有時候,身心放鬆後也會想,自己曾經定義的幸福,其實是對外部世界的一次討好和交差,而真正的悅己,是真正從這種表演中抽身出來,幸福,不是贏得認可,而是放棄取悅,是成長的感知,是內心的鬆弛,是不向任何標準低頭的清醒。”陳潔說。

當天下午,品牌工程師展示了最新的燕窩酸飲。四百年古方《三白湯》,融合98%高純度現代提純工藝。這一過程,慢、溫和,卻有不可逆的深度變化。
陳潔坦言:“這個過程,給我很多想法,真正的內調外養,從來不是為了快速修復外表的裂紋,而是要在長時間裡,慢慢修復被焦慮和自我否定撕裂的內在秩序。就像幸福,不是靠外界定義來完成的提純,而是自己在緩慢生長中,打磨出來的穩定、輕盈與真實。”

“40歲之前,別人都說我命好。30出頭,該有的都有了:靜安區的公寓,淮海路的辦公室,銀行賬戶裡的數字。連我媽都說:‘你這樣的日子,還有什麼不知足?我笑笑,心想是啊,這樣的日子,該知足了,知足常樂。”
“但仔細想想,我真的幸福嗎?從前我以為是一張清單,打滿勾就作數。25歲升職,30歲買房,38歲實現財務自由——樣樣都做到了。可做完才發現,這清單原是別人寫的,我不過是個盡職的執行者。”
“那天在玫瑰園,看園丁修剪花枝。他手下那株玫瑰,明明已經開得很好,偏要再修去幾枝。‘開得太急,根還沒長穩。’他這麼說。我忽然就懂了,這些年我忙著開花,卻忘了紮根。”
“現在我的梳妝檯上,擺著從園裡帶回的乾花。它們不再鮮豔,卻有種沉靜的香。所以,我覺得幸福就像一件精工裁剪的旗袍,表面上看針腳細密,款式得體,可只有穿著的人知道,那些暗處的線頭總在不經意時扎著肉。真正的幸福,不是外頭的光鮮,而是內裡的妥帖。”
“人生過半才懂得,最奢侈的不是擁有,而是可以不要。不是把日子過成別人眼裡的樣板戲,而是能在自己的節奏裡,從容地喝一杯茶,看一朵花開。”

在玫瑰谷的最後一個下午,無人機飛過每個女性的臉龐。王娟摩挲著茶杯上的花紋,突然說起那個失眠的凌晨,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已經很久沒做過“沒用”的事了;梁田分享著如何學會對鏡頭說“今天狀態不好”;於果展示著手機裡新拍的照片——不再是精心構圖的商務餐,而是偶然抓拍到的彩虹;陳潔則笑著承認,她終於刪除了那個折磨自己多年的《人生規劃》。
這些來自不同城市、不同行業的女性,此刻都捧著同一款萃雅玫瑰茶,茶湯裡沉浮的花瓣像極了她們各自的人生軌跡——看似隨波逐流,實則自有方向。

“東方靈萃,漢草鎏(liú)光”這八個字,在此刻有了新的註解。它不再只是產品手冊上的宣傳語,而成為這群女性重新認識自我的見證。
當王娟用萃雅的玫瑰精華油按摩眼角細紋時,她想的不是“要年輕”,而是“要舒服”;當梁田在鏡頭前說:“真正的悅己,是擺脫外界期待的束縛,傾聽內心真實的聲音。女性無需迎合社會定義的‘完美標準’,而應像自由生長的野玫瑰,在屬於自己的天地裡綻放獨特生命力”時,她要的不是讚美,而是自在;當於果堅持每天留出半小時喝茶時,她不是在養生,而是在練習說“這是我的時間”。
這些細微的改變,恰恰印證了品牌想要傳遞的核心——悅己不該是痛苦的修行,而是發自內心的自我接納。

現代社會總是習慣把女性裝進各種精緻的容器裡。職場要雷厲風行,居家要溫柔賢惠,社交要八面玲瓏,就連護膚都要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彷彿每個女性都應該成為標準化貨架上的商品,等待著被挑選、被評價。
但玫瑰谷的這些日子告訴我們:花其實不需要花店,而是花店需要花。那些被整齊碼放在玻璃櫥窗裡的玫瑰,雖然符合大眾審美,卻永遠比不上山野間自由生長的花朵來得靈動鮮活。每個女性都是一朵獨一無二的玫瑰,無論開在摩天大樓的格子間,還是小巷深處的咖啡館,都能成為動人的風景。

萃雅的特別之處,在於它理解這種“非標準化”的悅己。就像他們從不強行統一玫瑰的採摘時間,而是尊重每朵花自己的綻放節奏;不會為了追求即時效果而過度萃取,而是相信時間沉澱的力量。
這種理念與當代女性主義的自我定義權不謀而合。正如哲學家茱迪斯·巴特勒所說,“性別不是與生俱來的本質,而是可以自主演繹的實踐。”當女性開始按照自己的意願定義幸福時,那些被社會強加的期待就自然失去了約束力。

返程的航班上,於果望著舷窗外的雲海,突然想起花農老張的話:“玫瑰從不在意自己開在哪裡,它只管開得認真。”
這句話或許就是最好的結語——在這個習慣給女性貼標籤的時代,真正的悅己不是活成別人眼中的風景,而是活成自己生命裡的園丁。
畢竟,世上本沒有標準的花園,每一朵認真開放的玫瑰,都在定義著屬於自己的春天。
玫瑰不必問春風,風起時,自有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