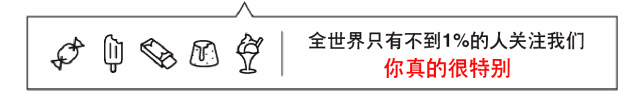文丨馬江博 編丨Thea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羅輯思維 (ID: luojisw)
今年以來,教育話題一直在各種會議上被重點討論。相信很多家長都在面臨類似的困惑:
比如,該不該讓孩子報文科專業?
以及,現在送孩子出國留學還划算嗎?
或者,要不要把資源都投在子女身上?
現在的教育領域,用馬江博老師的話說就是,正在發生重置,教育的舊邏輯已經失效了。

馬江博
資深政經趨勢學者、得到App新的年度大課《政經參考》的課程主理人。北京市領軍人才,研究政經趨勢20年,在國家行政學院和各大中央部委,培訓過數千名司局級官員和企業家。
那麼,新的邏輯是什麼呢?我們又該怎樣應對呢?

為什麼說舊邏輯失效了?
事實上,從1978年恢復高考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其實離不開三個歷史前提條件,第一是人口上行週期,第二是城鎮化的膨脹,第三是傳統工業的大發展。
這些分別形成了人口、城市和產業,對於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這過去幾十年這一整個大時期內,都處於紅利期。
但現在,抱歉,時代已經變了,比如人口上新生兒的持續降低;第一波城鎮化進入尾聲,城市不再大規模高速膨脹;傳統產業進入瓶頸期,產業結構亟待升級。

這些過往影響教育的因素都正在發生重置,因此,整個教育本身也在時代的座標下發生徹底的重置。
具體來說,教育的這種“重置”表現為四個方面:就是,教育槓桿的重置、教育產業邏輯的重置、教育價效比的重置,以及教育資源的重置。
我們一個個來說。

教育槓桿的重置
先說教育槓桿的重置。
什麼是教育槓桿?其實就是普通人透過教育實現階層躍升的可能性。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呈現出顯著的“教育槓桿”:一個普通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甚至中專,就能實現明顯的階層跨越。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沒有學歷,基本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底層人家的孩子透過一張試卷即可改寫命運。這種教育的高槓杆,持續了至少三十年。
但是現在,這種教育槓桿的效應正在被嚴重地降低和重置。

首先,具有高資源的孩子,在這場教育軍備競賽中天然具有優勢,不僅僅贏在起跑線,往往中途還能持續加碼。
財新雜誌2017年的報道說,最近幾年的統計資料可能只保持在10%左右,也有資料說是15%左右。
而更多的小鎮孩子,只能讀二本。寒門難出貴子,正在成為大家討論的問題。
其次,哪怕同樣讀了名校,就畢業後的工作和個人發展來說,學歷和學校之外的家庭資源因素也正在發揮更大的槓桿作用。
父母代際資源的傳承,正在超越教育本身的槓桿。
事實上,教育槓桿的衰減曲線,對應著社會財富的積累曲線,背後是我們社會資源和財富積累從無到有的週期演變。
40年前大家都比較窮,資源都很少,教育就是最大的槓桿資源;
但經過40年的積累,有些人資源越來越豐富,普通孩子只靠教育槓桿,就比不過別人的三頭六臂了。
這是一個所謂“成熟社會”的必然演變,歐美髮達國家也是如此。
而且當社會財富從“增量擴張週期”逐漸邁入“存量固化週期”,競爭越發激烈,這種資源的不對稱性也就越發明顯。
因此,教育槓桿的重置,本質是社會資本積累的速度,超過了學歷或者說教育紅利的速度,大家的突圍成本也從“十年寒窗”升級為“兩代積累”。
當然,這些問題國家都在規劃解決,要深層改革。

教育產業服務的重置
教育重置的第二個方面,表現在教育產業規律的重置。
客觀說,現代教育也是一種“產品”,培養出來的人才自然要適配於產業發展和國家戰略。而產業和戰略一旦鉅變,教育必然要跟著鉅變。
在改革開放後的前40年裡,中國有過四波大浪潮——外貿、基建、房地產、網際網路。
而教育的產業規律,很大程度上是和這四個產業繫結的,比如之前興起的“土木報考熱”,是瞄準了地產和基建的紅利,“計算機熱”是針對網際網路,“金融熱潮”則和幾個產業都相關,因為都要融資。
包括經管、法律和各種文科專業也是如此。
因為國家當時要靠金融融資發展,中國社會經濟體的高速發展膨脹又要大量的“普通通用型管理人才”,而這些文科專業的學生比理科生培養成本低。
所以你能看到大量的經管、法律類的文科生在過去二十多年被培養出來,本質上就是這個產品相對簡單,價效比更高。

但社會和經濟的高速發展膨脹,也帶來了問題,就是這些教育產品本質都是市場催動的,這種應激性的人才供給模式,存在結構性的滯後問題,就是說,當產業走完週期時,教育系統還在為上一輪產業週期,培養過剩人才。
而現在,教育產業化則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轉變。
一是教育服務的物件正在發生根本轉變,從傳統產業變為了高科技產業。
比如傳統外貿因為貿易戰被擠壓,同時內部的傳統產業開始轉型,高科技產業和數字產業崛起。
這個過程中,不需要大量的通用型一般管理人才了,前面提到的文科生培養產品線,不那麼需要了,改為了科學家和工程師。
二是主導教育走向的力量也在發生轉變。
我們對外要打贏這場中美大國博弈,必須依靠科技自立自強來解決“卡脖子”問題。
這時候,教育導向由相對單純的市場或者說就業推動,轉為很強的國家戰略注入。
國家透過一系列的高校改革、高考改革、專業改革的動作,來把教育資源向STEM領域,就是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集中。
因此你就能理解,為什麼國家要大力發展理工科,大力推進各種選拔計劃了,因為教育體系將成為科技創新的配套工程。
教育產業服務重置的背後,是產業結構週期的拐點。

教育價效比的重置
順著教育槓桿和教育產業服務的重置,以及它們背後的原因,我們繼續推匯出第三個重置,就是教育價效比的重置。
教育本身也是一種“投資”,但現在的教育投資正在從“穩賺不賠”,變成一種存在一定“風險”的投資。
做個不恰當的比喻,以前的教育投資就像存“存款”,到期了自動就有收益,而現在的教育投資則有點像“炒股票”,不一定能賺錢,還可能虧錢。
這種風險來自兩方面:
另一方面則是教育收益降低。

我們剛才說了,教育的槓桿率在降低,收益在減少;而且教育服務的產業在重構,很大一部分教育“產品”線其實早就應該被淘汰了,培養出來的“產品”是無效投資。
這背後也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就是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教育其實是“普惠式的精英教育”,普惠式是指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普及,而精英是指高等教育仍然以培養白領和中產為目標。
普惠式和精英這兩個詞一聽就有點矛盾,但是這個矛盾過去被高速增長的經濟體給消化了,沒有顯露出來。
但是現在,增速減慢,消化不了了,培養出來的大量的白領人才中產後備軍不被需要了,所以我們看到了學歷貶值、職場內卷、就業向下擠壓的情況。
而另一邊,社會對藍領工人、職業教育人才的需求,遠超當前社會的供給。
比如江蘇,不管是泥瓦工,還是掌握數控技術的藍領工程師,很多人的收入都能排在本地的前面。

如果我們從一個更深層次的視角,就是人力資本視角分析這件事,教育價效比的重置,其實是知識資本重新定價的過程。
工業時代的教育投資,遵循線性增值規律,學歷與收入呈正相關關係。
但在指數級的科技變革時代,知識更新週期急劇縮短,傳統學歷的“保值”功能正在失效。
所以未來,中國的人才會出現大分層:要麼向上走尖子路線,成為高價值的科創人才;要麼向下紮根,成為有特色的藍領職業人才;而夾在中間的普通人才,可能會很難受。
總的來說,普通白領的價效比正在削弱,職業藍領的價效比在快速放大,所以你在做教育投資的時候,需要重新考慮家庭的成本收益比。

教育資源的重置
我們要說的最後一個重置,是教育資源的重置。
在人口結構轉變、技術革命裂變、產業升級攻堅的疊加下,教育正在成為一種科技產業的新基建,是必須要大投入、大力度才能砸出來的。
因此,教育資源的分配也不會是“平均用力”和“撒胡椒麵”,就像我之前說的那樣,在區域發展中,國家要把最好的資源給到優秀的省份,讓他們去創新突破。
同樣的,在教育領域,最好的資源也要給到優質的選手,讓他們去突破“卡脖子”的技術難題。

我認為,未來主要兩類院校會明顯受益:一是理工類、國防類、醫農類高校,尤其是在STEM學科,就是前面說的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上有自身特長的院校。
至於財經類、政法類的院校,可能會受到擠壓。
第二類受益的是經濟和教育錯配的地區的院校。
比如深圳,經濟強但本地教育卻不如其他一線甚至二線城市,這類地方的院校因為當地的巨大經濟投入,會加速崛起,比如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學、深圳大學、杭州民辦的西湖大學,都是迅速崛起的新貴。

相信你看到這裡,會覺得機遇與挑戰並存,那我們普通人該如何做好準備呢?這裡我給到四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面對教育槓桿重置,行動上既要持續努力奮鬥,讀好學校、好學歷,把可依靠的槓桿用足。
同時,心態上也要降低預期,認識到階層躍升需要更長時間更多維度的因素,重新設定自己和家庭的心理座標;
第二,面對教育服務產業重置,選專業比選學校更重要,或者至少差不多。
建議你更多靠近面對未來的專業,以及國家戰略支援的理工類或者高應用型文科類專業;另外,普通學生可以多考慮技術型藍領這個選擇。
第三,面對教育價效比重置,理性看待教育投資。
社會的規則已經變了,普通家庭量力而行吧,教育投資已經具有一定的風險,沒必要都賭上。
比如我認為,對於很多家庭,沒必要花上百萬甚至幾百萬留學回來掙幾千塊工資,為難孩子也為難自己,留下錢給他買個房、買個保險,可能是更現實的選擇。
第四,面對教育資源的重置,如果其他條件差不多,建議優先選擇東部大省或發達地區的高校。
總之,教育決策必須要理解和遵從社會週期的執行規律,這是我們普通人能夠真正拿到時代紅利唯一的辦法。
▼精英說今日影片推薦



你“在看”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