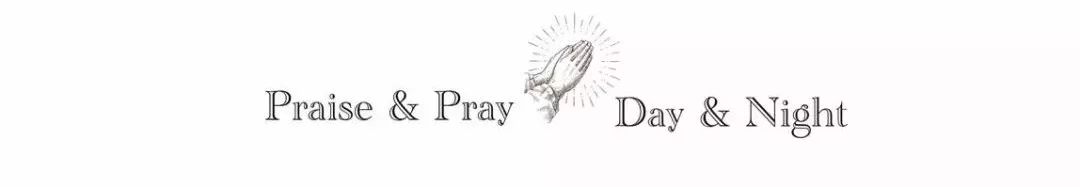我們已經處理了關於系統神學和歷史神學的一些基本原理。下面我們會透過這些基本原理來觀察一些在教會日常中極為流行的現象,而它們不得不印證筆者的擔憂——系統神學和歷史神學的地位在現今信徒乃至福音派著名學者的心中暴跌。
四、平信徒間的爭執
許多信徒受到現代思潮,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質疑權威的趨向,再加上中國大陸受馬克思主義語彙的影響,對既定的信條、教義特別排斥(大陸語境中常常斥之為“教條主義”),並對神學中的“權威人士”總有輕蔑感。若是在教會小組查經中,有人論及一些神學家(比如,路德、加爾文等等)對於某段經文如何解釋,很可能會有人質疑,何必關注那些人怎麼講?當然,平信徒有時可能害怕冒犯人,不會直言,但心裡仍然存留些許想法;而有人會進一步質疑這樣訴諸權威的合理性——即使是神學家所言,而神學家並非無誤,如果我個人覺得沒有道理,就大可不聽!
筆者不是否定在各種情況中,我們需要去搞清楚諸多結論的來由,以至於儘可能以理服人,這是完全合理的。筆者只是想揭示,活躍在這種平信徒常見態度背後的是“權威意識的喪失”,而且是選擇性的。
如果現在是討論科學,有位大學生平信徒發現,他在閱讀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玻爾(Niels Hendrik David Bohr)、狄拉克(Paul Adrian Maurice Dirac)等人的量子力學理論時,有些計算他不能理解,或有些內容仍令他疑惑,感覺好像他們是錯的。他一定會馬上打消這樣的念頭,畢竟他們都是專家,都是所謂“大佬”,而他和這些物理學家比起來還只是一個量子力學的“萌新”,出錯的一定是他自己,不會是那些科學家,且他們的理論早就被無數專家、“大佬”們檢驗過,這就更大大降低了他們出錯的可能性。
筆者藉此想說明的是,一位信徒在科學領域很可能同樣會保持這樣的“謙卑”,但一遇到神學,他“啟蒙運動的思想”就爆發了,他懷疑一切的精神不時就會興起。筆者給這“謙卑”打引號,是因為這樣的“謙卑”不是真謙卑;真謙卑不是選擇性的,之所以對科學“謙卑”,因為不這樣做,輕而易舉就可以被證明其實是自己蠢笨,而不是權威出錯(用不上臺面的話說,“慘遭打臉”成了“分分鐘的事情”)。但神學議題似乎不能從客觀上這樣操作,你總可以搪塞,可以抗拒,死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別人也不能奈你何。
難道不是這樣麼?多少信徒以“機智”的方式反對傳統神學拒絕信徒可以和非信徒交往、甚至締結婚約的論調?現在許多教會還需要不斷向信徒傳講這樣的資訊,甚至要在本教會的公眾號刊載回應的文章,不就是因為有許多信徒不服麼?“即便路德、加爾文這樣說了我也不信,有再多神學家說了,我也不信,他們就是絕對的權威麼?我看不出聖經有這樣的教導!”“牧者這樣說了就要聽麼?牧師難道是絕對權威?”“你腦子裡都是這些教義、這些‘別人’的思想有什麼意思?你的大腦不過是別人思想的跑馬場,你要有你自己獨立的見解!”筆者曾親耳聽到這樣的論調,也只能為這些信徒感到惋惜和遺憾。還有其他像“認同婚前性行為和同性戀”的案例也完全雷同。
筆者只想勸這樣的信徒謙卑、願意按照聖經來思想這一切。聖經恰恰教導了身為一名信徒,他有應該降服的權威。聖經並不認同、甚至強烈反對啟蒙運動中人的“獨立自主”(autonomy)——以自己的理性和判斷為至高權威。人自己的一切都不是絕對權威,但上帝是,且上帝也將權威賦予了教會,而表達在教會的教義、信條和教導上。如果這些內容確實符合聖經,信徒完全有義務將之視為從上帝而來的,不是有許多信徒在聽了合乎聖經的講道後,認定是上帝藉此向他說話、勸誡他麼?不正是這樣的道理麼?當然,這需要有智慧地操作,當今全球的教會教導都呈現出非常混亂的局勢,信徒更加有義務仔細查考大公教會所傳承的正統神學,作為判斷的基礎。

所以,筆者規勸眾信徒能夠有謙卑考察的心態。對一些問題,神學“大佬”們集體的看法總歸是有道理的;對於某些神學結論,你無法從聖經得出,不代表別人也得不出來,更不代表你能馬上對此結論做否定的判斷;可能是你比較笨,或在神學和解經上不太有恩賜。(請赦免筆者的直言不諱,但事實可能且非常可能如此。)筆者已經在前文中講明瞭科學的權威性其實還不如神學的權威性,如果你知道在科學領域需要“收斂”,也請在神學領域“收斂”,不要隨意“放飛自我”。
五、宗教改革的案例
有些思想敏銳的弟兄姊妹可能會反駁,那宗教改革如何呢?改教家難道不是一反以前的教會傳統,提出創新的教義嗎?
恰恰相反,改教家們所做的,絕對不是要創立新的宗教、創造新的傳統。他們乃是要在聖經的檢驗下,棄絕不合乎聖經的傳統,高舉合乎聖經的傳統,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恢復”最初合乎聖經的傳統。
在《答紅衣主教薩多雷託書》(Reply to Cardinal Sadoleto)中,加爾文回應薩多雷託的指責——宗教改革偏離了過去教會一千五百年一致的神學傳統——論證了改教運動與早期教會的教義一脈相承(加爾文對教父著作了如指掌,足以信手拈來):
“但是你指責我們。你說一千五百年來被信實之人一致證實的事物,卻被我們的輕率破壞和毀滅了……你知道的,薩多雷託……我們不僅僅比你們更接近古代的思想,而且我們竭盡全力所做的正是重建古代教會的形式,這形式起初被資質拙劣的文盲人士扭曲和玷汙了,後又被羅馬教宗及其黨徒以犯罪的行徑破壞甚至完全損毀了。……我請你放眼看看古代教會的形式,前人的著作早就證明了——希臘人克里索斯托和巴西爾,拉丁人西普里安、安波羅修和奧古斯丁;在這之後看看教會損毀的情況,這教會在你們手中殘存至今……”①
而那些“神學家算什麼”的言論恰恰出於重洗派激進改教家的口,塞巴斯蒂安·弗蘭克(Sebastian Franck)甚至說道:“愚蠢的安波羅斯、奧古斯丁、哲羅姆、格里高利——他們一個也不認識主,故此願主幫助我,他們也不是上帝差來作教導的。相反,他們全是敵基督的使徒。”②
與重洗派否定和棄絕傳統的做法相反,改教家們竭力要表明,他們的教義並非是“新奇的”和“新近出現的”。比如,加爾文在其《基督教要義》第一版的序言中,就竭力論證:“第一,他們[羅馬天主教]的教義和實踐實際上違反了早期教會的教導;第二,改教家們的觀點與教父一致無二。說改教家藐視和仇恨教父是毫無根據的。”③所以宗教改革神學不是在神學上的“創新”“標新立異”,而是迴歸合乎聖經的教會傳統。
一些信徒對宗教改革有這類疑問固然是好事,但同時也無意中流露出對宗教改革所傳承的神學及其精神的無知。這不是空穴來風,端看現今在教牧輔導中流行的世俗心理學就可想而知了。
許多信徒對這種“聖經與心理學結合”的教導模式趨之若鶩,這類書籍也在信徒中廣為流傳。其實這類書籍往往不過是以心理學內容為主軸,點綴一些聖經經文,便冠名為基督教的輔導類書籍了。甚至心理學博士已經成為福音派當中可以炫耀的資本,不少從未經過神學訓練的基督教心理學學者都著書、開講座,來“幫助”眾信徒解決各方面的生命問題,平信徒也對此頗為歡迎。
而當一些保守的改革宗教會批評這樣的趨勢時,不少採取或認同這種教牧輔導的人士開始反擊,斥責改革宗神學反學術、反理性。(非常諷刺,許多有敬虔主義傳統的教會常常指責改革宗神學“太學術”“太講理性”,這足以證明這兩種批評都是何等地有問題。)因為“理性得出的結論也是上帝的啟示”,“聖經並未明確教導關於人內在生命的許多內容,心理學完全可為之提供許多資源。”
筆者不想論斷他們的動機,這篇文章限於主題也不能系統地討論聖經與心理學結合的內容;筆者也不是說對於世俗心理學其中就沒有素材可以去發掘和使用(比如心理學研究的一些臨床資料)。筆者只是想強調,在屬靈的領域,隨意地讓世俗學科與聖經相結合是宗教改革的立場所反對的。因為讓聖經與一門世俗學科結合,甚至在某些方面受世俗學科的牽制,是天主教神學常常採用的方法。(比如,阿奎那將柏拉圖哲學和亞里士多德哲學融入基督教神學④;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天主教在現代更加容易接受神導進化論。)路德和加爾文指責這種操作不合聖經。
路德早在 1518 年 4 月的海德堡辯論提出的 40 條論綱中,就藉著後 12 條哲學性的論題,談及亞里士多德哲學對基督教神學的損害。對路德而言,哲學家並不能真正認識上帝和人自己,人的理性離開上帝、獨立自主,只會是“魔鬼的娼婦”“上帝的敵人”“畜生”。⑤路德雖然不排斥人的理性可以應付日常生活,但一遇到屬靈的事情,人的理性就全然昏昧。⑥
加爾文也是繼承路德對人性,特別是對理性的悲觀態度,理性是被罪惡玷汙和敗壞的,它對上帝普遍啟示和特殊啟示的回應都會深受罪惡的影響而產生扭曲,不認識上帝的人對於上帝和真理的總體傾向是抗拒和逃避,而非尊崇和追尋。人靠自己理性得出內容(人的哲學)也絕非上帝的啟示,而是人對上帝啟示的回應,若不肯以承認上帝和祂的啟示為前提,一定會是敗壞而錯謬的。
加爾文也根據聖經提出“普遍恩典”(common grace)的教義來彌補路德理性觀的空缺,外邦人還能在一些日常生活和科學、藝術、文學等領域保留某些知識和智慧,是上帝還賜下恩典,以使得墮落的人類社會可以繼續存留。否則,“他們棄掉耶和華的話,心裡還有什麼智慧呢?”(耶 8:9)但這樣的普遍恩典決不能使人產生對上帝正確的、救贖性的認識,也不能終極地解決人類屬靈生命的問題,這些上帝都保留給聖經和基督了。或者換句話說,一遇到屬靈的問題,人的理性全然無能。⑦
這正關係到宗教改革“唯獨聖經”教義所宣揚的“聖經的完備性”(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聖經沒有包含這宇宙中所有的知識,聖經中沒有啟示科學定理,這需要科學家去做研究。但是,對於“什麼是福音”“一個人得救需要相信什麼”“一個人想要過敬虔生活所需的一切真理”,上帝已經清晰並完全地在聖經中啟示了,信徒不需要在聖經之外再刻意尋求。“上帝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彼前1:3,粗體為筆者所加)改教家們刻意以此與天主教的教導對抗,因為正是天主教教導,信徒有了聖經還不夠,還要教會額外的傳統,因為有許多關乎得救的事情,聖經並沒有清楚啟示。
另外,面對心理學的問題,我們也需要冷靜反思,難道美善、恩慈的上帝並不願意在聖經中完全啟示與信徒敬虔生活和靈命息息相關的內容,還要信徒自己額外其追尋?甚至還要依賴那些不認識上帝的外邦心理學家興起的學科?難道上帝賜下的聖經和基督還不足夠解決人屬靈中的問題?難道學了心理學的人可以比使徒保羅、彼得、雅各、約翰更認識人,更懂得處理人與人的關係?
非常遺憾,許多鼓吹世俗心理學與聖經結合的教師和信徒只是一味批評改革宗或一些保守教會的立場,而對其中涉及的系統神學(啟示論)和歷史神學的問題所知無多,並且自己也未曾去好好地做出考察。不管過去的神學家怎麼說,只看重目前自己從聖經的領受,也不留“他人的觀點或許有其道理”這樣的餘地,這與前文中所言認同“基督徒可以和非基督徒交往”和同性戀的信徒在道理上其實如出一轍。或許,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們並不會刻意說自己認為系統神學和歷史神學無足輕重,但他們的態度其實已經很顯明瞭。
(未完待續)
相關推送:
註釋:
① Calvin,Theological Treatises,pp. 231-232. 其實天主教之前也沒有所謂一千五百年以來一致的教導,哪怕在中世紀,不同修會間為神學爭吵大有人在,後來多半被教區主教以息事寧人的方式擺平。而對於“人如何才能得救”,中世紀神學家和平信徒更是莫衷一是。參阿利斯特·麥格拉斯:《宗教改革運動思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第 29—30 頁。
② Alister E. McGrath,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5th edition,Wiley-Blackwell,p. 126.
③ 轉引自 D. H. 威廉姆斯:《重拾教父傳統》,2011 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 150 頁。
④ 不過具體問題很複雜,參見 W. 安德魯·霍菲克(編):《世界觀的革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第五章“中世紀神學與現代性之源”。
⑤ 蒂莫西·喬治:《改教家的神學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第 46 頁。
⑥ 霍菲克(編):《世界觀的革命》,第 225—226 頁。
⑦ 總體而言,加爾文在他的《基督教要義》和聖經註釋中對哲學的看法幾乎都是負面的。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第一章就言明,一個人不認識人自己,就一定不能認識上帝,一個人不認識上帝,就一定不能認識人自己,而這個迴圈是從上帝在聖經中啟示自己開始的。詳見大衛·霍爾、馬文·帕吉特(編著):《加爾文與文化》,團結出版社,2018 年,第六章“加爾文留給哲學的遺產”;心理學和基督教的關係,背後是基督教與世俗哲學是否能結合、如何結合的問題,非常複雜,參見拙文《耶路撒冷與雅典有何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