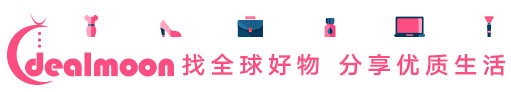作者丨趙曉曉
編輯丨關雎
圖源丨熊貓外賣
劉科路在二月中旬回國的時候,剛好趕上京東上線了外賣,國內靜寂已久的外賣市場重新變得熱鬧。
七年前,劉科路在英國成立了熊貓外賣(Hungry Panda),一個專為華人服務的外賣平臺。現在他的平臺覆蓋了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10個國家的80多座城市,全球每天有10萬華人會點開熊貓外賣。

劉科路最早想做外賣是在2012年,當時他在寧波諾丁漢大學讀書,學校食堂的飯貴也不好吃。當時國內外賣剛起步,美團和餓了麼還沒有打到寧波。劉科路就和幾個同學把學校周邊飯店的選單整理成冊子發給校友,有人點他們就送餐。只是沒等想法落地,劉科路就出國了。
等2016年回國,國內的外賣大戰已經分出了勝負。“有種錯過了一個好生意的感覺。”劉科路說,那是一個很不錯的機會點。隨後他選擇把美團在國內跑通的模式複製到英國。
很長一段時間裡,海外主流的外賣平臺上幾乎沒有中餐廳,而且介面簡陋,只有英文,沒有菜品照片,全球有超過6000萬海外華人,但他們想要吃外賣只能打餐廳電話訂,等餐過程中連個定位都沒有。熊貓外賣讓他們以最快的速度、最理想的價格,吃到了正宗的中餐。
現在熊貓外賣平臺上全球合作商家超10萬,騎手有8萬多,覆蓋運營地區超90%的中餐廳,一年交易額10億美元,每一個國家的業務都實現了盈利。熊貓外賣還拿下了美國華人外賣市場60%的份額,成為美國這個領域的第一。

有需求就是方向
劉科路是安徽人,家中4個孩子,他是家裡最小的,1995年出生。在寧波諾丁漢大學期間,劉科路還有兩段小的創業經歷。
他組織了一個公益團隊,每年送一部分同學去西藏,或者馬爾地夫、柬埔寨去支教,中間賺一些服務費。之後又成立了一個NGO(非政府組織),幫助一些刑滿釋放人員找工作。
劉科路思考問題的方式是有沒有使用者需求。“有需求,那我就去做。”
創辦熊貓外賣的時候,劉科路研究生還沒有畢業,他向學校申請了延期學業,並且加入了學校的創業孵化器。堅定先創業,有對在國內錯失做外賣機會的彌補,但更多是看到了英國華人外賣市場的空缺。
2016年左右的英國外賣市場剛從1.0過度到2.0,早兩年出現的Deliveroo、UberEats等外賣平臺,讓英國外賣市場第一次有了“配送”這個概念。兩個階段的外賣市場都忽視了華人這個群體,劉科路看到了一片乾淨的藍海。

當時有一組基礎資料,除中國外,全球有33個國家,中餐是被列為外賣第一的品類。這是劉科路當時看到的天花板,在國內驗證過的模式在國外應該也能行得通。來自身邊同學和商家的反饋是,這個事情可行。
後來在一家咖啡館裡,劉科路把公司註冊了下來。他拉著身邊幾個同學搭建了一個6-10人的小團隊,一多半來自劍橋, 一個來自麻省理工,劉科路是倫敦政經大學,幾個人湊了200萬元人民幣的啟動資金。
他們都是計算機專業出身,網站、軟體能自己搭建和設計,劉科路主要做市場、做管理,小團隊裡的每一件事他都參與。公司在2017年初開始運營。
劉科路和團隊從諾丁漢的校園開始突破,他們挨個周邊商家去談,磨了半個月才簽下第一家,在一家店耗費的時間平均在8-12個小時。
半年時間,平臺上已經有100多家商家,但訂單不多、一天有200-300筆,是在緩慢增長,每個人每月有500到1000英鎊(約5000-10000元人民幣)的工資。錢也燒的快,整體算下來是虧損的。

有幾個同學沒再繼續堅持,選擇了回去讀書,劉科路則堅持要做下去。他拿過年級第一,但花費了比別人十倍多的努力,他因此認為自己在計算機領域沒有天分。但創業能給劉科路帶來真正的“精神愉快”。
在原來的團隊裡,劉科路的年齡比其他人還小兩歲,他有比別人更多的耐心,“書晚讀兩年沒什麼,但創業機會錯過就再也沒有了。”劉科路說。

在那個節點上
突然發現賺錢了
在平臺日訂單200-300筆的這個階段,團隊內部有過分歧,是繼續守在諾丁漢這一個城市,還是往周邊城市去拓展下,換個場景試試。
折中方案是,只派兩個人圍繞諾丁漢周邊的城市核心區去打,其餘幾個人留在諾丁漢做拓展。場景突破校園,往社群切人,去覆蓋更多群體;餐廳標準放寬,開始談日、韓餐的商家。
增長出現轉折是在9、10月份的開學季,熊貓外賣給了剛到海外的留學生一個認知,在這裡可以點到想吃的中餐。在這個節點上,熊貓外賣順勢做了一些拉新、促銷活動,新使用者一下子湧進來。
到2017年底,熊貓外賣從諾丁漢拓展到伯明翰、萊斯特、謝菲爾德等4個城市,日訂單達到2000多筆。公司也摸索出來一個可持續的經濟模型。
比如,佣金必須15%以上,錢應該花在拉新上,而不是使用者復購上。把騎手一單的工資水平拉回到市場平均價格,之前為了留住騎手會不斷給騎手加錢,配送成本一漲再漲,為了招到商家,佣金一降再降。
“在那個節點上突然發現賺錢了。”劉科路說,意味著公司不需要再靠家裡的支援和投入。劉科路當時有了一個更清晰的認知,這個模式一定可行。
英國華人外賣市場有很大需求,社群外賣在當時市場也是空白,一切都在指向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做不成,一定是中間某些環節錯了。”劉科路說。
2018年春節剛過,劉科路回國談融資,公司要進一步發展各方面都需要錢,這個階段的熊貓外賣還在靠劉科路往裡投錢,不敢犯太大錯,也不敢招一些高價格的核心人才,束手束腳。
那個時候,國內風投都在找下一個美團、阿里,要求規模大、賽道要寬。劉科路在國內聊了兩三個風投後回到英國,決定拿當地資本的錢。在英國前後接觸了有100家風投,一個也沒有談下來。
劉科路在拒絕他的風投中找那個猶豫的——83North的合夥人,也是Just Eat前CEO,前後和劉科路聊過5輪。劉科路把資料擺在他面前:試點了5到7個城市,每天有5000到1萬單左右的規模,一個月交易規模約1200萬英鎊(約1.2億元人民幣)。

Just Eat前CEO David Buttress
到2018年底,劉科路才拿到一筆500萬英鎊的投資(按當時匯率約4400萬元人民幣),投資方是83North和Felix Capita,他們之前投過Just Eat,歐洲配送平臺 Deliveroo、Delivery Hero等,熊貓外賣是他們投的第一個華裔背景的創始人。
“歐洲投資人比較注重資料,一板一眼算賬。”劉科路說,這也是他在聊了100家歐洲風投後總結出來的經驗。之前劉科路會跟他們講商業模式、中餐的增長空間,他們會難以理解,但能看懂數字語言。
歐洲風投對網際網路專案的理解也跟國內不同,國內會追流量生意,但歐洲風投更容易接受一個在細分領域跑出來的中型而美的生意。
有了這兩家機構背書後,再往後,劉科路的融資就順多了。
拿到錢後,熊貓外賣進入了倫敦,這是劉科路和團隊在英國打的最後一個城市。
前期團隊去倫敦跑市場的時候,感覺這個地方太大、是十個諾丁漢。直到把英國所有小城都開發完了才進入倫敦,早半年也只是在倫敦的Chinatown附近做。後面團隊把倫敦切分成三十多個蜂窩狀的區域,把每個區域的使用者規模、商戶供給都拉出來分析。
比如,供給不好的區域怎麼解決,跨區域怎麼配送,市區不允許送餐汽車進入,腳踏車能否跟得上效率等。到2019年底,熊貓外賣基本上覆蓋了全英國。倫敦被當作是打了一個大城市的模型。

騎手和美團的不一樣
為了省成本,熊貓外賣的騎手都是眾包,與Uber Eats等主流平臺共享一個騎手池,騎手們以獨立承包商的形式與平臺合作,可以自由選擇在哪個平臺獲取訂單、配送訂單。

早些時候為了跟Uber Eats等平臺搶騎手,熊貓外賣每單給騎手的佣金會比對方高出20%-30%。為了效率,劉科路會優先給優質騎手派單,拉長他們的上線時間。訂單送不過來的時候,劉科路還會臨時加價。
到後期為了提升騎手粘性,平臺會多給騎手一些額外激勵,比如送到多少單就有激勵。平臺也有拼單體系,把順路的訂單拼在一起,保證騎手在單個小時內賺得更多。現在熊貓外賣平臺有8萬多騎手,月均收入大約能有4500美元-5000美元。
海外本地生活服務的發展整體落後中國五年。美團在國內驗證過的經驗,可以加快熊貓外賣在海外的程序。但也有50%的經驗不能用。
比如演算法。劉科路面試過國內有配送演算法經驗的人,他們經常會有疑慮:為什麼不鎖掉這些評價不好的騎手賬號?在用工方面,海外比國內要嚴苛很多,在沒有特別充分的理由下,平臺沒有權利無故封鎖騎手賬號,演算法無法判定一個騎手的優劣。
不能複製的還有與騎手的僱傭關係。美團騎手有兼職、全職和眾包三種類型,實行統一管理。但在海外,外賣平臺只能有一種模式,要麼眾包,但不能管理騎手。要麼納為正式員工,提供一切該有的福利。
熊貓外賣是眾包,平臺8萬多的騎手在全球管理起來會很困難,成本也會很高。熊貓外賣進過義大利,但沒做起來,政府要求騎手必須是正式員工,“成本撐不住。”劉科路說。
在商家端,熊貓外賣有一半的角色是賦能者。早期教育市場,劉科路和團隊會給商家提供包括最佳化線上選單、調整價格、設計適合外賣的餐品組合等,他們曾幫一些中餐館把選單從100個縮減到50個,把火鍋改成麻辣燙等。
“海外華人的消費習慣是有感受才有信任。”劉科路說。國內光沙縣小吃就有近 9萬家,熊貓外賣註冊商家才十幾萬家,“海外供給沒有國內那麼卷。”

一個適合自己的全球化
2019年,熊貓外賣開始走出英國,法國是其進入的第一個非英國國家,第二個是紐西蘭,再之後是澳洲、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

團隊判斷一個國家值不值得進的標準是,有多少個類似諾丁漢的城市,大城市有多少像倫敦,算使用者規模、司機成本、商家供給。劉科路還會和團隊挨個城市去驗證紙面上的資料,最後選擇一個最合適的城市去打。
美國最難,它太大了,從東部飛到西部要7個小時;它有50個州,每個州的稅點都不一樣,相當於50個國家。但潛力也最大,有700萬華人、密度集中、消費能力強。城市型別多,除了學生城,還有移民佔比、白領佔比很高的城市。
劉科路和聯創花十幾天在全美轉了下,一個個拜訪商家和使用者,去驗證之前能在其他國家複製的模型,是否在美國也可以。
當時熊貓外賣剛完成一筆1600萬美金的融資,公司團隊增加至近200人,已經有了去打最大市場的能力。他們在紐約旁邊的一個小城市試點,在這裡把模型跑通後,再去紐約其他的城市,都跑通後,就能在全美複製。
“紐約很特殊,它基本覆蓋了美國所有型別的使用者群體。”劉科路說。
現在,熊貓外賣已經覆蓋了全美20個城市。在劉科路和團隊的計算裡,美國有40個城市有做外賣的價值。團隊計劃未來兩年內,把剩下的市場開拓完。
歐美是熊貓外賣的核心市場,亞洲市場只進入了日本、韓國和新加披。平臺的經濟模型決定了它只能在高客單價市場打,均單價格接近、對騎手的要求和管理差不多,如果去東南亞和中東,公司就要換一套模型,“難度差不多再創一次業。”

按照劉科路的經濟模型算,公司已經進入的10個國家,外賣市場加起來有250億美元,增長空間還有很大。劉科路給公司定下了30%以上的增長目標,這是平臺盈利的底線。
2024年上半年,熊貓整體EBITDA(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轉正,營收保持了30%的同比增長,10個國家裡有8個都實現了盈利,今年交易額將突破10億美元。下一步,劉科路會專注於在現有的生態裡找增量。
2022年,平臺在英國上線了生鮮業務,像叮咚買菜一樣,給使用者配送2000至3000種SKU的亞洲食品,最快1小時送達。劉科路還在中國搭建了供應鏈團隊,反向賦能給商家,幫他們縮短採購時間,降低成本,部分品類能降50%。
熊貓外賣現在也在做輔助中國餐飲品牌出海的業務,平臺有超600萬的外賣使用者、十幾萬外賣商家,能幫中餐品牌更精準地確定在海外開店需要哪些能力,做到更大規模需要哪些詳細資訊。
“因為我知道哪些區域缺哪些品類。”劉科路說。過去兩年,熊貓外賣一直在講一個Vision:帶領中餐走向世界。從那時起,公司就在擴充套件業務邊界。
成長7年,熊貓外賣拿到了2.75億美元投資,是海外華人外賣平臺裡融資最多的。但他也開始會跳出“投資人就是老師”這個設定。很長一段時間內,他會用“老師”“獎狀”等學生時代的經歷類比,投資人就是老師,IPO則是“三好學生”獎狀。
“大多投資人並不是那麼瞭解我的生意,他們看到的是‘大家都這麼搞’,但不一定他們都是對的。”劉科路說。
最近,劉科路剛跟業內人士討論了一個重點話題,未來5-10年全球外賣會是什麼樣。他判斷外賣會進入3.0,AI的發展,行業會在配送上發生大變革。公司要增長,就要有實力跟上行業變化。
另外,劉科路到現在都沒有讀完研究生,學校把他的學費捐給了需要資金支援的校友。完成學業,這是他在而立之年要做的另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