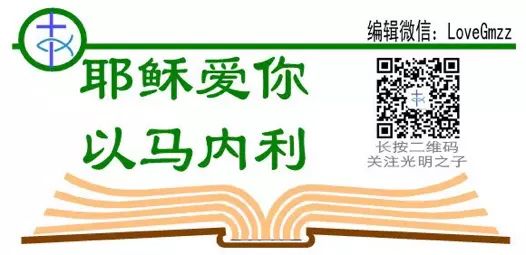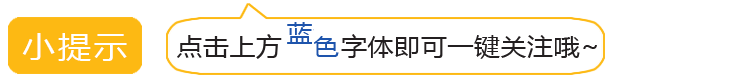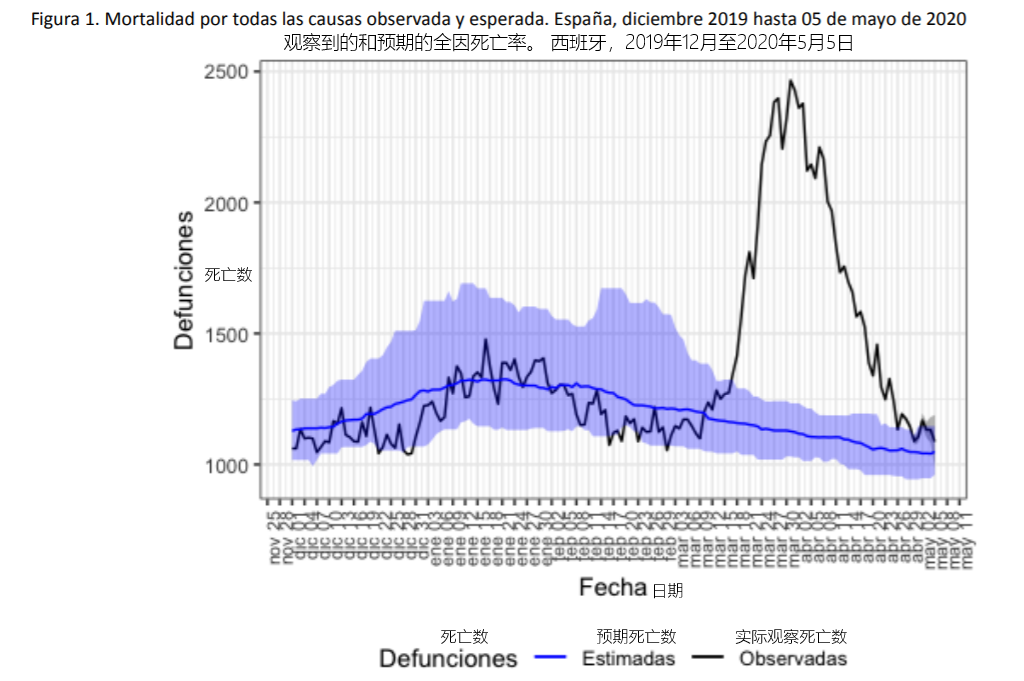政經哲思維
筆記君說:
經營之聖稻盛和夫在65歲時切除2/3胃部後,選擇遁入空門,法號“大和”。他坦言:人生最後20年,是為“靈魂新的旅程”做準備的階段。
這並非消極避世,而是對生命本質的深刻洞察。
在筆記俠PPE(政經哲)課程2025級第二模組“哲學·生與死”的授課中,武漢大學哲學院教授蘇德超老師指出:
死亡,恰是我們一切文明、文化、企業乃至個人活動存在的基礎。
蘇德超教授援引海德格爾的“畏死”狀態與普里高津的耗散結構理論,揭示企業家的生存困境與突圍之道:唯有領悟“空色不異”,超越有限遊戲,構建開放的生命系統,才能在生死邊界尋得真正的“不崩壞”之力。
這堂課,是給所有在高速時代負重前行的靈魂,一劑關乎存在本質的清醒劑。
以下,是蘇教授本次授課第二部分內容的整理,希望對你有所啟發。
一、二元論的生與死
樸素唯物主義最大的挑戰,是我的意識之外有一個世界存在;唯心主義會說,你怎麼知道?唯心主義所謂的悟道,都是直覺。
這一點上,他們認為樸素唯物主義者永遠無法自洽,這是後者最大的痛。
今天,在哲學家裡,完全相信樸素唯物主義的幾乎沒有了,這個痛點太痛了。物理主義本身是現象主義,一切講證據,而證據在經驗之中。
唯物唯心都只是一種信仰,不可能是科學。這裡的科學是指經驗科學意義上的。
科學家既可以相信唯物主義,也可以相信唯心主義。有些諾貝爾獎得主是唯物主義者,有些諾貝爾獎得主是唯心主義者。
為什麼樸素唯物主義有那麼大的痛點,還有那麼多人相信它呢?因為說話方便、簡潔。
比如,為什麼蘇德超存在呢?
唯心主義說,他就是我們的一個觀念,講臺也是一個觀念,他拿的麥克風也是一個觀念。一個觀念在另一個觀念上面走來走去,還拿著另一個觀念,這太奇怪了。
樸素唯物主義說,很簡單,蘇德超是個人,在外面存在著,講臺、麥克風都是東西,三者之間有一種關係。所以,樸素唯物主義說話特別方便,但最大的麻煩是邏輯不自洽。
唯心主義特別自洽,所有的東西都在你的感覺裡。

科學家的工作方式就是唯心主義,他要輸出感覺,輸出證據。什麼是證據,感覺到了的才叫證據。沒有感覺到的,那就沒有證據,不能瞎猜。
貝克萊說:To be is to be percieved。存在就是被感知。感覺不到了,那就不存在。
有人相信唯物,有人相信唯心,但他們有各自的麻煩:唯物的麻煩是太武斷了,沒有證據;唯心又不夠穩定,一切都是你的想法。
因此,笛卡爾提出了二元論。世界是二元的,心有意識,也有物質,這兩個東西同時存在,非常接近於我們的周易。
周易也是陰陽二元,心負責思考,物則有廣延(廣延是心靈對空間屬性的內在把握),還可以解釋剛才的那些難題。
樸素唯物主義問,愛在哪裡?你對老婆的愛在哪裡?找不到,因為那是你的心意,你對老婆的愛有多大、多長、多寬?看不出來,因為不佔空間。
物體是物理學可以研究的物件,服從因果規律。而心靈服從自由的規律,服從自由的理由。

二元論也許會認為,愛有兩種:你愛你的老婆,首先你的心必須愛她的心,你的身體愛她的身體,這才是完整的。
如果你的心愛她的心,你的身體不愛她的身體,那就非常遺憾:你們的愛得不到生理獎勵。反過來,你的身體愛她的身體,但你的心不愛她的心,那就非常危險:也許你在利用她。
二元論其實非常正常,普通人都是二元論者,既相信有物質,也相信有心。白天是樸素唯物主義者,到了晚上燈一關,都是唯心主義者,開始怕鬼。
佛教在跟普通人講的時候,都講成了二元,這是佛教不衰的原因。從某個意義上看,佛教要比二元論深刻得多,也比樸素的唯物、唯心要深刻得多。
大概為了讓普通人相信,佛教簡單地講成了二元論:你為什麼害怕死,為什麼害怕屍體?
禪宗就告訴大家:我們每天都揹著一具屍體,這就是我們的身體。為什麼要害怕死亡呢?真正的死亡,是那具屍體沒人背了。沒人背了,你去背上就行了,所以沒必要害怕。你為什麼怕鬼,他都沒有身體可背,你怕什麼?
二元論,既不唯物又不唯心,把兩者的優點都吸收進來消化。朱熹的“理在事先”在理論上非常接近西方的柏拉圖主義。神經心理學家約翰·埃克爾斯(John Carew Eccles)獲得1963年諾貝爾生物學獎,也是二元論者。
在二元論中,“我”是提線木偶的操作員,我的身體就是提線木偶。我是透過提線的操作者來操縱我的身體。
笛卡爾認為,真正的“我”住在大腦的松果腺(笛卡爾認為松果腺乃大腦中的一處“資訊交換站”,司職傳遞肉身與心靈之間的訊息)裡,沒有物質。
真我在松果腺裡觀看我的身體,在身體各處收集資訊,然後發號施令,身體只是傀儡。

二元論看外界,從來沒有真正接觸過世界,接觸的是我們的儀器,我們相互握手,目的是讓感測器碰一碰,碰的目的是收集一些生物資訊,有些生物資訊足夠好,可能有更加親密的關係,它就是最好的伴侶(靈魂伴侶)。
作為一個二元論者,在靈魂伴侶之外,身體的伴侶和靈魂伴侶應該同時存在。
二元論跟唯心論一樣,對轉世、對死後的生活,也可以滿懷期望。它的好處就是避免了唯心主義的一些麻煩,物理世界的穩定性就有了保障。

在笛卡爾的著作中有兩本書,一本是《論靈魂的激情》,一本是《方法論》。
在《論靈魂的激情》中,笛卡爾寫道:“靈魂具有這樣一種性質,它同廣延毫無關係,同組合成身體的質料的大小和別的特性也無關係,而只同它的整個組裝相關……
它並不會因為身體的一個部分的移去而變小一點,然而當身體器官的集合崩解時,它本身整個就從身體撤出去了。”
(在笛卡爾的定義中,廣延,是心靈對空間屬性的內在把握。)靈魂和廣延沒有任何關係,接受這一點,我們就不會死。
笛卡爾是數學家,他要用理性來證明他的觀點:身體會死,死是整體的分解,而分解一定要有部分才行,沒有部分就沒法分解。靈魂沒有空間,沒有維度。靈魂沒有廣延,也沒有部分,所以靈魂就不會死。
對於普通人來說,也是透過唯心主義、二元論緩解了對死亡的恐懼。
柏拉圖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證明了靈魂不會死,因為靈魂沒有部分,死是部分的分離,沒有部分,就不會有死亡。
笛卡爾在《方法談》中說:“我們的心靈有一個完全獨立於身體的本性,因此也絕不會與身體同死;我們既然見不到別的毀滅心靈的原因,自然會因此斷定心靈是不死的了。”
有沒有可能靈魂是肉體的一個功能,它只是一個過程?
樸素唯物主義有句話:肉體是刀,靈魂就是刀的鋒利。想想看,沒有刀,還有刀的鋒利嗎?

但唯心主義也可以反過來說:靈魂是刀,肉體是刀的鋒利。靈魂沒了,刀的鋒利有用嗎?更高階的認知可以是:如果鋒利象徵企業的發展方向、產品的設計方案,而你的核心團隊、產品設計師就是靈魂。
好的產品來自好的想法,想法來自靈魂。

類似柏拉圖的思路,我們用雙手可以證明靈魂的存在:
我們把兩個手合在一起,請問這兩個手是不是重合了?接近完全重合,好像完全重合。既然“好像”,那你一定見過完全重合,沒有見過,哪裡來的“好像”呢?
萊布尼茨說,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也不會有兩個完全相同的手掌。
完全重合,在物理世界是見不到的。
你見不到,就不敢說好像完全重合。你說兩隻手掌接近完全重合,說明你曾見過完全重合,你在物理世界見不到完全重合,一定在非物理世界見過完全重合,你在非物理世界見過,你就能以非物理的方式存在,我們可以叫這種存在方式叫做“靈魂”。
柏拉圖透過知識證明靈魂是存在的。
在變化的世界裡沒有知識,只有資訊,資訊是變化的,而知識是不變的,柏拉圖的世界、科學的世界、數學的世界是不變的事。我們變化的肉體怎麼理解不變的世界?除非我們有個不變的靈魂。
普通人活在變化的世界裡,我們的快樂,我們的痛苦都來自變化。

吃東西,如果總是一個味道,我們就不爽;唱歌,總是一個聲音,也不爽。一定要有變化。變化帶來快樂。
所有快樂、所有痛苦都是變化的。你要執著於變化的世界,對不起,你的快樂和痛苦都不是重要的。科學家、數學家要讓我們回到不變的世界,他解決的不是快樂和痛苦的問題,他要解決不穩定的問題。
在變化的世界裡有一個穩定的結構,因此我們可以對未來做一個穩定的預期,這才是科學家和數學家要乾的事情。
變化的世界之外還有一個不變的世界,變化的世界叫現象世界,不變的世界叫本質的世界,靈魂的世界,我們要回到那個世界。
柏拉圖說,人的靈魂是不死的。如此便能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其實,樸素唯物主義同樣可以克服對死亡的恐懼。
倘若我們真的相信伊壁鳩魯和盧克萊修,很多時候,我們的害怕、恐懼是自己嚇自己,因為我們想錯了。所有的錯誤並非世界錯了,而是我們想錯了,那些恐懼其實並不存在。
如果我們看那些矽谷企業家的傳記,能瞭解到他們的焦慮。
比如馬斯克的焦慮,他不是常人的焦慮,他的焦慮都是工具性的。他只是想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會把自己的情緒激發出來,甚至發脾氣。他這樣做只是為了激發身體的能量來解決問題。
笛卡爾重複了柏拉圖的觀點,他說我們的心靈有完全獨立於身體的本性,絕不可能與身體同時存在。
最重要的是,心靈或靈魂沒有廣延、沒有空間,也就沒有部分,因為所有的部分都依賴空間,所以靈魂不會死。

二元論者或唯心論者會為此開心。但靈魂不死未必是件好事,萬一遇到折磨,卻沒有逃避之路。而樸素唯物主義者有逃避的可能。做到“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真的很難。
唯物、唯心的觀點認為世界要麼是物質的,要麼是意識的,但中立一元論認為世界的基本材料是中性的,既非物質,也非心理。代表人物有斯賓諾莎、休謨。
斯賓諾莎認為,這個世界是無限的,是“一”而非“多”,不存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東西。我們看到的“多”是幻覺。這“一”個東西有無數的性質。
在這無數的性質裡面,我們只能認識兩種,即物質和心理,並且我們對這兩種性質的認識也是有限的。
他的觀點闡述得很透徹,現在科學家基本上也承認這一點。我們的一切生物現象、社會現象、文化現象都是電現象,我們所有的感覺,最終都取決於生物電。
但我們對電的感知非常有限,220伏能電死人,而高壓遠不止220伏,低壓電特別低時我們也感覺不到。
另外一個是休謨,他認為無論我們生活在哪裡,都活在感覺裡。感覺既非物質,也非心理,世界最基本的構成是感覺,整個世界由感覺拼裝而成,他的觀點也是中立的。
還有馬赫,愛因斯坦比較喜歡馬赫,在某個意義上愛因斯坦是馬赫的學生。
馬赫認為自我和物件都是針對這個世界臨時搭建起來的東西,這些臨時的東西會消失。

從中立一元論來看,二元論所認為的身體和心靈,不過是構成世界的材料的兩種構型。就好像水可以結成冰,也能重新變成水。
若把冰看作物質,把水看作意識,這其實是一種執著。實際上,水與冰本質上是一回事,並無不同,這就是中立一元論。
在中立一元論中,死亡是冰融化成了水。你覺得自己死了,其實一直還在,不必執著於非得是冰。而生就是水變成了冰,開始有了形狀,若沒有形狀,就成了水。事物在不停地轉化。
中立一元論這種說法有點懸,有點特別,有佛學的意味。
我們來看羅素文章裡的一個要點。羅素說身體並不持續存在,它總與環境交換物質,即便原子很重要,也不持續存在,我們無法分辨不同時刻的原子是否為同一個原子。
身體的尺寸只是外觀相似。學理科的人應該知道,進入亞原子內部,所有電子都相同,每個電子原則上與另一個電子不可區分。
不同的人能分開,但原子內部的夸克完全不可區分,它們性質相同。同一秒電子在這裡,下一秒就到了別處,所以不能說前一秒看見的電子和下一秒看見的是同一個電子,這是科學事實。
一旦進入原子內部,通常所說的同一性消失,但我們的世界、社會、企業經營必須建立同一性,否則月末不知道給哪個員工發工資,年末也不知道給誰發年終獎,法律關係、社會關係靠同一性維繫,然而從量子層面看,原子內部沒有同一性可言。
這是科學家普遍的認識,粒子一模一樣。“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適用於宏觀世界,微觀世界裡它們就是一樣的。

根據生物學說法,每隔7年,身體裡的物質就會更換完。我們認為,現在的我和7年前的我是同一個,只是因為外觀相似,物質並非同一個。
結婚的人有“七年之癢”,七年前後感情變化很大。這說明身體並不絕對同一,靈魂也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
因此,羅素說,靈魂只是各種活動及其內容,我們找不到自己在哪裡。
比如摸臉,臉不一定是“自己”,皮膚可換,肉、骨頭也能換,骨折可換鈦合金腿,心臟、大腦未來或許也能換,所以身體的相似只是外觀相似,靈魂也是如此。
我們找自己時,找到的只是身體,但並非同一個身體。有人說自己是二元論者,可當去想自己在哪裡時,根本想不出自己。
當我們想自己時,想到的只是念頭、對世界的牽掛,因為是自己在想,所以無法成為所想的那個“自己”。
這就是薛定諤講的西方理性精神的解離,將“我”和“我的觀察”截然分開,會陷入虛無。在找不到“我”的情況下,人們拼命折騰肉體、創造物質財富來填補空虛。
身體不是“我”,我們甚至找不到同一個身體。找不到“我”是因為排除身體後,要麼是對世界的想法,要麼是一片虛空,而虛空才是真正的“我”。
一個人若只關注自己,家庭關係不會好;只關注家庭,鄰里關係不佳;只關注企業,生意做不大。只有把自己融入世界,才能擁有整個世界。
靈魂也沒有連續性,所謂的連續性不過是習慣和記憶的連續性。有人相信死後靈魂倖存,這就像地震後河谷變成山峰,希望原來的河還存在一樣,不太可能,羅素這麼講很悲慘。
羅素認為我們害怕死亡是因為恐懼這種情感,讓我們盼望有來生。對來世的信仰並非源於理性論證,而是源於情感。
想明白了,就不會害怕死亡,就像高中生不害怕高中結束。不過,這種恐懼是本能的,且在生物學上有時是有益的。
羅素很睿智,他把神秘東西用理性方式講得清楚了。
羅素說:“相信有來生,可以是一件壞事,會讓人們更願意在戰爭中放棄生命,讓人世更殘酷。而相信死亡是最終結局,則會激發善良。”
人類及其低等祖先在漫長時代與敵人戰鬥,克服本能的死亡恐懼對勝利者有優勢,如破釜沉舟、背水一戰。
“在我看來,克服這種恐懼的最佳方法是逐漸拓寬你的興趣,使其變得越來越客觀,直到自我意識的壁壘一點一點地消退,你的生命越來越多地融入到普遍的生命之中。”
注意,自我意識的壁壘也能消解,就是去除我執。你認為我是有邊界的,這是我,那是你,其實這個邊界是不存在的,從自然科學角度看它都不存在。

用放大鏡、顯微鏡去看我的皮膚跟外面的空氣,差別微乎其微,這個差別在消失。
我們每個人跟這個世界是連續的,我就是這個世界裡面的一滴水,這一滴水跟整個河流的水是連續的,沒有斷裂過。我執,是虛幻的,必須讓自我意識的壁壘一點點地消除,你就不會害怕死亡。
當你的生命越來越多地融入到普遍的生命當中,這就是天人合一、人神合一、萬物合一。
千萬不要說只有我們的傳統文化才講天人合一,只要你是個人,你一定會講天人合一,要不然你怎麼克服對死亡的恐懼。
老是執著於我,區分這是我,這是你,一定會害怕死亡,最後可能不該死的時候被自己嚇死。
下面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比喻。羅素說:“人的生命應當像河流,開始是涓涓細流,受兩岸的限制而十分狹窄,爾後奔騰咆哮,翻過危巖,飛越瀑布,河面漸漸開闊,河岸也隨之向兩邊隱去,最後水流平緩,森森無際,匯入大海之中,個人就這樣毫無痛苦地消失了。”
起初,我們是細小的河流,被家庭包圍著。
漸漸地,河面變得寬闊,河岸開始後退,人開始有了自己的社交圈、自己的事業,也開始有了更加宏大的夢想。
然後河流開始變得平靜,就像小孩總是嘰嘰喳喳,人年紀大了就不想說太多的話,只是看一看、笑一笑,心裡便明白。最終在不知不覺中,它融入大海,毫無痛苦地失去了自己的個體。
中立一元必須消失,自我的邊界也消失了。
一個人在老年時,若能這樣看待自己的生命,就不會懼怕死亡。
“我希望隨著精力的衰減,如果疲憊感與日俱增,那麼休息的想法也並非不可接受。”
“希望能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知道其他人會繼續我無法完成的工作,並且心滿意足地認為自己力所能及之事以盡心盡力。”
這個時候安然去世,回到生命的本源,那就是大海,就像小溪來到河流,河流回到了大海,生命還在,只是邊界消失了,本來就沒有邊界。
邊界是個幻覺,不必在乎。破掉我執,接受一切發生的都是自己想要的。

邊界感是我們構造出來的,並非真實存在。若接受這一點,你會發現所有宗教、所有哲學,最終都在用不同的語言闡述同一個道理:不要有邊界感,要更豁達一些。
我極力推薦理工科頭腦的人去了解羅素。他能讓你更快地理解那些神秘事物背後的道理,而且他會用非常理性的方式把這些道理講清楚。他被愛因斯坦稱為“世紀智者”、“20世紀的聰明人”。
三、唯我論的生與死
唯我論認為自我是唯一的實在。
注意,不是說這個世界只有“我”,若這樣說便不是唯我論。以自我為中心,並非唯我論。
一個人以自我為中心,只是自私,比如有人說“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你們都得聽我的”,這是自私、自大的表現,並非唯我論。
唯我論是指沒有別的東西,只有“我”,確切地說,它認為這個世界就是“我”的想法,是“我”造出來、想出來的,是“我”的一場夢,這樣講才是唯我論。
唯我論在哲學上難以找到瑕疵,難以被駁倒,這著實氣人。誰都知道大概沒人會傻到接受唯我論,但就是駁不倒它,這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智力挑戰。
可以這樣說,“我”做夢時,夢中有個你也會這樣講,而夢中的你依賴於“我”。以此類比,又怎能判斷此刻“我”不是在做夢呢?此刻與做夢的情況可能毫無差別。
既然做夢時你依賴於“我”而存在,那麼現在你也只是“我”的一個夢、一個想法而已,就是這麼簡單。
你們是不是出現在蘇德超的夢中,你永遠不知道,可能你會說我,把我送到南通醫院,測一下腦電波,就知道有沒有做夢。你又怎麼知道你送我去南通醫院做腦電波測試,不是在夢中發生的呢?所以我們駁不倒唯我論。
雖然我們很不喜歡它,但它真的太牛了。唯一沒有理論缺陷的理論是唯我論。唯我論認為,你們都是我的想法,這聽起來很荒唐,然而最荒唐的東西恰恰沒有任何邏輯瑕疵。
這提醒我們,這個世界可能真的很奇妙,處處有奇妙之處,卻找不到它的漏洞。
其代表人物有古希臘的高爾吉亞,以及古代印度教的某些派別。
高爾吉亞做了邏輯證明,第一個定理是沒有任何東西存在,第二個定理是就算有東西存在,我們也認識不到,第三個定理比較簡單,講的是,就算我們可以認知,也沒辦法向別人傳達。
他說,我知道的是一些道理,而告訴你的是一些話,是聲波的振動。我知道的東西是像1+1=2這樣的道理,你不可能透過聲波的振動就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給你的東西和我想給你的東西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所以我沒辦法告訴你我在想什麼。
到目前為止,人類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可它每時每刻都在發生。我們相互傳達的工具和載體,跟要傳的東西完全不同。
我是什麼?我就是全世界。世界是什麼?世界就是我的想法。死亡是什麼?死亡就是整個世界消失。
注意,對於唯我論者來說,不是我死了,而是世界死了,是世界離開了我。
對於其他人來說,是我離開了世界,我逝世了,跟世界再見。唯我論者說世界對我說“再見”,然後消失了。
“視一切皆為自我,見自我於一切之中,如此之見者,無所退避。”
這是伊莎奧義書裡第六節、第七節的一個觀點。伊莎奧義書非常重要,印度聖雄甘地說過,只要伊莎奧義書前三節還在,印度教的基本教義就不會丟失。
佛教源自印度教,雖然佛教很厲害,但在印度本土一直未能超越印度教。印度教能發展並延續下來,肯定有其道理。
它說視一切為自我,一切東西都是我,見自我於一切之中,我在A身上看見了我,我在B那裡也看見了我,見自我於一切之中。
如此之見者無所退避。你跟世界打交道就是你跟自己在打交道。
你去解決世界的問題就是在解決你的問題,所以唯我論,它並不自私,它可以非常博大,一切問題都是他的,一切收穫都是他的。春天是他的,秋天是他的,夏天是他的,冬天也是他的。

唯我論者可不執著,因為世界都是他的。對於覺悟者而言,覺悟就是醒過來了,就是佛,一切存在無非是自我。知曉這一種統一性的智者,又怎麼會有痛苦或者迷惑持續呢?
你痛苦,是因為你的莊稼顆粒無收。但是你知道在這個地方不下雨,在另外一個地方必定會下雨,有的地方下雨,有的地方不下雨,這本來就是世界的安排。
你這個地方沒有收成,在另外一個地方有收成了,整個世界就是在做對沖,總收成不變。
唯我論者強大得很,看你有沒有足夠的勇敢去接受唯我論,你接受完唯我論之後,你就會接受整個世界。
你回到家老婆對你發脾氣,沒關係,那是你自己在對你發脾氣,你能接受自己發脾氣,當然也能接受老婆發脾氣。老婆對你發脾氣都能接受,那老婆對你做別的事情你也可以接受,老婆做什麼你都能接受。
你如此包容,老婆會很喜歡,家庭矛盾就消失了。以此類推,你的人際關係矛盾也會消失,企業內的矛盾以及你的社會關係都會變得非常好。
但唯一的一點是,我們沒有足夠理智上的勇氣接受唯我論。
雖然我們知道駁不倒它,但我們不相信它是真的。因為如果是真的,我們會害怕孤獨,唯我論會讓我們感覺這個世界沒有別人,只有自己,這是唯我論一個特點。
印度教跟佛教是有非常接近的,因為它們是同一個民族的傳統,非常接近。佛教會講“諸法無我”。
按照它的觀點,一切現象皆是由因緣和合而生,都是有條件生成的。
注意,一切都是有條件生成的,不要把它理解成原子論或物理學。一切都是因緣,連因緣也是因緣。
佛教講得特別徹底,比樸素唯物論、唯心論、科學都要徹底得多,要徹底杜絕有永恆不變的自我、實體自我,這就是它與其他理論的區別。
沒有任何東西不是緣起性空的。我們認為有東西存在是因為緣起。有因緣條件和合了,所以叫緣起。任何一個緣起和性空可以拆開來看。
我們認為有東西是因為有緣起,但這個東西本質上是空的。這裡說的空不是假,空就是空,真假都是從空裡蹦出來的,空比真假要底層得多。
不要對空做區分,甚至我們一般以為的不做區分都是一種區分,所以連這個也不要有。佛教禪宗師父會跟我們講破成見,每一種見都是一種觀點,都是一種區分。
要幹成事情,必須要有見識。但是你的所有都是你的成見,這個見造就了你,也會毀滅你,它會讓你執著,所以你必須破成見。

成見,有成才有見,有見才有成。你把它破掉之後,你才能到達佛教的境界。
要是沒破掉,成見可以讓我們成功,但不會讓我們有內心的安寧。
獅子什麼時候才能感覺到它是獅子?它看見它的食物在草原上跑的時候,它才是獅子,其實獅子是沒有幸福的,它只有快樂。
快樂就建立在,有一隻羚羊跑過來,有一隻鬣狗跑過來,雖然它很醜,但是它的肉還是可以吃的。
緣起性空,代表人物是釋迦牟尼、龍樹。“我”就是五蘊(色受想行識)暫時聚集在一起。我就是我的感覺。我就是一大堆感覺如柴薪所舉之火,並無自性。
我就是火,柴就是火的緣,這些柴在一起燃起了火,火就是我。你把柴去掉,火也就沒有了,所以就沒有自性。
範縝寫了《神滅論》,他想反駁佛教,卻沒意識到佛教觀點與他一致。佛教認為,就如同幾支火依附於柴火,柴沒了,火也就沒了,又像刀與刀的鋒利,刀沒了,刀的鋒利也就不存在了。
死亡就是柴還在,或者柴燃盡了。死亡是五蘊離散。
業力本質上就是行為,你的行為慣性會推動新的五蘊和合。就像火燃燒森林,火很難撲滅,是因為其憑著慣性會燒向其他地方。

若你相信自己有自性,就會變得具有吞噬性,因執著造成新的因緣,不斷吞噬新的資源,變成一個黑洞,不斷吸收新的資源,最後變得很可怕。
過於強調自我的自性,這就是輪迴。火燃盡了,但你不願意它熄滅;或者就如同火盡薪滅,但餘燼裡的溫度依然能點燃新的木柴,這就是獲得了新生。
這是佛教裡的講法。火從餘燼中重新燃起新的火,這就叫輪迴。輪迴之火與前面的火是不是同一堆火,我們不知道,但有連續性是沒問題的。
這是龍樹《中論·觀因緣品》:“因諸外道計一切法。或從自生。或從他生。或從自他共生。”
我們的一些東西、一些現象,要麼它是自己產生的,要麼它是從別的東西產生的,要麼是自己和別的東西一起產生的。沒有別的可能性。
“或從無因生。故說偈破雲。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
它沒有原因。若認為沒有別的可能,那就是沒有原因。若認為是自生的,那就是演化論者。
然而演化論存在問題,在自生方面根本就不存在“生”。就像在有我之前還沒有我,我自己生自己,沒有我又如何生自己,所以從邏輯上說,自生絕對行不通。
既然自生不可能,那麼他生就成了常識,普通人以及科學界都會認為是他生。並且自他共生也不可能,因為自生不可能,自他共生自然也不可能。
或者說從無因生是如今最新的科學觀點,量子漲落能將萬物丟擲來,這個世界原本什麼都沒有,但突然量子自發地出現漲落現象,就可以產生人以及其他東西,只是其機率非常低。
但佛教並非如此認為。佛教說不共不自生、不他生、不共不無因,這些觀點都不對,因此一切均無生滅,這很了不起,這就是破成見。
這次我們討論的問題是,一個東西到底從哪裡來,是自己產生的,還是別的東西產生它,或是自己和別的東西一起產生它,又或是憑空出現,就這四種情況。
若去回答這個問題,活該師父打一棍子當頭棒喝,佛教是要把這個問題取消。回答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過於執著“生”,沒有“生”,何必去找生的原因。
佛教的觀點非常徹底,將這些講給普通認知的普通人,他們根本聽不懂,也不明白為何要聽這些。
對於普通人來說,講他生、講因緣就夠了,因為這樣他們可以向善,這一世知道因緣向善,下一世可以提高層次,沒必要非得在這一世提高層次。
就像孩子本來只能考上武大、華科,最好也就能考上覆旦、上海交大,非要他考北大清華,只會折磨他,並非好事。
“一不自生,自即六根。謂根塵相對。則有一念心起。若無所對六塵。則一念之心畢竟不生。故名不自生。”
根是我們自己的,塵是外在的。

六根指眼、耳、鼻、舌、身、意,它們是我們現象世界的根。我們的現象世界由我們的感覺構成,而我們的感覺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眼耳鼻舌身在西方哲學中被叫做外感官,意是內感官。外感官是我們跟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途徑,另外一種說法是我們透過外感官把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說成是外面的東西。
內感官是我們內心的感受,如喜怒哀樂、愛恨情仇等,外感官感覺不到這些。人文是文化現象,主要靠內感官感受,我們的快樂痛苦,也主要靠內感官。
對於內感官來說,愛恨情仇和喜怒哀樂沒有空間、沒有廣延,但有時間,比如我們知道愛一個人愛了多久,很神奇。
時間由我們的內感官產生,空間是我們的外感官投射出去的,西方近代科學會這麼講佛教和西方哲學。
什麼叫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六根對六塵,每一根對一塵,眼對色、耳對聲、鼻對香、身對觸、意對法,如果六根六塵不相對的話,那它們相互就沒有喚起。
你知道你醒了,你的醒,喚醒了你,你也喚醒了你的醒,一樣的共同喚醒,不是誰在先誰在後的問題。佛教在這裡講得非常高明。
《西藏生死書》很值得一讀,這是經典中的經典。
誠如十二世紀的大師惹巴格堅所說:“人類一輩子都在準備,準備,準備;只是對下一輩子沒作準備。”
因為佛教強調輪迴,我們也就能夠理解為什麼稻盛和夫把生命分成三段,最後20年要為死亡做準備。如果你是二元論者、唯心論者,或者是相信佛教的人,那還得做別的打算。
我們可以把人的整個存在分成四個時相,即此生在世、臨終與死亡、死後以及再生,這就是四種中陰。
此生對應的是自然中陰,臨終是痛苦中陰,死後是法性靈光中陰,再生時是受生的業力中陰。
中陰在藏文中的發音“Bardo”,是指“一個情境的完成”和“另一個情境的開始”兩者間的“過渡”或“間隔”。“bar”的意思是“在……之間”,“do”的意思是“懸空”。中陰,就是我們生活在中間。
我們處於這個位置就是在輪迴。大多數宗教都告訴我們,生命是個過渡,當下並非最重要的。
記住,佛教禪定教導我們活在當下,但如果執著於當下,就會執著於聲色犬馬。當下其實不重要,過去、未來背後的東西才更重要,這一點很難做到。
“此生的自然中陰是準備死亡唯一而且最好的時間。其方法是熟悉教法和穩定修行。”
在這一點上,各宗教頗為相似,這也是佛教的一些觀點。
五、存在主義的生與死
存在主義包括有神論的存在主義、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唯物主義的存在主義、唯心主義的存在主義,甚至還有佛教的存在主義。它與這些理論相互相容,只是強調的要點不同。
存在主義關於世界本體提及較少,更強調人的存在。
我不想活成常人,也不想活成標本,我想成為我自己。
這就是存在主義,它強調做自己。在這一點上,它跟佛教不太一樣,佛教認為存在主義太過執著於自我,而存在主義就是要執著於自我,因為天下除了我自己,沒有別人是我,所以我尤其應該做我自己。是否喜歡存在主義,完全取決於個人喜好。
德國哲學家費希特說過,你選擇什麼樣的哲學,取決於你是什麼樣的人。你要吃什麼藥,取決於你生什麼病。存在主義代表人物是薩特、加繆。
我是一個不斷自我創造的主體,沒有先天本質。這一點跟佛教一樣。
我要成為我自己,是透過我的選擇塑造而成的。就好像我這一輩子是個即興表演的演員,沒有劇本。我在舞臺上的表演取決於當下每一刻,最後表演結束,我死了、退出舞臺,大家開始評價。
我每一刻的表演都是即興的,不是過去決定了我,對未來也沒有別的期待,是每一刻的表演決定了我是誰。所以這是非常英雄主義的。
死亡是什麼?死亡是我存在,是我表演的一個必然的邊界,但無論表演怎麼樣,一切終將落幕。

這是因為人類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在一個戰亂的世界裡,存在主義火了,是有道理的。做企業家,存在主義當然就算一種解藥。我就要把我自己塑造出來,不管外界世界有什麼樣的變化。
加繆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便是自殺。判斷人生值不值得活,等於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
你要不要死?To be or not to be,是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的問題。活還是不活,這是個問題。
“至於世界是否有三維,精神是否分三六九等,全不在話下,都是些兒戲罷了,先得找到答案。”
首先要解決的是,我要不要活下去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找到“我要不要活下去”的答案。如果不找到答案,人生就會很悲催,總是徘徊在要活還是不活的狀態,那就沒意義了。
“倘問憑什麼來判斷這個問題比那個問題緊要,回答是要看問題所引起的行動。我從未見過有人為本體論而去死的。”
他舉了基督教的例子,基督教經常討論上帝存在的證明,但從來沒有一個基督徒為上帝存不存在的證明去死。
“伽利略握有一個重要的科學真理,但這個真理一旦使他有生命之虞,他便輕易放棄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他行之有理,但不值得。他的真理連火刑柴堆的價值都不如。到底地球圍著太陽轉還是太陽圍著地球轉,壓根兒無關大局。”
伽利略因為支援哥白尼的日心說,被教皇叫過去訓話,教皇要求他要麼公開放棄,要麼受罰。伽利略選擇了放棄。
伽利略的學生很年輕,二十幾歲,在教廷裡跟教皇交談時,他對圍觀群眾說,大家一定要相信他的老師,鍾一定不會敲響,因為鐘敲響意味著伽利略會走出來,意味著他放棄了,而他的老師是真理的化身,會為真理而死。
這學生真是太年輕了。結果到了晚上5點鐘,鐘敲響,伽利略神采奕奕地走出來,他的學生很憤怒,說從此之後不再叫他老師,他不配做老師,因為他居然不願意為真理獻身。
加繆說,伽利略做得對,到底地球繞著太陽轉,還是太陽繞著地球轉,與家庭愛情、學問、收入都不相關。
不管地球繞著太陽轉,還是太陽繞著地球轉,我們依舊聽課、吃飯、回家、經營企業,對我們生命的意義不大。
因此,加繆認為,生命和真理,應該是真理為生命獻身,因為所有真理都是為了榮耀我們的生命,讓我們過得更好。如果有一種真理讓你去死,那它不是真理,是催命符。
如果有一種真理要取消所有美好,那它不是真的,是邪惡的,是撒旦的咒語。這就是加繆的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強調一定要活下去,只要沒死就要活下去。很多大學生抑鬱,推薦他們看存在主義,存在主義也有心理療法。存在主義能從很巧妙的角度擊中我們的心。

海德格爾,終其一生保持著農民的粗鄙氣質,卻擁有深刻的思想。他認為人分為兩種:常人和此在。
回顧德國曆史,《當權的第三帝國》等著作記載了二戰時期的教育理念——將人打造成機器零件。這種理念認為個人沒有自身目的,集體的目的就是個人的目的,因為集體代表了整體意志。
存在主義堅決反對這種觀點,認為這將把人塑造成喪失個性的常人。
試想,若將這種思維應用於家庭關係:丈夫是可替換的,孩子也是可替換的——這直接拷問著我們的良知。每個生命都是獨特不可替代的,存在主義正是要喚醒這種不可替代的自我意識。
每個人都應該做當下的自己,對待別人也要愛當下的他。跟過去的他打交道,會讓你產生不真實的埋怨或回憶;跟未來的他打交道,會讓你產生預期焦慮。
不要跟你想象的他打交道,那只是在跟一個替身相處,是對他的不尊重。他就是此刻存在於你面前的這個真實個體。這個觀點非常先進,很符合年輕人的想法。
死亡是“最本己的可能性”,是“無所關聯的可能性”。
死亡意味著我的死亡與別人無關。我吃飯與別人有關,我上課與別人有關,但我的死亡與別人無關。20世紀對死亡思考最深刻的很可能就是存在主義。
“死亡總只是自己的死亡”。
收音機收不到臺、電視機出現雪花點、空調停止工作,這是功能喪失,不等於死亡,但我的死亡是真實的死亡。死亡始終只是我的死亡,這是死亡的第一層含義。
上課有人陪伴,吃飯有人作陪,但死亡無人能與我們同行。在死亡降臨的瞬間,我們終將獨自上路。孤獨地面對死亡是最本質的可能性。
海德格爾說得很深刻。無論生前多麼榮耀,像秦始皇那樣有眾多陪葬者,但那些陪葬都是虛假的。只要保持清醒認知,就會明白死亡始終是孤獨的。我們註定孤獨,生或許不孤獨,但死必定孤獨。
“只要此在生存著,它就實際上死著。”
死亡並不是最後那一刻才到來,死亡每時每刻都在到來,它是一個漸變的過程。
“剛一降生,人就立刻老得足以去死。”
這句話說得多妙,你不出生就不可能死,但一出生就老得足以去死了,因為死也是一種資格。那些沒有出生過的人沒有死的資格,他們想死也死不了。
為什麼會有死亡?因為有出生。剛剛一出生就已經老到足以去死,已經有資格去死。這些話多麼毒舌。
“死亡是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終結的可能性)
在我們活著的時候,擁有各種可能性,我們是有自由的,可以做各種選擇。
死亡意味著這些可能性消失,所以說死亡是不可能。但這種不可能恰恰也體現著我們的自由,因為我們還可以選擇這種不可能。死亡也是一種可能性。
自由意味著我們可以選擇死亡,所以死亡也是一種自由。但死亡意味著所有可能性的取消,所以死亡是一種不可能。合在一起,就是“死亡是不可能的可能性”。
我要讓一切不可能,但這意味著我最後的自由。死亡可以捍衛最後的尊嚴,這就是我。
海德格爾可能是在歐陸哲學裡面最深刻的哲學家,20世紀你如果只讀兩個哲學家,一個是海德格爾,一個是維特根斯坦。他們都來自德語世界,一個是德國人,一個是奧地利人。
“死亡是不可逾越的可能性。”

你說你能夠越過死亡,跳過死亡,不可能。它是不可逾越的可能性,也是永遠不會到達的可能性。沒有到達過。
“日常的向死而在”是“在死亡面前的有所掩蔽的閃避。”
“死確定可知地會到來,但暫時尚未。”躲到“煩忙”之中“沉淪”。
日常的向死而生有兩種形式。
第一種是知道死亡必然來臨,卻選擇在死亡面前有所避讓和掩蔽的閃避。
人們透過不同方式逃避對死亡的恐懼:有人透過戀愛獲取快樂來克服恐懼;還有人依賴精神藥品來抗拒死亡。
死亡確定會到來,但暫時未至,於是人們開始狂歡作樂,今朝有酒今朝醉。
這種日常的向死而生表現為兩種形式:普通的活著和尋歡作樂式的活在當下。
第二種向死而生是沉淪於繁忙狀態。人們逃避死亡,要麼惶惶不可終日,要麼成為工作狂拼命忘卻。
他說還有另外一種向死而生,就是本真的向死而生,是我承認這一點,我就是在死。勇敢地面對生活,極度求真、極度透明,並且只要還沒有到達亡故之際,就始終死守,朝向死亡,這就是向死的自由。

我選擇每一種活法,都不可避免地在選擇死,我接受這一點。我同時在生,我也同時在死,這就是哲學意義上的、本質意義上的向死而生。
我絕不逃避我自己,而且我要活出我的存在。我絕不沉淪,我要活出我的樣子,大家一看就知道這個事情是我做的,這件事情是我乾的,這個想法是我提出來的。
你知道自己終有一死,因此會為整體謀劃。當下的生活也取決於對整體的想象。
未來和當下彼此成就,對未來的想象成就當下,當下的行動也成就未來。這不是單向的關係,不是現在成就未來,或未來成就現在,而是相互成就。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指出,人是唯一具有時間性的動物。因為有死亡,人才有時間概念。如果沒有時間,我們就不需要鐘錶或KPI,一切都不重要。
海德格爾這個人品質非常不好,因為他與納粹合作。存在主義並不一定會讓人變得高貴。一個人高貴還是卑賤,是否崩壞,不取決於聰明程度,而取決於選擇。
人最終是自由的,沒有任何選擇是透過推理得出的,都是我們主動做出的。
比如公司開會討論應該投A專案還是B專案,所有理性決策都指向A,但最後可能選擇投B。所有決定都是我們做出的,不是推匯出來的。即使推匯出結論,最終決定也是因為我們認可它。
存在主義認為我們只有一個地方不自由,那就是無法讓自己不自由。
比如上課可以選擇不聽、打瞌睡,這就是自由。有人說不自由,比如因為某人打電話要求聽課,如果不聽,覺得對不起某人。但依然是自由的,因為可以選擇對不起某人。
薩特舉過更極端的例子:有人用槍指著腦袋強迫上戰場。薩特說,從此這場戰爭就是你的戰爭,因為面對槍口時沒有選擇死,就意味著選擇了戰爭,必須為戰爭中發生的一切負責。
存在主義的偉大之處在於,我們永遠要對自己負責。即使逃避或不選擇,那也是我們的選擇。存在主義絕不會被打垮。
在存在主義看來,某些宗教觀點太消極。存在主義主張活出自我,雖然承認沒有自信、沒有自我,但既然現在有了“我”,就要活出自己,成為人的榜樣。
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說,“我既不能發現我的死,也不能等待它,也不能對它採取一種態度,因為它是表現為不可發現的東西,是取消了所有等待的東西。”
死亡不是事實,不是具體的東西,你不可能害怕、喜歡或對它採取任何態度。死亡取消了所有等待,當死亡來臨時,這個約會就被取消了。
“死是一種純粹的事實,就和出生一樣;它從外面來到我們之中,它又將我們改造為外在的。實際上,它和出生沒有絲毫差別……”
這話太深刻了,很容易忽略。死亡跟出生是一模一樣的,出生也是個命運,我們只能接受。出生比死亡更難受,但沒辦法,我們只能接受。
你無法問為什麼要生,因為問這話時已經出生。生是從外面來到我們之中的。生我們不知道,因為是從外面來的,死也不知道,同樣是在外面發生的。生死的事實都是外在的事實。
我們知道有生有死,接受有生有死,就是接受唯我論有兩個邊界。那個邊界是唯我論沒辦法控制的。你可以升維,透過生、透過死,超越現在所在的世界,到達更大的世界。因為還有外面的事情。
死不在我的世界之中,從唯我論角度看,生也不在我的世界之中。可見我的世界只是眾多世界中的一個,會連線到更大的世界。
宗教都會談生談死,原因就在這裡。宗教一定會讓我們超越所在的世界。任何宗教如果不讓我們超越,我們就不需要宗教,只需要成功學或PUA。
哲學是透過理性固定住可以固定下來的一切,固定不住,哲學就就提供選項,告訴你這些選項之間的關係。宗教就是讓你信,信完之後用這些信指導行動。
薩特說:“恰恰相反,我們似乎覺得死在我們發現它真實的樣子的時候,把我們完全地從它那所謂的約束中解放出來。”
死亡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解脫,這種解脫是把我們從自我中解放出來,讓我們看到更廣闊的存在。面對死亡就像開啟窗戶,你可以選擇看見外面的風景,或是永遠將自己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
“人們通常似乎相信,正是死構成了我們的有限性並向我們揭示了我們的有限性。”
自由就是要有選擇。但所有選擇都在表明你是有限的。今天中午選擇吃這盤菜,就不吃那盤菜;選擇去這個飯店吃飯,就不去另外一個飯店吃飯;這一刻選擇跟一個人結婚,就沒有跟另外一個人結婚。
自由以有限性為前提,因為有限才會做選擇。

再者,選項也是有限的。選擇a就不可能選擇b。自由以我們的有限性為前提,而不是要取消有限性。想要自由就得接受有限性,因為沒有有限性就沒有自由。接受有限性就可以接受死亡,因為死亡是有限性的體現。
自由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選項必須是有限的。要自由就必須接受有限性。死亡是有限性的體現,所以死亡也是想要自由的一部分。
他是這麼說的,“人的實在將依然是有限的,即使沒有死也是一樣,因為他在自我選擇為人類時自我就造為有限的了。
事實上,是有限的就是自由選擇,也就是說在自己謀劃著一個可能而排斥另一些可能時讓人們顯示著自己所是的。因此自由的活動本身就是對有限性的假定和創造。”
在自己實現著一個可能的時候,就排除了另外一些可能。向人們顯示了自己所示的我是我,我就不可能是別人。有限意味著我們在自我創造。沒有有限,沒有限制,我們就沒有創造。
帶著鐐銬跳舞,鐐銬並不是外在的,所有的舞蹈它本身就是一種鐐銬。
你跳民族舞,你就不是唱美聲,你唱美聲,你就不是通俗唱法。它就是鐐銬,自由就是鐐銬,鐐銬就是自由,這一點也很深刻,存在主義,它真的接受一切了,這很厲害,它在這個世界把一切都接受了,很了不起。
“死完全不是我的存在的本體論結構,至少在作為自為的存在時是這樣;正是別人在其存在中才是要死的。”
他說死是別人的事情,在我的生活中是別人在死。我的死是在別人的生活中。
死亡是我行為的極限值,是個極值。極值是我們無法觸及和達到的,它只是個理念值。即使存在死亡,我的自由依然是無限的。在這裡他又回到了唯我論的觀點:我活在我的世界裡,死亡不在我的世界中。死亡是我世界的一扇窗戶,最終開啟它是另一回事。
泛心論認為心靈是宇宙的基本屬性,萬物皆有某種知覺,複雜意識由簡單意識構成,它可以唯物也可以唯心。
但泛心論不同於中立一元論,中立一元論認為世界最基本的結構既非物質也非心理,而泛心論主張心理和意識無處不在。
滑鼠、麥克風、雷射筆、沙子都具有意識。
泛心論代表人物包括懷特海和查爾莫斯。在泛心論看來,我是神經元集合產生的意識,神經元以相同方式構成,就像大海由無數水滴組成。
每一滴水都是溼的,所以整個大海都是溼的。同理,宇宙各處都存在意識,人類也擁有意識。
泛心論認為死亡是身體分解,微小意識部分被拆解後可以構成更大的意識,就像水蒸發到雲層形成雨滴。
我們的身體超越了個體的存在,但同時也是個體存在的一部分。我們是自己與我們的身體緊密相連,人被視為身心的一個複雜的集合體,然而身體屬於外部世界,並且跟外部世界連在一起。
我們跟外部世界沒有邊界,我們一直連在一起的,我們從來沒有截斷過。這是泛心論的一個想法。這世界是由有死的活動世界和沒有死的價值世界一起構成的。價值,就其本性而言,它是沒有時間的,是不死的。
所以,我們就希望透過有互的材料構成不死的價值世界,泛心論在這個地方也是比較高貴的。我們肉體透過創造價值進入到不死的價值世界。因此在一個世界裡的暫時人格性伴著另外一個世界裡不朽的人格性。
英雄不朽,用泛心論解釋是能夠解釋得比較好的。我們透過可以朽壞的東西創造不可以朽壞的東西。
死亡不是終點,而是丈量生命意義的標尺;有限性也不是枷鎖,恰是創造價值的源泉。
諾基亞固守“摔不爛”、柯達坐擁數碼技術卻遲疑的教訓,正是封閉系統走向沒落的縮影。
破解之道,在於勇敢打破“鄙視鏈”的幻象,直面孤獨本我,向外部世界徹底開放。唯有如此,個體生命與企業組織才能在熵增的宇宙中,構建區域性有序,抵禦崩壞,在向死而生的旅途中,不斷進化。
蘇德超教授擅長將哲學轉化為治癒焦慮的良藥,在網路上吸引了數百萬粉絲,單條影片播放量破百萬。他學貫中西,從西方哲學出發,與東方哲學進行對比分析。他的西哲坊系列課程影響了諸多企業家和創業者。
蘇教授不僅是筆記俠PPE(政經哲)課程2024級和2025級的全稱授課導師,更是筆記俠PPE(政經哲)課程顧問委員會的創始顧問之一。
筆記俠為何要開創國內第一個面向企業家和創業者的PPE(政經哲)課程?
2018年之後,進入了改革開放後的第5個10年,基於全球化和數智化的第五代企業家應運而生。今天的企業家和創業者,不僅要面對全球化和數智化的挑戰,也要面對哲學、互生和智慧的挑戰。
第五代企業家要有哲學的底蘊,從而與時代互生,與社會協同,因此,第五代企業家是哲學型、智慧型企業家,方能長期生長。
筆記俠政經哲商學院以甄別、發展、陪伴第五代企業家為使命,開創中國第一個面向企業家的PPE課程;旨在幫助想成為第五代企業家的朋友,透過學習政治、經濟、哲學、商業智慧提升認知,鍛鍊企業家面對“極端複雜時代下”的決策能力。
掃描下方海報二維碼或點選“閱讀原文”報名,加入筆記俠PPE(政經哲)大家庭。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好文閱讀推薦:
分享、點贊、在看,3連3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