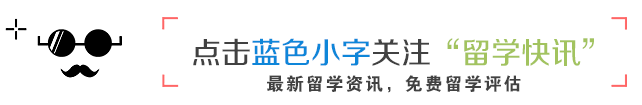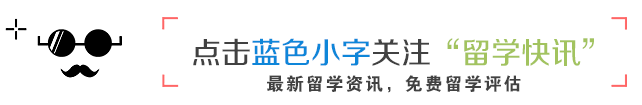對於如何認識日本,國內認知呈兩極化,一種是把目光停留在過去,認為日本仍是一個狼子野心,右翼軍國主義主宰的國家,隨時還要侵略中國;另一種是把日本的歷史與現實又想的太美好,貼上各種玫瑰色幻想,認為當下中日關係的波折,主要在於中國人誤解了日本。尤其是最近的暴力事件,以及國內對暴力的譴責話術,襯托出這兩種脫離實際的幻覺分別主宰言論市場。
筆者認為如何認識日本,是我國國民世界觀構成的重點話題之一,我們只有與時俱進、實事求是認識日本,才能有助於處理好中日關係。筆者就最近社會上關於日本討論較多的幾個話題,表達一些個人觀點。
第一, 日本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與戰前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實的日本與極端民族主義潛流想象中的日本,已經有了顯著不同。另外,東亞國際格局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日本獨立對華發動侵略戰爭的可能性很低。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一直努力追求民主化,早在1889年就制訂憲法、成立國會,但是成果很有限,建立的是一個很脆弱的憲政民主體制,天皇擁有至高無上的統治權,政府、國會之外,軍方也不受節制。從大正天皇繼位到犬養毅遇刺20年中,換了15任首相,政局一直不穩。並且當犬養毅被軍人刺殺後,民主派力量對法西斯勢力毫無抵抗力,軍人內閣從此代替文官內閣。
另外,當時的日本處於經濟高速發展期,從甲午戰爭到盧溝橋事變,對外擴張也不斷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所以,那時候國民的自信心、優越性也十足,並且近代全世界都流行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些時代性因素導致日本國民普遍流行一種狂熱的、暴力味的民族主義,要吞併中國,讓劣等的中國人為日本人騰出生存空間。
這種對無制約性的政治體制,以及極右翼民族主義生態,一定會讓國家成為戰爭策源地。日本如此、德國如此,日後很多地方小霸權也是如此。
不過戰後日本在美國強制之下進行了民主化改革,建立了成熟的分權制約體系,是亞洲民主政體最完善國家之一,軍事力量也完全在憲政的約束之下。美國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也不容許那種唯我獨尊、侵犯他人為榮的右翼民族主義思想,作為一種流行的社會意識形態而存在。
另外一個就是日本由於從1990年代初就處於經濟低迷、少子化雙重不利因素重疊的狀態,那種高速發展期的民族優越感當然無存,中青年一代普遍是對政治漠不關心,低慾望狀態,我們透過日本流行文化就可以看出來。
所以,你說日本還是對華天天處心積慮、狼子野心,從整體社會氛圍上至少已經不是了。無論我們去日本留學,還是去旅遊日本,99%以上的人體驗感都不錯,日本人對中國人表現的都比較友好,甚至比一些人所謂的鐵桿盟友的態度好很多,所以日本一直是出境遊第一目的地。你不能說這是為了錢裝的,如果是裝可以裝一時,全體國民、幾十年普遍性的態度,一定不是故意裝出來的。
再者,戰後東亞國際秩序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主導這一秩序的是美國,在美國的西太平戰略秩序中,日本只能是一個充分受它左右的棋子,所以美國一定要牢牢駕馭日本,不會允它在政治軍事力量上東山再起。進入21世紀後,中日力量對比也發生了發生巨大傾斜,現在日本整體實力落後於中國已經是事實。
所以,無論從日本國內情況,還是東亞的國際政治格局看,現在日本去主動侵略中國可能性,比越南、印度這些具有潛在侵略野心的國家挑釁中國的可能性都要低很多,除非美國在主謀一場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爭,並脅迫它的盟友參加。
第二,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日本是對中國經濟崛起助力最多的國家之一,日本的ODA援助和投資發揮了重要角色,未來中國崛起仍離不開與日本的經濟技術交流。
從1979年至2005年,日本先後四次對華提供援助性貸款(ODA),總計約439億美元,約佔中國接受外國貸款援助的67.2%。“六五”至“八五”期間,中國建設的13000公里電氣化鐵路中的4600公里,470個大型港口泊位中的60個, 1100萬噸每日汙水處理能力中的400萬噸,是利用日元貸款建成的。
日本的技術援助也扮演了特殊重要角色。自1979年至2014年,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先後為125個大型技術合作專案,派遣9220名專家來華工作,併為中國培養了36000餘名研修生。1991年至2009年,中國政府先後為1099名具有突出貢獻的外國援華人士授予“友誼獎”,其中,日本專家210位,獲獎人數位居各國第一。
不過我們也該客觀認識日本援助的性質。很多國內知識分子把日本開發援助描述成為一種無償的善舉,並指責中國人不懂感恩,這也是一種過度的想象。其實,日本開發援助是一種低息貸款,日方政治家推動這種貸款,具有作為補償戰爭罪責的初衷,但是這種低息貸款仍需要償還本金(無償援助不足其中的5%),並且利息優惠與日本對華應付的戰爭賠償相比,九牛一毛罷了。所以,對於日方的援助援助,既不能抹煞它的功績,也不能做脫離實事求是的讚頌。
在日企對華投資方面,截至2022年底,日本累計在華設立企業5.6萬餘家,實際投資金額近1600億美元,是中國第二大外資來源地,約佔我國吸收外資總額的8%,尤其是2000年以前,這個比例達近20%。中日之間先後成立了東風日產、賽格日立、首鋼日電、五羊本田、廣汽豐田、海南馬自達等著名合資企業,中國家電、汽車、通訊、電子等很多行業的起步,與日企在改革初期投資不無關係。
從一個大的背景講,改革開放後中國崛起主要是因為加入了美國主導的產業體系,而這體系中日本是最重要的配角和二傳手,日企日資對中國工業化起了重要的播種作用,這是客觀事實。
第三,近現代史上,日本對華侵略債孽太多,戰後一直又對歷史不進行切實的反思,日本人和國內一些對日本抱有玫瑰色幻想的人,把中國國民對日本的反感行為,完全指責為狹隘民族主義,是有悖於客觀、公正和正義的,是對罪惡的包庇。
歷史上俄國人佔的中國的地最多,但是這些基本上是邊疆地區人煙稀少的土地,尤其是漢族居民很少,所以,大家對俄國的侵略沒有切膚之痛。但是日本對中國腹地的侵略就太嚴重了,一直持續了長達上半個世紀,先後死於日本侵略的有兩三千萬人。日本侵華中的種種體現,是人類之惡的最經典集大成之一。
由於戰後美國的佔領中,為了防止日本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當時日本左翼力量很大),所以沒有對日本右翼政治力量做深度清洗,除了懲罰了幾個首惡元兇外,大量溫和派的軍國主義中高階骨幹被留用下來。這些人及其後代構成了日本政壇的主幹力量,也就決定了日本對歷史的反思程度。他們在和平民主政體下,雖然不再宣揚對外戰爭,但是對先人們犯下的歷史錯誤,進行百般掩飾。
以筆者在東京的觀感為例。皇居護城河旁即是日本軍國主義後人的聯誼組織——遺族會的辦公室,其選址顯示出對過去軍國主義的留戀,放在二戰時的軍人俱樂部九段會館裡面。旁邊是遺族會控制的日本最大的二戰史博物館——昭和館。昭和館展覽裡的二戰,日本不是侵略者,而是受害者,不提日本在中國和東南亞的殺戮,卻盡是日本遭受美軍轟炸的圖片,廳廊內最大一幅照片是美軍的東京大轟炸,這是對歷史的一種何等無恥的解釋。
在昭和館不遠,也就是距離皇居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就是靖國神社,筆者路過那天,祭殿門口一些人揮舞二戰中的軍旗,並打著沖繩字樣,估計他們的祖先是沖繩之戰的站歿者,沖繩是軍國主義狂熱青年的最大的粉碎機,是役11多萬青年人成為炮灰。
我們可以想象,如果是距離德國總統府旁邊,出現一個納粹後人聯誼會以及納粹黨人祭奠場所,世界是如何反應。但是幾十年來,日本人把這些當成天然合理,世界也慢慢認為這是天然合理。
而那些反思二戰史的組織和場所,處於一種邊緣無聲的位置。以筆者忘年交池田惠理子創辦的女性戰爭與和平紀念館為例,它只能蜷縮於西早稻田的一個寫字樓的幾所房間內,極不顯眼,並且財力上難以為繼。隨著日本經歷戰爭的一代逐漸老去,戰後出生的人們幾乎很快就要把反思這件事給遺忘了。
並且,我們國內現在總有一幫“理中客”,堅持不懈地為日本右翼的行為辯解。說什麼不要老是糾纏歷史啊,這是一種小氣;說什麼靖國神社是民間團體的財產,日本是憲政國家,保護私產,政府也沒法干涉取締。日本一有天災人禍,當我國一些人幸災樂禍時,他們就會不浪費一絲一毫的戰機,去諷刺我們的國民劣根性。總之,他們只看到我們的劣根性,而沒有看到日本右翼們的劣根性;用高的道德標準要求國人,而用極低道德標準要求別人。
筆者的觀點是,日本人和國內同情日本右翼的一些人,一定要正視中國人對日本的反感、痛恨的原因,不能一概論之為狹隘民族主義。為襲擊日本在華僑民辯護的言論是罪惡,但是為日本軍國主義開脫,同樣也是罪惡。知識分子,尤其是以普世價值信奉者自詡的知識分子,不能對待中國人和日本人搞雙標。
實事求是地講,中國人是善良的,容易遺忘仇恨的,只要是日本政府和國民有充分反思,中國人一定不會糾纏不休。現在不能說日本政府和國民不是戰爭直接責任人,就沒有義務去做反思,就像公司不能因為換了董事長,就否定以前的債務,日本政府和國民依然有反思的責任,況且很多高官們還都是那些軍二代、軍三代。
第四,中國現在國際處境不佳,切不可四面樹敵,尤其是得罪光我們的主要經濟、科技合作伙伴,那樣中國將失去現代化的必需動力,我們務必要以務實的態度對待中日關係,促進中日友好。
最近幾年,在中美關係變惡的背景下,中國對全球產業資源的吸引力在下降,美國企圖利用它在全球供應鏈的頂層地位,推動產業資源轉向東南亞和印度,以孤立中國。目前穩住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穩住外貿出口量,對於防止經濟失速的意義非常關鍵。中日產業契合度非常高,日本作為我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以及諸多產業供應鏈關鍵部分的供應國,是我們必須合作的物件。
從更全面的中美競爭視角來看,美國在亞太戰略主導權的幾個基石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菲律賓和澳大利亞。我們與美國全面的競爭中,理應是讓自己的朋友越來越多,分化美國陣營,而不是故意採取某種刺激手段,讓對方陣營更加緊密鞏固,這對中國是極為不利的。
筆者以前一直強調的一個觀點是,一個國家只有首先成為一個地區性領導者,才有可能成為一個世界性領導者。處理好中日關係、中韓關係的是中國崛起的必修課,沒有一個穩定的後院,遠方朋友再多,幫襯意義都會打折扣。
所以,我們仍舊有必要強化中日合作的紐帶,防止民間激進思潮把中日關係帶到歧路。人們可以不喜歡日本,但是一個健康有活力的中日關係,對中國的好處遠遠大於一個處於冰凍狀態的中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