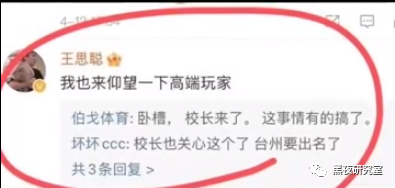文章來源:湖南大學法學院

湖南大學法學院院長 黎四奇
同學們:
大家好!宋末詞人蔣捷曾說: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真是時光荏苒,流年似水。轉眼之間又到了一年一度學子即將告別母校的日子。我現在還清晰地記得去年作畢業典禮致辭的時刻。每年到了學生畢業離校的時候,各種心靈雞湯式的致辭有些氾濫,但是“文明”本身就是使人不得不陷於俗套與儀式之中。雖然畢業典禮是一種比較固定的模式,但是對於我來說,畢業典禮表達的不僅是儀式與尊重,而更是老師給大家上的最後一堂課。說話做事應有比較明確的主題,我今年畢業典禮致辭的主題是:儘量做一個會獨立思考的人。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命題的邏輯,我想從構詞上對這一主題作如下梳理:“儘量+做+獨立+思考+人”。力求完美是一種人格缺陷。為人處世,我們也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所以我在主命題前加了一個限定詞“儘量”,即在認知與能力範圍內盡力而為。基於這一主題與邏輯,我談點自己的想法,以和大家分享。


在法律研習中,“人”是一個基礎性的主體概念,因為我們所有的法律思考與實踐都是緊密圍繞“人”這個字展開的。雖然在我們的潛意識中,“人”應該是一個司空見慣的詞彙,但是正所如黑格爾所言:熟知並非真知。可能當沒有人問時,大家都知道什麼是“人”,但是被人問起時,卻感到有些茫然與語塞,如法人是人嗎?合夥是“人”嗎?如何才能是個人並像個人呢?對於這些,大家可能都有自己比較確信的答案,但是當我再問,在數智時代,人工智慧是“人”嗎?當自然人的大腦被植入了晶片,他還是人嗎?有人認為是,也有人認為不是。關於其定性,許多學者發表了諸多灼見。今天,在這裡,我並不想從法律上來探討什麼是“人”,而更想從有血有肉的個體“自然人”的角度來強調“人”這個概念。
儘管我們基於某種需要,透過法律的方式賦予某些組織在法律關係中的主體資格,但我們應記住的是,其底色與根本是如同你我一樣的“自然人”。也就是說,歸根結底,這些被法律擬製的“人”是服務於你我這樣的人的。如果我們對於法律關係主體的考察偏離了這一點,那麼這就是對法律本質與宗旨的背叛與褻瀆。如何才是一個人?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言下之意是,人是且應該是會思考的動物。如果你不會思考,那麼就不能算是人。法國帕斯卡爾的名言是: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考的葦草。

在物競天擇的叢林法則中,人類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在於人能思,反過來,思決定了我們的存在與延續。貝克萊認為:存在即被感知。如果一個人不能思考,那麼就失去了其存在和本質。實質上,這一思想和法律中關於自然人行為能力的判定標準一脈相承。人是政治性的動物表明,人是社會化的物種。在法律正義中,正義不僅有利已的因素,且更應有利他的底線。在證明與成就自己的過程中,除了表明自己是個人之外,還更要承認他人也是人。人是一種溫情的動物。除了自私地愛自己,也要關愛他人。誠如托爾斯泰所言:如果你感覺到痛,那麼你還活著。如果你感覺到他人的痛苦,那麼你才配得上是個人。愛自己是一生浪漫的開始,但是除了愛自己,我們還要儘可能同理心地去愛別人,善待他人。古羅馬法即表達了這一情懷:誠實生活、不加害他人、使每個人各得其所。

命運多舛,世事艱難。人生應是一場“你好我好大家都要好”的旅程。德國人多貝里在《清醒思考的策略》中這樣寫道:“如果你的地位比別人高,生活比別人好,那麼請保持謙虛,這是你為世界做出的貢獻。謙虛的你,會讓他人少經受一些嫉妒的折磨,並讓世間少一分苦難。”我們所有人都是一個整體,誠如作家約翰.多恩所寫:沒有誰是一座孤島。別人的快樂也就是你的快樂,別人的不幸也就是你的不幸。無論是誰死去,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為我被包含在人類這個概念中。愛能讓家庭和睦,讓社會更加團結與協作,人與人之間更加寬容且有溫度。愛之花盛開的地方,生命更能欣欣向榮。時事無常,人生起伏,善與愛能阻隔、消彌苦難與厄運。法律事關善良與正義,尊重與關愛他人是法律人應有的擔當與責任,這也是做人的核心。大家都是法律人,無論以後大家走向何方及從事何種職業,都要時刻提醒自己:除了愛自己與家人,我們還要對他人心懷善意,讓我們的社會充滿愛。


人首先應是一個人,然後應是一個會思考的人。思考影響並決定了我們的存在、我們是誰、快樂與幸福。你會思考嗎?這是一個看似簡單但實際非常複雜的問題。問題的關鍵不是在於能“思考”,而在“會”思考。現實地看,人多能思考,但是不見得會思考,因為“思考”的內容決定了人是否會思考。康德曾言:時間和空間就像紅色的眼鏡,限制了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雖然我們看到的烏鴉都是黑色的,但是這並不必定表明,在這世界中,就沒有白色的烏鴉。會思考提醒我們,知識探求與人類文明前行的主要任務就是尋找可能存在的白烏鴉。
人是雙重性的動物,既具有物質性,又具有精神性,前者說明逐名逐利是人性,因為物質能使人活下去,後者說明除了物質,人還必須有精神追求。幸福是一個外求與內求相結合、相平衡的概念。叔本華認為:生命是團慾望,慾望不能滿足便痛苦,滿足便無聊,人生就是在痛苦與無聊之間來回搖擺。美國作家梭羅遠離塵世的喧囂,來到瓦爾登湖畔寫下名作《瓦爾登湖》,其以親身體驗告訴人們:人間最美是清歡。人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追求慾望是人之本能,慾望的實現也是對成功的註解,但是慾壑難填,慾望並不必然意味著快樂與幸福。在悖論上,慾望代表痛苦與折磨,放下的越多,精神則越富有。當我們行走到一定的程度,驀然回首,就會發現,大繁若簡,大美若素。不執著於金錢、名利和權力、不困於過去、無懼於未來,我們才能真正獲得內心的從容與淡定,才能真正地強大併成為自己。林語堂在《人生的樂趣》中說:“只有當一個人歇下他手頭不得不幹的事情,開始做他所喜歡做的事情時,他的個性才會顯露出來。只有當社會與公務的壓力消失,金錢、名譽和野心的刺激離去,精神可以隨心所欲地遊蕩之時,我們才會看到一個內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 為了生活,我們一直在路上,但是為自己而活才是人生真正的追求。人生就是一種責任,但是在所有責任中,最根本的責任是找到自己併成為真正的自己。

幸福與高貴並不是物質的堆砌。除了物質,每個人還應有專屬於自己的精神家園。生處人世,保持謙卑、和善寬容是靈魂高尚應有的模樣。人而為人,都有思考的能力,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正確地思考,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洞穴”。尼采有句名言:我們的眼睛就是我們的監獄,而目光所及之處就是監獄的圍牆。有時候,我們所看到的其實是別人想讓我們看到的,而不是我們真正想看到的。看到的並不一定就是真的。除了相信眼睛,有時,我們更應相信自己的心靈。童話《小王子》中有一句非常深刻的話:“人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到真實。真正重要的東西,眼睛是看不見的。”

目光所及只是通往真相的現象,真正的智慧源於用心對事物本質的體察和洞見。會思考的人不應成為物慾的傀儡,應物物而不物於物。誠如蒙田曾說:“世界上最偉大的事情,就是懂得如何屬於自己。”除了肉身,我們還應關注靈魂。會思考的人一定要知道,除了身份,還是自我。除了工作,更應有生活。當我們為了名利而疲於奔命,生活就已離我們遠去。生活的本質不是快與急,而是緩與慢。我們要時刻提醒自己:所有的職業與身份,只不過是為了謀生。人們所樂道的事業和成就,也不過是柴米油鹽之上的錦上添花。人生如白駒過隙,只要走在自己喜歡的道路上,無論你腳下的路是寬闊平坦,還是蜿蜒曲折,這都是幸福與意義。人生海海,真誠地祝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培根曾言:讀書不是為了雄辯和駁斥,也不是為了輕信和盲從,而為了思考和權衡。讀書的第一要義不是升官發財,而是精神自治與做一個真正的人。歷史告訴我們,會思考的人,並不一定會獨立思考。經典童話故事《皇帝的新裝》與王小波的《花剌子模信使問題》就說明,會獨立思考並不那麼容易。勒龐即認為:人一到群體中,智商就嚴重降低。為了獲得認同,個體願意拋棄是非,用智商去換取那份讓人備感安全的歸屬感。我們正處於一個“凡物皆可數與凡物皆可聯”的大資料時代。我們自以為,人類已憑藉突飛猛進的資訊科技打破了資訊繭房而擁抱了資訊海洋。事實是,演算法正利用“個性化推薦”、“我的日報”及“議事日程”等打造一個個新的電子資訊繭房。
依賴即控制與服從。我們自認為,網路、資料能極大地塑造我們的個性,但是我們的個性正在一步步地被定向、被塑造、被扭曲或甚至可能被毀滅。如果技術的目的在於實現一種標準和普遍、廉價且高度粘性的便利與快捷,那麼就極有可能降低個體智商、消解個人情感、擠壓個體自由甚至改造個性,個體已無處可逃地成為被資本與數字技術剝奪、圍獵與奴役的物件。對於網際網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知到,雖然網際網路是一個解放性工具,但同時更是一個控制工具。資訊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資源,其更是一種權力/權利資源。資訊時代,資訊即權力,其不僅可以決定人們需要思考什麼,而且還能決定我們該如何去思考。雖然我們並不願意承認,但是人人關係向人機、機機關係的異化說明我們正在日益成為資本與技術的奴隸。
資訊科技不僅正在改變我們的記憶,使得遺忘越來越難,甚至是不可能,同時也使得真與假、正確與錯誤、善與惡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甚至是不可見。強大的數字化記憶摧毀歷史,損害我們的判斷與及時行動的能力,讓我們無奈與無助地徘徊在兩個同樣讓人不安的選擇之間:是放棄自我的思考能力,還是心安理得地被幽禁於一個個電子資訊繭房中,讓資訊給自己上鎖?是將過去變成永久的現在,還是對現在視而不見?人之所以是人是因為人會思考,我們之所以是我們是因為人會獨立地思考。失去思考能力會導致人性的殘缺,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就等於失去了自我。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霞。我們都只是此時此地的過客,我們只是碰巧路過,我們來到這裡的目的是觀察,思考,學會成長,去體驗,去熱愛,然後我們獨自回家。雖然我們很可能不會被他人知道或記住,但是我們自己一定要知道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及最終要到哪裡去。會獨立思考的人能找到自己,但是如何獨立思考呢?對此,作如下分享。


一是要學會獨處。孤獨是高貴者的選擇,是優秀者特有的標籤。所有的王者,都成長於孤獨中。唯有孤獨,才能磨礪出一個人強大的意志。熱鬧與喧囂會擾亂人的心緒。學會獨處與享受孤獨,是一個人走向強大與成熟的必經之路。獨處能讓人找到自己,併成為自己,因為只有在獨處時,人才是最自由的。紀伯倫曾說:孤獨,是憂愁的伴侶,也是精神活動的密友。叔本華說:只有當一個人獨處的時候,他才可以完全成為自己。當你學會與孤獨為伴,便是你向自我的迴歸。沒有感受過孤獨的人,難以理解生活的本質。水靜至則形象明,心靜至則智慧生。孤獨意味著清醒。一個人的靈魂,只有在孤獨中,才能走出自己的洞穴而面見光明。一個人,要麼庸俗,要麼孤獨。
二是要堅持閱讀。沒有書籍滋養,人就是沒有靈魂的軀體。閱讀能尋找到相近的靈魂。未經思考的人生沒有意義,自發的閱讀會讓我們學會思考,但是必須注意到會學習並不一定會思考,因為學習並不等於認識,有學問的人和能認識的人是截然不同的,記憶造就了前者,而智慧造就了後者。為了不只是活著,我們都要儘可能地透過閱讀去尋覓自己存在的意義,哪怕生活本身就沒有意義。生活是一次且看且行且從容的修行,閱讀給人力量、方向與勇氣。人生哪能都如意,萬事只求半寸心。閱讀能抹平波瀾,讓人痛而不言,驚而不亂。雖然名利是人性使然,但是除了熱鬧與繁華,本質上,生命就是一場孤獨的旅行。為了能走下去並走得輕鬆、坦蕩與幸福,人總要有一段路是向內行走的。閱讀能讓人在別人的故事、經驗與感想中,反思與檢討自己的命運,能讓我們辨美醜知善惡,能讓我們最終與自已、世界和解,真正學會接納與喜愛並不完美的自己,並最終成為我們自己。人終其一生,都應像唐僧取經一樣去書本中尋找自己失落的靈魂。
三是適度的不知情權。為了維護權益及避坑,在法律中,我們主張當事人的知情權。為了活得簡單與安寧,除了知情權外,人也應該擁有不知情權。迅猛發展的資訊科技緩解了資訊不對稱,但是我們也深受資訊的侵擾與危害。人是環境性的動物,我們都是環境的“囚徒”。會思考意味著人的靈魂不應被那些破碎、惡搞、低俗、暴力與空談等資訊所充實。資訊時代,對一個嚮往美好生活的人而言,過度的資訊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與對生命的侵蝕與浪費。置身於真假難辨的資訊洪流中,為了避免靈魂被透支、心緒被打擾及被無處不在的“奶頭樂”所支配,人應享有不知情權。
我們只不過是宇宙的塵埃,時間長河裡的水滴。雖然只是曇花一現,但是我們的存在不僅承上,而且啟下,我們昭示著未來。雖然為人很苦,但是我們無法逃避。雖然為生很累,但是我們註定無法停歇。凡活著的都要活下去。儘管不去問什麼,我們每一個人也可以不經意間走完這一生,但是人不僅僅是要活著,而且還要去追尋為什麼而活著,因為人是靠價值而生存,人類及其文明靠價值來延續。會獨立思考能讓我們找到並賦予活著的意義。數智技術日盛之下,我們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更需要會獨立思考來確立人的本位並找到真正的自己。生活並不完美,但是誠如羅曼·羅蘭曾言:“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發現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熱愛生活。”
再次感謝大家。祝大家幸福安康,前程似錦。歡迎大家常回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