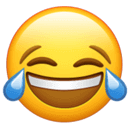文 | 底線思維
新學期開學,孩子們又領到了新書。不過翻看之下發現,無論是知識點還是例題、練習題,都少了很多,多是些遊戲類講解、插畫,許多人對此不禁有點擔憂:這還能學到什麼?
其實近年來,中小學教材是否“防自學”的爭議一直存在。支持者們認為新版教材摒棄了過去“死讀書、讀死書”的教學方式,更加“素養全面”、“學以致用”;反對者們則批評新教材“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教考分離”且加劇教育不公。
這一爭議背後,既是教材編寫邏輯的轉變,也是教育理念與社會對公平焦慮的交織。
01 從“操作手冊”到“研發指南”
“你們學校用的哪版教材和教輔資料?”自2024年秋,義務教育三科統編教材“煥新”以來,每逢開學,家長群裡對新教材和教輔的討論熱度總是居高不下。
根據計劃,義務教育三科統編教材將於三年內覆蓋所有年級。其中,2024年秋季學期小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使用;2025年,小學一、二、三年級和初中一、二年級使用;2026年,義務教育階段所有年級全部完成替換。
教育部英語課程研製專家、中小學英語教材改編的指導者張連仲,曾對新教材充滿期待:“我們要讓孩子像學母語般自然習得英語。”
這種理念背後,是一幅美好的圖景:透過海量素材,為孩子搭建類母語語言學習環境,讓孩子們在浸潤式的語言環境中,海量輸入輸出,最終實現學以致用,用英語順暢地溝通交流、閱讀書籍。
理想很豐富,現實卻頗為骨感。
“學生和家長們普遍反饋,新教材更難了,其中英語教材的難度還被罵上了熱搜。”一名英語老師告訴我,現在小學英語教材,有多個版本。教育部的規定比較靈活,英語課程從小學三年級開設,但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從一年級開設英語課程。“無論是一年級起點的,還是三年級起點的,不教字母和音標,大多開篇即是英語句子。”
亦有來自不同地區的多位初中英語老師直言:“我不是專家,身邊資料也不夠多,但使用新教材後,大家感覺初一新生對英語的厭學棄學率升高了。”
教材剛開篇即用完整句子和語法鋪墊,許多學生因為陷入“聽不懂、跟不上”的困境而選擇擺爛。“語言環境需要家庭與社會共同構建,僅靠課堂的碎片化輸入,反而讓普通家庭孩子更易掉隊。”
“某版教材一年級的標準說比雙減前簡單,那確實對北京的孩子來說簡單。”
與英語教材近乎一邊倒的“太難”輿論不同,中小學數學教材是此次“防自學”爭議中吵得“有來有往”的學科,同時也更為複雜和激烈。支持者們認為新教材注重課堂互動與思維培養,或許有利於遏制“超前學習”和“刷題制勝”;反對者則批評教材內容簡略、依賴教師授課水平,是典型的“防自學設計”。
對此,一位數學名家告訴我,數學是否有“防自學設計”主要看以下幾點:1.教材內容和章節,基礎知識的傳授和框架是否已搭建好;2.教材中的習題示例與考試的考點匹配程度。“教材改版肯定不是衝著防自學去的,但實際上諸如蘇教版、北師大版改後,確實很難自學了。”

左邊是舊教材,右邊是新教材。可以看到新教材更關注生活體驗
在新中考高考的改革風向下,新教材強調思維過程,將知識點拆解為生活場景中的問題鏈。數學教育研究者李明陽打了個比喻:“舊教材像組裝宜家傢俱,步步清晰;新教材像給你幾塊木板,說‘這是椅子’,卻不說怎麼拼接。”
另一名數學雙金教練感同身受。“有次我調研新教師們,問某版新教材第一二課是什麼內容,有人回答‘購物’,我又問了一次還是回答‘購物’。翻開教材一看,確實是購物,而且只有提問和引導,沒有具體知識點和解答。”
看著我疑惑的表情,他解釋,實際知識點是“小數和計算規則”——單元以“購物”情境匯入,不直接呈現知識點和方法。“就像只給你看一棵大樹的部分枝幹,卻不展示根系和樹葉,且枝幹也是東一塊西一塊散在不同地方。若缺乏教師引導,學生難以獨立理解其數學知識和深層邏輯——能否學好和學生本身聰慧勤奮相關度降低,更取決於教師備課水平和教育集團之間的資訊堡壘。”
教材如同散落的拼圖,需要教師用高超的水平為學生梳理還原才能呈現圖景。這種設計讓知識迴歸課堂,無形中放大了優質師資的價值,卻也為資源匱乏地區的學生設下更高門檻。
當然,支援新教材的理由也很充分:1.契合未來人才選拔方向;2.教材要簡明,避免冗雜,反對過去的填鴨式教育,引導學生自主思考;3.知識點採用螺旋式排布,考試內容在教輔資料及練習題上有所補充。
教材改革契合未來人才能力培養。“新版教材的設計理念與新中高考改革方向一致。當前選拔性考試更注重知識靈活應用與現場分析能力,舊教材‘重結論、輕過程’的模式已難以適應。例如數學考試強調‘海量閱讀、跨學科、學以致用’,旨在培養獨立解決現實問題的思維。長遠看,這種轉型有助於學生應對複雜的社會問題,而非僅成為應試刷題機器。”
“舊教材模式追求高效的基礎知識傳遞,好比‘操作手冊’,新教材倡導培養深度思考能力,好比‘研發指南’。這必然會引起教育轉型陣痛,但就像南山區數學考試點明方向一樣,與其抱怨,不如順勢而為,轉型需要家長、教師同步調整教育觀念。不要再以應試結果為導向,而要適應過程化學習。”

1993年與2022年人教版數學教材對比
為什麼一線師生都對新教材的“知識碎片化”印象頗深?
“部分家長認為新版教材是故意讓知識點缺失的,但客觀上,教材排版和頁數還受限於如內容減少、字號放大、行距增大等‘雙減’和保護視力等要求,很難面面俱到。”
教材知識點採用螺旋式排布,已成為教學共識,螺旋即知識點“多樣且不重複”的層層遞進學習機會,從而達到循序漸進的效果。
因此,螺旋式編排是教育界認為目前最符合學生認知結構的模式。但同時確實會帶來知識點零碎,由此對老師專業性要求更高,也對學生提出“多面手要求”,易使學生“顧此失彼”。
對於教輔資源不均衡等問題,多地也在探索用科技手段將頂尖學校的授課資源與遠端學生共享,例如新疆、甘肅多所中學與成都七中網班實現直播教學,進行即時互動。英語新教材被罵上熱搜時,專家們也支招了,“可以科技賦能,藉助某某牌學習機等智慧工具產品”,但此番解釋並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
綜上所述,舊版教材是“結論導向”,以知識點結論為核心,透過明確清晰的表述、短平快的口訣和簡化學習路徑,使學生可快速掌握和應用。而新版教材是“過程導向”,學習需要回歸課堂主陣地,不僅倚仗教師備課水平和教學質量,也需要家庭為學生提供生活感受和情境探索。
02 公平之困:當教材成為“資源放大器”
“教材越簡略,我們越要買‘說明書’——這究竟是減負還是增負?”一名家長評價。新版教材的“簡略化”初衷本是減負,卻催生了龐大的相關市場。
例如,2023年中國教輔規模突破834億元,折射出家庭對教材補充資源的迫切需求。其中,“知識點彙總”類書籍銷量激增300%,封面上“補全教材缺失環節”成為宣傳點。城市家庭尚可透過教輔、網課填補教材缺口,而農村學生往往因經濟條件與資訊壁壘,陷入“課堂學不透、自學無門路”的困境。
這便是反對聲音最為集中的一點——很多人認為新版教材和選拔方向放大了教育資源差異,對偏遠地區的學生造成了不公平影響。
首先,教材簡化增加了學生獲取知識的成本。例如,有家長指出,新版教材刪除部分知識點後,考試仍涉及相關內容,不得不“考的課外補”。許多家長也難以有效協助孩子,因此近些年,“縣裡學生去市裡補課、市裡學生去省會補課、省會學生跨多區補多學科”愈演愈烈,這無疑加重了家庭的經濟負擔和孩子的壓力。
那為什麼不把教輔補全的知識點內容整合進教材呢?既能降低成本,又能減少自學障礙,但似乎又與現行政策“書包減重”、“視力保護”等要求相悖。

2024年,中國圖書零售市場碼洋規模為1129億元,其中教輔類圖書佔比達25.33%,僅次於少兒類圖書
其次,教材內容的城鄉差異也加劇了不公平現象。不管是教材還是考題,涉及的內容多以城市生活為背景,例如地鐵路線、博物館城市地標景點等,越來越多“生活化、情境化的題”也在製造隱性的認知壁壘,如“制定一份去知名景點研學的攻略”、“在科技館當講解員”等需要一定生活體驗的題目。
當一道包含“自動售票機”、“立體投影廳”、“抖音打卡點”的“為科技館遊客設計路線”的大題出現在某地中考卷子中時,有些山區學生從未見過題幹中的票券,更不知“立體投影廳”為何物。而城市學生的答案裡,甚至還有額外標註——這些經驗來自他們每學期都會參加的研學旅行。
而農村學生對這些內容缺乏認知基礎,寒暑假也沒有家庭文化資本支撐他們去涉足,這不僅影響了他們的學習興趣,還可能降低他們對家鄉文化的認同感降低。
最關鍵的還是師資配置。缺乏基礎知識點和知識體系的新版教材,學生需要依賴教師在課堂上的講解才能理解。這種設計使得偏遠地區的學生在缺乏優質教師資源的情況下,更難以掌握知識。
或許有人會說,“科技彌補差距”,但這個願景在實踐中屢遭挑戰。
誠然,學生確實可以找教輔補充知識、透過在網路上找到名師課程資源彌補名師差距,但義務教育階段實際具有壟斷性,學生的絕大部分時間,還是花在了學校的課堂裡。所以即使師生意識到了這一點,要額外獲取資訊,其經濟負擔和時間精力成本是難以估量的。
而教育資源匱乏的地區要利用網際網路學習,還有兩大疑問,一是如何利用?二是如何防沉迷?
縣鄉網際網路教育體系,依賴於教師的資訊檢索能力。老師先學會,再傳授給學生一個系統的網際網路學習方案以獲取網站資源。網際網路有如此豐富的資源,但是大多數農村中小學生的視野只侷限在貧瘠的課本與落後的師資裡。誠然,會有一些聰明學生主動搜尋去了解,但絕大部分學生還是需要引路人。而網際網路的誘惑力,在沒有家長嚴格監督的情況下,使缺乏自制力的孩子們倉促開啟網路世界,其弊端已無需贅述。

2月17日,樹人景瑞小學的一堂語文課上,孩子們正在進行跨學科主題學習。新華社
儘管成都七中網班等模式為偏遠地區輸送了優質課程,成效斐然,但多數學校仍缺乏相應資源,老師們篩選網路資源、設計數字教案的能力也參差不齊。“我們告訴學生‘善用搜索引擎’,卻無法教會他們如何辨別資訊真偽;想提倡AI助學,但一些鄉鎮學校連機房和網路都難保障。”技術本應是打破資訊差的鐵錘,是公平的槓桿,若缺乏宏觀性系統性的支援,反而可能成為新的分化工具。
“我自己也是農村苦讀書摸爬滾打實現階級跨越的,對新教材編寫組的那幾位也有所瞭解。”一名大城市知名教育專家對我坦言,“現在教材小組編輯或修改的時候確實很用心,甚至改版、試點試驗多次,收集了10萬多學生的試用反饋和建議,但他們目光觸及的都是那些本身底子就很好的孩子們了,你懂我想表達的意思嗎?”
03 回到最初的問題,新版教材“防自學”?
答案並非非黑即白。它既不是某些人口中的“陰謀論”,也不是“知識灌輸”向“全面素養”轉型帶來的必然陣痛。
爭議的核心,在於如何看待教材的功能。舊版教材如“操作手冊”,追求高效和紮實的知識傳遞;新版教材似“研發指南”,強調思維建構和能力拔高。我們既要警惕基礎教育被“思維培養”異化為“精英的遊戲”,也不能因噎廢食、退回機械訓練的老路。
教育學者章勤瓊提出了他的理念——“教材要服務課堂而非替代課堂”。同時他也提出“教材應為課堂提供腳手架,而非讓師生在迷霧中自行摸索。”要實現這種理想的教材設計,需在知識完整性與思維開放性之間找到平衡點——既保留基礎知識和框架,又留出思維探究和拔高空間。如此,才能在理想和現實中找到平衡點,讓教材成為“基礎牢固”又兼具“啟迪思維”的鑰匙,而非加深焦慮和教育不公的枷鎖——基礎教育從普惠到精英化傾斜。
解決這一矛盾,需在教材設計上更注重學生與教師的真實需求,同時透過政策引導緩解教育資源不均。
義務教育的真諦不在於教材是否完美,而在於能否讓孩子的眼睛裡——無論他/她身在城市或鄉村,都能繼續燃燒探索求知的慾望。唯有如此,“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才會成為照亮書山學海的光,而不只是一句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