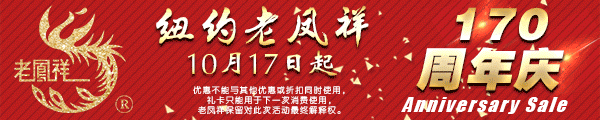作者 | 高興 中國政法大學 博士生
一審 | 胡惟禕 康奈爾大學 L.L.M
二審 | 鄧雅元 復旦大學 本科
編輯 | 劉曉鈴 西南財經大學 研究生
蘇桐 華中科技大學 本科
責編 | 馬語謙 武漢理工大學 本科

漂移的中國式陪審

【摘要】
現代意義上的陪審制起源於英國,併為其他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國家所承襲,形成兩大法系陪審制與參審制的對立。二者雖然聯絡密切,但呈現出審判權力、適用範圍、審理組織等方面的差異。[1]我國曆史上並無民眾參與審判的制度,陪審實屬是移植西方的“舶來品”。[2]上世紀50年代,我國正式在法律層面確立了人民陪審員制度,並不斷在司法審判中積累實踐經驗。與兩大法系的國民參與司法審判的方式相比,我國人民陪審似乎融合了陪審制與參審制,形成了中國式陪審制度。例如我國陪審員與審判員擁有同等權利,這與參審制類似,但在7人合議庭裡又只對事實部分進行評議表決,這又與陪審制類似。但相比域外實踐,我國人民陪審員“陪而不審”的現象尤為嚴重,導致司法民主的應然功能無法得到實現。“陪而不審”的實踐問題,不僅與我國“偵查中心”的縱向訴訟構造等訴訟體制有關,而且與陪審制度的具體程式設計有關。由於體裁與篇幅的限制,在此不作過多贅述。文章僅從規範層面選取了三項代表制度,並進行理論提煉,對比域外,以說明世界主流法治國家盛行的陪審制度在中國是如何“漂移”的。
一、事實認定的自由度:從“自由裁判”到“法定裁判”
除了“事實審”,陪審員的職能是否還應當包含“法律審”,是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核心問題,向來也爭議頗多。
反對“法律審”的學者稱,由於現代法律體系日趨複雜,專業法官解決法律專業性問題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法官專業知識“權力化”,導致陪審員被法官所支配,這是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在實踐中形同虛設的根本原因。[3]支援“法律審”的學者稱,人民陪審制的“法律審”並非一無是處,相反,由陪審員就法律問題發聲具有體現司法民主、有利於司法監督以及幫助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等作用。[4] “事實審”與“事實+法律審”的觀點碰撞在2014年由官方裁判出勝負,《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逐步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就此,“事實審”觀點被官方所採納,我國《陪審員法》也在保留傳統共享模式的同時,引入了分權模式進行實效檢驗。[5]
既然人民陪審員的裁判範圍限於事實認定,那麼“自由裁判”的需求就呼之欲出。作為公眾參與司法最直接的形式,陪審制度有利於打破法官的職業偏見和思維慣性,將公眾對案件事實的理解與良知灌注於司法活動,而這種功能實現的前提就在於陪審團(員)具有對案件事實“自由裁判”的機會,若法律仍對陪審團(員)的“事實審”作出證據證明力和全案證據認定事實的證明標準方面的限制,那麼陪審的“大眾化”就難以在司法審判中發揮實質作用,“平民”與“職業”的思維互補就變成了“非專業職業”與“職業”的思維互認。
從比較法上看,在英美法系,一旦案件進入陪審團審理程式,作為案件事實裁判者的陪審團具有實際的自由判斷證據之證明力以及宣告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的權力,正因為如此,英美陪審團制度被稱為“自由證明的堡壘”。在大陸法系,隨著法定證據制度退出歷史舞臺,自由心證原則得以確立。最初,德國僅將自由心證與陪審制度繫結,認為陪審員不受證據規則的限制,根據對案件的總體印象進行裁判,而法官仍需受到證據規則的約束。這種對職業法官心證的過度限制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於是自由心證原則最終脫離陪審制度而獨立存在,但陪審員對案件事實的“自由裁判”仍未改變。[6]總之,根據現代證據法的基本理論,證據法所要規範的僅是證據的證據能力和司法證明要素,對於證據的證明力和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明標準,交由裁判者根據其理性、經驗和良知自由判斷。是故,陪審制就擁有了司法民主價值實現的施展空間。

(圖片源自網路)
隨著我國證據法的不斷發展,證據規則日益豐富,但與域外不同的是,我國存在大量的證明力限制規則和內心確信客觀化現象,而這些認定事實的證據證明力判斷以及綜合全案的內心確信本該是“自由”的。
陳瑞華教授將這種旨在限制證明力的立法理念成為“新法定證據主義”,與歐洲中世紀實行的法定證據制度相區別。這種“新法定證據主義”的主要特徵有:對不同證據的證明力加以區分、印證規則的確立、內心確信標準的法定化以及間接證據證明體系的法定化。[7]以印證規則為例,印證是指兩個證據所包含的證據事實發生重合或交叉。這種規則旨在強調證據的真實性,主要適用於自相矛盾的證人證言、前後不一的被告人供述以及一些特殊的言詞證據。[8]印證規則要求法官重視證據之間形式上的佐證,但陷入了司法證明的機械化窘境,即將原本屬於經驗上、邏輯上的問題上升至法律問題,使得法官對案件事實的判斷流於形式和表面。[9]
雖然“新法定證據主義”的理念在我國確實有其存在的必要背景,即防範冤假錯案、防止法官權力膨脹等功能,但不可掩蓋的是,這樣的證據法要求也同樣會導致與法官擁有同等權力的人民陪審員無法對案件事實進行“自由認定”,陷入同樣的“機械化”裁判,司法民主的價值期待遭遇制度供給上的障礙。
二、陪審適用的介入度:從“參與裁判”到“邊緣裁判”
隨著現代刑事訴訟中案件量激增,各國司法機關均面臨訴訟爆炸的局面。為解決這種狀況,各國均透過合作型司法來提高訴訟效率,改變不堪重負的司法實踐。
相較於傳統對抗型司法模式,合作型司法模式的最大特徵在於被追訴人作有罪答辯而非無罪辯解。在這種情況下,陪審制度面臨存在必要性的審視。一方面,由於被追訴人認罪,其可罰性降低併為國家節省了司法資源,故法院為提高訴訟效率和使被追訴人擺脫“程式即懲罰”的困境,會採取更為簡易的審理程式,其對案件事實真實性的審查也不會像傳統對抗式那樣嚴格。有學者指出:“雖然美國聯邦法院和州法院在有罪答辯事實基礎的具體審查程式上存在一定差異,但均採取非對抗的言辭或書面審查方式。”[10] 這就意味著陪審團(員)無法在正式完整的庭審過程中認識和感受案件事實全貌,“效率導向型”庭審也與陪審制度的最初定位——推進司法民主、促進司法公正——相沖突。另一方面,棄權審判案件中控辯爭議的焦點往往集中於歸屬法律適用範疇的量刑問題,而非事實認定,故陪審制度無法在此類爭點上發揮作用。
因此,為確保陪審制度的參與性,保證其能實質發揮裁判事即時的效果,英美國家均限制了陪審團(員)事實裁判的案件範圍,以期實現陪審資源利用的“帕累托最優”。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可能被判處6個月以下監禁刑罰的犯罪不適用陪審團審判,而在可能被判處6個月以上監禁刑罰的犯罪案件中,陪審團的適用也必須限制在被告人“答辯無罪”。[11]
而在大陸法系國家,由於法律傳統的影響,合作型司法與職權主義構造存在內生性衝突,為消弭此種困境,多數國家仍以“實質真實”作為法院裁判的核心任務,透過對案件事實真實性的查明來消除審前程式與審判程式主導權、合意真實與實質真實的衝突關係。
例如,根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57c條第4款第1句和第2句,法院在合作型司法案件中將認真核實每一個細節,即使是有細微的錯誤,也會導致認罪協商的終止適用。[12]
因此,在持續強調“實質真實”的大陸法國家,即使被追訴人作有罪答辯,法院仍需對案件事實的真實性進行全方位審查,陪審制的適用也就不存在僅限於無罪答辯的情況了。只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合作型司法並未影響陪審制的適用,但與英美法一樣,大陸法國家仍秉持輕重刑罰區分的觀點,一般將陪審制的適用框定在重罪案件中。例如,法國刑事訴訟規定被追訴人可能被判處10年以上刑罰的案件均適用陪審制度審判,軍事重罪以及毒品走私重罪等除外。[13]這種做法的原因有二:一是重罪案件通常涉及長期監禁甚至終身監禁,對被告人權益的影響深遠,引入陪審制可以增強審判的正當性,透過大眾參與減少對司法公正的質疑;二是陪審團審判程式複雜、耗時較長,需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若廣泛採用陪審制,可能嚴重影響司法效率。

(圖片源自網路)
可見,域外國家在陪審適用範圍的設定上,均強調陪審的實質參與,透過限制陪審的適用範圍來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效果。
我國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將簡易程式的審判組織從原來的“獨任制單用”改為“獨任職與合議制並用”,即規定對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可以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也可以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對可能判處的有期徒刑超過三年的,應當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雖然立法者的想法是無論是三年以上還是以下刑罰的案件,均會出現案情、證據相對複雜的情況,引入合議制有利於查清事實和案件的公正審判。[14]但規範上的修改給實踐中陪審制的異化適用“開了口子”,有學者透過實證研究發現:基層法院為緩解案多人少、法官人手短缺的壓力,讓陪審員大量參與無事實爭議的簡易案件,但在這些案件中,陪審員並未發揮實質作用。[15]有的陪審員稱,在其參與的一個案子裡,被告人認罪態度很好,案件沒有任何爭議,庭審中無所事事,且其還為此請假半天,乘坐兩小時公交車完成這十分鐘的陪審。[16]
可以發現,相較於域外,我國在陪審適用範圍的設定上過於寬泛,導致司法實踐中陪審功能的異化,很多法院僅將陪審制的適用當作“勞動力補缺”的工具,陪審制度的本質——人民群眾參與司法活動——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使得陪審員成為法庭審理的邊緣人物,無法發揮陪審員的審判實質效果。
三、評議參與的指引度:從“獨立裁判”到“依附裁判”
陪審團(員)均系非法律專業人士,缺乏正確理解法律規定的專業知識,其並不查詢證據,也不會找出案件所適用的法律。但若陪審團(員)忽視了法律或沒有正確判斷事實,則他們可能會作出錯誤的裁決;若他們不理解案件可能適用的法律的含義,則肯定會出錯。[17]
因此,如何增強陪審團(員)作出正確裁判的能力一直是英美陪審制度改革的重要問題。為此,英美國家發展出法官指示制度,透過法官對陪審團(員)作出一系列有關陪審職責、審判流程、證據規則等內容的指引,並不斷完善告知方式、擴充告知內容等,以幫助陪審團(員)在準確理解法律的基礎上正確認定案件事實。例如,《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30條專門規定了法官指示的相關問題,明確了訴訟雙方申請法官向陪審團指示的諸多權利。[18]當然,法官指示制度並不會影響陪審團裁判的獨立性,這主要是由於英美法實行的是“二分式”庭審,即將法庭劃分為法官與陪審團兩部分的內部分工,每一部分均單獨作出決定並與另一部分相隔絕。[19]
在大陸法國家,由於採用的是一元法庭,法官和非專業陪審員作為同一個群體進行審理並共同作出決定,陪審員往往折服於法官的專業性,自然產生一種權威屈從心理,其在判斷時更容易受到職業法官的影響。[20]故大陸法國家在幫助普通公民準確認定案件事實的同時,也注重陪審員裁判的獨立性。例如,法國設定了“問題列表”制度,審判長在法庭辯論結束後,案件評議前,不對控訴和辯護要點進行總結,而是根據移送案件裁定文書將案件事實和量刑情節細化為具體的問題,向陪審員當庭宣讀,以幫助陪審員更清晰地理解案件要點。在評議前,審判長進行“自由心證”的訓示。在陪審員進入合議階段後,審判長提出的問題會寫在一張紙上,陪審員對每一個問題進行一次“是”或“否”的投票,票上的內容不得讓其他人看見。[21]可以發現,法國在透過問題列表制度增強陪審員認定事實的能力的同時,也運用了諸多技術理性手段,支撐陪審員裁判的獨立性。
我國實行一元法庭,這點與大陸法國家相同。2002年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合議庭工作的若干規定》第10條規定:“合議庭評議案件時,先由承辦法官對認定案件事實、證據是否確實、充分以及適用法律等發表意見,審判長最後發表意見;審判長作為承辦法官的,由審判長最後發表意見。對案件的裁判結果進行評議時,由審判長最後發表意見。審判長應當根據評議情況總結合議庭評議的結論性意見。”此項規定中未提及陪審員在評議中的意見發表順序,導致實踐中很多法官為將陪審員拉攏至自己陣營,先發表對案件的看法,給予“外行”的陪審員相當“心理暗示”,故陪審員往往會人云亦云地附和法官的意見,表述最多的是“我同意”,從而影響陪審員的獨立裁判。[22]
意識到這個問題後,2010出臺的《關於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活動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了評議時陪審意見發表的順序,將其置於專業法官之前,以防止其被法官所影響。[23]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國陪審員“依附裁判”的現狀。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陪審員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在七人庭中借鑑域外,設定了“問題清單”制度,分別在開庭前和評議時列出案件事實問題清單以幫助陪審員作出正確裁判。但這種“問題清單”制度也引發了陪審員“依附裁判”的迴歸,使得原來的“主動依附”向“被動依附”轉變。該司法解釋規定,在陪審獨立性最為強調的評議階段,審判長應當歸納和介紹需要透過評議討論決定的案件事實認定問題,並列出案件事實問題清單。這就導致陪審需要進行評議和發表意見的物件,不是檢察官所指控的犯罪事實,而是審判長聚焦的案件事實,這與法國審判長一般按照移送案件裁定書而非自行總結的控辯要點列出具體的問題的做法形成對比。若審判長認為某些事實不需要透過評議討論決定,則陪審員在評議階段無法對這些事實發表意見。
可見,現行“問題清單”的制度構建雖然降低了陪審員認定事實的難度,但也使陪審員“獨立裁判”的空間限於審判長列出的事實範圍,對於沒有列出的部分,陪審員只能被動地“附和”審判長的意見。
如果說陪審制度本身的執行現狀深受訴訟體制影響,那麼陪審制度反過來也會以其功能成為撬動“審判中心”的支點。如今較多學者主張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成功的關鍵在於解決刑事訴訟的結構性難題,屬“結構主義進路”,但由於我國國家治理的體制機制等方面原因,實務界更傾向於“技術主義進路”,透過對周邊訴訟程式的最佳化,在不觸碰訴訟體制的前提下,促進審判中心改革,陪審制度的完善便具有積極價值。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規範改進固然應該注意與本土的適配性,但較為成熟的比較法經驗也具有相當參考意義,可以說,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刑事程式現代化的回應。

(圖片源自網路)
向上滑動閱覽
參考文獻
[1] 參見張培田:《陪審制和參審制的歷史考察與比較》,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2期,第36-37頁。
[2] 參見步洋洋:《中國式陪審制度的溯源與重構》,載《中國刑事法雜誌》2018年第5期,第89頁。
[3] 參見龍宗智:《中國陪審制:出路何在》,載《中國法學網》,http://iolaw.cssn.cn/sxlm/xspl/200307/t20030727_4586147.shtml,2025年4月23日訪問。
[4] 參見張思堯:《人民陪審制度事實審與法律審的困惑與出路》,載《法律適用》 2015年第6期,第52頁。
[5] 參見陳學權:《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中事實審與法律審分離的再思考》,載《法律適用》2018年第9期,第29頁。
[6] 參見王穎:《揭開自由心證的面紗:德國意涵與中國敘事》,載《比較法研究》2024年第6期,第104頁。
[7] 參見陳瑞華:《以限制證據證明力為核心的新法定證據主義》,載《法學研究》2012年第6期,第150-153頁。
[8] 參見陳瑞華:《論證據相互印證規則》,載《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3-115頁。
[9] 參見陳瑞華:《論證據相互印證規則》,載《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1頁。
[10] 史立梅:《美國有罪答辯的事實基礎制度對我國的啟示》,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第33頁。
[11] 參見張瀚文:《陪審員事實裁判模式的域外考察與本土展開》,載《世界社會科學》2025年第1期,第191頁。
[12] 參見[德]貝恩德·許乃曼著,黃河譯:《德國刑事認罪協商制度的新進發展及評析》,載《法治社會》2023年第1期,第124頁。
[13] 參見劉林吶:《法國重罪陪審制度的啟示與借鑑》,載《政法論叢》2012年第2期,第93-94頁。
[14] 參見刑事訴訟法的法律釋義與問答,載《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zgrdw/npc/flsyywd/xingfa/2014-02/10/content_1825866.htm,2025年4月26日訪問。
[15] 參見孫長永、周媛:《刑事案件陪審員制度實證研究——基於J省、C市部分基層法院的考察和分析》,載《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第156頁。
[16] 參見孫長永、周媛:《刑事案件陪審員制度實證研究——基於J省、C市部分基層法院的考察和分析》,載《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第157頁。
[17] [美]倫道夫·喬納凱特:《美國陪審團制度》,屈文生等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頁。
[18] 參見劉梅湘、孫明澤:《刑事陪審團指示制度研究——論中國刑事訴訟人民陪審員指示的完善》,載《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第133頁。
[19] 參見達馬斯卡:《漂移的證據法》,李學軍等譯,何家弘校,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頁。
[20] 參見左衛民、周雲帆:《國外陪審制的比較與評析》,載《法學評論》1995年第3期,第60頁。
[21] 參見施鵬鵬:《法國參審制:歷史、制度與特色》,載《東方法學》2011年第2期,第126-127頁。
[22] 參見唐力:《“法官釋法”:陪審員認定事實的制度保障》,載《比較法研究》2017年第6期,第10頁。
[23] 該檔案現被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陪審員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所取代,但評議表達順序仍未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