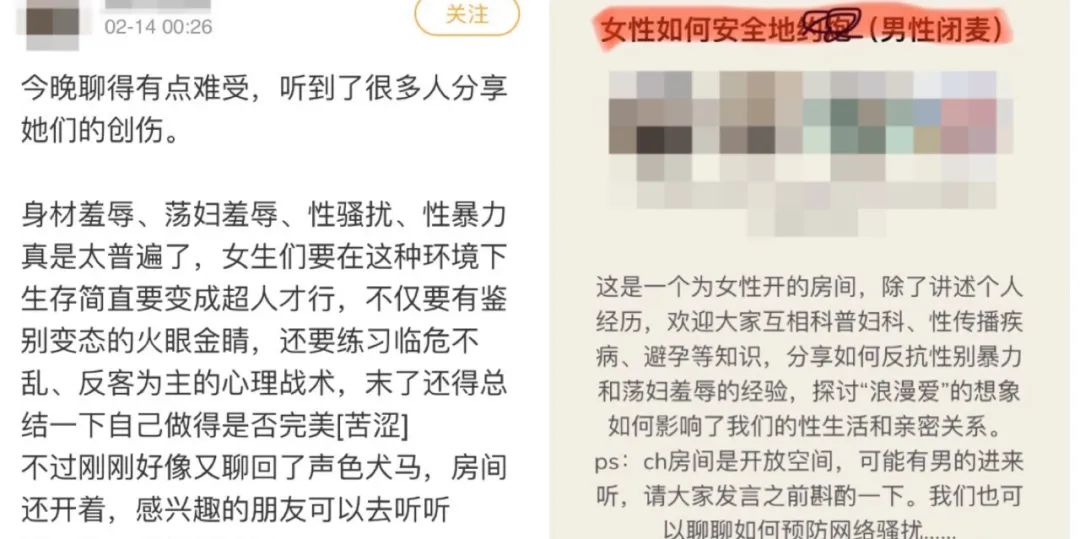近年來,多地相繼曝出“婚託式買房”騙局,這類騙局通常以婚姻為誘餌,誘使受害者在情感中步步陷入,最終背上沉重房貸。在全國各地,一群大齡離異女性也成了這類騙局的目標。這是一群經歷過失敗婚姻的女人,她們帶著各自的創傷,卻依然渴望愛,敢於愛。有一天,當網路上出現那個幾乎是為她們量身定製的“理想伴侶”時,她們迅速而又熱烈地墜入其中。
然而她們不知道,所謂的愛情背後,其實是一張精心織就的大網——和愛人的相遇,約會,甚至親密行為,都是對方用來俘獲她們的工具。
當真相浮出水面,醒悟過來的女人們開始奮力反擊。雖然有人最終成功爭取到了退房退款,但留下的情感傷痕卻難以癒合。至今,還有人困在那段虛構的關係裡,無法徹底抽身。
文丨魏芙蓉
編輯丨王珊瑚

目標又出現了。根據線人訊息,車子剛駛入小區,車上兩人,副駕是個女人,開車的,正是她要找的那個男人。
訊息傳到手機上時,是2024年5月,在北方一線城市開著網約車的顏梅,方向盤一轉,立即趕往800 公里外的S城。
8小時後抵達目的地,但就像過去數次一樣,她又撲了空。車子和男人不見了,他的出租屋也無人回應。
過去一年,這個48歲的女人一直在找一個消失的男人。以他的出租屋為原點,她幾乎織起了一張“人力網”。多年的生意經驗讓她知道怎麼和人打交道:跟保安嘮幾句家常,講出自己的遭遇,對方便爽快地表示願意幫忙;跟保潔、社群網格員、房產中介、外賣小哥也都搭上了線,男人的車牌號、照片,她一一留給他們,誰看見人或車了,她能第一時間收到訊息。
這個人,是她口中的“未婚夫”。一年前他們在網上認識,顏梅離婚六年,經歷過幾段感情,卻說這是最刻骨的一次。也正因如此,相識不過幾個月,她就決定在他所在的S城,買下一套房子。他們約定,房子一辦完,就去領證。
她以為那是感情的落腳點,沒想到成了一個轉折點。
房子一買下,氣氛變了,男人開始疏遠,說是異地太忙,結婚計劃一拖再拖。後來又說母親查出癌症,前妻逼迫他復婚,總有理由和藉口。連當初承諾的“首付一人一半,男方承擔其餘房款”,他也沒再提起,還款壓力最後都落在她一個人身上。
後來越來越多的細節都指向,這很可能是一場以賣房為目的的設局,但當時顏梅沒往那方面想。她曾懷疑他是不是另有女人,所以故意挑晚上十點多給他打電話。他接了,兩人能嘮上一個鐘頭。她便安慰自己:要真有家庭,怎麼可能這個點兒還接電話?
男人越躲著她,她越要想方設法找到他。2023年11月,男人說要出差,婚期再推。她不信。點了份外賣,送去他出租屋。提前把照片發給外賣小哥:“你敲門,看清楚是不是這個人。認出來了,你就說送錯了,外賣拿走吃了。”
外賣員去了,電話回過來,“姐我沒法跟你說,公司不允許”。她心裡大概有數了,轉頭又在網上找了一房產中介,佯裝看房,繼續上門打探。得到男人確定在家的回覆後,顏梅第二天就從800公里外“翻過去了”。
她終於見到了他。開門那刻,男人愣住了,“狗坨子的(東北方言,形容人脾氣犟),你可真厲害”。他生氣她突然上門。她反問,“我為什麼來,你心裡不清楚嗎”。兩人相處了幾天,顏梅一離開S城,他很快又消失了。行蹤越來越不確定,總說自己出差、工程急,一會兒東北,一會兒廣西。
愛人徹底成了微信裡的一個頭像——見不著,觸不到,只有隔三差五傳來的訊息。
她只能用自己的方法不斷追蹤他。透過微信轉賬,她發現對方認證的實名,根本不是告訴她的那個。她又透過他的銀行卡號查到了他真實的身份資訊——不只是名字,年齡差得更遠,不是小四歲,而是整整小了她十歲。
等到他們的房子驗收了,她也沒有見到他。 2024年1月,她準備去S城辦驗收手續,有訊息說男人出現在小區裡。她連夜出發,怕撲空,不敢耽擱。離目的地只剩50公里時,她困得撐不住,撞上高速護欄,車尾幾乎穿透,好在人沒事。
那套新房距離海邊三百米,高樓層的一居室,當初他們一起挑的,約定以後每年來度假。她一個人完成了驗收,他始終沒有出現,但她確信他就藏在附近——她那天在他租住的地方發現了剛簽收的快遞,也注意到了浴室裡晾著未乾的毛巾。
男人消失的日子,她繼續跑網約車,人活著,心卻像少了點什麼。她頻繁走神,有陣子,一個月連出三次車禍。她不是沒有懷疑過——她曾在他抽屜裡翻出房地產銷售經理的胸牌;好幾個中介也跟她說過,那套房,賣得比市場價高。可她始終想見他一面,要一個解釋。一個清楚的、不再逃避的回答。所有的事,她要聽他親口說。
2024年5月,原本是他們約定見家長、領證的時間,她一個人回到男人的出租屋,“1802”。貓眼透出光,她知道屋裡有人。敲門,開門的卻不是他——男人搬走了。
她本可以就此離開,但她停住了。屋裡站著一男一女,兩張中年人的臉,看起來跟她年紀差不多,身後的桌上擺著紅酒、鮮花——她不可能忽視這一幕,一切太熟悉了,像極了,當初她在這間屋子裡經歷的那樣。


“1802”,是顏梅第一次和那個男人見面的地方。2023年的“520”,他們在珍愛網上認識三個月後,她從外地趕來。屋子裡乾淨、明亮,客廳裡擺放著米色沙發、齊全茶具。香奈兒香水和海參已經提前準備好,她端起海參罐頭,還是溫熱的。
男人瘦高個,戴副框架眼鏡,自稱做綠化工程,一年收入幾十上百萬。初次見面他一身西裝皮鞋,衣櫃裡掛滿品牌衣褲,鞋子排得整整齊齊。“乾淨到那種程度” ,顏梅說,“連女孩都沒他這麼講究。”
顏梅自己條件也不差,早年做過生意,有房,有點積蓄。但她更看重的是一個人的人品,真實的經濟狀況她沒說太多,只透露自己跑網約車。男人聽了並不在意,從不收她紅包,吃飯搶著買單。住在一起後,每天早上他總早早起床,為她熱好粥,只為讓她多睡一會兒——細緻、體貼、不張揚,處處“閤眼緣”,這是顏梅最初愛上他的原因。
但一年後的2024年5月,當尋找男友的顏梅兩次敲開“1802”的門,都在屋裡撞見了相似的約會畫面。有的女人聽了她的經歷後,拉著箱子就要走,告訴她:姐,我跟你的事兒是一樣的。
顏梅後來才知道,她不是進入“1802”的第一個女人,也不是最後一個。全國各地有不少女人都經歷了跟她相似的愛情:同樣的相識,同樣來自S城、事業成功、體貼入微的工程男人。
她們大多是離異的女人,四五十歲,上珍愛網、世紀佳緣這樣的婚戀平臺,一開始就說明了,不是“隨便談談”,都奔著找老伴、結婚去的。
江蘇鹽城的張德珍是其中之一,56 歲,從沒真正談過戀愛,19歲就跟相親認識的前夫結了婚,十年前離了。
單身十年,張德珍一個人經營一家小飯店,又當老闆又當服務員,忙得沒時間談戀愛。2023年春天,聽說朋友的女兒跟網上認識的男人結了婚,過得還不錯,張德珍動了心。她在婚戀平臺上聊過好幾個男士——要麼不肯影片,要麼說著說著就讓她下載些亂七八糟的軟體,她察覺情況不對,全拉黑了。只有這個來自 S 城、做門窗工程的男人,她覺得最“真”。他們天天影片,男人長相憨厚,“從頭到尾不遮掩”。
剛開始張德珍沒太動心,直到有天她摔了一跤,腿扭了,影片時她跟對方隨口提了一句,沒想到男人反應那麼大,他急死了,埋怨她“怎麼不趕緊去醫院看看?”接著每天關心她腿怎麼樣了,疼不疼,叮囑她別亂走路,要多休息。一句接一句的關心,一下子走進這個單身女人心裡頭去了。
江西九江的楊麗芬,對感情一向理性。47歲,創過業,平時喜歡研究心理學,說話乾脆,邏輯清晰。她不是那種輕易動心的人,兩段婚姻,接觸和交往過幾個男人,都覺得“沒有精神上的共鳴”。
但一個來自S城、做建築工程的男人,讓她覺得遇到了“愛情”。吸引她的,不是甜言蜜語,而是對方的人生經歷。男人告訴她,前妻癌症晚期時,孃家人選擇放棄治療,是他一個人陪診、喂藥、熬夜守護。更慘的是,治療期間,他們唯一的女兒寄養在殘疾大哥家,出了車禍,當場撞死。接連的打擊,讓他一度靠酒精撐日子。
這個聽起來慘到近乎失真的故事,楊麗芬信了。她太清楚跌落谷底的感覺,兩年前,她剛離婚不久,被查出胃癌,確診那天在醫院哭得不成樣子。之後一個人四處求醫、調理、找偏方,才慢慢熬過來。
所以她不僅信任這個男人,還覺得他踏實、沉穩、值得託付。男人的表現確實讓她感動:剛認識時他並不知道她的病情,後來知道了,不但不退縮,更體貼了,定期給她寄水果,隔三差五快遞一些小禮物。
中年人的戀愛就像屋頂著火,大多還沒見過面,就已經互稱“老公”“老婆”。相識幾十天,長不過幾個月,在男人們的邀請下,她們陸續前往S城。
在機場,張德珍的“老公”用一束鮮花迎接了她。她說,長這麼大,從沒人給她送過花。男人把她接回自己的出租屋——就在“1802”對面的小區。
他們開始像老夫老妻那樣過日子,男人白天去工地,中午到點就回來接她吃飯;有時兩人也一起逛菜市場,買菜回來張德珍給他燒飯。趕上開海的季節,他開車帶她轉遍了城裡的景點。他們手拉手去海邊散步;在溼地公園買饅頭餵鴨子;還去了好多張德珍叫不上來名字的地方……“我們玩得可開心了”,張德珍連說了三個“幸福”,“幸福幸福太幸福了”。
顏梅在“1802”第一次跟男友同住的那幾天,還被領著參加過兩場飯局,都是十幾個人的大場面——當地做生意的,自稱體制內的,一個個圍著男人敬酒,誇他做事周到、講義氣。話頭一轉,聊起S城的發展,說沿海城市氣候好,規劃新,前景佳,總之是定居的好地方。熱鬧的飯局裡,男人的目光始終不離她,給她燙碗夾菜,為她擋酒,甚至瓜子都一粒粒為她嗑好,放進盤子裡。
種種貼心又浪漫的安排,事後再看,其實是不斷被複制的劇本。來自天南海北、素不相識的女人們,走過同一片海灘,出入同幾家飯店;跟男友同居的出租屋雖然不盡相同,卻都集中在相鄰的小區。
愛情正濃時,談論未來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也因此,不約而同地,她們都被帶到了同一個地方——當地售樓處。


怎麼就被帶到了售樓處,張德珍說自己當時也是稀裡糊塗的。那天她跟男人準備去看電影,路上接到他朋友電話,說趕著交房款卻打不到車。他們便順路把人送到了售樓部。沒成想銷售熱情得很,一把拉住張德珍看樓盤、參觀樣板間。張德珍說,樣板房裝得很漂亮,陽臺可以望見大海,人人看到都喜歡,男人也跟她說,我們以後結婚住這種房子最好。
晚上兩人回到出租屋,張德珍喝了點酒,暈乎乎的。男人攬她到身邊,說老婆你人真好,想永遠跟你在一起。張德珍有些不好意思了。對方接著說,我們也買套那樣的海景房吧,首付二十萬,老婆出十萬,剩下的老公出,等年底工程款一到,就幫老婆把貸款結清,再把房子裝修好,房子只寫老婆一個人的名字。
張德珍猶豫了。她在老家有房,兩人見面才兩三天,能不能走下去,還說不準。她試著更瞭解他,卻發現越來越多拿不準的地方。她提出看證件,他拿出的行駛證上名字卻不是他。他解釋,說是離婚時怕分財產,才把車過到別人名下。可離婚證卻始終沒拿出來。張德珍心裡沒底,遲遲不肯鬆口買房,兩人冷下來,幾天後,她一個人回了江蘇。
一模一樣的承諾和買房方案,當初那個男人,也是這樣對顏梅說的。她沒像張德珍那樣猶豫太久,幾天的相處,她已經認定這個人值得“託付終身”。
她一直是個敢愛的人,只是感情這條路走得不順。在她口中,前夫是外人眼裡的“老好人”,可對家人,總是不上心,還是個“媽寶男”。兩人合夥開公司,顏梅總得跟在他身後收拾爛攤子,掙點錢很快就折騰光了。直到離婚,還留下一堆債務給她處理。
後來她又談過一次戀愛。那個男人自稱小她十四歲,模樣周正,辦事麻利,是她欣賞的型別。她被他拉著投資三百萬。可到頭來發現也是個沒擔當的。處了七個月後,有天男孩說家裡催婚催得緊,不允許找年紀大的。顏梅主動提了分手,不想他為難。
兩段感情,傷神又傷財,這個年紀再重新投入,難免畏畏縮縮。跟這個男人交往時,顏梅試探過:四歲的年齡差,他介意嗎?父母會反對嗎?男人一口回絕了她的擔心:這跟年齡有什麼關係?我自己的事我能做主。外出散步時,她害羞不好意思牽手,他一把握住,怕啥,你以後不跟我過嗎?
一旦認定一個人,顏梅就會毫無保留地投入。同居那幾天,她幾乎從頭到腳為他添置了整套衣物、生活用品,看見他缺什麼全都買上,不同季節的穿戴分門別類準備好。後來當男人提到買房,還說以後家裡的大件、小件,都要寫她名下,她很難拒絕。“對女人來說,房子就是一種安全感。”顏梅說。
這也是張德珍猶豫過後,仍決定買房的原因。在老家待了幾天後,她又回來了,帶著錢和買房的手續材料。她想通了,“結婚確實需要有個房子,這人各方面都挺好的,適合自己”。
具體哪些方面適合自己,張德珍說,最重要的一點,兩人說得上話。張德珍過了二十年沉默的婚姻。和前夫沒有共同語言,回家不說話,一開口就吵架,感情早就沒了,只是捆綁著過日子,一直捱到女兒結婚才離。現在這個男人,不僅有說不完的話,還比她小三歲,人家都不嫌棄自己。
“我是真心想跟他談戀愛的”。正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心意,所以她出這十萬元首付。閨蜜說她太草率,女兒也反對,她都沒聽,拿不到戶口本,她就悄悄去派出所打了戶口證明。沒人能攔住她奔赴愛情。
張德珍轉變了心意,楊麗芬還遲遲沒做決定。眼前這個男人太完美,她覺得幸福得好不真實。真有從天而降的愛情嗎?她反覆問自己。是真愛來了嗎?媽的有點不敢相信,我真這麼幸運嗎?
工程男人提到買房時,她本能地警惕。太倉促了,她推脫說自己名下的兩套房沒還清貸款,貸不了第三套。可男人不死心,說乾脆買在她女兒名下,房子反正早晚都要留給孩子,不如一步到位。一個男人的未來規劃裡有她,也有她的孩子,楊麗芬的心,又鬆動了。
仍在猶豫時,在S城的出租屋裡,男人抱著她,手機劃過一張張照片——老婆癌症,女兒車禍,艱難創業的過去再次提起,他哭得“稀里嘩啦”的。“這玩意能裝嗎?”楊麗芬有過懷疑,只是一瞬,很快就煙消雲散了,因為男人拉起了她的手、注視著她的眼睛,“你最後再相信我一次……”
那晚,他們發生了關係。
幾天後,楊麗芬把上大學的女兒帶來S城,刷了五萬塊首付,房子和貸款辦在女兒名下。她決定賭一把,萬一是真愛呢,不就五萬塊嗎,“我輸得起”。


房子寫在她們名下,貸款從她們賬戶裡劃扣,卻沒能像女人們期待的那樣保衛愛情,相反,愛情開始撤場了。
在江蘇,等著結婚的張德珍很快發現,“老公”像變了一個人。她像往常一樣給他發訊息,老公在幹嘛,不回;打電話過去,他說在開會,掛了;隔兩天再打,他冷冷地回一句,煩死了,去哪裡還要向你彙報?你是我什麼人?
剛開始張德珍也生氣,但是一想,兩個人已經買了房,就該像夫妻一樣相互理解、包容,或許他在工地上遇到了煩心事,有點脾氣,也正常。可後來,男人越來越冷淡,她追到S城,發現即便面對面坐著,“老公”對她也愛答不理的。
顏梅的男友則跟她玩起了“捉迷藏”,她找了他五個月,才見到第二面。相處了五天,但男人態度已經變了,別說牽手,連一張合照都不願留下。一到晚飯的點,他就藉口有酒局,接著順理成章去朋友家睡。
還能怎麼樣呢?房子已經買了。2024年8月,顏梅再次來到S城,準備自己裝修。之前她曾把高價買房的疑惑發在社交平臺,這時收到了回應——一些也買了房的女人意識到有問題,來樓盤維權。她們透過網路搭上了線。
那一晚,S城一間民宿,燈光徹夜未熄,這些女人們面對面建了個微信群,“趕緊的,把照片發裡邊,都來認認自己老公”。男人們的臉一張張貼出來,直到這一刻,她們才終於確認,她們的“真愛”,不是奔著結婚來的,而是奔著賣房去的。她們買下的房子,總價在70-100萬之間,都集中在S城一個新開發區。
“男友”營造的人設也如出一轍——多金、成熟、做工程,戀愛沒談幾天,就開始規劃未來,提出買房。有人不僅被“賣”了一套房,還被搭配推薦了理財產品。一腳踏多船是常規操作。楊麗芬的男友同時和三個女人談戀愛,她寄去的營養品,他轉手送給另一個女人;她深夜的安慰,也被他複製到不同的聊天視窗——在三個女人的線下會議裡,她們一點點拼湊出愛人真實的樣子。

男人們身兼數職,一邊談著戀愛,必要時還要當群眾演員——顏梅參加的那兩場飯局,男友“各行各業”的朋友、表哥,其實都是演的,飯局上她看見的好幾個男人,包括帶著老婆來的,飯局幾個月之後,她上珍愛網一搜,個個都掛著徵婚。
楊麗芬現在後悔極了,那男人真要是做工程的,她其實動動手指就能查到——工作原因,她有許可權,也有渠道。那時她沒查。等意識到被騙再回頭去查,發現他早就上了老賴名單,欠債200萬,她真恨不得“呼自己兩巴掌”。顏梅倒是交往初期就上天眼查查過,名字、工程都能對上,但那時她哪裡預料得到,這個男人連名字都是假的。
女人們都回過神來了,也意識到奔赴真愛的代價,遠不止想象中那麼簡單。不是楊麗芬以為的5萬,而是45萬(包括貸款),由還在上學的女兒來揹負,她覺得沒臉面對女兒。張德珍則算了筆賬,房貸至少要還到75歲,每月3500元,她的小飯店疫情後因為生意不好早轉讓了,如今在別家飯店做服務員每月工資只有3000元。
顏梅是其中最受打擊的那個,精神和身體一起垮了,吃不下飯,幾個月頭髮就花白了,“月經都不來了”。“他如果騙錢,那是有數的,但騙感情,那能毀人一輩子。”這已經是她那年遭遇的第二次打擊。年初,就在她翻遍幾個小區找失蹤工程男友時,警察先找上了她,她經前男友介紹投資的300萬金融產品暴雷,她這才知道,上一段她全情投入的感情,背後同樣是一場騙局。接連兩次背叛,徹底擊潰了她。
顏梅要求退房。被欺騙的感情她無能無力,但被騙的錢,必須要回來。她去報警,沒能立案。又找到售樓處,對方讓她死了這條心:絕對不可能。可這回,她下了狠心,“我誓死必退,退不了房我不會走”。
那年8月,她徹底停下了工作,在樓盤附近租了房,她要用自己的方法退房。她重新登入珍愛網,把已經掌握的騙子名字一個個搜尋出來,最近的跟她距離幾百米。她知道,他們還在附近。
她懷疑這是一整套團伙作案。她去男人常帶人約會的飯店蹲守,一看到熟臉進店,就守在門外,把車牌號一一拍照、登記。這些舉動,男人們當然也看在眼裡。起初,他們還在樓上看她怎麼“折騰”;時間一長,見她就像見了瘟神,甚至當著她的面抱怨:怎麼又來了?看,又在這兒。
她要查出他們到底住哪。她跟著那些車離開飯店,看它們在哪棟樓前停下,男人們消失後,她挨家挨戶敲門,逐一排查。三個月過去,據她說,至少摸清了十幾套房,裝修風格都和她住過的“1802”一樣。
這些材料後來都交給了警方,能起多大作用,她心裡沒底。但她手裡攥著幾份關鍵證據:買房的全程錄音和開發商偽造的貸款資訊。這些,成了她退房最有力的籌碼。
博弈之下,那年9月,開發商與她簽訂了協議,正式撤銷《商品房買賣合同》,由開發商償還剩餘全部貸款。而她繳納的7.5萬元首付款,則需要她與“男友”協商償還。顏梅當時就在微信裡問男人,既然開發商拿了錢,就該開發商還,對方才承認,那筆錢是他拿了。首付最後也是男友還給她的。

追討房款的過程中,女人們一邊聯絡、共享資訊,也受到各種挑撥,彼此提防。大多時候,顏梅都是在獨自應對,她明白,解決一個人的問題要比解決一群人的問題,更為現實。其餘的女人也在各自尋找突破口。顏梅和楊麗芬瞭解,有人在“男友”出租屋裡悄悄裝了監控取證,有人請了七個律師起訴“男友”,還有人出錢,想從“男友”手中獲得直接的行騙證據。
也是在那段時間,越來越多受害者的報案被正式受理,當地警方也啟動了對案件的立案偵查。
2024年11月,顏梅一分不少地拿回了自己的購房款,離開S城前,她在微信上給男人留了一句話:從此走正路,不要再做這些事,一旦讓我發現你還做,我絕對不會放過你。
男人的回覆一如既往,他說自己不在S城,沒有騙過人。


那個男人現在還在顏梅的手機裡。2023年認識到現在,兩年多了。因為他的迴避,兩人只見過兩趟,真正相處的時間不到二十天。但線上的聯絡,從沒斷過。他們聊每天的天氣、吃了什麼,他會叮囑她別太累、早點休息。她也習慣了,把日常瑣碎都告訴他。
前陣子她又被騙了,借朋友的賬戶投資,十萬本金,賺了幾千利息,最後連本帶利都要不回來。她第一時間告訴他,他還替她出主意。
她對這個男人當然有過怨。但房款已經退回來了,甚至男人也出了力。顏梅說,騙局敗露後,男人沒有斷聯,反而勸她去報案,“你把所有責任推到我身上。”那時她既氣他的欺騙,又覺得,跟那些被騙後遭拉黑的女人相比,自己算是“幸運”的。
對男人的感情,是“愛”嗎?顏梅不願再用那個詞。她更願意說,是“習慣”。他出現之前,她的生活裡只有工作和女兒。每天六七點出門跑網約車,晚上七八點收工。之前做生意雖然掙了不少錢,但也敗掉不少,如今的條件算不上富裕。
上大專的女兒只在週末回家,她就把雙休都空出來陪女兒。真正屬於她自己的時間,一週只有半天——限號那天,拉完早高峰,她下午才捨得歇著,收拾收拾,給自己做點好吃的。
一個人的日子,最難熬的,總是晚上。每次收工進門,屋裡黑著,“沒人等你,也沒有一盞燈是為你亮著的”。她有時會從後視鏡裡看見她理想家庭的樣子。那次是一家三口上了車,兩口子年紀看起來跟她差不多,女兒剛高考完,氣氛原本有點緊張,男人一路說笑,慢慢把氣氛帶活了。顏梅看著,覺得他八成是個有文化、拿得了主意的男人。她羨慕那樣的氛圍,也羨慕那個女人。
工程男人也曾讓她有過類似的錯覺。認識他之後,她的生活像是被什麼填滿了。每天早上八點多,他的問候準時發來,起了沒,早上吃了啥;中午吃飯、晚上幾點回家,他也都要問一聲。下暴雨、冰雹那會兒,他的訊息像天氣預報一樣,提醒她挪車、注意安全——說不上哪裡特別,就是離不開,“如果他有一天不跟你說話,反而會不習慣。”
張德珍有段時間也緩不過來,戀愛談得好好的,突然失戀了,“我有一種被騙(的憤怒),又有一種思念”,焦慮、失眠,最難受時,她“恨不得跳樓”。
過去她一直挺自信的,“長得不醜,對得起大眾,人比較賢惠,從不亂花錢,對男人也沒有索取”,這個年紀遇見初戀,本想著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現在出了這樁事,除了家人和閨蜜,她誰都不敢說,“(怕)人家笑話我”。
當初攔著她買房的女兒,現在反過來安慰她,“多大事,不就一套房子嗎。”張德珍離婚前後一直和女兒住,女兒成人前,她拉扯女兒,女兒成家後,她幫女兒拉扯孩子。這些年飯店裡她圍著客人轉,飯店外圍著孫兒轉,感情幾乎是空白。女兒明白她的孤單,過去總催促她,媽媽該找個伴兒了。被騙後的這番安慰,張德珍也知道,不過是忍下了焦慮,心疼她一個人扛房貸。
張德珍相信時間最終會平復心情,她還想再談戀愛,“人還是要多多談戀愛才不會被騙”。年近六十,這是她悟到的最重要的道理。

楊麗芬則把所有失敗都歸因於“認知不足”。“你是缺愛的,想透過別人來獲得愛。你外求,不自足、不自愛,所以才容易被人勾住。”她在一個暴躁、控制慾強的家庭里長大,從小缺乏安全感。讀書時拼命學,工作後拼命幹,婚姻裡不斷付出,一直在努力證明自己。高強度運轉多年,忙到生理期紊亂,身體亮起紅燈時,又試圖尋找另一半,獲得喘息的空間。
第一次婚姻結束,她靠讀《佛陀傳》把自己“渡回來”;第二次離婚後,她報了心理學的“教練課程”,鑽研《親密關係》《生命的禮物》。她還把這兩本書寄給工程男友,後來才發現,被他隨手扔進了出租屋的櫃子。第三次感情崩塌後,她再次扎進教練課程,又花了四十多萬。
講述這些經歷的時候,兒子、女兒都在旁邊,楊麗芬從來不避開他們。孩子們看待問題比她更直接,中學的兒子說,“你就是戀愛腦”,大學剛畢業的女兒語氣裡透出無奈,“你必須要踩這個坑,你要輕易過去的話,你就會不停地掉進去,(所以是)老天爺把你往那個地方推。”
只有顏梅始終瞞著女兒。不是怕丟臉,而是擔心“影響女兒將來對感情的態度”。
現在提到男人,她都稱呼他,“我那個騙子”,沒有生氣或者憤怒,就跟說我那個朋友一樣自然。對這件事,她慢慢有了另外一種理解——“他剛開始確實是來騙的,但是接觸一段時間以後,可能就不是了”。她覺得,男人對自己不是完全沒感情。
她能舉出很多細節來印證。比如還沒買房、剛同居那幾天,有天晚上男人突然發脾氣,把她的行李箱扔出門外,逼她走。她猜測對方是故意用這種方式阻止她買房。她至今沒找到第二個被他騙過的女人,她還透過關係查查了男人名下的信貸記錄,發現他這幾年幾乎每半個月就要貸一次款。“他如果能騙到錢,他不會這樣(貸款)”。
種種細節,都讓她認定,“(這人是)黑道上有點正直的那種。”男人曾跟她說,就當我上輩子欠你的吧,這輩子來還;等把債還了,再說感情的事。
半年來,朋友幾次要給她介紹男朋友,她都擺擺手,“上一段就沒理清,不想往這方面想”。她還在等案子的偵破結果,給自己一個最終交代。其實還有一個小小的私心,她相信男人行騙是身不由己,如果那個“團伙”被徹底剷除,男人是不是就能真正脫身,“走正路”。交往一場,還是希望他過得好。
就在前幾天,她又接到男人的電話。她的手機誤觸,電話不小心撥給對方,被她立馬掐斷。結果男人立馬撥回來,語氣著急:怎麼了,以為你又跟人吵架了。
一句簡單的話,又走進她心裡去了。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版權宣告:本文所有內容著作權歸屬極晝工作室,未經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宣告除外。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