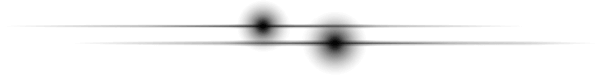(圖片攝於8月17日,寧波東錢湖)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當存在激勵因素促使人們去攫取而不是創造,也就是從掠奪而不是從生產或者互為有利的行為中獲得更多收益的時候,那麼社會就會陷入低谷。[1]”
攫取或者創造,掠奪或者互利,在很多人看來,掌權者只有這兩種極端行為。然而,經濟學家奧爾森不以為然,他發現,掌權者有時也會保護私產,但也不全然促進創造。
問題是:為什麼他們要攫取?在什麼情況下他們願意使用權力去促進生產與社會合作?
奧爾森認為,“權力問題歷來是政治學研究中的聖盃(the Holy Grail)[1]”。本文使用經濟家奧爾森的理論解釋權力的邏輯,重點回答:統治者為何既侵佔私產又保護私產?
本文邏輯
一、罪犯的比喻:黑手黨家族與小毛賊
二、國家的起源:流動匪幫與固定匪幫
三、社會契約論:私有財產與私有產權
【正文6500字,閱讀時間15',感謝分享】
洞察掌權者的行為,是一個千古難題。
權力是人來掌控、執行的,人的行為又極為複雜。人的動機,難以證實又無法證偽,幾近玄學。掌權者的行為,可能依賴於他們的理性與自利動機,也可能源自道德、性格與觀念。
如何理解權力執行的邏輯,以及集體行動的邏輯,是行為經濟學與公共選擇重要議題。
奧爾森是一位洞察能力極強、且原創力豐富的經濟學家。他在《權力與繁榮》一書中用一個“罪犯的比喻”,給這個複雜的問題打開了一扇窗戶。
奧爾森深入分析了黑手黨領導與小毛賊的行為差異。在一個權力失控城市中,小毛賊橫行,猖狂偷盜,導致居民不安,商家無利,人人自危而搬遷逃離,結果當地寸草不生,小毛賊無東西可偷,這座城市最終陷入蕭條。
經濟學研究表明,在無政府狀態下,由於自建防護隊伍的成本太高,人們往往只選擇投資“不動產”,即不易被搶走、被偷走的資產,如此自然金銀窖藏、商業凋敝。
如果有權力介入這座城市,例如黑手黨家族接管了這座城市,他不會縱容這種犯罪橫行,他會盡量控制這座城市的犯罪活動,即壟斷犯罪權,維護治安、保護私產,促進安居樂業、商業繁榮,並從中獲取最大化租金(保護費)。
他用了一箇中國的例子。他說,20世紀20年代,馮玉祥的軍隊鎮壓西北盜賊,擊敗了當地頗有影響力的匪幫“白狼”,成了當地的實際控制者,而當地人希望他持續統治。
這種例子在歷史上比比皆是。在古代,國家機器不夠強大,統治力難以滲透到南方山村鄉野,這給地方流寇留下空間。最開始往往是土匪、山賊、流寇橫行,民不聊生,統治者後知後覺,可能組織集中剿匪。但是,久而久之,也可能出現地方自治,例如宗族自救、鄉紳治理。但更多時候更可能是地方官、鄉紳與黑勢力形成的混合權力,三者之間也常有衝突。
近代,東亞諸國解除黨禁報禁,大量社團成立。最典型的莫過於日本,同盟會當年也是在日本成立的。後來,有些社團轉化為軍閥,持槍上崗;有執政綱領與能力的軍閥/社團轉型為政治黨派,即持證上崗;有些則淪為黑社會,即無證上崗。那麼,三者有沒有本質區別?
在近代日本,社團林立,有些地方的居民願意給社團繳納保護費,而不給政府繳納稅收,原因是前者收錢可保護其安全與營生,後者收錢不幹事。據說,我們的香港廟街,早期也是如此,社團對該地控制強。
問題來了,為什麼小毛賊、土匪、流寇只顧偷盜搶掠,而黑手黨領導卻願意打擊犯罪、維護秩序、保護私產?
奧爾森在《國家的興衰》中分別用狹隘利益和共容利益來解釋。
他認為,在一個人口眾多的社會中,單個強盜的盜竊行為對社會造成的損害很小,同時獲得的利益也較小,他無法意識到他的盜竊行為會導致本地蕭條,從而最大可能地偷竊。但是,控制著這座城市的黑手黨家族,對當地的犯罪活動具有壟斷權,其與這座城市的居民存在一定的共容利益,從而相對理性地思考如何可以持續地獲得最大收益——放長水,養大魚。
更好的解釋或許是,黑手黨家族掌握了當地的犯罪壟斷權,即他家的城,而小毛賊們沒有壟斷權,他們容易出現搭便車動機,將此地淪為“公地悲劇”。
因此,黑手黨家族不允許小毛賊收割他家的“韭菜”,也不允許手底下的人謀私、貪贓以及跨區收割他家的“韭菜”。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黑手黨家族的統治要比小毛賊胡作非為更有效率。為什麼?
相對小毛賊的肆無忌憚,黑手黨家族下手知輕重,會更加理性地計算長期收益率,奧爾森稱之為竊稅率。如果竊稅率過高,與小毛賊無異,導致流民或暴民遍地;竊稅率過低,不僅導致收入下降,還可能讓利於民,民富而黑手黨窮,危及其統治根基。所以,為了實現收益最大化,黑手黨家族在邊際上尋求最優竊稅率,即邊際稅率等於邊際收益。
黑手黨家族還願意給被統治者提供一定的公共用品,比如防洪防盜設施、限制疾病傳播的制度、甚至一套打擊犯罪、保護私產的司法制度。
為什麼黑手黨家族願意提供公共用品?
黑手黨家族依靠壟斷當地暴力權獲得收入,投入公共用品尤其是暴力基礎設施,可以保障其壟斷權,同時投入更多的公共用品,有助於促進生產、擴大稅基,從而獲取更多的竊稅收入。
但是,黑手黨家族不可能給你建立一個高度福利制度。當邊際公共投資等於邊際竊稅所得時,黑手黨家族將停止對公共用品的投入。所以,儘管被統治者也從公共用品中獲得便利,但是其所獲得的好處,是不可能超過黑手黨家族的。這就是統治者的底色。
有意思的是,被統治者似乎願意接受黑手黨式的統治。流寇、山賊、土匪將他們淪為涸轍之鮒,洗劫一空,而黑手黨家族至少還留有餘地。被統治者自發組織防護隊伍的費用過高,相比之下黑手黨的保護費可能更低。這就是奧爾森所說的黑手黨家族與被統治者彼此之間有共容利益。
也因此,聰明的統治者會利用被統治者的“願意”為其建立統治合法性,他們不會承認自己是匪幫,宣稱其統治是為民除害、為民謀利,甚至藉助宗教為其掩護,自稱君權神受、真命天子。這就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秘訣。
“他不是一匹捕食鹿的狼,而是一個要確保其所養的奶牛能夠得到護養的牧場主。[1]”這叫天子牧羊。
奧爾森的智慧在於,將“罪犯的比喻”上升為國家的起源、興衰的一般性解釋。
在《權力與繁榮》一書中,奧爾森將統治者區分為流動匪幫和固定匪幫,小毛賊、土匪、馬匪被稱為流動匪幫,即流寇,黑手黨家族被稱為固定匪幫,即坐寇。奧爾森從中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流寇和坐寇的行為差異,決定著國家的起源。
例如,長期以來,對中原王朝和定居農民來說,大漠遊牧民族是極具威脅的流寇。匈奴、契丹等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其統治者沒有固定的統治疆域。每當進入秋收時節,中原農業區容易遭到流寇洗劫,北方乾旱年份更甚。
陳志武老師的團隊在其《文明的邏輯》中展現了量化歷史的研究成果:他們收集了從公元前220年到公元1839年的歷史資料,發現平均10年中每增加1個旱災年份,北方遊牧民族在該10年中攻打中原的機率會增加26%,在更長時間內進攻中原的機率增加57.6%[2]。
可見,乾旱增加,遊牧民族發動戰爭的收入預期增加;降雨增加,可以抑制遊牧民族的戰爭。這就是風險催生了暴力。
與流寇相對的中原王朝屬於坐寇。坐寇是定居文明的統治者,他們有著明確的疆域意識,從秦漢開始大修長城,試圖阻擊大漠流寇的侵擾。與黑手黨家族無異,坐寇願意投資一定的公共用品,包括司法體系,制定刑法和民法,打擊犯罪,保護私產。或許,坐寇也會制定所謂的憲法,但這憲法是他制定的,不是約束權力的。
在中國歷史記載中,坐寇可謂源遠流長,似乎很難追溯到流寇時代。長期以來,我們並未發現流寇與坐寇有何區別。流寇,殺雞取蛋,竭澤而魚;坐寇,懂得調整漁網的密度,還可能分休漁期和捕魚期,有時放水養魚,有時適度捕撈。
歷史學家吳思對此做了精彩的論述,他將暴力掠奪的收益定義為“血酬”,將“全部稅收-公共開支”的收益,定義為“法酬”。他指出,“法酬也是暴力掠奪的收入,但是比較高階,有節制,有自律,有規矩。法酬是血酬的升級版,血酬的2.0版。[3]”
在奧爾森看來,二者有本質的差異,流寇意味著毀滅文明,坐寇意味著創造文明,而且是創造國家文明。流寇一旦走下馬背,畫地為牢,促耕、勖植、督獲、徵稅,那就標誌著國家的誕生。當然,此國家非彼國家,意為王朝國家/城邦國家。
對經濟學乃至政治學來說,奧爾森這一發現可謂價值連城。政治學對國家起源的解釋有暴力學說、神權論、祖權論、社會契約論等,沒有深入考察人的經濟行為。奧爾森考察了在自然狀態下,人們是如何有限約束條件下行動,進而形成國家的。
坐寇與民眾,是統治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同時他們之間還是一種基於經濟人假設的交易關係。儘管他們之間的交易,並非完全自願的,也非社會契約論所說的公平與正義的,但是在當時約束條件下的最不壞的交易。
考察二者之間的交易關係,比統治關係更有價值。流寇與民眾,是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這種關係只會毀滅文明,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又無法解釋文明。如果我們想知道,坐寇創造了效率,而非流寇,我們只能從交易的角度去解釋。所以,我將坐寇的誕生,理解為國家市場的起源。
與一網打盡的流寇相比,民眾更願意接受坐寇的統治,為坐寇提供稅收,後者為被統治者提供一定的公共用品。防水防盜等基礎設施,促進了生產與定居文明。當時約束條件下的這種交易產生了經濟效率,從而解釋了國家的作用。
蒙古族的鐵蹄踏遍亞歐大陸,他們試圖走下馬背,建立王朝統治。這就是從流寇轉化為坐寇。今天的說法是“革命黨變成執政黨”。但是,蒙古王朝在中原的統治並不成功,不到一百年時間就被漢人王朝擊敗,最終退居漠北。
這裡藏著兩個問題:
一、既然坐寇比流寇更有效率,為何坐寇還會被流寇擊敗?這個問題等於雅典城邦為何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被斯巴達所擊敗?
二、既然坐寇有效率,那麼王朝國家/城邦國家不斷更替?
第一個問題很難回答。在冷兵器時代,坐寇對比流寇的效率沒有拉開代際差,進入熱兵器時代,流寇擊敗坐寇的機率極低。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坐寇並非總是有效率的。以上討論的坐寇的經濟行為,都是基於一種理性假設,而實際上坐寇的行為,不總是理性的。坐寇常常橫徵暴斂,魚肉鄉里,甚至與流寇無異,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這就是諾斯說的“國家的悖論”:國家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經濟衰退的根源。
上面我們討論了在什麼情況下,坐寇願意保護私產、願意投資公共用品。下面需要關注的是,在什麼情況下,坐寇可能破壞私產、沒收私產,甚至巧取豪奪,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原因可能來自多方面:
其一,暴力壟斷的挑戰。
與流寇的最大差異是,坐寇擁有區域壟斷權。坐寇一旦意識到其壟斷權遭受威脅,不管是內部威脅還是外部威脅,他們可能做出最不可思的動作,如不顧一切地壓制民間活動,打壓輿論與思想,大規模徵稅,武裝暴力機關。儘管他們可能意識到,這些舉動對經濟構成傷害,但他們認為,這是維護權力必須付出的代價。歷史的教訓是,王朝國家往往毀於權力的瘋狂行為擊潰了經濟根基。
其二,王朝國家的合法性。
權力合法性來自三方面:一是權力來源,即公眾授權,或民選;二是權力監督,即權力使用未突破憲法;三是權力使用,即權力使用帶來效益,包括安全、經濟等。
坐寇統治的合法性是不充分的,至少前面這兩個方面是缺失的,那麼其統治合法性就依賴於權力績效。在古代,民眾甘受統治的重要原因是坐寇能夠提供安全保障。一旦經濟績效無法保障,權力合法性變得脆弱,坐寇只能尋求安全保障,設法為被統治者樹立一個假想敵,長期仇恨之、醜化之;同時,對內部的控制更加嚴格,甚至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其三,坐寇治理缺陷。
王朝國家的權力合法性問題,決定了坐寇治理缺陷。盧梭將政治制度劃分為民主制、貴族制與獨裁製三種,坐寇不可能使用民主制,只能可能是貴族制與獨裁製。其中,貴族制有三種:自然的、選舉的、世襲的。盧梭推崇貴族制,尤其是第二種,但是正如盧梭所言,最開始,坐寇的權力配置最終會走向世襲制,其實就是家族獨裁製。
坐寇比流寇更重要是私產的保護,這也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但是,在家族獨裁製、獨裁製中,不論是明君還是聖主,坐寇對私產的保護都不可能是徹底和穩定的,隨時可能因個人意志而改變,因此其統治不可能帶來持續的效率增長。
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使用統計方法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給我們揭曉了答案:在公元后的第一個千年裡,不論是東方王朝國家還是西方城邦國家,經濟都處於長期停滯狀態,我們稱之為“千年停滯”。直到15世紀開始,西歐經濟才開始增長,此時正好是黑死病之後城邦國家的衰敗階段,而東方長期停滯的時間則更長。
儘管坐寇的出現,代表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達成了交易,但是被統治者過度被動、脆弱、不公平與不自由。真正自由公平的交易,私有產權的永久保護,才可能帶來經濟的持續增長。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私產保護是國家興衰的關鍵變數。王朝國家一定程度上保護私產,但是並不徹底,而現代國家的憲法原則之一是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
奧爾森提出經濟繁榮的兩個基本條件:第一,私有產權必須牢靠、明確。第二,必須根除任何形式的掠奪[1]。
張五常與弗裡德曼的第一次相識便源自關於私產的對話。1963年,在洛杉磯一個小市鎮的研討會上,弗裡德曼發言談私有產權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舉日本明治維新為主要例子,說明治維新是因為土地有了私用權而使經濟發展一日千里。
還是學生的張五常聽後提出不同意見:“那不對!土地的私用權在明治之前的日本早已存在,明治維新的主要改革,是把私用的土地加上自由轉讓權。”他接著說,這似乎是“封建”地權與“現代”地權的主要分別。
弗裡德曼對張五常的回答很滿意,問道:“你是在哪間大學任教的?”張五常答道:“我是個學生,艾智仁的學生”。弗裡德曼回了三個字:“怪不得!”艾智仁就是Alchian(阿爾欽),是產權理論大師。
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對話。但是,張五常沒有抓住“封建”地權與“現代”地權之間的根本區分。在古代,也存在私產,坐寇也一定程度保護私產,但是現代國家將私產上升到產權的概念。從私有財產到私有產權,這在政治與司法觀念上是一次重要飛躍。
二者有何區別?張五常說,日本封建時代的土地允許私有,但不能轉讓,明治維新後允許自由轉讓。其中,轉讓權就是產權概念,是私有產權權屬的一部分。除了轉讓權,所有權還包括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可見,日本封建時代的土地私有,只有私產,但無產權,或徹底的產權。沒有轉讓權、收益權,私產就無法流通,無法有效配置,進而抑制經濟效率。
所以,王朝國家與現代國家之間的歷史鴻溝,便是私有產權(非私有財產)的確立與保護。自然,如何保護私有產權,也就成為歷史難題。
人類在近代走了一段歧路,即對私有產權的否定。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兩種物權:一是私有產權,二是無產權。沒有第三種可能,也沒有公共產權。一切公共產權,都以私有產權的形式存在。如果你認為存在公共產權,那一定是你對它失控了,它正成為了別人的私有產權。國家不是公共產權嗎?實際上,現代國家的最大進步是國家權力的私有化。
很多人認為,設立憲法就能保護私有產權。實際上,幾乎每個國家的憲法都寫著保護私有產權,以及賦予公民各類自由,但執行結果卻千差萬別。所以,更根本的不是憲法,而憲法治理。
奧爾森主張民主政府或代議制政府,但是民主政府不是憲法治理的全部。真正的憲法治理,是如何有效地分配與約束公權力。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對此做了精彩分析:“如果主權者想要進行統治;或者,如果行政官想要制定法律;或者,如果臣民拒絕服從;那麼,混亂就會替代規則,力量與意志就會不再協調一致,於是國家就會解體而陷入專制政體或是陷入無政府狀態。[4]”而譯者的註釋或許更易懂:“主權者權力過大則政治體便不能正常地行使職能,政府權力過大則成為暴政,臣民權力過大則成為無政府。[4]”
最後,一條鐵律,放在任何國家都成立的鐵律:保護私有產權,則文明;毀滅私有產權,則野蠻。
從自然法的角度來看,私有產權的合法性是生命權——最本源的私有產權,其它一切私有產權都是生命權的衍生之權利。
參考文獻:
【1】曼瑟·奧爾森,權力與繁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
【2】陳志武,文明的邏輯(上),中信出版社,2022年3月;
【3】吳思,從血酬到法酬——暴力要素及相關均衡,辛莊課堂,2024年07月;
【4】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