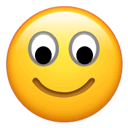*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許多年輕護士同行自嘲是醫院的“耗材”:拿著不高的薪水,做最忙碌的工作,還有被辭退的風險。年輕護士變得如此疲憊,和護士在我國的醫療體系裡的角色有關,他們扮演著醫生的配合者,一個執行醫囑的人,這樣的“配角”定位讓護士的地位、收入和發展空間嚴重受限。
記者|吳淑斌
許多年輕護士同行自嘲是醫院的“耗材”:拿著不高的薪水,做最忙碌的工作,還有被辭退的風險。年輕護士變得如此疲憊,和護士在我國的醫療體系裡的角色有關,他們扮演著醫生的配合者,一個執行醫囑的人,這樣的“配角”定位讓護士的地位、收入和發展空間嚴重受限。
記者|吳淑斌
“日行萬步,不算太忙”
孫樂今年29歲,兩年前跳槽到上海一家三甲醫院神經內科當護士。按照規定,白班是從上午8點到下午3點,但今天新收入院的一位腦卒中患者情況反覆,孫樂用了將近一個小時才交班結束,又小跑回科室參加留置胃管操作考核、開復盤會、寫今日記錄。一直到晚上7點,孫樂擠上回家的地鐵,才掏出手機回覆三個小時前的訊息。
孫樂細數她一天的行程:白班從早上8點開始,護士要在7點到崗,先清點物品、簽字確認、配藥;7:50開始交班,由夜班醫生彙報昨夜情況,科室主任講話,隨後到病床邊交接每一個病人,再回到治療室由護士長交代注意事項。這個環節結束後大概是9點,接下來是馬不停蹄地核對藥品、配藥、輸液、做霧化,等到輸完最後一個病人時,差不多就要回第一個病房拔針了。整個過程中還會有病人不斷地按鈴呼叫,如果遇上急診日或是有新收入院的病人,又是上監護、吸痰、胃管、尿管等另一系列操作。忙起來時,連午飯都沒時間吃。

《你是我的人間煙火》劇照
如果一切順利,孫樂能在下午四點前結束工作,此時她已經站了將近五個小時,“坐下來時腿肚子都酸了,一看微信運動,才一萬步!那還不算太忙。”
最消耗精力的是夜班。大夜班是23點到早上8點,每隔三四天,孫樂就會輪到一個夜班。這段時間人手少,孫樂算過,在病區滿員的情況下,值班的3個護士要照看45個病人。
除了對抗身體上的睏倦,精神壓力也壓得護士喘不過氣來。工作3年的護士小趙回憶,有一年冬天值夜班時,因為感冒咽部發炎,她只好不斷喝水、上廁所,一起值班的年長護士很不高興,“你這樣不停跑出去,要是病人突然血壓崩了呢?要是正好液體滴完了回血呢?如果病人因為你的一點差錯出事了,一切就完了。”後來,小趙只好每次都抿一小口水,潤一下嗓子,又不至於頻繁上廁所,一直熬到天亮交班才敢肆無忌憚地喝水。

《樹下有片紅房子》劇照
“三班倒”縫隙之內,還需要塞進的各種考核。
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是年輕護士的日常。孫樂舉例,她所在的科室每週會進行一次動手操作考核,內容從15項護理專案裡隨機抽取,包括靜脈穿刺、吸痰護理、鼻飼管置入與護理、偏癱患者體位擺放與轉移等。考核時間也是不確定的,“比如我今天是白班,可能會在交班前突然通知我,有時也可能安排在我休息的那天。”一次考試、覆盤的流程下來,至少需要兩個小時,考試不合格的護士還會被通報批評、扣除績效工資,還需要在下一次覆盤會上自我檢討。
雖然繁瑣,大部分護士尚能接受這樣的操作考試,“畢竟每個動作都關乎患者的安全。”讓她們難以理解的是一些無關緊要的考核,一位護士告訴本刊,她所在的護理部會不定時抽查護士對醫院工作目標、未來五年工作計劃、科室管理規章制度的背誦情況。
護士們如此忙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人手不足。早在1993年,世界銀行釋出的《世界發展報告:投資於健康》就指出,醫護比的最低要求應為1:2。也就是說,護士數量得是醫生數量的兩倍以上,護理效率才能追得上開方速度,不至於“醫生張張嘴,護士跑斷腿”。另外,國家衛生健康委釋出的檔案也要求,二級以上醫院全院病區護士與實際開放床位比不低於0.5:1,也就是說,理想狀態下每個護士只對應2個病人。
但實際情況是,幾乎所有護士都在超負荷工作。根據國家統計局釋出的資料,2024年我國的醫護比大概是1:1.15,每一位受訪護士都直言,“一個護士負責2個病床是絕對絕對不可能的。”

《紅衣手記》劇照
資料顯示,從2005年到2024年,我國的註冊護士數量從不到135萬增長到了564萬。儘管如此,按照1:2的醫護比要求,護士絕對數量仍然存在缺口。而且,三甲醫院尤其是經濟發達城市的三甲醫院擁有極大的招聘選擇權:新畢業的護理專業學生“擠破頭”,常常出現上百人競爭一個崗位的情況。
然而,營收壓力之下,大醫院也不會選擇招聘足夠多的護士。
公立醫院運營承壓已不是秘密。據國家衛生健康委通報,2020年,全國有753家三級公立醫院醫療盈餘為負,佔比43.5%;全國三級公立醫院醫療盈餘率為-0.6%,醫院資產負債率為44.09%。田曉華是中部省份一家三級醫院的管理層,他告訴本刊,公立醫院的收入主要來自財政補貼和醫院自身的醫療服務收入,各地財政補貼的力度有所區別,但基本都在醫院收入中佔不到兩成,“問題就在於,最近幾年醫院的營收很難。”

《急診科醫生》劇照
田曉華記得,他所在醫院面臨的第一波衝擊,是2017年開始實施的藥品“零加成”政策,以及2019年公立醫療機取消構醫用耗材加成。這讓“以藥養醫”的方法徹底失效,田曉華舉例,此前公立醫院可以在藥品和耗材實際採購價格基礎上加價15%銷售給患者,醫院每年藥品銷售將近4000萬元,按15%的加成計算,僅藥品利潤約五百萬元,這些利潤至少可以保證人員薪酬的定時定量發放,但改革之後,醫院只能拿到大約100萬的政策性補貼。
第二波衝擊是最近幾年推行的DIP(病種分值付費)/DRG(疾病診斷相關分組)醫保支付模式改革。新的付費模式下,每種疾病有固定的醫保支付標準,醫院的治療成本如果超出標準,超出部分需自行承擔。“我們也知道要精細化管理、最佳化診療過程,但醫生現在的治療方案和習慣都是過去三十年傳下來的,一時半會根本改不過來,醫生開治療時都小心翼翼,生怕超標了。”讓田曉華十分苦惱的是,一些病情複雜的患者在實際治療中,診療費用很容易就超過DRG病組定價,“有些病人,我們一收進來就知道‘要賠錢了’。”
開源節流成了大勢所趨,嚴格控制護士的數量就是節流方式之一。“有一種直觀的說法是:招醫生是能賺錢的,招護士是賠錢的。好醫生可以為醫院帶來病源,但沒有哪一個病人會因為護士護理得好、態度好,選擇去這家醫院。”35歲的朱程虹是西南一家三甲醫院的護士長,她告訴本刊,如今醫院招聘護士時基本都是以合同制形式,且用於護士薪水的支出預算把控得十分嚴格,“醫院給你這個科室招人就只有這點錢,用在10個人身上和20個人是完全不一樣的,於是10個人咬咬牙也就把所有的活兒都做下來了。”

《關於唐醫生的一切》劇照
朱程虹負責的是手術室,按照規定,手術室護士與手術檯比例不低於1:3,“大多數醫院達不到,‘上頭’要來檢查時就會有一些辦法應對,比如我的科室日常上班的護士就只有10個,比規定的少一半,要檢查時,就會把某些人的名字既寫在手術室裡,又寫在其他科室,這樣看上去人手是足夠的。”
被招聘進來的護士也很難在有限的預算下得到滿意的報酬。在跳槽到三甲醫院之前,孫樂也在老家的二甲醫院工作過,她和同事們的大夜班(一般在23點至次日8點)的費用在100元左右,“算下來,熬夜通宵的時薪比奶茶店打工還要低。”
有時候,一些控制薪酬的手段很隱秘。陳琳曾經在2022年進入廣州一家三家醫院做規培護士,她告訴本刊,根據醫院規定,不同級別的護士對應不同的工資係數,最後能拿到手的錢由績效和夜班費乘以工資係數,再加上基礎工資。工資係數依次遞減:護士長是1.3,普通護士是0.8,而她作為規培護士,試用期內第一年只有0.25,熬過試用期後,每個月到手的薪水大約是6000元。有時候,績效還會以各種理由被減扣,科室裡的紗布、碘伏等耗材有規定的使用標準,如果超標了,還需要從護士的績效里扣除。陳琳還發現,醫院會嚴格限制大家考取護士職稱,因為“職稱越高薪水也就越高”,護士考取職稱之前要在醫院官網登記,獲批的比例很低,即使考得了職稱,醫院也很少給護理部分配聘用名額。
在這家三甲醫院工作了不到一年,陳琳就辭職了。她至今還記得護士長經常對新人說的一句話:“我們幹護理,不只為了那點兒工資,還要為那份熱心去幹。”
初當護士時,許多人確實對護士職業帶著熱心和“濾鏡”,但這些情感很容易在繁瑣的工作和日益緊張的醫患關係中被磨去。採訪中,每位護士都能回憶起與病人相處時被投訴、呵斥甚至謾罵的經歷,起因往往只是自己沒有在第一時間回應病人的各種需求。

《急速救援》劇照
朱程虹做護士14年,她覺得自己越來越像個服務員。她還記得一件10年前的事情,上夜班查房時,她發現一個住院的小男孩的腳很臭,就叮囑陪床的男孩爸爸打盆水給孩子洗腳。這位爸爸的手因為長期做農活,結了厚厚的老繭,對水溫不敏感,男孩的腳被熱水燙傷了。事後,領導要求朱程虹寫一份檢討,“領導問我,‘你為什麼不全程參與他的洗腳?’。”這是朱程虹第一次對這份職業的價值產生了懷疑。後來,護士要做越來越多與專業無關的事情,“病人睡在床上,護理部來檢查,發現床單有褶皺就要扣我們的分;病人床頭櫃擺了水杯,又要求我們要幫忙收到櫃子裡去,要看起來整齊劃一。平時沒事就給護士發個指甲刀,去給病人剪指甲。”
不受尊重的感覺另一部分來源於病人對護士專業能力的不信任。“病人會覺得,治病的是醫生,護士能懂些什麼專業知識?”幾個月前,朱程虹家裡親戚生病了,她和媽媽一起在醫院照顧。朱程虹告訴媽媽,手術後可以給病人用枕頭,媽媽不信;查房的護士同樣建議用枕頭,媽媽依然不信。查房護士走後,媽媽跑到醫生辦公室詢問,聽到醫生親口確認,才相信了朱程虹的話。“我一個護士長,工作14年了,連我親媽都不相信我。”

《手術直播間》劇照
“重醫輕護”和護士在醫療體系裡的角色定位有關。現代醫療體系脫胎於19 世紀的歐洲,核心是“醫生主導、護士輔助” 的分工模式,我國計劃經濟時期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模式。護士是醫生的配合者、醫囑的執行者,一個配角。我國《護士條例》中規定,除非遇到緊急情況,否則護士都需要正確執行醫囑,不能脫離醫囑獨自進行醫療操作。一位護士告訴本刊,“理論上講,我們給病人用一個冰袋降溫,都需要有醫囑允許。”
這種分工導致護士的專業價值被嚴重低估——患者將康復主要歸功於醫生“妙手回春”,而忽視護士在術後護理、病情監測中的關鍵作用。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釋出的調查報告顯示,“94.1% 的調查物件認為護士工作就是打針、發藥,對護士的具體工作並不瞭解。”
其實,一個老護士的經驗可能比一位年輕醫生更充足。55歲的鄧萍退休前是武漢一家二甲醫院的護士長,當護士已經35年了,有一次在急診值班時,他們收到一位喝腳氣水自殺的病人。當時負責搶救的醫生讓鄧萍馬上準備給病人洗胃,“我說‘不能洗胃,這個藥是腐蝕性的,洗胃會造成消化道大出血。’醫生質問我,‘你是醫生還是我是醫生!’”鄧萍堅持馬上把值班領導找來,事實也證明她的決斷是正確的。

《問心》劇照
護士們的職業天花板也很明顯。國家衛生計生委衛生髮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閆麗娜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我國大部分醫院對護士實行簡單的平臺式管理,不論學歷、職稱,承擔同樣的任務和責任,“一個班組的護士都承擔大體上相同的工作內容,主管護師與護師只是在職稱、工資方面有所不同,其餘的沒有區別。”
更何況,護士想要得到職稱上的晉升十分困難,鄧萍所在醫院有500多名職工,副高、正高醫生有很多,護士寥寥無幾,“並不是大家達不到條件,是名額太少了。”鄧萍說,醫院共有200多名護士,每年只給不到十個職稱聘任名額。走行政級別的晉升更是希望渺茫,“一個科室幾十個人,只能有一個護士長。”
困境之下,護士們自然而然地產生疑問:這份職業的未來在哪裡?有人選擇辭職,但發現辭職後“能應聘的工作也只有其他醫院的護士”;也有人徹底轉行,考公務員、做個體生意,或是乾脆迴歸家庭,“以前的經驗和積累全都清零”。
在國內一家三乙醫院工作將近10年後,方姝選擇了另一條路:到美國去當護士。在備考美國註冊護士資格考試時,方姝發現了它與國內護士考試的差異,“不是簡單考察護理知識的運用,而是一種思維模式。比如給你一個病例,要求你判斷病人的情況以及可能出現的併發症,並做出對應的護理計劃,還要制定與醫生、物理治療師、營養師等多部門溝通的方案,後續根據患者病情可能出現的變化調整計劃。”
後來方姝才知道,這是因為美國護士在醫療系統裡的角色與國內區別很大,他們不是簡單的醫囑執行者,需要調動自己的專業知識做決策。

《明天會更好》劇照
美國的護士體系按專業許可權從低到高,分為四個層級:助理護士(CNA)、執業護士(LPN/LVN)、註冊護士(RN)和高階執業護士(NP)。其中,助理護士主要負責基礎生活照護,執業護士可以在註冊護士監督下執行基礎護理操作。註冊護士與高階執業護士屬於高度專業化人才,和國內護士相比,他們擁有更大的自主權:註冊護士需要獨立完成病情評估、護理計劃制定及多部門協作,是臨床照護的核心決策者;高階執業護士有診斷、開具處方等診療權,不用依賴醫生就能獨立給病人看病。不同層級的護士也有細緻的專業區分,比如高階執業護士包含麻醉護士、美容護士和助產護士等,在美國屬於高階稀缺人才,年薪普遍超過12萬美元。
Nicole是西雅圖港景醫療中心急診精神科的註冊護士,她向本刊描述了自己的日常工作:在接診各類有精神健康問題的患者後,她們會對患者做基礎評估,根據抑鬱症、焦慮症、自殺傾向等不同情況制定方案,有些患者可以直接離院,有些患者會被推薦至康復門診,由家庭醫生後續跟進。對病情嚴重的患者,護士可以採取強制住院措施,同時為有需要的患者開具藥物。
Nicole覺得,美國護士的職業認同感比國內更高。在美國,醫生和護士是兩套不同的專業體系,“很少出現重醫輕護的情況,無論病人還是醫生,都會尊重護士。如果醫生對護士的工作有意見,可以向醫院投訴,但醫生不是護士的上級,管不了我們,很多新醫生還會以比較謙虛的態度向老護士請教、合作。”護士的上升空間也更廣闊,低層級護士可以透過系統培訓與學歷深造向高層級晉升,Nicole在醫院工作7年後,申請了一所大學的精神科護理學博士,她的規劃是畢業後能開一家自己的診所,獨立接診病人。

《我家的醫生》劇照
一位在美國就讀護理學碩士的受訪者這樣形容美國的護士職業:“護士是一條職業路線,它不是簡單從護士升到護士長,而是有不同的升級路線。比如從執業護士升級到註冊護士後,就會分化出許多分枝,每個方向都有自己獨特的技術和職能,有足夠的空間讓護士往前走。”
在社交平臺上,Nicole曾經發布過一個帖子,介紹在美國當護士的幾種途徑。帖子下方有上千條評論,內容很相似:介紹自己的基本情況,再詢問成為護士的具體操作辦法。其中一條兩年前的留言比其他人簡單得多,“我已經超過40歲了,還有希望嗎?”Nicole回覆“沒有年齡限制”,但對方再沒有回應。本刊記者私信了這位留言者,她回覆,自己是一位三線城市醫院的護士,無意間刷到了這個帖子,“那段時間想轉行,到處找機會……不知道該幹嘛去,但肯定不可能出國……我還在醫院當護士呢,量血壓、輸液、上夜班。”
(文中孫樂、朱程虹、陳琳、方姝、田曉華為化名)

排版:小雅/ 稽核:雅婷
詳細崗位要求點選跳轉:《三聯生活週刊》招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