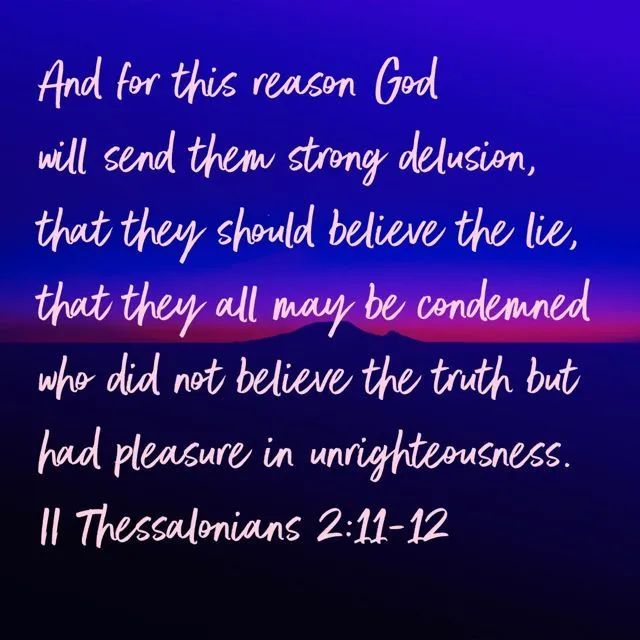永珍課程「從未實現的平等:權力、身份與社會分配」已更新13-14集。這一部分將要討論,平等與進步的要求之間是否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
在前進的道路上,平等的願景已然成為海市蜃樓。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在為平等而進步,還是為進步而不平等?甚至,我們難道是在為了固化不平等而擁護進步嗎?
▍進步的想象:無限的增長,無盡的遠方
我們都熟知“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而被奉為自由主義之父的洛克在《政府論》下篇中對於財產權的論證,正是這一觀念的奠基之作。洛克說,一片有人種的土地,能長出比沒有人種的土地多出十倍百倍的東西,所以圈起地來耕種的人是在為整個人類生產更多的儲備。
我們需要想象,有一個人聲稱自己世世代代生活在一片土地上,這片土地提供了他生存所需的果實和獵物,而另一個人跑來聲稱自己有權透過耕作佔有這片土地。洛克的意思是,這片土地應該歸後者所有,因為後者能帶來更大的財富。
打著自然權利的旗幟,洛克還有一個真正想要證成的東西:資本主義發家的兩大秘訣——原始積累和殖民擴張。
美洲大陸顯然不能被視作是處在自然狀態的無人之地,殖民的後果也不只是開荒,佔有和勞動在根本上是兩個互相沖突的理由。於是,這兩種活動中的哪一種能產生更大的利益就成了判斷是非的標準。
這個標準有一個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它叫“進步”。它是“殖民主義”最重要的理據:誰能成為地主取決於誰有生產力,誰有科學技術,誰能為所有的人創造出更大的財富。

這個意義上的“進步”實際上是一個概念群,它包括“進步”“發展”“增長”,乃至於“現代化”,諸如此類。在我們的集體意識中,它們基本上是可互換的,都意味著透過有效的、有技術含量的生產和積累而獲得更多的財富,從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這種進步觀是一種對於無限性的信仰。它令人相信財富可以無止盡地增長,我們的生活水平可以無止盡地提高:我們可以生產更多的商品,技術可以解放出更多的生產力,人類的壽命可以延長,基因可以被增強,等等。
今天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認為這種對於極限的挑戰就是最值得我們為之付出努力、最有意義的事情。也就是說,“進步觀”是今天在世界範圍內佔絕對主導的意識形態。
就像所有長期佔主導的意識形態一樣,“進步”在成為硬道理之後,就漸漸地成為想當然的事情,漸漸地不被追問,大家不再問:進步究竟意味著什麼,又究竟是為了什麼?
它最終變成了一種同義反復,變成了自己的目的:為什麼要進步?因為要進步。為了進步而進步。
我們逐漸滿足於一種包治百病式的說辭:進步總是好的,總是值得追求的。如果一畝地裡可以種出10倍的糧食,我們就不應該滿足於5倍,如果我一年能寫出10篇論文,就不能滿足於5篇……
這種對於無限增長無限改良的盲目信仰,越來越像一種東西,它叫“貪婪”,也就是說,一種永不滿足的慾望:再多一點,再快一點,再強一點……
電影《華爾街》中的反派主角高登·蓋克(Gordon Gekko)有一段非常有名的關於“貪婪”的讚歌,道出了現代進步觀的實質:貪婪是好的。貪婪是對的。貪婪是有效的。貪婪令萬事變得明晰,貪婪令我們勇往直前,貪婪把握住了進化精神的實質。

▲ 電影《華爾街》(2010)
▍發展是如何變成硬道理的?
不僅高登·蓋克們是這麼認為的,處於兩極另一端的很多人也是這麼認為的。在《飢餓》這本書裡,作者馬丁·卡帕羅斯道出了處於極端不幸中的人對於進步抱有的同一種信念:
這個世界上還有太多人在忍飢挨餓,他們吃不飽飯,這是事實……我想說的是民主和發展正在解決這個問題……當然了,他們確實留下了一大部分財富,不過那歸根到底是他們應得的,更重要的是,他們給多少人提供了工作機會啊!他們給那些人付了多少工資啊!要是沒有這些豁出去開工廠、僱傭他們、付他們錢的人,得有多少人睡大街啊!又有多少人會悲慘地死去啊!

▲ 卡帕羅斯《飢餓》
貪婪就這樣變成了一種美德:炫富的人在製造財富,在給別人帶來福利,總有一天,拜這些野心勃勃和永不滿足的人所賜,總會輪到我也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有積蓄和庇護所……
大家大概已經發現,進步觀能使人對於再極端的不平等都抱有幾乎無限的容忍度。更確切地說,這種無限度的容忍有兩個理由,它們表面看來正好是相反的。
第一個理由在於:只有進步到一定的程度,平等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說,進步是平等的前提條件。反過來說,如果平等離我們還很遠,那是因為我們還不夠進步。
第二個理由在於,進步必然以不平等為代價。就像洛克所主張的,能者多勞的前提,是讓能者多佔。那個為所有的人帶來更多福祉的人,應該是第一個受益者。
大家對於這個理由是不是有種既視感,因為它背後是我們已經很熟悉的“優績主義”:那些為進步付出更大努力、帶來更多利益的人,如果他們不能最先並更多地享有進步的好處,那麼這種分配方式本身就是不正當的——因為它不符合優績主義的分配正義。
不僅如此,從功利主義或者說結果主義的角度來說,這可能會產生勸退效應,會使得本可能“卷”出優績的人選擇“躺”下來“坐吃等死”。簡單地說,絕對平等的結果是不進步。
一個是為了平等而進步,一個是為了進步而犧牲平等,這兩個說法看上去正好相反,但它們實際上具有同一個預設:如果不發展,那麼大家都很慘。
我們可以稱此為“霍布斯式的預設”,霍布斯在描述自然狀態時強調的是自然狀態中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但是他們平等地處於不幸中。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還是走出自然狀態為妙;並且如果所有的人同時富起來是不可能的,那麼就應該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發展就是這樣變成硬道理的。

這就是為什麼,對於在探討“平等”的我們來說,“進步”是一個關鍵問題。“進步”和“平等”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我們是進步主義者,那麼我們是否應該放棄平等呢?如果我們同時是進步主義者和平等主義者,我們是不是在做一件用左手的矛去打右手的盾的事情呢?
我覺得,“進步觀”中有一點是有道理的,它可以幫助我們反思平等理念可能存在的問題,因為它提醒我們,平等不應該是我們行動的終極目的。如果平等的結果是所有人的不幸,那麼我們確實要對平等打上一個問號。
“追求平等地不幸”不應該是一個選項。所以說,我們不能為平等而平等,如果我們追求平等,我們總是應該進一步追問:“平等地幹嗎?”
換句話說,平等不應該像通常那樣被寫作名詞(equality)並被當成一個好的東西來追求,而應該寫作副詞(equally),它是一種行動的模式,這種行動模式的特殊性在於,它涉及到一個群體的所有成員之間的關係。
因此,“追求平等”這句話並不完整,它需要被補足:追求平等地滿足生存需要/平等地快樂/平等地獲得知識,等等等等。
▍進步到什麼程度,才能顧及平等的程序?
但是這並不反過來證明進步觀是不容置疑的。首先,這並不意味著霍布斯式的預設是真的。如果自然和野蠻並不意味著不幸呢?之後的一講中,我們會討論這很可能是對於“原始社會”的一種偏見。
此外,我們還可以質疑進步是否真的能帶來最終的平等。在導論中我們就提出過,在進步和發展成為硬道理的三百年之後,不平等並沒有因為進步和發展而得到緩解,發展的程度與不平等得到緩解的程度並不成正比。
一方面,消費主義社會在瘋狂地暗示大家,滿足了溫飽之後,現在我們可以無限度地追求舒適和享受;但是另一方面,面對在溫飽邊緣掙扎的群體,我們還是搬出同一套措辭,聲稱這說明進步和發展還不夠。這兩種說法難道不是相互矛盾的嗎?
我們到底要進步到什麼程度,到底要使得多少人可以有富餘,才願意去拉一把在掙扎的人?
我們還可以追問,那些被認為促進了發展而獲得很多回報的人,究竟在什麼意義上促進了發展?從圈地從事農業的殖民者,到創業和創造就業機會的實業家,到令股票期貨增值的金融家,到各種體育和娛樂產業在製造的明星,全都因為帶動著進步而理應擁有更多嗎?
所有的這一切都令人懷疑:“進步”會不會是一種“話術”?為了進步而被容忍的不平等之間的關係有沒有可能是倒過來的:並非為了進步而暫時犧牲平等,而是為了製造並鞏固不平等而高舉進步的旗號?
▍當進步成為硬道理,我們失去了什麼
當我們對進步的實質這樣發問時,我們應該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當“進步”成為佔絕對主導的意識形態時,它的含義變得非常狹窄。
廣義上的“進步”泛指一種對於人來說變得更好的過程,並且一般是透過人為的努力實現的。因此,進步是一個褒義詞,一個正面的價值判斷。
但在現代人的語境中,當進步和文明、發展等變成同義詞,並變成硬道理的時候,它的含義也在變窄。

它是以一些特定的標準衡量出來的“更好”:生產力,科技水平,人均壽命和醫療手段,等等。總體來看,我們現在所說的進步意味著我們擁有了更多可以享用的東西,並且擁有更好的身體去享用它們,而這成為一個適用於全人類的絕對標準。
從廣義上來說,一個人有沒有變得更開心,更幽默風趣,他和家人鄰居的關係有沒有改善,他是不是越來越坦然地接受生老病死的過程,一個地方的民風有沒有變得更淳樸,人與人之間是不是更親切更互信,這些本來都應該被視作是進步。但是在“進步觀”的語境下說這些屬於“進步”,會被視作是無稽之談。
這種用狹義取代廣義的做法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在傳統道德中被視作罪惡的“貪婪”可以與進步畫上等號,搖身一變成為了美德。
慾壑難填之所以會被視作是罪惡,常常是因為慾壑難填的人失去了人之為人最重要的東西。這不僅出現在前現代的民間寓言中,處在世俗化和現代化程序中的歐洲也有對於慾壑難填的警示。這些故事的寓意都在於貪得無厭的人為了自己所欲求的東西而失去了更珍貴的東西:生命和靈魂。
這些故事萬變不離其宗的主題,可以說是一杆天平:如果我們要計算自己擁有的好東西的總量有沒有增加,那麼在做加法的同時,還要做減法,我們在獲得一些東西的同時,總是應該小心我們會不會必然地失去什麼東西。
但是,當狹義的進步已然成為廣義上的進步,我們就會認為沒有減法要做了,更強、更多、更快,幾乎就意味著普遍意義上的更好,意味著絕對的善。我們也不再追問,當我們追求這些芝麻的時候,有沒有可能同時丟了西瓜。
但是,真的沒有減法可做嗎?在特定標準下取得的進展,是不是就意味著總的來說一個群體乃至於整個人類的生活變的更好?有沒有可能,以其他的標準來衡量,我們沒有進步,甚至於是退步了呢?這個問題一旦被提出,那些只可能讓我們做出減法的標準就會浮出水面。

盧梭不能說是第一個做減法的人,但是“減法”絕對是他在思想史上的註冊商標,是大家稱他反啟蒙的主要原因。
理性與科學、技術與藝術,這些被啟蒙思想奉為文明和進步的東西,盧梭卻說,要用一杆天平去衡量它們,才能知道它們究竟給人帶來了什麼。盧梭手中的天平所衡量出來的,是人類的墮落史:文明令人“退化”“墮落”“腐敗”,文明的程序(人類進行協作生產,發明科學技術,建立社會制度的過程)是人類“從他最初的狀態漸漸過渡到最徹底的腐敗的過程”。
這是整個《論不平等》的結論。“進步”帶來“墮落”,這看上去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說法。但是將近300年後,西爾維婭·費代裡奇從拉丁美洲的草根女性主義運動者那裡聽到的是類似的控訴:“很多人口中的進步,我們女性稱之為暴力”。
👇掃描下圖二維碼購買和觀看

▍進步的規訓,不幸的身體
這些“一身反骨”的思想家和革命者,是在做什麼樣的減法呢?我們一起來看看盧梭是怎麼把一部好端端的進步史寫成了墮落史。
盧梭做了兩種減法,第一種是相對於個人的幸福而言的。要理解這種減法,我們需要首先理解盧梭的幸福觀。
這是一種古典的幸福觀,它尤其在古希臘思想家伊壁鳩魯那裡得到了集中的表述:幸福是身體沒有病痛(aponia)和心靈不受困擾(ataraxia)。以此為準繩,盧梭說,生活在文明社會中的人只會越來越不幸,因為它必然帶來越來越多身體上的病痛和靈魂上的困擾。
首先,整個的文明史在盧梭看來就是人類的疾病史。他說:
我們給自己造成的疾病是否比醫學能向我們提的療法更多?而這種情況又是如何成為可能的?
生活方式的極度不平等:有些人過分閒暇,另一些人過於勞累;我們的食慾和感官的享受非常容易被刺激和滿足,富人的食物過於考究和富有營養……窮人的食物十分粗劣,並且就是這樣的食物大部分的情況下他們都不夠……
熬夜,各種放縱,各種激情的不加節制,疲勞,心力交瘁,悲傷,以及那些不斷侵蝕著我們的靈魂的數不過來的憂慮。這些都不幸地證明,我們的大多數疾病是我們自己一手造成的……
盧梭提醒我們,醫療的進步並不必然意味著我們的身體在更大程度上處於無病痛的狀態。如果醫療的進步總是跟不上疾病的增長呢?
盧梭列舉出了很多“文明社會”在發展醫療的同時又令人深陷病痛的原因:飲食和生活作息,過勞或活動不夠,還有各種放縱,各種負面的心理情緒——這難道不就是儘管平均壽命已經大大增長,醫療水平已經非常先進的現代人的現狀?
但是盧梭的這段文字還沒有窮盡病痛增加的原因。福柯所提出的生命權力和生命政治為我們提供了繼續理解這個問題的抓手:當我們的身體在生命政治之下變成被管理和利用的機器,醫療變成一種修理我們的手段,它的目的並不是身體沒有痛苦,而是它可以更有效更聽話地運作。

▲ 福柯《生命政治的誕生》
現代文明在製造越來越抗打的身體,我們藉助各種身體管理,藥物,乃至於軟毒品(咖啡,糖)而使自己成為“天選打工人”,能熬夜更久,伏案更久,抗壓更久……
如果我們認為這樣的身體是更健康的身體,那麼也應該認為,工業化農場中那些在各種抗生素和激素的加持之下長到一定個頭的家禽和牲畜,相對於它們那些野生和散養的祖先,也在變得更健康。
出於生命政治的需要,現代文明在製造療法的同時也在製造疾病,因為原本可以健康存活的個體現在可能被視作是不合格的,原本並不影響我們存活的一些缺陷現在被視作是需要治療的。
還有一個令我們被過度治療的原因,在於醫療變成了一門生意。

▲ 電視劇《成癮劑量》(2021)
最後,文明程序的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結果,是自然平衡被打破,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頻繁的大型流行病。新冠病毒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些都還只是aponia(身體沒有病痛)意義上的幸福與不幸。那麼以ataraxia(心靈不受困擾)為標準呢?很顯然我們也沒有變得更幸福。
進步所必然帶來的結果之一,在盧梭看來,是我們因為永不滿足而永遠地失去了ataraxia的狀態。為了說明這一點,盧梭提出了“可完善性”這個概念:
這種特有的,並且是幾乎無限的能力,是人類一切不幸的根源;是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將人類從最初的狀態中抽離出來——人類原本過著平靜而無邪的生活,是它在時間的長河中令人的智慧與謬誤,罪惡與美德都顯山露水,最終使他成為自己和大自然的暴君。
“成為自己與自然的暴君”這個隱喻很不幸地再次說中了我們所處的時代:人類對於自然資源的過度開採以及我們的過度消費和浪費已經對環境產生了不可逆的後果,發展史從這個意義上說就是對於自然的暴力史。
而另一方面,在一個奴隸制和暴政被認為離我們已經很久遠的時代,卻有越來越多的人覺得自己深深地“困在系統裡”,被沒有面孔也沒有聲音的、因此都無法抗議的、而且還不斷在生成的各種要求和規範壓得喘不過氣。
但是,說可完善性“是人類一切不幸的根源”會不會有點聳人聽聞呢?盧梭提出“可完善性”概念,是緊接他上文中的“自由意志”概念,兩者相輔相成。自由意志是不按本能行事而偏離自然軌跡的願望,而可完善性是偏離自然軌跡的可能性。
動物沒有這樣的願望也沒有這樣的可能性,所以它們的慾望總是與自然環境相平衡。而人一旦因為自由意識和可完善性打破了這種平衡,偏離一旦發生,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進步一旦發生,它就是一個只有起點而沒有終點的過程。
更有甚者,由於這條偏離了自然的軌跡被視作是無止盡的,每一個新的零點都被視作是新的起點:我們會期待更多,這使得哪怕我們根據這個新的標準已經滿足了自身,仍然又會很快感到不滿。
豐裕馬上就會顯得是貧乏,博學很快顯得是無知,高登·蓋克口中的“貪婪”一方面令我們擁有的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令我們總是充滿挫敗感。就這樣,進步極度諷刺地令人總是處於匱乏而不是豐裕之中,這種匱乏不是物質上的,而恰恰就是心靈上的永不寧息。
▍進步成癮,卷無止境
大家有沒有覺得,貪婪帶來的折磨,很像一種現象,這種現象是“上癮”。它們的機制,可能真的是一樣的。
提到“上癮”,我們容易想到海洛因和可卡因這樣的違禁品。它們是能令人高度上癮的東西,一旦上癮,基本上很難憑藉自己的意志去脫癮。
但是還有很多合法的“毒品”,最常見的例如糖。本來人體不需要遊離糖(也就是新增糖)的刺激就可以分泌多巴胺,把自己維持在一個嗨皮的狀態。遊離糖也有這樣的效果,所以當我們攝入遊離糖,我們會快樂加倍。
但是很快地,當我們習慣了糖分帶來的快樂,我們自己的身體就不再像以前那樣分泌多巴胺,於是我們開始依賴奶茶和快樂肥宅水,不然就不嗨皮。這就是上癮。
咖啡、菸草、酒精、電子遊戲、短影片,它們的生效機制是一樣的。這是不是很像盧梭所描述的那種進步所帶來的不幸呢?總是想要做成更大的生意,完成更高的KPI,擁有更先進的技術,探索更遠的地方……不然呢?不然不嗨皮!

▲ 電視劇《成癮劑量》(2021)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進步觀就成了一種不折不扣的慣習:它不是從自然中生長出來的,但卻像本質屬性那樣深入作用於我們的身體和心靈,造成了生理意義上的、實實在在的不幸。
但是,孤立地看每一個個體的舒適程度與財富,還遠遠不能解釋我們心靈受到困擾的全部原因。這件事情真正變得沒有止境,是當人與人之間開始比較,是當慾望不是相對於自己,而是相對於其他人的慾望而產生:因為別人渴望那個包包和那款車,所以我也渴望,乃至於渴望更貴的包包和更豪的車。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卷,我們知道,卷是沒有底的。盧梭稱,這是不平等的最糟糕的結果:“別人越是缺少他們所有的東西,權貴們就越是享受這些東西,並且,無需改變他們的狀況,如果普羅大眾不再不幸,那麼他們就不再幸福。”

▲ 電視劇《成癮劑量》(2021)
▍我們為何甘願受到奴役
這種不平等所帶來的結果是盧梭所做的第二種減法,這一次他放在天平負面那邊的,不僅僅是心靈的困擾,而是它的全面變質。
我們在閱讀《論不平等》第二部分時,會發現在盧梭筆下的人類社會史中有一個很明顯的分水嶺,它是冶金和農業的發明,也就是社會分工的出現:農民需要工匠製造工具,而工匠需要農民提供食物,他們無法離開彼此而存活,這是嚴格意義上的社會分工,也就是每個人都從事一種專門化的勞動。
社會分工變得越來越細,每個人對於其他社會成員的依賴就變得越來越強,這被視作進步的一大標誌。但是盧梭說,這就是“使人紛紛走向文明但使整個人類走向墮落的東西”。
要理解這一說法,我們需要看到,盧梭劃分人類社會史的標準是人際關係的型別。他非常敏銳地看到,在社會分工出現之前,已經存在著一種社會關係,它建立在共同性之上,人們擁有共同的語言、習俗、生活方式,以及因為所有這些共同性而具有的親近之情。讓我們把它稱作最初的共同體。
但是與此同時,因為沒有明確的分工,每個人都大致掌握了生存所需要的技能,所以每個人也都是獨立且不依賴別人的。最初的共同體與分工社會之間的區別,就是後來社會學家涂爾幹所稱的著名的“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
為什麼被公認為能帶來進步和發展因而屬於更好的社會關係的有機團結,在盧梭看來反而是使人墮落的社會關係呢?
我們在探討財產正當性時曾分析過為什麼分工會導致財富積累與不平等,而盧梭現在進一步說,正是不平等,將導致人際關係的普遍惡化和心靈的普遍墮落。
分工與財富積累所產生的第一個結果,是“自尊”。分工使得人所具有的不同品質被估值,分工越細,財富積累的要求越強烈。這在人心中種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慾望:比別人具有更多的品質。
這就是盧梭所說的自尊心(l’amour propre),它是“得到別人誇讚的強烈慾望”,是“對於出人頭地的痴迷追求”,它“使我們總是活在自身之外”,因為它是一種“相對的情感”,只有透過將別人比下去才能得到滿足。
既然現在我們活在別人的眼中,那麼我們實際所有的知識和品質並不重要,表象才是重要的,如果沒有那些會被誇讚的品質,就想辦法裝出來。真相因而也變得不重要,謬誤只要長成知識的樣子就可以被用來證明自己的高超,就可以被用來建立權威。
總而言之,在自尊心的驅動之下,人是在變得虛偽、變得表裡不一的意義上在墮落。人際關係則是在表面上阿諛奉承、實際上相互嫉妒的意義上惡化。
分工和財富積累所帶來的第二個結果,在盧梭看來,是普遍的奴役狀態,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永遠失去了最初的自由。他說:
一旦一個人需要另一個人的幫助,一旦人們發現一個人擁有兩個人所需的食物的好處,平等就消失了,財產就出現了,勞動變得必要,廣大的森林變成了欣欣向榮的田野,它需要用人的汗水去澆灌,並且奴役和不幸在其中隨著收成一起到來並增長。
財富的積累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越來越多的人需要用勞動來謀生,這使得後者失去了自主行動的最基本的前提,後者只能聽從前者的差遣,這也是今天很多人的切身體會。
這樣失去的自由不能說不是徹底的,如果有人膽敢詭辯說,處於如此奴役之中的人還是可以在匱乏以至於餓死和做奴隸之間做選擇,那麼我們只能祝願他有一天可以在這種選擇之中去歷練他的自由意志。
但是盧梭所指出的更扎心的一點,是現在哪怕並沒有淪落到只能任人擺佈、被人統治才能存活的境地的人,在愈演愈烈的不平等之下,因為自己的野心,而心甘情願地做奴隸:
公民們是隻有在受到某種盲目野心的驅使時才會任由自己被壓迫……統治別人對於他們而言變得比獨立更可貴,他們同意帶上枷鎖,是為了有一天能輪到自己把枷鎖帶到別人身上。
當統治和被統治、命令和服從的關係成為佔絕對主導的人際關係,也就是說自由的人自發構成的共同體關係幾乎絕跡,那麼一方面自由顯得像猴子撈月一樣不現實,另一方面野心勃勃越來越像是唯一的生存之道——為了不被別人徹底地踩在腳下,必須不斷地往上爬。

▲ 電影《華爾街》(2010)
因此,哪怕是不受生存所迫的人還是會想盡辦法在更多的關係中佔據統治地位,並不惜為此進一步失去原本就所剩無多的自由。但這條通往統治的路,常常始於也停滯於被統治,因為當自由變得如此不值得捍衛,已經處於統治地位的人就能更輕易地透過為野心勃勃的人們畫餅而為自己找到更多的奴隸。
與此同時,統治者本身也高度依賴受他統治的人,如果沒有他們,且不論他無法依靠自己的雙手來謀生,而且他的財富也會在很大程度上變得沒有意義。
出於這種依賴,他們發展著越來越有效的,令人被迫或甘心被奴役的手段。就這樣,無論是處於強勢還是弱勢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鞏固著這個越來越建立在統治和被統治關係之上的社會。
最終,愈演愈烈的不平等令人心和社會都變得很糟糕,盧梭在《論不平等》接近尾聲時這樣總結道:
忙個不停的公民流著汗,心神不寧,不停地折磨自己,為的是找到更辛苦的工作:他勞作致死……
他奉承他所痛恨的大人物和他所鄙視的有錢人;他為了能獲得為這些人效勞的榮譽不擇手段;他驕傲地吹噓自己的卑微和顯貴們的保護,以作奴隸為榮……
翻譯成今天的網路用語,是“社畜”和“牛馬”,“996”和“過勞死”,“舔狗”和“裝逼”。但是盧梭的重點,在於提醒我們:所有的這一切都不是人性中本來就有的,而是人在不平等的關係之下難以避免的處境和傾向。
如果說這是進步的結果,我們還能不能視此為真正意義上的進步?如果“進步”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平等,以及隨之而來的偽善與敵意,統治與剝削,也就是說社會關係的普遍惡化,這還是不是進步,還值不值得我們追求?

▼ 課程大綱

▼ 如何觀看
● 一席會員
一席會員可在會員有效期內免費觀看包括本課在內的全部付費永珍課程;
● 單獨購買
影片課程《從未實現的平等:權力、身份與社會分配》共20節,每節20-30分鐘;
現在購買可享早鳥優惠價98元(原價198元);
識別下方圖片中的二維碼,或點選文末的“閱讀原文”,以早鳥價購買課程;

● 觀看方法
下載“一席”App(用安卓、蘋果手機或iPad下載,支援投屏、音訊播放、文稿、快取等功能)或登入一席網站(yixi.tv),在“永珍”欄目頁面觀看。
*購買和觀看中如遇任何問題,請聯絡小編微信: yixixiaobian(一席小編全拼)或yixikedaibiao(一席課代表全拼) 。
編輯丨馬路
聯合出品丨光啟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