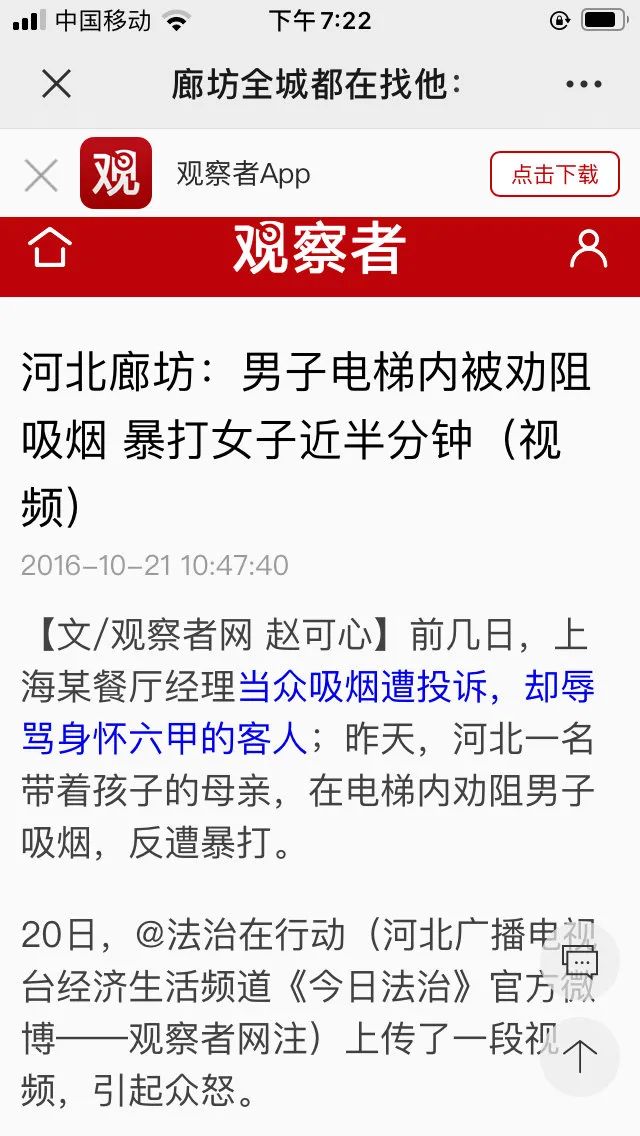尚萌萌是北京一所電影類高校的在讀研究生,從今年春天起,他持續在學校的室內公共空間裡拍攝菸頭和菸灰的照片,然後打包向12345和衛健委投訴有人違規吸菸。
據他估算,投訴了有120次左右。此外,他常常在社交媒體上更新控煙的動態,控訴二手菸與二手菸製造者。
因為控煙,他在校內變得小有名氣。他的賬號評論區裡出現了兩極分化,一邊支援他,叫他「當代林則徐」;一邊認為他是刺兒頭,太「魔怔」。
我聯絡到這所高校的幾位學生,試圖還原「林則徐」身上的爭議來源。
一位畢業生回憶,在校時,常看到有人在教學樓和宿舍樓的樓道、廁所裡吸菸。她本人不抽菸,也很討厭煙味,但因為身邊人都抽,「會縱容、放任二手菸的存在」。她最近聽說了「林則徐」的事蹟,認為他是一個勇敢的人。
另一位在校生說,過去,因為教學樓樓道里煙味太重,她總是不得不繞道而行。但今年5月以來,她發現校內的空氣突然清新了,不知道這與「林則徐」的控煙是否有直接關係。
輿論的另一邊,則是對「林則徐」不間斷投訴行為的厭煩。
一位在校生告訴我,自己是菸民,但也討厭寢室樓裡隨處飄散的煙味,所以原本是支援「林則徐」的。但逐漸地,她覺得他「變得極端化了」、「鬧得大家魚死網破」,連帶學校的聲譽岌岌可危,也多少會影響畢業生們的學歷價值。她認為,要改善校園裡違規吸菸的情況,「急於求成往往沒有好的結果……要一步一步落實」。
一位不抽菸的在校生說,她佩服「林則徐」的堅持抗爭,但不贊成他與網友在社交媒體上「很有情緒地互相攻擊」。
一位既是菸民,也正在這所學校參加短期培訓的學生告訴我,大家下了課聚在一起抽菸,常常講起這位「林則徐」,「一般都是不喜歡他的態度」。他舉例,一次下課,他和同學們在消防通道里抽菸,保潔阿姨過來和他們一道討論,「林則徐」到底是誰?保潔阿姨埋怨,因為「林則徐」的出現,學校要求地上不能見到菸頭,自己的任務量變重了。
「他做的事情其實是正確的,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但正確的同時,給大家都添了麻煩。」這位同學總結。
為什麼做一件正確的事會這麼難?
6月初,我在一家咖啡館見到了尚萌萌。與網際網路上對他的猜測與描摹不同,他是一位溫和的年輕男性。他告訴我,控煙的初衷是自己對尼古丁的敏感與不耐受,一聞到煙味,他的頭腦、呼吸道和腸胃都會有不適反應。
我們當天的經歷證明了他的說法。
在咖啡館裡坐下不久,他突然說通風管口飄出了煙味,我沒有聞到,但循著管道路徑向外看,另一側管口邊上,果然有人在抽菸;我們轉移到了咖啡店外的綠地上,很快,他又聞到了附近飄來的煙味。
為了躲避煙味,我們總計換了七八個訪談地點。最後找到了一個商場裡的麥當勞,才勉強坐下來。沒有煙味的時候,他的語速和思維都變得很快。聞到煙味時,「大腦反應馬上就呆滯了」。他會想吐,想腹瀉,並且多次要求暫停訪談,好讓他去遠處透一口氣。
在這樣高敏感的身體裡生活,他很痛苦,但這不構成他堅持投訴的最重要理由。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是,在室內的公共場合抽菸本就不對,製造出的二手菸,會傷害許多人的健康。
他回顧了自己被二手菸侵害的經歷,這種侵害,除了在他現在就讀的學校裡,也曾在很多地點發生過。開始控煙後,他接觸到更多有相似經歷的人,統稱為二手菸受害者。這些人的鼓勵與支援是他堅持控煙的動力之一。
他也提到了那些反對他的聲音,他知道學校裡有不少人牴觸他,但他願意接受相應的代價。
尚萌萌說,他的訴求不是徹底不許人抽菸,而是希望菸民能在更規範、更顧及他人的地點抽菸。
在尚萌萌的觀察中,控煙的困境與爭議,大概與我們對二手菸一貫的忍耐與包容有關,與文藝圈對煙的美化有關,與對煙危害的共識的缺乏有關,可能也與對自由的理解不同有關。
這有點像一場關於煙的自由之爭。尚萌萌說,曾有人給他發私信,稱抽菸是一種個人自由。對此,他想引用哲學家穆勒的話回應: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自由。
以下是尚萌萌的講述。
文|馮雨昕
編輯|李天宇
我到這所學校念碩士,最早是想逃避二手菸。
本科畢業後,我在老家雲南的一家公司做管培生。入職培訓期間我就注意到了,不少職員在工位上吸菸。當地很熱,從早到晚關門打冷空調,整個辦公廳又是開放式的,大家撥出的煙就悶在廳裡到處飄。我發現,我只要坐在工位上就無精打采,老走神兒,腦子也轉得很慢。但那會兒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半個月後,我被下派到縣級崗位,經常要坐車去各鄉鎮辦公。一輛車裡四個人,除了我以外,另外三個同事都抽菸。在車廂那種密閉又狹小的空間裡,我被燻得上吐下瀉。我在這崗位待了17天,平均每天嘔吐三次,腹瀉七八次吧。實在受不了了,就把工作辭了。但那會兒還以為是水土不服。
後來我又入職過很多個城市的很多個小公司,逐漸領悟出了規律——唯一的變數是我有沒有吸到二手菸,只要上班時有人在我身邊抽菸,我就噁心、頭暈、心跳加速,各種不適;如果在無煙環境裡辦公,就神清氣爽,做事效率也高。
我查過文獻,煙裡的尼古丁又叫菸鹼,它會啟用人類的乙醯膽鹼受體,讓人愉悅,同時也讓人噁心——醫學上把這叫做噁心獎勵雙重機制,不同的人對於噁心和獎勵的偏重程度是不同的。很不幸,我是那個噁心感遠大於獎勵感的人。
我也去看過各種醫生,他們都告訴我,沒辦法,對尼古丁過敏不像對蟎蟲、花粉過敏,無藥可治,只有儘量遠離有煙的環境。
當時我特別無奈,能想到的辦法只有逃離。我想如果能到美術館或者博物館上班,是不是就可以不被煙燻了?畢竟這種場所是嚴格禁菸的。也想,是不是我家鄉省份的室內吸菸率太高了?不如到大城市去生活吧。於是來到北京考研,我本科學的管理學,跨專業考美術類院校沒成功,被調劑到了一所電影類院校。
後續的發展完全不符我的預期。
2023年9月2號,入學的第二天,我剛走出宿舍門,就看到有個學生蹲在走廊上,一邊抽菸一邊看手機。我特別震驚,怎麼會有人在大學校園的室內抽菸?我本科時的菸民同學們都是到樓下抽,沒有誰明目張膽在室內抽菸。
我就對那位抽菸的同學說,「我們宿舍的人都不吸菸,你在這裡吸菸會燻到我們,你能不能去別的地方吸?」這位同學還是很配合的,馬上就走了。
但隨後幾天,我慢慢發現,校園裡抽菸的人太多了。有些人要下樓,還在電梯裡就把煙點上了;有些人懶得出門,三四個人站在宿舍走廊兩側,吞雲吐霧,形成一個天然煙幕,過路人都要從那煙幕中穿過;甚至公共浴室裡還有人邊沖澡邊吸菸——我都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不讓水汽打溼菸頭的;宿舍樓和教學樓的廁所裡經常有人抽菸;不止是學生,我上過一門課,老師講著講著,就掏出電子煙來吸一口。
頭暈、頭痛、腹瀉,這些症狀又回來了,我還開始反覆地咳痰、流鼻涕、胃食管反流。
最嚴重的一次,我去辦公室找老師聊開題報告,幾米外,另一對師生也在聊學術問題,聊著聊著,突然就點上煙了。那時候是冬天,門窗緊閉,我被燻了一個多小時,呼吸困難、頭也劇痛。從辦公室出來後,我在外面吹了幾小時的風,又吃了布洛芬,到晚上快睡覺時才緩解。
因為這些不適,我三天兩頭往醫院跑,北京的醫生的說法和過去一樣,要我主動避讓二手菸。但事實是,避無可避。
我採取過特別多自保的方法。我手寫了一個禁菸的牌子,貼在宿舍門上,但作用不大,走廊裡還是常有人吸菸。我在宿舍擺了臺空氣清淨機,又買了小拇指粗的海綿條和透明塑膠貼在門縫上,防止煙從縫隙裡鑽進來,只兩個月,塑膠就變成了黃綠色。我洗臉、刷牙、方便都得一層一層找廁所,但凡在廁所門口聞到煙味,就得立刻去試下一間,有時甚至得走到隔壁樓去。
校圖書館的門口總有人圍著吸菸,玻璃門一開一合,會把煙吹進樓裡。我後來就不去校圖書館了,非要借書,就戴著防毒面具進去。其他時候,我只去國家圖書館自習和看書。不誇張地說,那陣子,我除了上課和睡覺,其他時間都不能留在校內。

圖源視覺中國
剛入學的頭幾個星期,我嘗試過勸阻室內吸菸者。素質高一點的人,聽到我的請求後會到外面去抽,或者至少走遠一點。另一部分人就只是看我一眼,好像我在做什麼奇怪的事,然後無動於衷。
勸多了你就會知道,勸是勸不過來的。後面再遇到那種煙霧繚繞的走廊,我經常捏著鼻子快速跑過,邊跑邊聽到身後有人討論,那個人在幹什麼呀?
我看過學生手冊,在公寓樓內吸菸的,經查實要給予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甚至要記過。但入學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我和學生處、總務處、保衛處都反映過室內二手菸的問題,始終得不到什麼有效回覆。我向校圖書館的管理員投訴,館廁所裡有人抽菸,按規定是要在90個開館日里禁止這個人入館的,但後來我又在館裡看到過他好幾次。
所以整體上我覺得特別被動。我到現在也很難理解這件事,在室內吸菸明明是錯的,為什麼我想糾錯卻這麼困難?
轉機在今年寒假,我在家刷到了無煙北京的公眾號,又透過這個賬號加入了北京志願者群。有群友告訴我,在室內吸菸違反北京控煙條例,比如第九條,「公共場所、工作場所的室內區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內禁止吸菸」,還有第十一條,「吸菸區的劃定應當遠離人員密集區域和行人必經的主要通道」。如果發現控煙違規現象,我是可以保留證據,然後在12345小程式上向衛健委發起投訴的。
於是,這學期開學後,我就開啟投訴之路了。
我當時的生活節奏是這樣的,白天出校實習或者到國圖自習,晚上9點左右回來,教學樓、辦公樓、宿舍樓一棟一棟走過去,重點看廁所和消防通道——這兩個地方是室內吸菸的重災區,認真走一圈,有時能拍到十幾二十處菸灰或菸頭。有時甚至不需要我專門去巡邏,上個廁所,就能發現蹲坑附近的地面有菸灰。如果碰到有人正在室內吸菸,又恰好是在有監控的地方,我會記錄下時間和地點,回頭衛健委可以調錄影。
從3月到現在,我定期把證據打包、上傳,投訴了有120次左右吧。衛健委接到投訴後的態度很積極,基本都是第一時間聯絡我,也會盡快派人到現場調查。有大概個位數的案例,準確地定位到室內吸菸者,就實施行政處罰,罰款50到200元不等。
說實話,一根菸三五分鐘,抽完人就走了,留下的菸灰和菸頭經常是在監控盲區,真要定位到是誰抽的是很難的。但我表達了、嘗試了,總比什麼也不做要好。

圖源電影《駕駛我的車》
我知道,在校內控煙不討喜,至少討不了所有人的喜。學校裡開始傳有我這麼一個人,討論我到底是誰。很多人開始叫我「當代林則徐」,這背後誇讚和諷刺的意味都有。有些校友覺得我的行為是過激的,或者覺得我太較真,是個沒事找事的刺兒頭。
我把控煙經歷發到網上,很多人留言或者私信罵我。有人指責我抹黑學校;有人問我,你這麼討厭這所學校,為什麼不退學啊? 輔導員經常找我談話。有校領導也委婉地和我說,吸菸的人這麼氾濫,管不過來的,意思是要我理解一下,不要這麼上綱上線。
我的現實生活也受了一點影響,有一段時間,我的宿舍門口一天能被丟幾十個菸頭。有人經過我身邊時,會突然點打火機嚇我。我去廁所拍菸灰和菸頭,有傳聞說我是在偷拍。就不久前,我在學生公寓的消防通道里碰到三個學生正在點菸,我下意識地錄影,他們對我吐了口水。
我明白,是我的行動打破了以往被默許的某種平衡——在室內,突然不能隨心所欲地抽菸了。當然會有人不高興,我當然也會受到非議。
有壓力比較大的時候。比方說,我上著課,突然聞到走廊裡飄進來煙味,直接走出去檢視怕影響別人上課,但不管的話,就只能硬聞著、硬挺著。還有幾次我半夜在宿舍被煙味燻醒,到陽臺上打電話給宿管投訴,宿管來我們房間找我反饋結果,很容易就會把室友吵醒。我還是不太想影響到無辜的人。
但單說控煙這件事,沒什麼壓力能逼我放棄。一方面,我的身體確實受不了尼古丁,即使是為了自己,我也會想盡一切辦法堅持控煙。
另外,在更大範圍內,我能感受到善意和支援。透過社交賬號,我聽到太多相似的故事了。有個校友說,自己所在的宿舍樓裡,有時「煙大的(得)能起密度」;有畢業生跟我說,自己在校時也多次投訴二手菸,但成果不佳,要我繼續加油;還有個畢業生說,雖然他也抽菸,但他是個素質菸民,他理解我的控煙訴求。
也有來自校外的響應。一位其他學校的男生聯絡我說,他去阻止室友在宿舍裡抽菸,室友覺得面子上掛不住,差點和他打起來。一個女生留言說,因為受不了同事在辦公室吸菸,她乾脆辭了職。
我們的經歷能安慰到彼此。這些向我訴說的人們,或許未必像我這樣,對尼古丁有強烈的生理不耐受,但他們的困擾也是真真切切的。我們的需求和動機都很簡單,抵制二手菸,請菸民不要在室內的公共場合吸菸。

尚萌萌全套的防護服受訪者供圖
我本科在綜合性大學,吸菸的人有,但很少。到了這所電影類院校,我感覺菸民數量陡增。去劇組實習的同學回來也告訴我,組裡的人多半是人手一根菸。我在雲南逛過一所藝術類院校,成條的香菸會直接擺在小賣部的櫥窗裡。聽在北京的美院朋友講,校內的菸民比例也很高。
我的幾個室友都不抽菸,其中一位卻特別愛做和事佬,總勸我不要過多幹涉別人抽菸。他的理由有很多:菸草能給國家帶來鉅額稅收;搞藝術的人都抽菸,從事電影行業的人更是不能不抽菸;搞藝術的人都叛逆,我越勸,人肯定抽得越厲害。
這對我而言是一種詭辯,但確實,在我的觀察中,吸菸在文藝圈是被浪漫化的。這是我想讓大家警惕的問題。
你去看那些最經典的電影,不管是鄉土、都市還是黑幫主題的,吸菸經常會作為一種動人的意象出現,可以指向灑脫與叛逆,也可以指向沉穩與冷靜。
創作要找靈感,也常常和吸菸掛鉤。美院的朋友說,許多藝術生的煙癮是在藝考集訓時養成的。我在北京電影節做過志願者,活動場地裡有那種小房間,志願者、嘉賓可以用來採訪或者寫稿。每天輪番進出幾波人後,那屋子裡的氣味我難以形容,算是我此生聞過煙味最濃重的場所之一。
也是在北影節,來過一個匈牙利導演叫貝拉·塔爾,很受文藝青年的喜歡。這位導演在活動現場給粉絲簽名的間歇,出去吸了兩次煙。很多人覺得他這個行為既文藝又可愛。他有一張穿著大衣吸菸的照片很出名,被評為帥氣。
我覺得我們需要反思,吸菸是怎麼從一件平常事被抬成一個浪漫符號的?因為這種浪漫化,要求控煙反而讓一部分人不能理解。
這兩年我也開始回顧我的成長經歷,我發現在更大的世界裡,二手菸的危害是經常被忽略的。
我只有三四歲的時候,有一回經過村裡的小賣部,老闆在門口抽菸,朝我的方向噴了一口,我的頭就發痛。但好在我同住的家人裡沒有抽菸的,所以我的童年多數時候沒什麼問題。但後來念小學、中學,都有教師在辦公室裡吸菸,哪怕殘留的煙味也會讓我覺得皮膚辣痛,偶爾會腹瀉。
我想過特別特別多的原因,是不是我的大腦缺水或者缺氧?還是我的腸道有寄生蟲?我甚至為此吃過驅蟲藥。就像我一開始說的,我是參加工作後才意識到,我是被二手菸侵害了。在此前,我從沒有設想過這種可能性,因為沒人告訴過我二手菸的危害,好像也無人在意。
我小學、中學的老師們,公然在辦公室吸菸的時候,那些不吸菸的教師從不抱怨。所有人都好像很習慣、很預設,煙就是可以隨時隨地抽的。
後來時代有些進步了——有網友和我提過,我自己也碰到過類似的場合——有人要吸菸,先禮貌地問同伴,我現在能不能吸?你介意我吸嗎?這其實是把責任推到不吸菸的人身上,因為在許多關係中,說「不」是要勇氣的。你就想,你和領導吃飯,領導這麼問你,你作為下屬敢說不嗎?
我想舉一個相對友好的例子。有一節課後,我和一位女同學在教室裡做課題討論,她突然把煙從口袋裡掏出來,但大概是想到我在身旁,就問我:你抽不抽菸?我說我不抽。
那時我還沒開始大規模控煙投訴,也沒告訴她我對尼古丁不耐受。但是她聽到我的回答後,就默默把煙收回去了,後來再也沒有在我面前掏出來過。不知道她是出於尊重我,還是其他什麼考慮。哪怕只是一瞬間的體貼,我也挺欣慰的。

圖源電影《下一個素汐》
還有一件我覺得弔詭的事。自從我在網上發帖後,支援我的、反對我的網友都不自覺地叫我「姐妹」。似乎有這樣一種性別刻板印象,男性更愛、更理解抽菸,而厭惡煙味的只有女性。
首先我承認,不管是習俗也好,社會規訓也好,煙在男性社交圈裡的作用更大。男性們聚在一起,我發你一根菸,你發我一根菸,就是示好。我也經歷過這種時刻,如果太強烈地表達對煙味的厭惡,就好像和男性群體格格不入,可能也需要一點勇氣。
但在我的經驗裡,任何性別的人都可能抵制二手菸,也都可能包容二手菸。
我在一個藝術中心實習,有一天午飯後,我發現有人在展廳出口的廁所裡抽菸,就去門衛室找保安。保安是一對六十多歲的夫妻,那個大叔告訴我自己特別討厭煙味,很支援我把這事兒上報。但那個阿姨勸我們不要聲張,她說她一會兒去把菸頭掃了就行。意思是我要和室內吸菸的人保持友好,不要惹事。
在我宿舍樓裡,情況是反過來的。我只要發現有人在公寓廁所裡抽菸,就會報告給宿管。幾個男宿管通常都要磨會兒洋工,過幾分鐘才去廁所檢視,抽菸的人早走了。然後他們就會來找我說,別投訴了,沒有人在抽菸。但有一位女性宿管是做實事的,我向她投訴,她會立即去現場記錄,並把記錄交給來巡查的衛健委。
還有一回,我發現有人在公寓洗衣機旁邊吸菸,打電話給男性宿管,他說讓保潔阿姨來處理。結果保潔阿姨上來後,就是默默地在吸菸者旁邊守著,菸灰掉下來一點,她就掃掉一點。我理解,控煙確實不是保潔阿姨的工作內容,她也委屈、也不容易。但我還是有點驚訝,她站在那兒吸了好幾分鐘的二手菸,沒有說一句阻止的話。
我還想說說我媽,其實她和我一樣對尼古丁不耐受。她坐縣城之間的班車,只要車上有人吸菸,她一定會頭暈、嘔吐。有一次她在車裡被燻了一個多小時,下車的時候幾乎失去意識了,被送去急診搶救。但她是怎麼理解自己的這個反應的呢?她覺得坐車犯暈就是暈車。她不承認二手菸對我們有害。
以前她叫我回老家工作,我說不行,老家在工位上吸菸的人太多了,我受不了。她就問我,那暈血的人難道就一輩子不能當醫生了嗎?我說是啊,暈血的人為什麼非要逼他當醫生呢?她覺得我對二手菸的厭惡就像暈血一樣是心理作用,是一種「怕」,而「怕」是可以被克服的。她希望我克服對二手菸的「怕」,她覺得那樣我才能更好地融入社會。
要「融入社會」,我覺得這是二手菸受害者的另一個困境。
我在網上發帖後,全國各地都有網友聯絡我,有些人感慨自己很討厭二手菸,但害怕衝突、怕得罪人,很多時候都不敢出言阻止。有個網友說,外出就餐,遇到有人在餐館裡吸菸,她請服務員去阻止,被吸菸者指責「矯情」。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勸一個校友不要在室內吸菸,他跟我說應該是人來適應環境,而不是環境適應人。這種論調我想許多不吸菸的人也聽說過,好像在不知不覺間,忍受二手菸才是高情商、社會化的表現。
更重要的是,如果說控煙會引發矛盾,那矛盾的根源一定是有人違規吸菸。這時候,再去指責不吸菸的人「事兒多」、「不願融入」,這真的合理嗎?

圖源電影《獨自在夜晚的海邊》
經過我這三個月的投訴,學校的情況有在變好。
5月底,學校釋出了新的控煙規定,提到如果發現教職工或學生違規吸菸、亂扔菸頭的,第一次批評教育,二次或以上就會有通報批評、約談、處分等處罰,也說明了「校園內除設立的吸菸區外,所有場所禁止吸菸」、「吸菸區設定在室外通風處」。
其實學校裡以前就有吸菸點,但很多菸民不會去,還是習慣隨時隨地抽。而且以前的吸菸點選址我覺得很不合理,要麼在行人必經之路上,要麼在樓房的門外、窗外,只要門窗一開,二手菸就會灌進樓裡。
新的吸菸點基本都遠離人群了,點位上還會豎幾根回收菸頭的柱子。我宿舍樓的廁所裡裝了禁菸的語音播報,室內垃圾桶上本來有滅煙板,現在用塑膠牌子堵住了,不讓人往裡扔菸頭。
有了這一系列舉措,最近宿舍空氣好了不少,至少外面走廊裡沒有人不管不顧地抽菸了。我在校園裡能夠停留的時間也就稍長些。
我前陣子還刷到了一個校友的帖子,說最近去找導師,發現導師在辦公室裡不吸菸了。他問了句為什麼,導師說,最近查得嚴,不敢吸了。可見,我們不是雁過無痕。
但新規是否能持續地執行到位,有沒有真正的威懾力,我覺得還有待觀察。
有些室內垃圾桶上的塑膠板已經被掀了,還是有人在那上面滅煙。我現在隨機去校園裡走走,有時還是能碰到有人躲在監控盲區吸菸,廁所和消防樓梯間還是高發地區。
說到底,這也不只是我學校有的現象了,我覺得大家對於「該去哪裡吸菸」是沒有共識的。我老家省會的酒店裡甚至會提供菸灰缸和火柴;你留心去看看各個城市裡的寫字樓、公園或者路邊的公共廁所,尤其男廁所,走進去基本都有煙味,低頭都能找到菸灰。我猜測現在的普遍認識,是最好不要在室內吸菸,但是在廁所和樓梯間還是例外,反正一般沒人管,大家都在裡面吸。
在我的期待中,比如北京的各個公共空間,在未來能完全執行本市的控煙條例,「所有公共場所、工作場所室內區域及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菸」,就已經很好了。在這個基礎上,再去談室外抽菸的注意事項,比如最好不要邊走路邊抽菸,那樣也容易燻著路人。
我覺得國內城市中,上海和香港在控煙方面做得不錯。除了最基本的室內公共場所不可吸菸外,上海去年9月出臺了吸菸點新規,要求吸菸點的設立與建築物出入口、門窗、排風口等保持不小於6米的距離。在香港,有天花板的地方都不能抽菸,否則可能被罰款好幾千元。
所以你現在要問我,我個人的控煙行動算不算成功,我很難說已經成功了。我覺得還有非常多的提升空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知道我在控煙後,有校友來找過我,說想要模仿我來拍一個作業。他們照我樣子買了防毒面具、雨衣和護目鏡——為了避煙,我在學校裡就是這樣全副武裝的——一個穿戴上後在學校裡走,另一個跟在邊上拍攝。
校友問我,他們這樣模仿我,我是支援還是反對?我說我是中立的,但我希望這種模仿越多越好,最好能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就是光明正大地討厭二手菸。
還有意料之外的好事發生。我認識一個美院的學生,本身是個菸民。最早,他可能是覺得好玩,拍了些他們學校裡禁止吸菸的牌子給我看,牌子下面是一堆堆菸頭。我就把我抗爭二手菸的故事和他說了說,他是我知道的第一個叫我「林則徐」的。
前陣子,他告訴我,受我的故事的啟發,為了自己也為了他人的健康,他把煙戒了。我真的還挺驚訝的,因為他說過,他從高中美術集訓開始吸菸——一個有十多年煙齡的人,把煙戒了,我很為他高興。



圖源視覺中國
(應受訪者要求,尚萌萌為化名)
親愛的讀者們,不星標《人物》公眾號,不僅會收不到我們的最新推送,還會看不到我們精心挑選的封面大圖!星標《人物》,不錯過每一個精彩故事。希望我們像以前一樣,日日相伴。